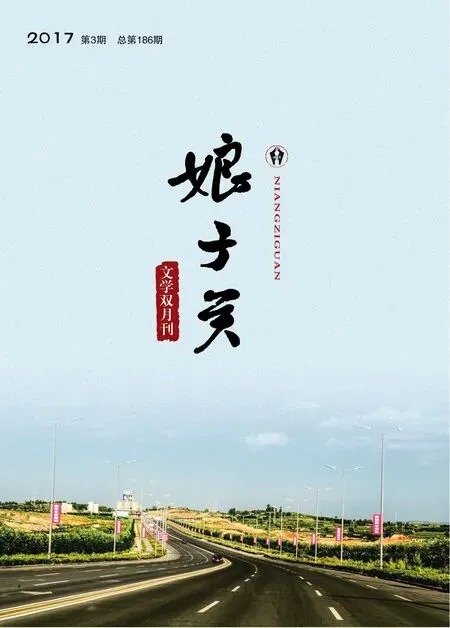鹿洞泉鸣
●梁耿华
鹿洞泉鸣
●梁耿华
一夜间千树万树的白,已远走他乡。越冬的土地,仿佛揉着惺忪的睡眼,哈欠连连。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确定又是一个春天,细雨沁人心脾,阳光握手言和,距离万紫千红已为时不远。迈进三月门槛,踏着市文联的旋律,一路同行,再次拾起鹿洞泉鸣的断章。似乎有些忐忑不安,惊扰了翠屏山的沉思默想,事实上神泉人的热情洋溢,让我多余的担心不攻自破,让我的三思而行相形见绌。神泉村的不同凡响,源自我对老武的了如指掌。每一次走进神泉,他就是不能或缺的拐杖,因此,这一次市文联深入农村的采风活动,仍然由他导游。
3月29日,市文联副主席赵存珍带领市各艺术家协会一行20余人,第一步跃上松柏掩映的珠山,又名翠屏山。解密人杰地灵的神泉。
站在珠山顶文笔塔下,挑起三月目光,透过山坡蔓延的荆条,神泉村尽收眼帘,坐落在寨山脚下的村子和颜悦色,在阳光的普照下安闲自在。薄薄的烟雾被风扯着尾巴挂在树梢,一望无际的沃土肥田,荡漾着春天的芳香。一下子,我就跌进了故乡记忆的深渊,让我又一次深深地阅读着那片黄土地上长出的朴实无华。当你停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很久之后才想起回头去看看,屏风恰好。老屋古朴典雅,楼宇色彩鲜明,瞬间,唤醒我对生命的敬畏与祈祷。
两条通往村外的路,在沧桑的岁月里拓宽、硬化,拉近了城乡一体化,显得更加朝气蓬勃。那缠绕着无尽思念的影子尚未完全被岁月风干,腾空而过的一声鸟鸣划出一道弧线,让梦里的诗画升腾成现实的版本。几经跌倒爬起的文笔塔,曾经托举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情怀与梦想。从这里走出去的历代名人遍布各个领域,可敬可佩,可圈可点。告别松柏掩映的文昌阁,我们依旧兴致盎然。边走边看,李村长一番慷慨陈词,对村子的远景规划,更让一行人对神泉村肃然起敬,迫不及待地融入它的前世今生,顿悟它的朴实、敦厚、谦恭。
无论时光走得有多远,来时的路,去时的路,还是一如既往,不会因为朝代的迁徙而变更,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丢掉老百姓的命根——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许多生命都微小如沙砾,我们可以记住的,真的不多。王谢堂前燕犹在,帝王将相已作古,沧桑世事,谁主浮沉?俯瞰烟火人间,万物遵循自然规律,安稳地成长。人的生命,与万物相比,真是渺若微尘。
情到深时,总免不了问一句:“为什么要让我遇到你,神泉。”相遇,我就有责任解密,随您的喜悦而喜悦,痛苦而痛苦。石楼院苟延残喘,依稀可见它曾经的辉煌;老槐树风烛残年,而它斑驳的纹理一样与它庇护的宅院深不可测;有道是侯门深似海,门外高大的牌楼依旧令人咋舌。是啊,假如没有相遇,假如没有这秦砖汉瓦留下的残垣断壁,那这清一色的白墙红瓦,又将会是多么的索然无味。
阳光下,我们翻读着过往无言的故事,让我们感动感叹着这些残缺不全的古老,带着一种神伤的大美,它们早已学会了舔伤自疗。在或不在,神房、戏楼、当里寺、吕祖庙这些遗迹都彰显着神泉村的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还有历代文人雅士到此留下的诗篇墨宝都弥足珍贵。
在吕祖庙下的鹿洞泉鸣,清澈见底的一湾碧水,拂去浮尘,成就了一方热土的名副其实,送来又一季的柳绿桃红,一缕乡风,吹醒这宁静闲和的世外桃源,伴随着生命的拔节、生长。
你可以不知道鹿洞泉鸣,但你不能不知道神泉寺底,如果说你还是仇犹的一位子民。神泉是一个大村,村域面积11平方千米,耕地4000余亩,全村570户,1600余口人。它与藏山毗邻,可以说一衣带水,一脉相承,完全可以称兄道弟。都属于苌池镇,神泉村就在县城北的十五公里左手,交通便利。神泉很早以前,“此地无水,居民苦之。忽有鹿洁白如雪,跑乱石,泉源涌出,滔滔不绝”。鹿洞泉鸣,遂名泉为神泉,村为神泉村。周诗曰:
慰渴泉堪掬,人行鹿洞清。
投钱来饮马,伫听佩环鸣。
神泉又名寺底,因村北寨坡有当里寺,村在其下,故得寺底。此名源出明崇祯八年的《灵雨再记》,不仅如此,寺底村,寺庙林立,有当里寺,吕祖庙,观音庙,弥勒寺,三义庙,大王庙,火神庙,玉帝庙,文昌庙等诸多庙宇,要不说命名寺底,名副其实。
街巷里行走,这里的狗似乎也很有礼貌,或许是认出老武,或许是文明教育,反正我相信,上个世纪的盂县人都相信,只有神泉村的柏叶香闻名遐迩,只有神泉村的莜面河捞货真价实。
手扶斑驳岁月,漫步时光回廊,在这个石雕、石刻的庭院静默,宛立。思绪千顷,感叹屋主独具匠心,感叹古代能工巧匠,同时也感叹岁月流水无情。尽管房子风烛残年,尽管荒草替代了雕梁画栋,这里仍然彰显着古人的举世杰作,彰显着神泉村的出类拔萃。爬上无冕之王,神泉风光尽收眼帘,白鹿山、狮子头、吕主庙、白鹿泉、珠山等一览无余。
白鹿山亦称慕容岭。据《山西历史地名志》载:“晋元兴年(404),后燕主慕容熙与后符氏游此,故名。”明嘉靖《盂县志》亦有“燕王狩于此,虎伤甚众”之说。此山原有寺庙一座,宋神宗时期进士张象仁曾隐居白鹿山三十年。隋朝名臣卢大翼二次隐居白鹿山,潜心研学,博览群书。相传卢大翼精通术数,料事如神,已达上乘境界。暮年的他,双目失明,竟能用手摹书而知其字。白鹿山有一山洞,起名“天窗”即是当年卢大翼隐居之所,现今,洞内尚存石炕,石凳等遗迹。古往今来有诸多文人雅士到此观光并留下不朽诗篇。清乾隆间贡生,盂县人孙世爵曾写一首:

摄影:赵存珍
白鹿山怀古
山以泉名名白鹿,
嶙峋万叠争奇突。
前迹依稀想慕容,
野花葱蒨为谁绿?
折来屐齿数幽寻,
今古茫茫感客心。
为问霸图何处是,
踟蹰聊复伫高岑。
白鹿山又被称作“寨山”,在几版旧县志中记载,“神泉寨在白鹿山,高百余丈,四壁峻险,不可攀,”还有一句民谚,“骏马跑不完苌池川,好雁飞不过寺底寨。”
远眺褪去盛装的白鹿山更显现它的挺拔与高傲,就像我们目睹眼前的李宅,仅高大的门楼以及它的精雕细琢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要不古人说:侯门深似海。不过它们曾经的绽放与现在的没落都化作一缕轻烟,化作生命的沉淀,不需要回忆,却挥之不去。
在历史里徘徊,总会沐浴一身伤感。神泉村的街巷算得上宽展,至少有小车的容身之地,但大都有坡度。我们顺着坡度走向下一个环节,接二连三的房屋稳坐两边。与一千二百年的老槐树望闻切诊,它悄无声息,与很多房子一样,除了安静还是安静,幸亏靠近午时太阳给了足够光线,我们的脸面才足够高兴。要不三郎庙的毁尸灭迹会让我们更加伤感。尽管如此,我还是为灰飞烟灭的当里寺,观音寺,三义庙,大王庙,火神庙,玉帝庙感到惋惜,感到遗憾。人类世界的痛苦,便是损坏与毁灭。
坡度越来越大,历史越来越远。可惜那些古建,幸亏造物主不知,要不那该何等伤心。无比硕大的石场落落大方,这让我们的心情无比舒畅,要是夏日,该是多好的憩息之所,要是有想不开的事情,这里就是最好的回旋余地。
白鹿泉与吕祖庙共生共荣,和睦相安。周边的草木我大多能直呼其名,尽管是在歇息的季节,我还是能觉出它们的丰沛茂盛,盘根错节只是为了汲取养分。所谓自由的羊群在修养的土地上自由活动,它们没有足够折腾的语言折腾,时常显得呆滞与郁闷,幸好有这神来之水,它们才得以膘肥体壮。佛像,泉水,草木,动物相生相克,相安无事。不言不语,却同样感情丰富。竟有这样一处水乳交融的祥和之地,以一湾泉流用甘甜的乳汁滋润着一村人恬美安静。
无数次隔河相望,无数次擦肩而过,真不知神泉的举足轻重?真不知寺底的由来已久?真不知要为错过眼皮底下的风光旖旎而抱憾终身。此时此刻,身临其境;此情此景,相见恨晚。我用腿走路,用脚丈量,双眼扫描,双耳聆听,专心记录。一张嘴今天只是预备,一切问题由老武准备就绪。他的博学多知,他的记忆犹新,他的一丝不苟,他对神泉的情有独钟,以及他对寺底的了如指掌,加上一张口若悬河的嘴,不会有任何蛛丝马迹遗漏,所有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冈,走过了草地,来到神泉,泉水呀泉水,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我心田,请你带我感谢白鹿问声您好!吕祖爷吉祥!
立在有故事的地方,故事便纷至沓来,故事就像这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当然还得先从白鹿泉说起:相传,早年间,此地十年九旱,村民饮水紧靠少得可怜的夏雨冬雪挖水窖储备。遇到干旱严重的年头,便要到十里之外的龙华河驴驮肩挑,其中之苦,苦不堪言。一个烈日当空,焦土冒烟的正午,忽见两只白鹿从寨山飘然而下,跑跑停停,觅觅寻寻,在一片乱石岗上驻足,不用扬鞭自奋蹄,四蹄破碎石,灵角斩荆棘。就这样一股泉流挤出石缝。白鹿痛饮甘泉,身体更显洁白如雪,灵角更加挺拔秀美。耳听一声长鸣,两朵白云遁入山后,无影无踪。好奇的村民,循声觅迹,唯见清澈碧透的溪水喷涌而出。掬水饮之,甘甜润肺。于是奔走相告,于是普天同庆,于是感恩戴德,于是修建了《鹿洞泉鸣》。
沿山泉而绕,听泉水而歌。有福不用早起,有缘自会相逢,有缘更会不打自招。没有初识的陌生,没有巧遇的尴尬。吕祖庙大门敞开,感谢上天恩赐!感谢吕祖爷医泽万民!因此我们匍匐在地,虔诚跪拜,万语千言,不单为心有灵犀。
吕祖,名吕洞宾,即相传中的八仙之一。唐时山西芮城人,科考及第,两为县令。概因不满官府黑暗,不与贪官污吏为伍,于是把家财济贫,在南山修道成仙。道教正阳派称为:“纯阳祖师”。
相传,某年某月某一天,白鹿山下来了三位不速之客,居长者道骨仙风,背负三尺青峰宝剑,气度非凡;第二位,弯腰驼背,肩拂柳条,面目狰狞;第三位,一介书生,身负书箱,衣冠楚楚。三人临渴掬泉,顿感欣慰。放之四野,奇花异草。不禁喜形于色,不禁满意之色溢于言表,于是三人便在白鹿泉旁结草为庐,安营扎寨。采鹿山之草,摘四野之花,分门别类,集束成把。
不日,村民听说是三位郎中,便相约前去问诊,长者打坐草庐,钻心读书。见有来人,书生便引见长者,待患者陈述病灶后,书生按长者吩咐,取其草药给予患者,并嘱咐取其白鹿泉水煎服,三剂服下,病灶痊愈。经多例验证,无不折服。于是口口相传,于是草庐里患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如遇神志不清,呆傻癫狂之病理,拂柳者便手持青峰剑,施法驱邪,无一例外,都完好如初。忽一日,求医者发现人去楼空,村民痛惜之余,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收到吕祖托梦,禀明三人之身份,长者即吕洞宾,拂柳者即柳仙,书生即纪晓棠。三人修道成仙,济世救贫。因到他处行医,故不便久留。在草庐留书一卷《吕祖药签》。并告知,今后患者可按签索隐。于是村民感恩戴德,撤除草庐,大兴土木,雕塑金身,修建了这座纯阳宫。
老武还在他幼小之时,偶染伤寒,高烧不退。便来到吕祖庙,取一碗鹿泉水,摆放供桌前,燃香三柱,虔诚祈祷,念念有词,瞬间碗中清澈之水便生成灰暗之色,并有微粒之物漂浮,一口气喝下此水,三天后,病灶全退。
故事里的故事,存在就是合情,全凭了听者那一份心境。有道是,心诚则灵,兼听则明。
手扶吕祖庙的曲径通幽,俯瞰神泉村的欣欣向荣,村子扩展延伸,早已摆脱老武耿耿于怀的护村长城,或许这就是不可逆转的岁月变迁。看那一排排新房,一辆辆小车,还有那一垛垛金黄的玉米,无不诉说着神泉村的富足安宁。老武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问号,我在此借用他人的论点给他解惑释疑。白鹿山盛产蝴蝶化石,尽管现在找不到它的原型。其实就是盂县很多地方都有的“竹叶状灰岩”。这种灰岩形成于晚寒武纪,距今五亿年左右。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此种石头底色暗红,因为在形成过程黏合了红色胶质泥土。至于说“蝴蝶化石”,他人不敢苟同,只能说:“竹叶”更像“蝴蝶”而已。举头仰望,小寨山的摩崖石刻弥足珍贵。小寨山又名狮子山,还有人说:该山壮如大肚弥勒坐佛,始在元代古人就发现了这点,由姚与邢两姓人立村,并在山下建了当里寺,并命名寺底村。至于当里寺的灰飞烟灭,以及姚,邢两姓人移居他乡的前因后果,笔者眼下还无从考证,权且留着疑问。
一个村的历史,不能与国家的历史相提并论。寺底村的历史像雨,像雾又像风。当里寺觅无影踪,但我知道寺底村形成的过程一定包含了荣辱艰辛。石壁上的二处摩崖石刻记录着它的形成,寨山下的窑洞说不准就是姚姓人家爱情的完美结晶。寺底是神泉的起源,因此,这段历史不能忽视,当里寺重建有着非常重大意义。假如姚邢两姓挖掘姓氏族谱,那么这段历史必将浮出水面。
来去无心的白云不语,瘦了又绿了的寨山神不语,这永不枯竭的一湾碧水也不语。它们为了一个简单的诺言,可以永生永世守口如瓶。就让我对着温厚宽容的岁月,许下善良的心愿,唯愿这世间的每一条河流都可以清澈无尘,每一座山峦都可以平和沉静,每一片草原都可以不分彼此。愿山河静美,盛世长宁。
伴着市文联采风活动的落幕,关于神泉的影子随着匆忙合上的本子被夹在了里面,我计算着抛物线的周期,想象着神泉,却又恒定的疏离着鹿洞泉鸣。如果把脑海里关于您的记忆,用一个点来表示的话,那我大概可以书写出足以延绵到宇宙尽头,那么长的省略号……可我遗漏了句号。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也许神泉的明天会更好。
我相信,借助全域境旅游开发,借助市文联吹风造势,依托藏山这个响当当的名片,未来的神泉更加声名鹊起,更加人文荟萃。神泉的莜面,豆腐,柏叶香将享誉华夏,走进千家万户。未来的仇犹十景之《鹿洞泉鸣》将享誉全球,家喻户晓。
若时间是一个圆,我期望更多的人与你在圆的另一头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