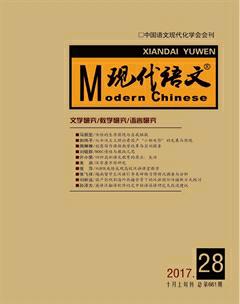《沉钟》与“有意味的形式”
摘 要:“有意味的形式”的术语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克莱夫·贝尔,是指一种能激起读者的审美情感的线条、色彩的有机组合。《沉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普特曼的戏剧作品。《沉钟》的人物美、环境美和对话美呈现出超功利的“形式美”。戏剧中的爱情与事业的悲剧实质、象征的社会典型以及生命性体现了浓厚的“意味”。
关键词:沉钟 形式 有意味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1912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霍普特曼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的出色成就”。霍普特曼一生在文学创作风格上曾有过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自然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第二次是1894年带有想象色彩的剧本《翰奈尔升天》的出版,标志着霍普特曼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转向象征主义。之后,霍普特曼陷入了事业与家庭的低潮时期。他爱上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玛格丽特·玛夏克,以致妻子几度带孩子出走,最终家庭破裂。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玛夏克不断给予他支持和帮助。1896年,霍普特曼的戏剧《沉钟》在柏林戏院首演。该戏剧情节曲折、故事动人,借铸钟人海因利希沉钟坠谷到重新铸钟,再到死于精灵怀中的悲剧,向读者展现了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沉钟》中塑造的“钟”和“森林世界”极具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展现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的术语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贝尔是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其《艺术》一书自1914年出版面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艺术》是基于对以塞尚、高更和凡高等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整个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以及英国“新实在论”的肯定,构建以“视觉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美学观。它认为“绘画的本质在于对自然、现实的再现性模仿,再现性的内容只会引起生活情感,而线条和色彩的排列组合(即形式)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即有意味)。”[1]由此,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假说,为探究艺术的本性提出了新思路。霍普特曼的《沉钟》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在精神实质上有很多的共同点,甚至说两位作者观点相通。基于此,文章擬从“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解读霍普特曼的《沉钟》,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审美价值。
一、《沉钟》的“形式”
形式是超功利的美。贝尔指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成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2]贝尔强调了“形式”是特殊有机的组合方式。“形式是美与艺术的内在的表征方式,它与艺术本性发生着深刻的关联,从而揭示与凸显出艺术与美的存在。”[3]形式是表现内在的特殊组合方式,体现出了作者的灵感和才华,彰显着艺术之美。富含历史价值的画像、摄影作品、连环画和插图等只能激发我们的生活情感而非审美的情感。贝尔所指的“形式”是非功利的,不掺杂教育、认识、道德和消遣等因素,也不是为了传达信息,亦或暗示情感的形式。贝尔并不是主张形式必须要革除美,而是担心作者为了表现美而使得形式功利化,最后不能实现有意味的形式的终极目标。所以说,贝尔追求的形式是指以线条、色彩的特殊组合为表征去揭示事物的本质,激发人的审美情感的形式。这种形式归根到底是凌驾于功利之上,不为表现而表现的脱俗的“美”。
《沉钟》借人物美、环境美和对话美给我们创造了视听、想象全方位的美。作品主要人物是铸钟匠海因利希及妻子玛格达、劳登莱茵、老妇人威蒂恒、水精尼格曼和树精等。在戏剧第一幕,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位头长着一把浓密带红的金发、长着蜜糖般甜蜜的嘴、蜜蜂群绕的劳登莱茵。继而,作者又浓墨重彩地渲染劳登莱茵的美。例如,文中描述她的头发是用太阳光线做成的,闪闪的,像渔网一样。显然,这种力度还是难以让读者把劳登莱茵美的形象烙印在心中。作品中为了表现“人物美”,巧妙地淡化或“黑化”其他人的形象以形成视觉的对比,从而突出劳登莱茵的形象。首先是铸钟匠的妻子玛格达,戏剧中没有用任何笔墨去表现其外貌形象;其次是威蒂恒,一个口硬心软的正面人物。但作品不惜把她形容为“雪白的头发蓬乱、脸孔像男人,长了胡须” [4]。这和读者期待的温柔慈祥的形象相去甚远;最后是长了如象般长的鼻子的怪水精,能用蹄子点亮烟火的、残缺不全的树精。这些被淡化或者丑陋化的形象无不为了突出“劳登莱茵”的美丽。戏剧还借树精之口,强调劳登莱茵是精灵之中最美的。总之,作品致力于塑造一个标致至极的美人形象。
该戏剧构造了两个典型的世界。一个是山下的世界,代表教会盛行、工业文明的现实世界。主人公海因利希在山下生活时无私地为“神的事业”奉献,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犹如百姓眼中的守护神。他和山下的人们观念一致,认为森林是妖魔鬼怪驻守之地,必然要遭受人们的摧毁。另一个则是山上的世界,代表自然、虚幻的森林世界。《沉钟》对森林世界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百花吐艳,有番红花、紫罗兰、樱花等;动物报春,有鳟鱼、地鼠、兔子等。精灵群舞,一派热闹。自从坠谷后,海因利希在森林世界休养了一段时间。亲身的经历使他对精灵世界的看法大为改观,并着迷般发出赞美之词,如“这儿很美、森林的呢喃声有些奇怪。枞树伸出黑色的手臂,也很奇妙。”[5]可见,森林世界确实美丽梦幻。
《沉钟》戏剧对白的描写富有特色,借人物之口发出诗般语言,优美活泼;或采用“互文”的表现手法,含蓄而有力。例如,树精抱怨人类在山顶铸钟,发出:“我们可惨啦/会像野兽一般吠鸣/向立在高处的钟,狂吠/那钟是湖泊,我是噗通一声的溺死鬼”一系列的悲鸣。作者把钟比喻为湖泊,把树精比作溺死鬼,语言十分生动。这既让读者读出了精灵们强烈的厌恶情绪,也让读者明白了在山顶上铸钟给森林世界带来的巨大威胁。再如,精灵刚赶来参加跳舞时,说了一句:“我刚从霍拉妈妈的花圃悄悄脱身而来。”霍拉妈妈是日耳曼神话中掌管家事和婚姻的女神。句子精简俏皮,符合人物的说话风格。用“霍拉妈妈”一词精妙地表达了精灵刚处理完家事后愉快的心情。又如,海因利希用短短的一句“喂,威兰特之子”来教训偷懒的侏儒。铸钟师傅在山顶上重新铸钟,请了六个侏儒帮忙。其中一个侏儒因为贪玩偷懒,用自己的手做模型,而遭到海因利希的呵斥。“威兰特之子”相传是德国传说中的铁匠,会用自制的翅膀逃离幽禁之地。此处的用典,显然是海因利希对侏儒的讽刺,话语强而有力,恰到好处。endprint
戏剧在对“劳登莱茵”的刻画、对“森林世界”的描写、对人物语言的叙说可谓独具匠心。这些人、景、话莫不是形式的表达,其为激发、唤醒我们的审美情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沉钟》中的“有意味”
(一)“有意味”即对创作对象本质的把握
贝尔认为:“艺术品是排除了所有偶然因素,把对象视为由线条、色彩交织而成的纯形式的组合。这要求创作主体从根本把握创作对象。”[6]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有本质可言。欣赏者品味艺术的过程也应该抓住作品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对创作主体还是对欣赏者来说,艺术品的根基都非偶然的,都应从本质入手,即从“意味”入手。
任何作品必然被打上时代背景的烙印。创作的背景既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等大背景,也包括作者的家庭生活、教育经历、情感经历和工作经历等个人背景。由此,要把握《沉钟》的本质需追溯到霍普特曼的生平背景。在创作方面,曾与他一起崇尚自然主义创作的作家,如哈特兄弟和史拉夫纷纷开始转向研究神秘主义。这对于霍普特曼的事业来说是重重一击。在家庭方面,霍普特曼难以忍受到妻子内向的性格,从而选择了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玛格丽特·玛夏克。家庭的破裂给他带来第二重痛苦。《沉钟》的基调是来自霍普特曼的爱情、事业的双重悲情。铸钟师傅海因利希原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妻子玛格达和两个孩子的相伴。由于受伤,海因利希遇见了森林中最美丽的少女劳登莱茵,并发现自己对她产生深深的爱慕之情。当他从森林回到家中,跟妻子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山谷的工作也无法吸引他。最后,在死亡之际,他找到了劳登莱茵并倒在她的怀中。这一幕爱情的悲剧象征着作者现实中的婚姻状况以及他坚持选择真爱的决心。戏剧的“钟”是事业的象征。海因利希把铸好的钟运到山顶的过程中,被精灵施法,导致人和钟双双堕入谷底。“钟”是海因利希大半生的理想追求。作者在戏剧的第一幕设计了“沉钟”的剧情,也是在表明他的创作风格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彻底决裂。基于此,悲剧和痛苦是作品的底色,并贯穿始终。整部戏剧迈不开的苦楚,正是作者向读者诉说自己的事业不得意和家庭的悲欢离合。
(二)“有意味”即物化的审美情感
艺术家创造艺术品多是借助纯形式的排列、组合将审美情感物化。形式是审美情感的承载物,也是审美者审美情感的激发点。“有意味”的本质是物化的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有着区别于一般的审美情感。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创造者而言,“有意味”即是一种在生活情感之上的“纯粹”的审美情感。其次对于欣赏者来说,他们对同一作品会有诸多不同的情感,而审美情感则是必然引起的、普遍产生的审美情感,具有一致性。同时,这种审美情感恰恰和创作者最根本的、终极的情感相吻合。
《沉钟》没有直白地诟病社会上形形式式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相对含蓄的象征手法塑造了一批文学形象来讽刺现实。“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用一种看得见的符号来表示看不见的事物。”[7]象征背后,正是作者隐晦地表达的情感。象征的对象则是审美情感物化的典型。在戏剧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象征了懒惰的六个“侏儒”,象征束缚人信念的牧师,象征墨守成规的教师。海因利希在戏剧中的态度正是作者的的立场。
除了反面的象征人物外,霍普特曼还塑造了两位非常突出的正面人物。第一位是威蒂恒老夫人。她久居森林,心地善良。她把弃婴劳登莱茵从地衣中捡起来抚养,每天照顾侏儒们的饮食,还把男主人公从死亡中拯救过来。在她身上显现出来的乐于助人的精神并非来自上帝或神灵,而是源于人性的美好以及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她激烈的言辞是有指向的,尤其是对准像牧师、教师等这样一批有社会身份但内心腐化的人。威蒂恒老夫人象征着反宗教,敢于打破清规戒律的人物。第二位是劳恩莱登。她是森林中的宠儿,个性鲜明、敢爱敢恨。她不轻易接受爱慕者的情意。在爱上男主人公之后,一度受到了老太太的劝阻,但她勇敢,不顾宗教所谓的道德观,礼义廉耻。她执着于爱情,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而甘愿吃尽苦头。她甚至肯为了爱人而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她是新时代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女性的象征,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象征式的人物是霍普特曼对审美情感物化的结果。读者在品读戏剧时不难感受到作者对宗教黑暗的厌恶以及对人性、情感和理想的渴求。《沉钟》中的“象征”式人物蕴藏着深厚的意味。
(三)“有意味”即生命性
吴甲丰把“有意味的形式”和中国书法结合起来,认为该思想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书法的精粹相近。书法讲求笔墨,重视神韵、意味。书法旨在通过形去传达无形的生命感和运动感。以此,我们可以认为“意味”富有生命的内涵。[8]朗格认为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中的“意味”是一种生命意味。[9]由此,我们可以视“有意味”为一种生命活动。台湾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游惠瑜指出,追求超越存在的限制或宗教追求灵性生命的思维,人得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10]
《沉钟》处处散发著生命的气息,其中较为显著的两点是:现实中的人类追崇宗教信仰与海因利希对生命的所思所想。在山下的世界,宗教和神是人的全部的信仰。所有人都企图在山顶铸钟镇压森林里的“精灵作怪”。他们认为“自鸣钟”是神的力量,定能帮助他们驱逐邪魔鬼怪。他们把有神的词语当作金玉良句,如牧师有一次听到“打开窗子,让光和神进来”后,大为认同。在牧师看来,不靠上帝,海因利希是不会在病榻中醒来的。上帝是主宰大地的神,拥有叫人生即生、死即死的力量。所以,他们对生命的思考都遵循“上帝至上”的原则。
在戏剧第一幕中,海因利希伤病醒来后说了一段话:“现在终于明白了,以前可不明白,原来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我掉下去。掉下去时是活的……现在我已经死了。”[11]这一段话语饱含了深刻的生命观。生死是可以转换的,当主人公认为自己掉下山谷是“生”,则说明“肉体”虽“死”,但此刻“灵魂”才活过来,才是生的。换言之,他领悟到了当初在山脚下从事的神圣工作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看似美满的家庭和让人歆羡的工作都不是“灵魂”“生命”所要追求的。后来,即使他想要重新铸钟,亦宣称不是为教堂而是为一棵向他“发布命令”的枞树而铸。这听起来荒唐,但实际上是主人公找到了生命的依托。
三、结语
霍普特曼的《沉钟》可被视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贝尔主张用线条、色彩的有机组合去传达审美情感和生命感。《沉钟》的篇幅不大,但其一戏五幕为我们展现了戏剧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戏剧的形式具有超功利的、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人物美、环境美和对话美三方面。戏剧中爱情与事业“双悲”,其象征式的社会典型、富有生命感的人物对话具有深刻的“意味”。
注释:
[1]凌继尧:《美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2]薛华译,贝尔著:《艺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张贤根:《20世纪的西方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4]李斯译,霍普特曼著:《织工》,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5]李斯译,霍普特曼著:《织工》,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6]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二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7]张洁:《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社科纵横,2009年,第5期,第177-178页。
[8]汝信:《外国文学(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318页。
[9]荣佳,国柱:《“有意味的形式”与艺术符号——贝尔与朗格的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03期,第64-69页。
[10]游惠瑜:《生命教育的哲学意义与价值》,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2年,第5期,第89-105页。
[11]李斯译,霍普特曼著:《织工》,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吴雪莹 广东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14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