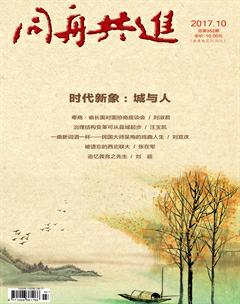开放、包容:从深圳看城市发展的秘诀
聂日明


2017年上半年主要城市经济数据陆续发布,深圳上半年GDP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速超过京、沪、穗,考虑到深圳下半年数据往往比上半年更好,专家预计深圳2017全年GDP有望超过广州,成为全国第三城。
“圳”字在客家话中,意为田间水沟。深圳起步于渔村,从无到有,平地起大城。40年前,当它还只是宝安县时,人口只有30万;今天,它已成长为常住人口超过1100万,经济总量稳居中国第四名的大城市,也早已超过天津、武汉、南京这样的老牌中心城市,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明白是什么成就了深圳,我们也就明白了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
【“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圳这些年的发展轨迹说明,经济全球化以来,区位和开放程度越来越成为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学者陆铭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使得大港口及周边地区具有明显的贸易成本优势,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更需要面对面交流,这使得人们在城市里相互提供服务和分享知识变得更为重要,进而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同步集聚。中国现有的大城市大多都在区位较好的地段,开放程度也较高,从效率和发展前景看,这些城市不该拒绝人口流入,反而应该强化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
当然,区位和开放只是理解深圳奇迹的两个维度。同样的地理位置,成为特区之前,深圳是无足轻重的小渔村,显然,转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特”。同样是特区,厦门、汕头、珠海虽在区位上有一些劣势,但基础却要好于深圳:厦门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汕头是“岭东门户”,珠海是新型花园城市。但如今,它们的经济规模都远低于深圳——规模最接近的厦门也只有深圳的1/4。可以看出,它们的“特”与深圳的“特”是有一定差距的。
特区创立之初,深圳底子薄,人口、GDP均不如当时的厦门、汕头,这是劣势,但也是优势,因为在改革与试验上,深圳没有历史负担。以价格改革为例,1980年代,中国还实行计划经济,城市需要的物资靠计划调配,由政府统一定价。深圳不是大城市,没有纳入当时的经济计划,无法获得体制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当时的市领导不得不放开价格管制,用市场机制在价格“双轨制”中的“市场轨”里获得物资。1984年,深圳率先取消了商品票证配给制,开全国之先河。深圳也是全国首个公开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城市,推动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已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被视为颠覆性的举措。
在不断改革和试验的阶段,深圳创下一个又一个城市建设奇迹。比如,建造深圳国贸大厦,速度最快时,曾3天就盖完一层楼,让“深圳速度”举国皆知。在这速度的背后,是理念的突破——国贸大厦的承建合同中有这么一条条款:提前一天完工,奖金5万,耽误一天,罚款5万。1979年,改革先驱袁庚就在蛇口尝试过多劳多得的工资体制,打破“大锅饭”的平均分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激励手段在那个时代还是饱受争议的。
特区有了政策的支持,虽然“自带光环”,但特区名号本身无法吸引人口的持续流入,市场化体制所带来的利益才是人口持续流入的关键。从人口流动看,深圳一直在鼓励人口的流入,“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度是深圳最知名的城市广告语。1980年,深圳人口仅33.29万,城镇人口不到3万,大多是农村人口。成为特区后,全国人口向深圳流动,常住人口快速增长,迫于管理压力,深圳曾率先采用暂住证的方式来限制人口流入。但从结果看,流入人口只在当年有所放缓,随后又恢复常态。整个1990年代,深圳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3万,到2000年时,常住人口已达700余万。
总的来说,深圳的“特”与其它特区的“特”差别有二:第一,更包容、更开放;第二,依靠大改革、更加市场化。开放是深圳的底色。深圳本地人少,是中国目前所有大城市中最像“移民城市”的城市,大家都是外地人,在心理上没有排外的基础,对外地人的心态自然开放。城市有了人,才有资格谈经济总量高低、创新多寡。而更市场化的改革,能吸引靠能力吃饭、靠本事赚钱的人才和资本,裙带主义、国企作风在这里难成气候,效率、竞争力自然彰显。
【城市是规划出来的还是生长出来的】
最近40年,中国城市从计划经济起步,曾一度迷信于规划,城市发展的起点往往是做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结果与城市规划目标都有或多或少的偏离,深圳也不例外。1982年,深圳市政府編制完成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将深圳在2000年的远景规划为人口80万、建设用地面积98平方公里。由于发展速度很快,1986年又修正为110万人和122平方公里,而实际情况已经到了701万人和467平方公里。10年后,深圳总体规划2010年的目标为430万人和480平方公里,实际情况则为1037万人和918平方公里。
这就表明,规划总是容易滞后于实际表现,这个现象有两层含义:第一,城市不是规划出来的,在1980年的时间节点,再高明的规划师、计划者也料想不到深圳的前景会如此美好、生机如此蓬勃;第二,落后的规划如果被彻底执行,人口和用地规模被严格控制,今天很有可能就没有深圳乃至上海了。
改革开放的案例告诉我们,城市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深圳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年来,深圳在一些领域其实存在着“非正式”现象,但深圳总是能包容它们。以外来人口为例,正式制度要求外来人口在深圳居住要登记身份,就业要签订劳动合同。而位于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市场,就是“低收入者的乐土”。这里聚集着所谓的“三和大神”,没有身份证、没有正式工作、流动性高;但同时,这里的生活成本极低,也有大量灵活的就业机会,有不少日结工作可供选择。这种环境给那些在正规制度中无法生存的人一个临时缓冲的场所,让他们在困难时不至于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深圳的土地制度也值得一提。据资料统计,2014年以前,深圳共有61万栋建筑,其中“合法外”和“违法”建筑有30多万栋,超过一半;深圳总建筑面积7.52亿平方米,“合法外”和“违法”的就将近4亿平方米。但实际上,如北大学者徐建国指出,所谓“违法”值得商榷,因为有些是建时合法、后来被划为违法;有些是政府因规划原因不批准建房许可,村民顺应形势而建;还有的是政府补偿机制存在问题,村民抢建、“种房保地”。
综合说来,城市的一些“非正式”现象有其问题所在,固然需要整治,但也要知道,每个城市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非正式”制度及现象,它们往往是在正式制度过于刚性,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自身被迫形成并自发演化而来的。这些“非正式”制度及现象对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益处,这时,我们究竟是应该指责这些行为“违法”、铲除它们呢,还是正视它们产生的背景,将其改革为正式制度,进而包容它们呢?显然,深圳选择了包容。
此外,深圳的包容还体现在,它在吸引外来人口时,对人口素质不加以挑剔,这客观上使其人口的学历水平要低于其它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的产业也是低端的,产业自我更新使深圳成为高科技和金融驱动的城市,这也是最初的规划者并未能预见的局面。
过去,深圳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外向型经济虽然赚钱,但难言体面。随着经济发展,深圳也经历了放弃“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产业升级的过程。2003年新一轮经济增长以来,深圳长期停滞的劳动力薪酬水平开始上扬,土地成本随之飙升。到了2008年,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开始外迁。这时,深圳已成长为一线城市,人口与经济总量的基数让它容易在服务业、创新上突围。
规划者衡量创新的能力,看的是大学、高端人才等指标,如果看数据,深圳在这些方面是败于京、沪的。在新近的国家创新规划里,依然将“科创中心”的任务交给了上海。但创新也不是规划出来的,并不是指标越高,创新能力就一定会强。2015年全国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10名中,有5家是深圳企业,没有一家上海企业。上海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是35.2件(2016年底),深圳是82.6件(2016年底);在更具含金量的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上,深圳占了全国50%左右,上海同期不及深圳的零头。可见,从市场里长出来的创新可能更具生命力,也更让人期待。
【城市之存在在于满足人的需求】
城市由人构成,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为人们在城市里交流提供便利。理论上,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的思路是预测人口,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的前瞻性建设。这里要明确两点:第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城市经营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服务,而不应该挑选特定人群;第二,预测人口不是为了控制城市规模,而是为了前瞻性的规划,量体裁衣。
但直到今天,国内有些城市的规划,其发展目标并不是为了让人满足,而是规划者闭门造车给出发展目标,那些落后与过时的目标限制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规模。按1000万常住人口规划的城市里生活着2000万人,交通怎么能不拥堵?学位怎么能不紧缺?治安如何能好?
具备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不仅是文明的象征,包容带来的人口增长最终将决定城市的地位,有人流入,城市才有希望。一个城市市辖区的城镇人口超过1000万人,它即使不是一线城市,也是最有希望成为一线城市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人口集聚也有坏处,但城市不能只想要人口集聚的好处而拒绝坏处。
时下,一线城市甚至杭州等二线城市已全面拉开了爭夺人才的“战争”。然而,部分城市对所谓“低端人口”存在一种偏见。多个城市推行居住证或积分入学政策,给人口打分,让高学历、有正式工作、有稳定居所的人留在城市;而低学历、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居所的人则难以靠近;进而通过“以学控人”、打击群租、淘汰低端产业的方式限制他们。在很多人的眼中,人口是负担,会消耗社会资源,导致交通拥堵,扰乱社会治安,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更是要加以限制。
这种偏见亟待改变。现代城市需要多元化的劳动力,既需要白领,也需要清洁工人,驱离清洁工人的后果就是相关工作岗位的薪酬直线上升,一些大城市正在承受这种恶果,诸如“大学生的工资相当于月嫂收入零头”这样的新闻并不少见。什么人是“人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并不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偏好,因为后者的管理知识永远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如果18世纪末的纽约管理者凭借当时人类的知识,只允许熟练的工人进入纽约,而拒绝其余人才的话,还会有后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吗?
这些正在争夺人才的城市还是没有明白:人口规模是人才的基础,人才无法脱离人口规模而单独存在。只要人才而不要人口的城市治理,必然是不包容的,也无法吸引足够体量的人才。没有人口规模的扩张,这些被吸引来的人才很快就会发现,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工资增长,城市生活服务差,他们最终也还是会离开那个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