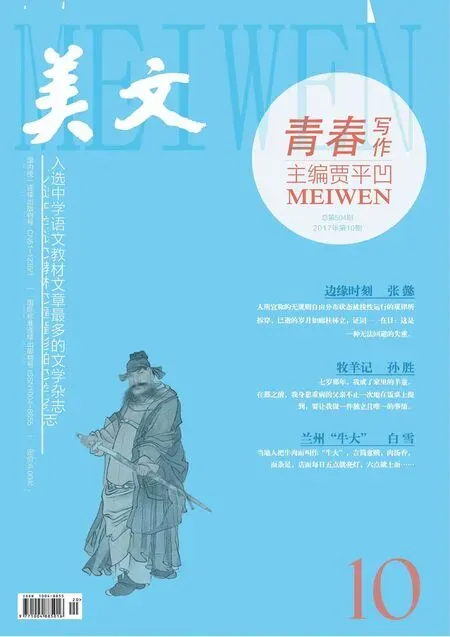边缘时刻
|张 懿|
边缘时刻
|张 懿|
生 辰
一个人的生辰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一个冷淡的泄密者,一种背叛的标志。
人所宣称的无规则自由分布状态被线性运行的规律所拆穿,已逝的岁月如廊柱林立,证词一一在目: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失重。
你纵放烟雾以使事物迷惑,子宫之水却令一切虚掩的努力落空。所有攀援的路,最终都引向诞生之初。哭泣以本能追上你,而你以环形方式进入时间内部。
灯
高纬度的地方,窗外的天光暗得早,下午四点,就需要点灯。
小小的一盏,光芒慢慢升腾起来,那是节能灯所特有的开启仪式。
这是一种小巧而庄重的典礼。你等在黑暗里,犹豫着是否应当把手指放到按钮上——那是分割黑暗与光明的跷跷板,仿佛只要光明的一头翘起,黑暗的一头便永远坠下。人类的进化,已经把这亘古而沉重的抉择,简化成了一个手势——你面容静谧,内心却奔腾着千军万马,你挣扎着,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坚持什么。自我怀疑与反问的重锤连绵落下,如击木鱼。终于你软弱下来,甘愿让恐惧占了上风,扶墙的手却坚定起来,食指毫不犹豫地轻轻一摁,“啪”,那光芒便由无至有,由弱至强,沿着墙角,墙裙,墙壁主体,再至天花板,次第爬升上来,直至在屋内蔓延。
灯光的走势,和水以及记忆,有着惊人的相似。火焰的光芒炽烈而明晰,像洪荒旷野里的小兽潮热的舌,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固执,袭面舔来。而灯光却是温吞而暧昧的,它只是一波一波地叠合起来,终至抵达明亮的界地,隐约还带着些不能言说的幽怨,宛如薄暮四合时初升的凉意。
若试着在深秋的黄昏,雨丝将断未断时刻走将出去,寒意了了,被一两滴稍大的雨点侵入脖际。惊蛰的你,举目看见那昏黄路灯下,自绝于世般兀自飘洒下来的雨丝,直直冲你面孔而来,仿佛一把光的锥子扎下,落手却又失了力量,化为细碎的针刺,最后只是一种令人惊愕的湿意,那委实是要令人断肠的。
反视
在夜的中心反观自己的骨骸,像瘸鸟凝视落羽。
思维是断续的荧光,在纪年的平面上微弱地颤动,获得蛛丝蛰伏于阴影下的形态,而意识是笼中的船,在铁丝蒺藜中模拟走私与偷渡。
四月在上升,四月在下沉,微小物什的馥郁令人震动。囚禁的人徒劳地从身上擦去寒冷,擦去雪和冰冻的记忆;而当雨水滴穿一个人的春季,没有一阵足够温煦的风拥有复活的技艺。
一个正午
正午的镇中心像稀释了十倍的热带丛林。年轻的黑人女子像移动的豹,青春丰满的肉体闪动着钢炭的光泽,紧身背心里,她们自己都无法掌控的性感几乎要蜂拥而出。她们像风暴中的树梢,彼此致意,卷走路边等车老人的艳羡。他腆着肚子,摇摇晃晃地找位子坐下,吞下眼里最后一点不甘的馋涎之光。
白种女人们,则是冷寞的白象。她们更像是放置过久的人工奶油,或是僵硬的蛋白糖,在日头下散发着腻白的光泽,像一片片灰白的阴影,阳光经由她们而减少直射,落掷在地就成了秋。
公车依序而行,无人拥攘。秩序感让人心安,却又有些单调,人与人保持着让人心酸的距离,并以种族、阶层、偏见等作为距离的填充物。
风起时,碎塑料包装纸沿街相逐,正如漂浮在街道上的人类记忆,总是在即将交汇时折转方向不了了之。
我背靠着墙,站在一家超市前。一个多月前我还在此买过法棍面包,寿司和果汁,如今已闭门大吉,只有卷帘门不知疲倦地颤动着,发出有节奏的愉快声响,像一支踢踏舞。它那无忧无虑的样子,像极了从我身边走过的,那个哼着歌的清洁工。
那个时刻我意识到我的悲哀:更多的人将生命的一瞬向我展开,他们的片段交叠陈列,而我只能束手旁观。我的片刻,和他们的片刻,就此埋葬时间的深海,不复有路回来。面向这巨大的人类数据库,我空洞的像一座冰山,孤独的像最后一只猛犸。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再也无法将这个午后的热力与荒寂传达。横亘在这洲际洋流与时辰之上的空白,将永远是他人无法企及的荒山。我惧怕读解,更惧怕解码后的无奈。我知我必将如海底沉船,以铁锈度年,对于所历,只字不言。
村庄
小村庄,夜色也细窄得像一条溪流。只米宽的青石路上,流过嘈切的闲聊声。
白天忙碌的农人归来饭罢,搬了小凳围坐在自家门口。院坝是水泼过的,伴着让人肃然的清洁感。昼热这种冥顽又霸道的固体物质,晚饭时刻,伴着“哧啦”一声,都化了汽——一只被渔夫收回瓶中的魔鬼。
蒲扇是一根神秘的绳索,在昼的尾上系了活结,就散出菩提似的觉醒之光。圆融,舒散,让人解甲归宅,结束劳作,遵蹈自然之力。
零丁几个游人,是虚线勾出的横切面,在酒吧咖啡红灯笼古玩店边,和村民产生了经济学的松散连结。影子漂浮在石上,一只一只,现代城市自愿流放乡野的游魂。
路灯是桅杆,是灯塔,是廊柱,无谓地承担了夜游者的心安,无数虚谬的寄托。路灯只是懂得释放的沉默者,光亮即孤独。
乐声是有的,每隔几步路,就是一个间隔年。走调的女声七七八八唱着生日快乐。淹没半条街的卡拉OK。霓虹招牌里的蓝调爵士。无人听,顾自拨奏的渔舟唱晚。古筝的清越,夹在粗糙电子乐中,有种美而凛然的异质感。
而我,像初生的鱼仔,悬浮在这一切当中。我是一只冷静的眼睛,是一种隐形的抽象。我只负责白描和想象。
边缘时刻
最艰难的是边缘时刻。白昼已经瓜熟蒂落,而夜尚未完全成熟。灰橙色的黄昏像放久的柑橘,疲惫地干燥和萎缩,日复一日地榨干你的新鲜与柔软。你只是松散无味的白絮,倦意胜于飞鸟。
你甚至懒于搭理天色,弃置微光不顾。
再一次站在莽荒旷野里,除了漠然的风,再没有别的分镜头。
黄沙是好的,戈壁滩是好的,枯草是好的。它们让你对人世的信任感完美归零。
只有虚影来来去去,一个个都像形影相吊的鬼魂,在你的阴郁里穿梭交错。
对于实体的渴求已经超过了你对于自身塑形的执着,你满足于只要能抓住点什么:只要握在手里有形态、温度和质感,哪怕声响也可以。为着这一点不可得的实体,你试图化身为苔,为石,或是树皮脱落的部分,虫豸死去的躯体,沙里的一块土,甚至是草上的光斑。
直到对它们的虚幻,也彻底失去信心。
只言片语,从你的枝干垂落。这是欲望的秋天,你剪净落叶,等着初雪覆盖上黑色的心。
萧瑟里的静寂,荆棘里的沉默,这是你的收尾。无人知晓的爱,像鸦阵落地一般冷却。
你匆匆掩藏哭泣,草率的像月夜落单的野狼。你隐晦的像多足的爬虫,扭转琥珀色的脊背,向土壤深处沉去。
你沉入你的孤独,像石落于井。
小提琴呵
小提琴真是一种非常忠于自己的小乐器。神经质,纤细,尖利,刻薄,敏感,骄傲又脆弱。再轻快的调子,拿小提琴拉出来,都带着一丝酸涩,像新鲜的柠檬皮。竖笛就不这样,轻灵起来就像缭绕在春神跳舞的森林里的风,耳朵和指尖都捉不住。小提琴呢,小提琴它是晨曦与薄雾,是归舟与烟渚,音色再美,也像漏风的帘子,一面表演着虚构的愉悦,一面又笨拙地泄露宿命般的哀矜。琴声又稀薄,就算是最浑厚的第四弦,也带着点虚散的意味,草茎似的疏松,不够紧实,没有钟器那种黑土似的沉实感。
慢调的曲子尤其要命——细腰的日本美人,匍匐在神位前哭泣,繁花飘缀的和服后摆大摊着,吸掉了半个太平洋,过剩的悲情,枯寂的庭院也镇不住。快板则让人焦虑,螺丝似的一圈圈绞紧脑里的弦,肢体在音乐空间里无限收缩,迅疾地团成一个点,又被急匆匆放逐,仓促的像永远赶不及的道别。
我唯一喜欢的部分是越弦跳弓,果敢,意志清绝,音色的截断感非常诱人,带着一种无可驳斥无可挽回的坚决和清澈。碎弓则难以忍受,疾驰的犹豫也是犹豫,改变不了它徘徊的本相。
同样作为弦乐器,大提琴就比小提琴可爱得多。那种可爱就是河马相较于小扬子鳄的可爱,后者危险多了。也悲哀啊,却不是站在冰洋上孤岛尖的那种悲哀,不孤立破碎也不狭长,而是一种浑厚辽阔的悲哀,像俄罗斯苍茫无际的冻野,像某个壮阔又苦难的民族,像有世纪以来,宇宙的空寂,是一种有空间感的惆怅。
小提琴如果有版图的话,那应该是苦竹成阵的南方。夜漏清长,竹筒冷响,空阶到明。那种雨水漫患的调子,风湿一般植入人的疆土,用身体就能记得住。
我不能听小提琴,太忧伤了,会让我想起生命里最好的一切,如何急不可待地消逝,离我远去。想起我如何凝视着你,最后却垂下了眼睛。想起六月,你如何像最晴朗的孔雀蓝釉,星散在我熄火的窑壁。想起夏季,那不可捉摸的天色,要如何将落日完美地呈示于你。想起陌生的森林,鹿在奔跑,湖水沉吟,鸟阵徘徊,想起山妖把音符织成网捕捉灵魂,而我不能,与你一同,因为敬畏、恐惧和出世的美而颤栗。
到底有谁会喜欢小提琴呢,那么悲哀。和人生太像了。
此前
早晨醒来时你在等我,像火车等待它的乘客。你静止而宁穆,仿佛已经抵达。不再出发了,你卸下你的烟雾和喧腾,并任由它悬挂在一幅印象派的画上。
在此之前,你是悄然晃动的钟摆,等待整点的“咔塔”声。你熟悉那声响,如同熟悉早春时,冰上的第一道裂缝。日子如绸,绵密而细致,而你总是知道一天的线头,准确无误地夹住它,并从连绵的时间之匹里抽出。你是黎明本身。你不驱使鸟群,也不逐赶飞霞,只待以耐心,仿佛那是滴入我梦境的清露。
有时我醒来,还佯装睡着,怕一转身,就被你身体里的耕地与炊烟放逐。就像手足无措地站在你的童年,看柴火的刺呛味与潮湿一同升起,而你奔跑着,不知有我。

张懿,女,目标是成为卡夫卡或狄金森式的地下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