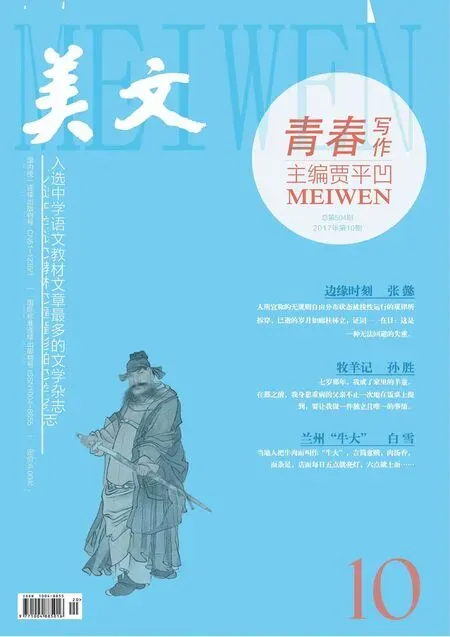她
孙 婷
她
孙 婷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她虽生于富裕家庭,却早早地被算命先生认定是命贱不详之人,受到父亲冷遇。幼年丧母。母亲去世当年,父亲就迫不及待地续了弦,把继母接进家门。
少女初长成,好奇之心未及探索这万千世界,分明世上的善恶之心,便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一个没有人生理想,只喜欢抽鸦片的小学教员。那一年,她14岁。
她不甘心。她要自由。她要读书。父亲大怒,强迫她辍学在家,形同软禁。一年的时光,她是在阻挠、逼婚、恶言恶语中捱过来的。童年已是万分不幸,唯有祖父的爱能抚慰她多愁善感、孤苦飘零的灵魂,如今,父亲的压迫反让她的性格越来越倔强、极端,如同导火索一般,触发了她一生不幸的潘多拉魔盒,命中了算命先生的定论。人就是这么奇怪,总是往对自己充满负面评价的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头也不回,然后把这叫作“命运”。
18岁,祖父去世。世界上最疼爱她的那个人走了,家也再无可留恋之处。
19岁,她逃离了那个没有爱和温暖的所谓的家。
她结识了读大学的远方表哥,并在他的帮助下来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她用多么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听着它巨大的喘息声,想往着没有束缚和压抑的生活啊!然而北平居大不易,她必须停下所有美好的想象,低头瞅一瞅身上的破衣烂袜,发愁每天的吃饭钱从哪里能筹措到。逃婚的“出格行径”让整个家族都震怒,感到“蒙羞”,为此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无奈之中,她只得再次回家。软禁,打官司,败诉,轰轰烈烈的一番折腾后,全家搬往乡下,她也被迫同外界隔绝。
在乡下的时候,因为帮佃户说情,她遭到伯父痛打和软禁。伯父扬言要劝她的父亲勒死她,以免再连累和危害家族。恐惧一次次攫住她的心。后来,在小姑和小婶的同情和帮助下,她再次出逃。
那段日子居无定所,险些流落街头。家乡封闭的空间和落后的思想让她压抑,但她不得不依附于此。她的一切行为在那个小小的天地里,都被看做是离经叛道,惹得亲友痛恨不已,就连她嫌弃的未婚夫,那户人家也厌恶了她。爱也好,恨也罢,那就是她的家,她的故乡,刻进骨子里,融进血液中的地方。她该怎么办呢?她能怎么办呢?
她同未婚夫找了间旅馆,住了下来。虽不至于流落街头,但生活的困顿让她灰心丧气,苟延残喘。她开始和未婚夫一起在逼仄的旅馆住处吞云吐雾,行尸走肉般的生存于世。半年后,她怀孕,产期临近时,未婚夫不辞而别。
挺着大肚子,无力支付房费,又无生存技能,只会写作。万般无奈之下,她写信给报社,并寄去自己的小诗。她是那样有才情,一首小诗就打动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心。他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在旅馆门口。那一年,她20岁。
孩子生下后随即送人,后夭折。她不是不愿意抚养孩子,她那颗善良敏感的灵魂连一只小金鱼的死都难过万分,何况自己的骨血?但她实在无力抚养这个孩子,自己饥一顿饱一顿,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21岁,她同那个文学青年生活在一处。同他在一起的那几年里,他一边做家庭教师赚钱养活两个人,一边在外借钱度日,她则在家徒四壁的旅馆小房间里,看着外面的鹅毛大雪,等着他回来。
等的无聊了,她便拿起笔写作,写下她的困顿,她的饥饿,她的寂寞。二十多岁的她写了那么多文字,唯独没有写下的,是她的青春。
她同他一起生活了六年。六年里,她为他洗衣做饭,叠衣铺被,抄写文稿,日日等待。她像一个孩子一样依恋他。尽管逃离了那个压抑逼迫的家,但她的思想被那个家浸淫腐蚀已深,女子的自卑生生地压在心头,使她无法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成长环境,让她既然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便只能依靠另一棵大树。
六年里,他不断地爱慕上别的女子,与她们暗通款曲,她心有不快,却装作不明就里的糊涂样子,最后一次,她终于愤怒相向,换来的却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体和心灵遍布伤口,再医下去已无必要。一场爱情悲剧就此收场。
可笑的是,他在友人面前不断地强调她没有“妻性”,作为对他们分手的解释。他认为她有着普通女人一样爱吃醋的性子;他认为妻子就该像旧社会的正妻一样,贤淑到主动为丈夫纳妾,才算有德;他认为她的写作才华太突出,作为妻子,怎么能抢去丈夫的风头,甚至独领风骚?六年里,他看到的都是她的缺点,却看不到她的付出和等待,也读不懂她的寂寞和忧伤。
作为文学上的伙伴,他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付出,满意她为他抄写的手稿,允许她与自己走得很近;
作为生活上的伴侣,他厌恶婚姻里的“平等”“相互尊重”,嫉妒她的才华,瞧不上她和她的创作,带着怜悯和施舍的目光远远地打量着她。
散了吧。
怀着他的孩子,她投入到另一个男子的怀抱。那一年,她27岁。
她累了,也倦了,与新婚丈夫的关系不过是想安稳地过普通人的生活,不再颠沛流离。她想找一棵坚实的大树依靠,却不想这棵树还是小树苗,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都未可知。这个依赖性很强的新婚丈夫在日军轰炸时,丢下大腹便便的她,一人跑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抛下她,独自逃亡。
她躺在异乡冰冷的医院里,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生命的最后44天,守护她的,是另一个才认识不久的男人。
她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她没有林徽因的理智,没有张爱玲的决绝,没有丁玲的飒爽,没有冰心的美满。她离世时才31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心有不甘。
她以卑微之身,写出世间冷暖,不恨不怨,一切皆受;
她说自己就是《红楼梦》里的香菱,“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
她在生命弥留之际,留世的最后一行文字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