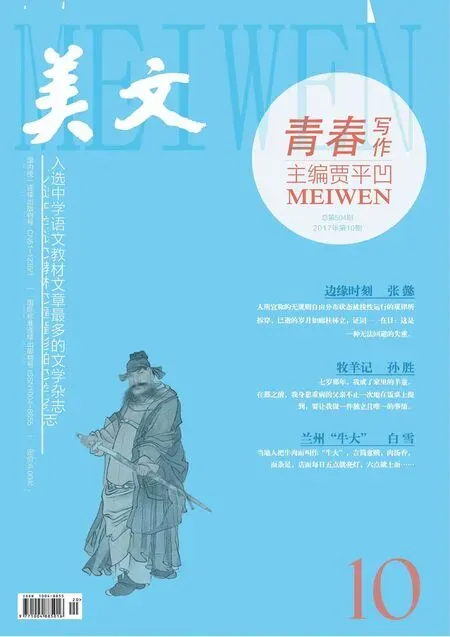归 宿
曾 晨
归 宿
曾 晨
我的家乡是一个名叫陶山的小镇,在我小时候还遗留着古江南的一些色彩。梅雨季节挺长,河流却总是缓的,有一芥只容三人的小木船在水上晃荡。家门口,祖父有时会坐上那张吱嘎作响似快散架的摇椅,望着外面白茫茫一片,说:“亦落雨啦——”祖父是用带着一丝神秘触感的本地语说的,很入耳,有种莫名黏稠悠长的沉重苍凉。
当然,我是站在现在去回味过去的,从现在的时间点、地理位置,去回望这条一维坐标轴上我曾经踏过的那些岁月。视线放远,就是我的身体触及不到的地方,只能摆脱肉体这沉重的负担去凝望,这就是历史的奇异。而这种奇异的荒凉与窒息,在文化历史上更甚于现实历史。
这个孩童,从“灼灼其华”的《诗经》中诞生,看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言,“春江潮水连海平”的唐诗,听过“无言谁会凭阑意”的宋词,“一点飞鸿影下”的元曲,尝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三国》,“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的《西游》,走过“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的《水浒》,“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的《红楼》,至今,已历经千年,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当我转过身,直视这个老人的眼睛时,我是无法言语的。就像长大的我回到小时候的家乡,家旁那个不知何时起就存在的菜场,熟识的阿婆朝我笑,露出几颗金牙,用她说了一生的本地语问我:“别淘啦,吃了吗?”可当我驻足想要回答,那个位置只剩下一个外地妇人在磕瓜子,见我停留,就用生硬的普通话问:“要买菜吗?”刹那间,脑中一片空洞。
我在翻阅《中国人的心灵》这本书时的心情大致如此,倒是想到了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系统一与系统二,若是用本书中的词汇为它们重命名,便是“情感”和“理智”。理智告诉我,故人逝,故事散,是历史前进的必须;而情感,却似复读机不停重复:那本归宿。
很少有人再转过头了。我想。
古老的城,古老的事,古老的人,介入其间者也好,冷眼旁观者也罢,亲身走过看过经历过的人与物,也几乎消散了。曾经繁荣的古镇,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古事,又有多少人会去梳理思索?
文化历史,数不清的人从这个老人眼中走过,从少到多,从屈原到司马迁到曹操再到陶渊明、张若虚、陈子昂,又从多到少,从李白到李贺到辛弃疾到欧阳修、关汉卿。再到纳兰性德。
然后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加速衰老。就如我的家乡。
但——似乎又不是这样。
祖父的摇椅声又响起来了,莲花腔从河对岸隐隐传来,菜场一如既往的喧哗。谁家童子,笑吟风雨任平生?然后,千年青雨,就再次来访,淅沥作响。
是了。少,不代表会更少。我们不能武断地判断这是一个一次函数。他确实已经老了,却并不羸弱。回过头的我,在这个老人眼中,看见了信仰与希望,这是随时可能爆发的力量,人性的力量。理智和情感,交叉、碰撞,互相渲染,那是震撼人心的灿烂光芒。有人离开,亦有人在坚守,守着那些旧事,旧人,旧诗,旧文。
这就够了。
落满梅雨的家乡,亦或是长得望不尽的历史,这两者并没有太大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根,是归宿,是一个等待我们回头的地方。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