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黄娅的秘密
◎何荣芳
有关黄娅的秘密
◎何荣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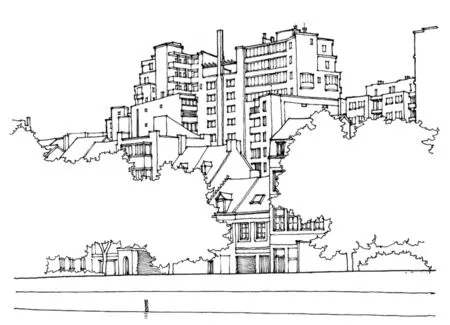
1·
黄娅的那点秘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守着一个板栗蓬一样的秘密,是一种痛。
黄娅是黄思迢的女儿,不,黄娅的事情有点复杂,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搞不清黄娅到底是谁的女儿。
第一次见到黄娅是去年秋季刚开学的时候。她站在她妈妈米淑珍身后,丰满得像迫不及待要跳出枝头的水蜜桃,胸部高傲地挺立着,一看就是营养过剩了的。个子已经高出米淑珍一头了,皮肤不算白皙,五官都很端正,但表情生涩。一头染黄的长发瀑布般地垂下,遮住了半边脸,一只眼睛便在另外半边脸上冷冷地盯着我,让我极不舒服。
这女孩便是黄娅。
“哦,女儿都这么大了?”我惊诧着。
“总算把她带大了。”米淑珍大大咧咧地不请自坐,一脸幸福的笑容。
这之前,米淑珍给我打过电话,“易绣啊,哎呦好久不见,没事想不起来给你打电话,罪过啊。”声音热情而夸张,她说女儿黄娅初三了,功课不是很好,想到我的学校来借读。我所在的二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以魔鬼般的训练而令千万学子望而生畏,又以教学质量突出而被千万家长仰慕。米淑珍说女儿是很聪明的,她的老师都这样说。但她的老师们又都一致认为:黄娅这孩子,学习上没有尽力,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米淑珍说想在初三的最后一学年,把女儿的“空间”往上抬一抬,她又不认识什么熟人,所以就找到我这里来了。她说,至少我也可以多辅导一下,这也是黄思迢的意思。
我摔了课本,小声咕嘟道:真是的,你以为你们是我什么人啊?
放下电话,我的心湖还是起了波澜。惊涛骇浪是不会了,毕竟那件事已经过去了N年。水波不兴也不可能,至今未嫁,说明那件事影响深远。
黄思迢是我的初恋。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男人。
我们曾经爱得那样疯。刚上班时我节衣缩食,攒下的第一笔钱给爱好摄影的他买了一架傻瓜相机;他为了买我喜欢吃的那家杨婆婆麻辣烫,在交通阻断的雪地里来回走了两个小时。黄思迢聪明能干,又对我呵护有加,和他结合,幸福似乎都已经打了包票了,谁知道后来出了那档子事呢?
尽管我在电话中含糊其辞,第二天米淑珍还是拎着果篮找到二中来了。她一把把女儿从身后拽过来,推到我面前,“快叫阿姨。”
那女孩扭扭捏捏地甩着胳膊挣脱了米淑珍的手,含含混混地叫了一声“阿姨好”,眼睛却盯着自己的脚尖。
既然人家找来了,我也就不好再推诿。想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可不容易,学校早就人满为患,校门外想进来的还排着长长的队。我知道学校领导会给我面子的,就像我在教学上一向都不会让他们失望一样。可如果能预知到后来会出现那么多的麻烦事,我就不会在米淑珍面前卖弄我那点可怜的能耐了。
我去找校长,找教导主任,找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一趟流程走下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我心里打着小算盘,我不想和米淑珍或者说黄思迢有过多的交集,我不想把黄娅放进自己教的班。但别班班主任也长着小心眼呢,你不愿意要的,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生,所以也都委婉地拒绝了我。不得已我还是找九零四班的班主任迟芳芳,迟芳芳和教语文的我是多年的好搭档,她没有理由拒绝我。就这样,黄娅最终还是宿命般地和我纠缠到了一起。
米淑珍在校外租了学区房陪读。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米淑珍不仅宴请了我和教导主任、迟老师等人,还特意买了一套高档化妆品送到我的单身宿舍。
“哟,还是一个人啊?”她把装着化妆品的礼盒放在我桌上,自己就一屁股坐在了我的床上,翘起了二郎腿。我觉得她的话中别有意味,很想来个针锋相对,但懦弱的我没有把嘴里的黄蜂放出来,我抿嘴朝她笑笑,“一个人过日子省心。”
我不愿意和父母一起住在大房子里,尽管我爱他们。母亲总是贼心不死地想解决我的单身狗问题,絮絮叨叨,叨叨絮絮,小桥流水似的家常中总是暗闪着刀光剑影,我不堪其扰,只好搬进学校的单身宿舍,过着孤家寡人清净自由的生活。
“也该找个人了,一个人过日子老了怎么办?”米淑珍突然收敛了笑容,很知心地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拍拍,像我母亲似的苦口婆心起来。“哪天,我给你介绍一个?我有个老表,是个开车的,前年死了老婆……”
我站起来,看着她笑:“不好意思,我今天上午还有一节课,马上要到点了。”
哦,那不打扰,不打扰了。她也慌忙站起来,走出门后还不忘回头叮嘱我,你好好想想啊,过几天我带人来给你看。
看你娘的脚。我一把把她坐过的椅子推进桌肚里。
2·
迟芳芳见了我有点不高兴,“那个女孩,怎么搞得怪模怪样?”
迟芳芳嘴里塞了大饼,腮帮子鼓得像遭了蜂蜇。说着话,把早点袋子放在桌上,端着一杯玫瑰花茶站到我桌边,一边吹着嘬着,一边要求我跟黄娅说说,把头发重新染黑了,别学生没有学生样,搞得像个社会小青年。我只好满口答应。
黄娅倒是听话,很爽快地答应了。行,不就是看不惯我头发吗,放学后我就去理发店。
黄娅没有食言,放学后她真去了理发店。第二天上班,我还没有进办公室,就听见迟芳芳气急败坏地嚷嚷: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把头发整成了什么样?是不是故意和老师作对?
走进去才发现墙壁上靠着黄娅,一只腿伸得长长的,不住地晃着脚尖,脑袋勾着,头发已经染回了黑色,厚厚的刘海齐刷刷地遮到了鼻梁上,如同躲猫猫故意蒙住了双眼,也难怪迟老师生气了。我走过去帮助迟芳芳教育黄娅。黄娅把厚厚的刘海撩开一道缝,目光便从缝隙中桀骜不驯地看着我们。
周末我去找米淑珍还人情,不想白白要她的化妆品。老剩女都是有点个性或脾气的,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不喜欢和人有交集。何况我也没有觉得把黄娅安排到二中来读书,算是立了什么功。学费可不便宜呢,学业的结果也难以预料。
我拎着礼品找到米淑珍的出租房,还没有进门就听见黄娅大声尖叫:“不吃!不吃!不吃!”
我推了门进去,黄娅正气鼓鼓地用筷子捣着碗里的饭。一向强悍的米淑珍系着围裙站在她身边,一副犯了错的样子。黄娅见了我也不打招呼,兀自生着气。米淑珍向我解释,说让女儿吃西红柿,惹她生气了,一边小心翼翼地朝女儿那边看。十点多钟,是早饭还是午饭?米淑珍说孩子晚上做功课休息得晚,周末嘛,就让她多睡了一会儿。我关心了几句,又婉转地说了几句不挑食的好处。黄娅闷头吃饭,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米淑珍送我出来,我俩在小区的绿化带旁站定。我直言,一个母亲如果在孩子面前低声下气,不是母亲做了亏心事,就是把孩子养得太专横跋扈了。你对女儿太娇惯,这样会害了孩子。米淑珍目光游离,无奈地抽抽嘴角:“不是亲生的,怎么管呢?怎么管都不落好哩。”
我赶紧伸手扶住要掉的眼镜,眼镜后面的双瞳瞪得溜圆。
怎么不是亲生的呢?黄思迢到底离了几次婚?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看米淑珍一脸的尴尬和无奈,我还是很修养地缄默了。
米淑珍和黄思迢都是我高中同学,我们仨关系一直不错。黄思迢起初给我写的情书,米淑珍总是抢着看。总拿黄思迢信中肉麻的句子在我耳边絮叨,惹我追着打。我师范毕业后,黄思迢也大学毕业了,我们很快就领了证,我也住进了他家。只等到选定的秋后好日子昭告亲友,步入婚宴的礼堂。
但是,那份婚检报告却像一场飓风,把我对幸福婚姻的憧憬吹得无影无踪。不能生育——几个黑体小字立即催生成几把锋利的长剑,把我刺得血肉模糊。我蹲在地上抱住双膝哭成了泪人,黄思迢抱起我,亲吻我的泪眼。没事,宝贝,不能生我们就不生。一旁的婆婆把脸盆摔得雷响,嘴里咕咕叨叨骂个不停。
不久婆婆的咕咕叨叨变成了尖利的指桑骂槐。因为不舍黄思迢对我的好,我只能对婆婆的敲敲打打忍气吞声。有天婆婆一个老姐妹的儿子娶亲了,那对新人是奉子成婚。婆婆吃了喜宴回来,把一包喜糖丢进了我脚边的垃圾桶,“娶媳妇就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家不能娶一个花瓶回来当摆设啊。趁婚礼还没有办,你们散了吧。”
黄思迢还没有辩解两句,他妈妈已经是又哭又骂,摸出一瓶农药作势要往嘴里送,我只好含泪收拾我的衣物。黄思迢抓住我的手不放,我倔强地杵在门边。他在我脚边慢慢地跪下来,双手捂住了脸。我没有理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那道门……
想到黄思迢妈妈的刻薄蛮横,我投向米淑珍的目光已多了几份同情。米淑珍叹口气,恳切地对我说:易绣,抽空帮我女儿补补课吧,她语文不行呢。从小就给她补英语,英语成绩上去了,语文成绩却一塌糊涂了。
性格懦弱的我,无法拒绝一个母亲殷切期待的目光。
3·
我静静地端详黄娅的侧影,心里柔柔的。她正勾头做着作业,白白的颈脖和颈脖后面细细的绒发进入我的眼帘。
每个周六上午,她都准时到我宿舍来补习语文。我在黄娅身上既看不到黄思迢的影子,也看不到米淑珍的影子。她身上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冷漠。这种冷漠,让一个花季女孩更像掩映在众多肮脏叶子后面的,一朵皱巴巴没有光泽的花。以前我讨厌她的桀骜不驯,可想到一个孩子从小就缺少亲生母亲的疼爱,我不仅能够理解她,也想多给她一点温暖了。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骨子里有一种东西,让人怜惜。
黄娅的“阅读理解”题做起来没有大问题,照说作文应该也能写得好。但事实上她的作文结构布局混乱,内容也大幅度跳跃。意识流、先锋派、蒙太奇手法都无法给她的行文做个合理的注释。我从杂乱无章中似乎找到了一个线头:这孩子的内心感受过于细腻,而她的内心世界又过于复杂。我试图拽着这根线和她继续交流,结果种豆得瓜,黄娅的作文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却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
黄娅补完课从书包里掏出两块巧克力,她一块,我一块。我撩开黄娅遮住眼睛的刘海。你头发还不错,又黑又柔顺,我要有你这样一头好头发就好了。她抬起眼睛,从头发缝里看着我,眼睛里掠过一丝羞涩的云。
我把书桌上扣着的一面小圆镜翻转过来,送到她的眼前。你的脸本来就圆,这样一遮住,就剩下个半圆了,也影响视力不是吗?下楼梯没有差一点踩空掉?
黄娅低了头,看自己的脚尖,抿嘴笑。你去校门口的理发店,叫师傅给你刘海搞漂亮一点行吗?没带钱的话我这里有。
老师,我有钱。
那就去吧。
黄娅一只手撑开额前的刘海,转身一溜烟地跑了。
黄娅过生日是在期末,那时一场小雪已经问候过江南小镇,校园里的香樟树全都变成了憨态可掬的圣诞老人。我抱着一只布袋熊,踏着咕吱咕吱的薄雪走到了米淑珍的出租房。
“哟,你来啦。上次我叫你过来见见我表哥为什么不来?我知道你心气高,瞧不上他。哎呦,我那表哥后来还催问过好几次……”米淑珍正在和着饺子馅,见了我就亮开大嗓门自顾自说开了。
我不想解释,洗了手帮她包饺子。馅是荠菜猪肉的,米淑珍还在馅里加了剁碎的胡萝卜和荸荠,说是女儿喜欢吃。我夸她对女儿真好,米淑珍自嘲地摇摇头,“是把她视如己出呢,恨不能把她含在嘴里捧在手上。但我怎么做,好像都不如她意呢。”
我说:“小孩子嘛,没到懂事的时候呢,又处于叛逆期。以后她会明白你的好。”
米淑珍把包好的饺子放进托盘中,又拿起一张圆圆的饺皮,一边装馅,一边装着漫不经心地问:“你这么喜欢孩子,干嘛要单身?”
我轻挑了一下嘴角,努力挤出一个干巴巴的笑容。她也把包好的饺子放进托盘中,似乎没有摆放整齐,又给它重新挪了位置。
“当初……你能放下他?好像当初是你死活要离的。”既然话已经问出了口,米淑珍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有点恼,很想报复性地问一句:你为什么不生个自己的孩子?但这话也只能在心里冒下泡,是不好意思让它露出水面的。出口伤人,我做不到。
我无法回答米淑珍的话,我没有勇气把自己血淋淋的伤口展览给人看,即使母亲那里我也瞒得死死的。
见我不说话,米淑珍便解嘲道:我也闹过离婚呢。但是随后他就把黄娅带回来了,有了黄娅我还能走吗?走不了喽。养着养着,就跟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是一样的了,也就不再想自己也生一个了。
“黄娅是你们抱养的?”
“是他从福利院领回来的。十二年前和今天一样的日子,阳光暖暖的,院子里的山茶花正在开放,他抱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从霞光里走回来。”
哦,原来黄娅的生日是这样来的。
“你也不生育?”
“怎么会是我呢?难道你不知道他不能生育?”
我糊涂了,思维断路,大脑空白。空白的大脑瞬间又仿佛注入了水和面粉,搅成了一锅糊。他不生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离开米淑珍后我立即去了全城口碑最好的一家医院,挂了妇产科的号,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诊室门外排着队,有骄傲地挺着肚子的,身边总是有一个鞍前马后小心伺候的男人;有羞羞怯怯躲闪着目光的小女孩,多半是未婚先孕来做人流的;有拿着病历愁眉苦脸的妇人,大概是被妇科病困扰着的。我站在她们中间,心情很复杂。我自卑自怜着,像一棵被上帝忽视了的小草。接诊的女医生,面无表情。她给我做了视诊、触诊后,又开了单子叫我去做B超,做输卵管照影。
我拿了检查的单子坐在医生面前。我紧张害怕又无限期待,像一个等待揭榜的考生,也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囚徒。
“结婚几年了?”医生埋头写病历,并不看我。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医生这才抬起她扁平的大脸,看见我满脸涨得通红,便和缓了语气,“没有什么毛病啊?”
“我有生育能力?”我像一个溺水者迅疾地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谁说你没有生育能力?叫你丈夫来医院做检查吧。”
我有生育能力?我有?老天,为什么作弄我!为什么?过山车般地心理折磨,使我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应该大哭。走出医院大门,看见明晃晃的太阳,我才在似梦非梦般中醒过来,我仰头对着太阳笑了,眼泪却哗哗地流下来。
一个谎言,还是一个失误?让我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我咽不下那口气,我要讨一个说法。我拿着自己的妇产科检查报告,找到了妇幼保健院的程医生,当年就是她给我做的婚检。当我啪的一声把妇检报告摔在程医生面前时,头发稀疏、眼袋松弛的程医生看看我发紫的脸,再看看面前的妇产科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她抬起肥胖的身子赶紧去关上办公室的门。程医生双手作揖,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程医生说,思迢来找我这个做大嫂的,叫我在婚检报告上写上你不能生育,我知道他爱你想留住你。对不起!对不起!
我站在那儿发抖,咬着嘴唇任凭泪水长流。我恨眼前的这个可恶的医生,更恨黄思迢。
4·
黄娅不是黄思迢的孩子,这还不是黄娅的秘密。黄娅的秘密,是黄娅自己告诉我的。
我不喜欢夜晚,一个人的夜晚弥漫的不仅是孤独,还有浓浓的惆怅。为了消磨晚上的时光,我总是把学生的作文带回宿舍里晚上改,一字一句,每一篇都给他们理顺了调好了。但无论我怎么消磨时光,我总还是要上床。
孤独的枕上生活,我总会杜撰点什么来滋养自己。我想象自己遇到一个很痴心的书呆子,一直执着地追求我,我终于羞涩地把自己的手伸给了他;我想象一个青年才俊,离婚的,有孩子,理解我包容我,很儒雅地向我求婚了,我幸福地流泪;或者有个冷峻而另类的彪悍男人,很霸道地对我说:我不管什么情况,我要定你了!那么我也会小鸟依人地偎过去。这些男人的影子,无论开始时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最后都会和黄思迢黑黑、高高的身影重叠了。只是想象而已,这么多年来,我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任何类型的追求,我总是用冷淡的拒绝来伪装自己的无助和无奈。我不敢把想象中的甜蜜变成现实中的苦涩,就像黑夜不敢面对白天。
但是这天晚上我再也无法进行想象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我对不住黄思迢,因为我不能为他生孩子。我一直以为黄思迢真心爱我,正因为这样,我才更要离开他。离开了,疼痛中裹挟着酸楚,酸楚中又带有殉道者的悲壮。这种感受在我拿到妇产科“生育能力正常”的报告后就烟消云散了。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想象不出这样的桥段:黄思迢,那个口口声声爱我的男人,却给我栽了一赃!我为此痛苦了十八年,我为此蹉跎了我十八年的锦瑟年华。
我产生了一种被亲妈卖掉的感觉,我站在痛苦的断崖上,一下子跌入到绝望无助之中。恨和鄙视,在痛苦的土壤中很快就长成了两棵荆棘,生生刺痛的又是我自己。
因为黄思迢的原因,我对黄娅也不待见了。我明白自己迁怒于她毫无道理,但感情上对黄娅就是疙疙瘩瘩的。黄娅也感觉到了我对她的疏远,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她总想和我套近乎来修复我们的关系。春天的早晨她给我端来一盘水仙花,漂亮的蓝瓷盘里,葱绿的叶片间,几朵白瓣黄蕊的小花正在探头探脑。我说,我对花粉过敏哩。她一脸的笑来不及收敛,就僵僵地皱在脸上。放学时她在人群中朝我挥手示意,我转过脸装着没有看见。而且我告诉她,周六我忙了,没空再给她补课,那时我整天沉浸在征婚网站守株待兔。
黄娅面对我,有点患得患失,又有点无所适从,上课时竟然常常走神。
“黄娅!”我正在讲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黄娅的目光又游离了,我没来由地生气,大声地叫道。黄娅吓了一跳,站起来,以为老师在提问,茫然地看着我。我瞪了她一眼,向她压压手,示意她坐下去。
下课时,我叫黄娅去我办公室,突然心血来潮地想挑起一些事端。办公室里有几个同事,我便站在空旷的走廊上,侧脸斜视着黄娅,挑衅地问:“小时候的事……”
“我不记得了。”没等我说完,黄娅浑身就绷紧了,立即抛过来答案,如同在战场上早已拧了手榴弹的弹盖,就等发现敌情拉了引信抛过来。我的心紧了一下,不忍下手,挥挥手,示意黄娅回教室去。
隔天,下课时,黄娅抱着一个本子,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
“进来呀。”我知道黄娅是找我,毫无表情地招呼道。
黄娅站在门口看看其他老师,又看看我,有过一刹那的犹豫,还是迟迟疑疑地进来了。她把本子递给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跑了。
她给我的是一本周记。我把本子带回家,一篇篇仔细地看。大多是三言两语的流水账。有些页面,什么也没有写,就是乱七八糟的划痕,心事重重又心不在焉的涂鸦,似乎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有几篇写到了妈妈,写妈妈为了她跟奶奶吵架的情景;写妈妈晚上缩着脖子,站在寒风里的校门口等待她下晚自习的情景。看得出,米淑珍真的是把黄娅视为己出,也为黄娅付出了许多。最后一篇,却是给我的一封信:
老师,小时候的事,我是记得的。我知道因为我不信任你而让你生气了。我有自己的爸妈,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有一年,爸妈带我回贵州过年,在火车站(那里好多人,应该是车站),现在的爸爸给我买了一根棒棒糖……爸爸妈妈在我的记忆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他们教过我家里的住址和他俩的姓名,但是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贵州”……老师,我想回家。
我被她的信烫着了,跳起来扑到电脑前,搜索“宝贝回家”。我的心脏咚咚乱跳,既兴奋又紧张,还有莫名的幸灾乐祸。是的,我想给黄娅找到家人,我要主持正义,我要让黄思迢鸡飞蛋打,要让他海底捞月白忙活,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报复!是的,我想报复,我看见了断崖上隐约垂下一根救命的绳索,黑色的,在山风中颤颤巍巍,我想抓住它,逃离这痛苦的深渊。
我估算着黄娅丢失的年份,飞舞着双手,哒哒地在键盘上敲着,输入一些关键词,很快就搜索到了一组与“贵州”有关的信息:一个叫张三长的男人在找女儿张小裕;一位叫吴山茶的女人在寻找她叫熊小玲的女儿;一对公务员夫妻在找女儿方骞骞……这些寻找信息中都有对孩子的描述,身上什么地方有疤痕、有痦子、有胎记,都写得清清楚楚,好像那些孩子留下了这些,就是为了方便将来被寻找。也有的什么具体特征也没有,就是大众化的描述:丢失时身高多少,操什么口音,穿什么衣服等。大多数都附有被丢失孩子的照片。我把那些小女孩照片,一个一个地仔细端详,没有找到黄娅的影子。
我把这些网页一一放进收藏夹中,并记下来一串联系的电话号码。
5·
这晚我辗转反侧,我思考着怎么能够尽快地帮黄娅找到亲人。我知道如果把黄娅DNA资料报送到寻子网站,可能很快就能找到她亲生的父母。也可以和那些家长一个一个取得联系,让他们自己来相认。黄思迢的生活从此即将打乱,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他给黄娅带来的痛苦,他给黄娅亲生父母带来的痛苦,生活将一一还给他。不管他爱不爱黄娅,至少黄娅在黄家是一副粘合剂。米淑珍不是说过,如果不是黄娅的到来,她也选择了离婚吗?让黄娅离开,让他经历一次押错了赌注顷刻间倾家荡产的痛苦。
我想象着黄娅离开后,黄思迢的种种窘境,心里有了一种复仇后的快感,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这晚的梦却乱糟糟的。我和黄娅坐在一列咔咔作响的火车上,火车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一辆要散架的自行车,自行车没有胶胎,我们就骑着铁轱辘走,好累。然后黄娅扑进一座高大的房子里,房子富丽堂皇,然而房子怎么又有点像牌坊呢?
我已经把黄娅送到她亲生父母面前了。我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休息,却一眼瞥见了坐在荒郊野地里的米淑珍。米淑珍伤心地缩成一团,气若游丝。我慌忙跑过去,却被米淑珍怨恨的目光狠狠地扎了一下。一身黑衣的黄娅奶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她伸手揪住了我的头发,唾沫雨点一样砸在我的脸上。我挣脱了,赤着脚跑,米淑珍婆媳俩跟在后面追。我哪里跑得动,恨不得长出四条腿来。我双脚乱蹬地把自己救醒,忽地坐起身,靠在床头捂着胸口喘气,头发湿漉漉的,心口犹自咚咚乱跳。
后半夜我再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正拿了抹布擦桌椅,黄娅就进来了,好像一直躲在哪个角落里等着我。黄娅来交作业,问了句老师好,迟迟疑疑地把作业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转身跑了。
我知道有蹊跷,是不是又夹了一封信?我赶忙去翻她的作业本,一张旧照片从练习本中滑落出来。我捡起看,是米淑珍带着一个小女孩,看样子是黄娅小时候的照片。我明白了黄娅的心思,把照片收进自己的包包里。
黄娅的照片在我的包包里像块烫手的山芋。昨晚的梦境又历历在目,我还没有从惊惶中完全逃离出来。我很怵那个喜欢穿黑衣的老女人,她骂起人来可以三天三夜不重复一句,句句带刀,字字甩钩,能把人骂得血肉模糊。我想,如果老太婆知道是我把黄娅鼓捣回她亲生父母身边的,还不生生将我撕了?我领教过老太婆的厉害,希望生生世世都不要再和她遭遇。
但是没有泯灭的道义混杂着复仇的情绪,又使我太想给黄娅找到亲人。我打算去找迟芳芳,想把黄娅的身世告诉她。她是班主任,她应该能够出来主张正义。可我又觉得这样做有点卑鄙,就像假慈悲的人不愿意杀鸡,却把鸡拎到屠宰场让别人动手一样。所以我在见到迟芳芳时,还是艰难地咽下了这个念头,并在心里自嘲地苦笑:报仇也好,伸张正义也好,原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我回家仔细看过黄娅的照片: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剪个娃娃头,带了一个粉红蝴蝶结的发箍,穿了一件粉红的公主裙,很漂亮,很可爱,只是神情有点拘谨,有点害羞。她的身后蹲着一脸灿烂的米淑珍,米淑珍伸出一只胳膊紧紧揽着她。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寻找类似黄娅的小女孩。有一个女人手中举着的小女孩照片跳进了我的眼帘。小女孩叫“熊小玲”。熊小玲扎着两根朝天辫,穿着一件碎花的小罩褂,胖嘟嘟的,笑得很可爱。资料上显示,熊小玲是在火车站和爸妈失散的,丢失时熊小玲才四岁零三个月。她和小时候的黄娅有点像,仔细看又不像。
那位手里拿着熊小玲照片的女人憔悴枯槁,眼里汪着一泓深深的忧伤。像很多丢失了孩子的母亲一样,这位妇人被悲伤击垮了,已经过早地衰老。我继续翻看这位叫吴山茶的妇人的资料,知道她家处穷乡僻壤,为了找女儿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十几年她没有停止过寻找,一路打工一路乞讨,丈夫已经和她离婚,她现在浑身带着病痛……似乎她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散的孩子。这就是黄娅的母亲?
我的心里凉凉的,复仇的情绪,像刚刚燃起的火焰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戛然而止,转瞬即逝。我既悲悯吴山茶,又替黄娅揪心。如果吴山茶就是黄娅母亲的话,黄娅会不会认她。如果不认,那个女人不遗余力寻找到的岂不是更深的悲伤?如果黄娅认她,跟着她走,黄娅的人生就要走向另外一条艰难的轨道了……
我很想拨打吴山茶留下的那个电话,我很想把黄娅的信息输入到网上去。现在我知道了黄娅是被拐来的孩子,撇开对黄思迢的怨恨,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但我不能。一晚上我都在做着比较:江南花红柳绿,贵州贫瘠干旱;米淑珍待她视如己出,生父母早已陌生;这里物质优裕,那里日子肯定捉襟见肘……失去了孩子,无论是她的生父母,还是养父母,都会痛不欲生。黄娅虽然不是米淑珍的血脉,却早已融进了她的血脉中。我知道,只要我多此一举,对黄娅自己是恩人、罪人很难说,对米淑珍我一定是罪人。
吴山茶忧伤期盼的眼神和米淑珍怨恨痛苦的眼神,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晃得我心里发毛,腰塌气短。我左右为难,纠结不已,很希望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能把我此时的思想批改一下,就像我无数次在学生的作业本中批改过的那样。我希望能有一位圣贤来指导自己。
这一晚,我在荧屏前久久呆坐。
6·
自从我把“宝贝回家”的网页从收藏夹中删除之后,我就不敢再看黄娅的眼睛。对她的事,我选择像路人甲似的袖手旁观。不是我不愿意解救她,我不知道我如果多事,会不会像大洋彼岸蝴蝶扇动的翅膀,给黄娅的生活引来一场龙卷风。
黄娅把照片交给我后又来过我的办公室几次,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每次来,我都尽量找其他的话题缠得黄娅无法说自己想说的话。我对黄娅感到愧疚,所以对她的作业改得格外认真。但她来得多了,愧疚便衍生出厌烦:你为什么老是在我眼前晃,让我心生不安?
黄娅是个敏感的孩子,她以为我喜欢她,以为我们之间除了是师生,还能有些更好的关系。也许米淑珍就告诉过她,她爸爸是我的初恋?她那么信任我,期待我能够帮助她,帮她把小时候的照片发到网上,帮她找一找亲人。家里的电脑有锁,以前,每逢周末,她还能在父母的监控下上去玩两个小时。初三后,她就和电脑绝缘了。她想不到我对她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也许她会想:难道就因为自己不是现在父母亲生的,大家都歧视吗?
黄娅心思恍惚了,成绩也开始下降。米淑珍想通过请老师吃饭来对女儿的成绩进行拯救,被迟芳芳果断地回绝了。迟芳芳认为学习上的事,更多的需要主观努力。
不久,迟芳芳就气咻咻地来找我,她把教科书往我桌上一扔,我赶忙侧了身子避让扬起的粉笔灰。
“干嘛呀你?”
“黄娅和王龙打架了!”
“哦?王龙打了她?”一想到王龙的人高马大,我不由自主地替黄娅担心了。
“她打了王龙。这丫头也真是的,两人为‘三八线’越界吵起来,王龙骂了她一句野种,她就把中性笔扎进了王龙的手背。没看过这么暴戾的女孩子……”
我到教室找黄娅,准备好好批评她一顿。人是我安插的,我有义务解决问题。黄娅伏在桌上抽泣,好像捧着红肿的手的是她,而不是王龙。我把她带到了办公室。
她还是哭。站在我身边,一边啜泣,一边抬起胳膊擦眼泪。我递给她纸巾,她倔强着不接。我想替她擦,她又扭着头避开,好像我给她带去了天大的委屈。
半节课后,她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些,眼睛红肿着。我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她几句,又扯了一些学习上的事。我还该跟她说些什么?总要跟她说点什么我才能心安。我拐弯抹角地告诉她:当务之急是好好读书,马上就要中考了哩,上个好高中才能上个好大学。等到你翅膀硬了,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了……我其实是在暗示黄娅:到时候,你要是想找家,谁也挡不住你回家的脚步。怜悯和负罪感使我对黄娅温和了许多。
此后,我又找黄娅谈了一次。那天早读课,我把黄娅叫到走廊上,跟她说老师对她的欣赏和期待。我伸长脖子恳切地看着黄娅,黄娅却不看我。黄娅看天空中飞过的白鹭,我只好陪她看天空中的白鹭。白鹭逃出了我们的视线时,黄娅看了我一样,难得地抿嘴笑了一下。
此后,黄娅的心思好像集中到课本上了,学习成绩也在稳步上升。有次开完家长会,米淑珍还特意找到我办公室里来,满心喜悦。我的心也渐渐宁静了,疲惫中渐渐愈合了伤口,无奈中滋生出一种妥协。至于对黄思迢,我决定给予宽恕。宽恕别人,就是解救自己。况且,在婚恋网中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很聊得来的男友。
中考后的一天,晚饭后我陪母亲散步。我挽着母亲的臂弯,一路上唧唧叨叨地说着新男友的事,母亲笑眯眯地听着。灰白的天底下,亮起了昏黄的路灯。马路上散步的人渐渐多起来,有牵着孩子的,有遛着狗的,有聚堆高谈阔论的。
小广场入口处,准备跳广场舞的几个大妈,聚在一起,大着嗓子说新闻,神情肃然,语调充满同情。说一个孩子跳江了啊,刚刚发现的,因为中考没有考好。有人问是男的是女的?回答有说是女的,有说是男的。我正想打听是那个学校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迟芳芳的,紧跑几步,离开嘈杂的人群,接了电话。
“黄娅到现在没有回家,她妈在到处找……”迟芳芳在电话里咋咋呼呼地叫道,“听说有个女孩跳江了,会不会是她?”
啊?我心脏狂蹦,像呛了一口水,憋得喘不过气来。惊惧、疑虑、心疼,还有巨大的自责,像山一样朝我压过来。眼镜从鼻梁上滑落下来,握着手机的手臂也软软地垂下了。一声低沉而悲怆的哀叹,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不要啊……
责任编辑/董晓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