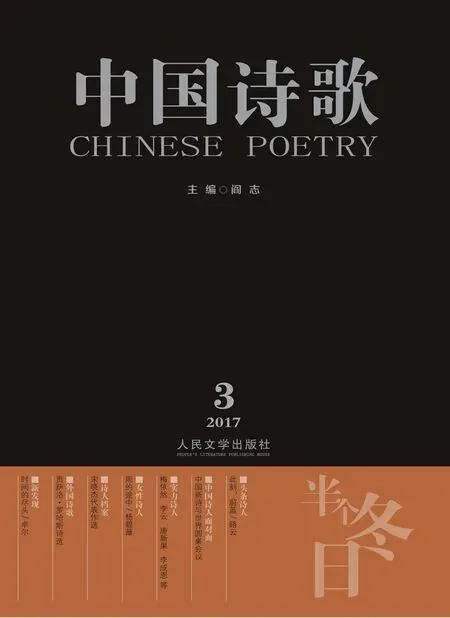传奇与废墟
传奇与废墟
□杨碧薇
假设你现在的坐标是我的母校海南师范大学,假设你沿着种满椰子树的道路走到校门,过人行天桥,来到龙昆南路的另一侧,就会看见伫立在路边的中国城。在听多了老一代人再三讲述的“闯海人”故事后,我曾怀着无限的好奇心,前来观看这栋早已废弃的建筑物。
透过紧闭的玻璃门,我打量着里面的大厅:天花板上的镭射灯被蛛网包得严严实实;地板上堆着厚厚的灰尘,即使是龙昆南路昼夜不歇的车马喧哗,也无法惊飞它们;沙发和桌椅凌乱地叠在一起,像一群被遗忘的符号,那些曾经覆盖它们的身体,如惊鸿掠过,在时间里苍老……但这些都不足以畏,因为,正如里尔克所言,“这里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寂静”。
这就是中国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曾是东南亚最大的娱乐城,名噪一时的东方红磨坊。我想象着:灯火璀璨的夜色里,中国城的大门外曾站满数以百计的美女,热风裹着海洋的水汽,沾湿了她们的鬓发。纵横四海的闯海人,在她们的热烈欢迎下,一头扎进了这个太虚幻境。我听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多少年轻女子辞去公职,只因在这里陪一场舞的收入,抵得上半个月的工资。然而,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一掷千金的辉煌不再垂青于海南这座梦想之岛,诸芳流散,春梦如烟,荣耀与繁华“宛如风前之尘埃”。我眼前的中国城,正是那一段历史的活化石。它用沉默与颓败等待年轻的我——那时,新世界的大门正向我打开,我已经看见前方的奇珍异宝投射过来的光。
也正是从那时起,在进行了兜兜转转的文类尝试后,我开始认真对待诗歌这件事,无论是写作还是研究。当然,我还太年轻,不足以清晰地意识到:我的生活,本就一直迂回在艰难的跋涉与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中。在我有限的经历里,那种在黑暗中挣扎着向上的欲力、跌宕起伏悲欣如歌的青春,为我掀开了颇具弹跳度的大景观,这一切,宛如我少女时期常常做到的梦:我张开双腿,每一秒都在越过一道道山脉、一条条河流;高山与峡谷、平原与大海在我身下撤退。2016年底,我重返海口,用“故人+陌生人”的身份再次去体悟这座城市,同时也反观自己的诗歌书写,这才触摸到一条隐线:传奇与跋涉相互砥砺,产生一种必然性,使我投身于这种大景观。它陶冶着我反性别、反秩序、反呢哝软语。世界太磅礴,更多的问题在朝我涌来,若不想被击倒,就只能伸手拥抱。而诗歌,正是我痛苦的思考、纠结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另一方面,诚如对中国城衰败的形象念念不忘一样,我摆脱不了废墟的诱惑。我觉得,废墟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的死亡,也是对现实秩序的否定。我心中有一座废墟,我对生命最初的理解源自于此,它也是命运、爱恨、离合的源头。它是站在上帝对面的声音,拥有危险的力量。其危险并不在于强度,而在于其缠绕与绵延的能力。在《桃花扇》、《红楼梦》、施叔青的《行过洛津》里,在SoporAeternus和木玛的歌里,我感受到了它。这座废墟使我保持乐极生悲的本能,并且提醒我:离繁华远一点,离流行的写法远一点。正是因为废墟的存在,我还在相信一种与热闹全然不同的价值、一种自己独有的美学。与其将诗歌修建成虚假的精美宫殿,倒不如正视它废墟的一面:它的断壁残垣,它的碎片,它的稍纵即逝的激情,以及——再往后看一点,它在时光中弥射的更大的空无与从容。
传奇与废墟,是与我常相伴的两种光景。传奇构成了我诗歌的面貌,诗歌又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限度,而废墟恰恰是一种审慎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