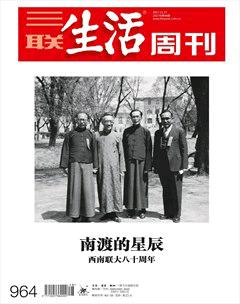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6)
朱伟
《酒国》是莫言的第三部长篇,从1989年那个多事之秋后,拖了两年才写完。这不是莫言唯一一部非一气呵成的长篇,他自己的说法,《蛙》也是写了几万字就放下,然后另起炉灶再写成的。优秀作家的预知力真是了不得。我记得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才做了一期《酒神疯了》的封面故事,说山东疯狂的酿酒业;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个亿》,深度报道全国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说,莫言在90年代初就锐利地割到了十年后才让我们都感触到的黑色肿瘤。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种种五花八门的吃法,被象征为侏儒的“余一尺”与各种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被披露的贪官丑闻。这叫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呢?——我感觉是,莫言写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用极其锋利的手段,提前撕开了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很难用概念对他的创作形态作一个归结。我只能说,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超越了以往我们熟悉的概念,说它“魔幻”其实不准确,因为他只不过习惯了夸张,令你感觉到荒诞。他憎恶分明,嫉恶如仇,他的心在流血,他超脱不了,冷酷不了,刻骨着嬉笑怒骂,心却是软的,暖的,多情的。这强烈的爱憎、冷暖交织的态度,爆发出夺目的,令人震撼的色彩迸溅。
如他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构思,其实只因一篇随意读到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而产生的触动。牛的是它的套装结构——外面包的故事是由小说中人物“莫言”,根据“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李一斗”寄给他的小说,产生灵感而创作的。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省检察院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酒国”市以宣传部长“金刚钻”为首的官员吃婴儿,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因此奉命前往调查的过程。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第三人称,里面套着文学青年“李一斗”以第一人称与“莫言”的通信,每一封信都附他写的一个短篇。这些短篇从《酒精》到《酒城》,共九篇,彼此连贯成实际的故事,其实是内核,写得都特别精彩。这个套装结构里外一直对应,了不起的是,套在外面的故事是里面故事的想象;里面的故事似乎是“李一斗”亲历,其实也是他写的小说;是小说,却又像现实,这就构成了似幻似假似真。
莫言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小说写完后,余华回海盐,他托余华将小说给了浙江的《江南》杂志。《江南》为难,没敢发。幸好,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甄别了一下,食婴是假,就出版了。

莫言
小说外壳中,举报信是“李一斗”在“酒国烹饪学院”任教授的岳母在精神失常后写的。“李一斗”在他的第二篇小说《肉孩》中,描写了肉孩的买卖过程;第三篇《神童》描写了“小妖精”率领肉孩们的暴动。这个“小妖精”后来变成在《驴街》上开“一尺酒店”,腰缠万贯,左右着酒国经济命脉的“余一尺”,其发家,是因投其所好的一对双胞胎侏儒的父亲乃京城大官。“红烧婴儿”本是《烹饪课》中,“李一斗”描写他岳母在精神正常时研发的一道大菜。他岳母在讲授这道大菜时,特别强调:“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不是人,它们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它们本质上与鸭嘴兽没有区别。”
这是“李一斗”,而不是“莫言”的小说。医院里,人工流产的胎盘被当作补品是现实。“莫言”的小说中,描写“丁钩儿”到矿上,矿长书记给他接风的第一顿饭,在轮番的劝酒轰炸,使他的意识被酒牵引出躯体后,“金刚钻”出场,豪饮三十杯,压台大菜就是“红烧婴儿”——“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 。令我想到“金发婴儿”的意象。在这场戏中,“金刚钻”告诉已经喝得神魂颠倒的“丁钩儿”,这其实是“酒国”烹饪的创新发明:婴儿的胳膊是藕,腿是火腿肠,身体是烤乳猪基础上加工的,头颅是银白瓜,头发是发菜。小说中也是真幻难辨,“莫言”是这么表达的:“明知盘里是,可怎么看都不是;明知盘里不是,但怎么看也是。”
这部小说,“莫言”所写外面套着的部分是荒诞——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在去矿山的路上,就经不住女卡车司机的勾引。进了矿山,就像泡在了酒缸里,酩酊大醉如死狗;然后又被情色牽引,怀疑女司机是“金刚钻”所设圈套,幻觉“金刚钻”以捉奸与他交易。这部分写得最精彩的是,酒色导致的躯灵分离,意识如脱茧飘飞的蝴蝶,能悬在空中;在袅袅香雾中,又能任意附着;视觉能任意放大、缩小,改变物体的形状。这是志怪小说里的常用伎俩,莫言用现代想象,将其夸张到令你大呼过瘾的程度。在这个外壳小说中,“丁钩儿”是个悲剧角色,他一上卡车就不由自主;到了“酒国”,就如堕入酒色之海,神不守舍、浑浑噩噩、狼狈不堪、个体尽无,一直如在五里雾中,最后掉进粪坑淹死了。小说扉页,他的墓志铭是:“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兄弟。”我理解,莫言以这个外壳,是要写腐败这个毒瘤中,公务员们的身不由己。身不由己构成了生态链,或者说,生态链使无数人身不由己。墓志铭中的“兄弟”,应该就指这根链上的无数有血肉者。这恰恰构成了酒池肉林的繁华腐败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外面套着的故事,又成了内核;里面“李一斗”那些小说,又变成外壳了。我其实不喜欢莫言小说中必然要写到的残酷。“李一斗”小说中的残酷是不断升级的,从驴街上的杀戮,这条街上“每一块石头都浸透了驴的鲜血,每一个厕所都蓬勃着驴的灵魂”,到《烹饪课》上杀鸭嘴兽、给肉孩放血,《采燕》中不忍卒读的屠牛与洞中群燕的泣血啼血,正是这些残酷杀戮绽放了“酒国”的美味佳肴。这当然是全国各地,当街杀羊杀狗杀驴杀牛,在动物凄厉告别声中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缩影。按“李一斗”岳母未疯前的理解,既然饲养的牛羊猪驴狗都可肆意用各种残酷方式宰杀,那么,饲养的婴儿亦是动物的一种,只要褪去“人”的标识,就不必再有道德压力了。这“肉孩”形成一个供人追问的惊叹号,这是“李一斗”那些短篇更刺激我神经处。
莫言小说中,经常有一个咒骂与厉声责问者,这小说里,他是那个鄙夷、痛骂“丁钩儿”的,用双筒猎枪守卫烈士陵园的老革命。这个老革命脸上的器官,后来被饿鼠全部啃光,“丁钩儿”开枪打鼠,又将他的脸打成“千疮百孔”。
这个套装结构的结尾,“李一斗”迎接“莫言”到酒国,“金刚钻”又出现在酒席上,“莫言”又开始重蹈“丁钩儿”的覆辙。这小说1993年出版时,莫言在后记里说,被《我曾是个陪酒员》触动,他本来就想单纯地写“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颜如玉”,但真进酒场,就入了奥秘社会。读完这小说,我想到:一是,优秀小说的警示、警醒作用,其实乃极重要的社会保健品,粉饰的甜点反而破坏健康;二是,当年这小说问世,若党的干部们都能读到而有所触动,之后的众多悲剧大约可减少许多。我这当然是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中国文学之可悲就在,要不被斥为“利用小说反党”,夸大了其作用,要不被鄙为“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太不把反映社会脉动的小说当回事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