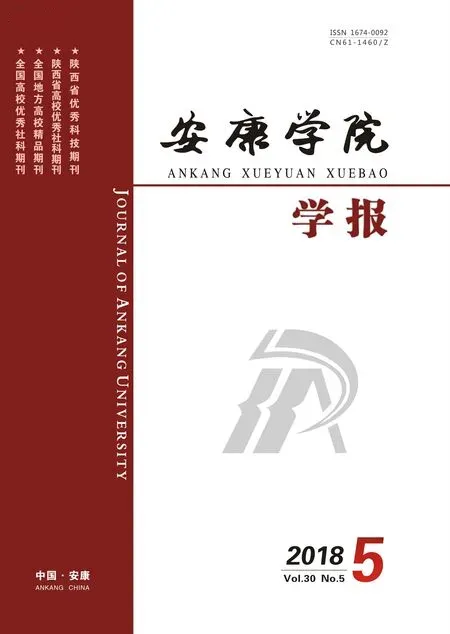熙宁政局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周 斌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熙宁变法,乃北宋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大事件,它开启了神宗朝至北宋末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持续斗争的序幕。两派相互倾轧,更替掌权,将北宋的党争推向了高潮。这场变法改变了苏轼的命运,影响了北宋国运,也影响了文学史的发展。其中,对于熙宁变法与苏轼词之间的关系,论者多着眼于黄州词,认为苏轼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之后,在词的创作上达到了巅峰。但是,如果把焦点前移就会发现,这场变法的影响不仅在于令苏词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还在于正是熙宁年间苏轼的外放杭州“催生”了苏轼词的创作。同时,熙宁七年政治局势的动荡,也向外扩展了苏轼的创作心态,这为其词创作的成熟提供了条件。
一、熙宁四年的自请外任与苏轼词的发端
治平四年元月,宋英宗崩,神宗即位,改元熙宁。面对内忧外患,宋神宗欲大有为,不满富弼等旧臣的保守建议,而对提倡“变风俗,易法度”的王安石大加赞赏。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同年,苏轼除丧还朝。苏轼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在熙宁二年至四年间,先后上《议学校贡举状》 《上神宗皇帝书》 《再上皇帝书》 《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文攻击新法,又劝谏宋神宗对于国事不要操之过急,成为了变法的绊脚石。于是,王安石使御史谢景温攻击苏轼,指控他在扶柩还乡期间乘舟商贩,但“穷治无所得”。虽然没有在政敌的攻击中受到伤害,但党派斗争的激烈,新党势力的繁盛,还是使苏轼决定离开朝廷,自请外任,通判杭州。
这是苏轼仕途中的第一次真正的挫折。在此之前,苏轼先后签书凤翔府判官,判登闻鼓院,判官告院,从地方到中央,仕路顺遂。宋仁宗更是在读苏轼制策之后,感慨“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1]10819韩琦也认为苏轼“他日自当为天下用”[1]10802。此时的苏轼,可谓是朝廷中的“明日之星”。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苏轼更多表现为“奋厉有当世志”。他写在嘉祐、治平年间的策论,汪洋恣肆,指陈时政,主张革新,正可反映此时其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自信和锐气。他在诗歌中或感叹“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2]23,或激励自己“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2]215。可以说,在神宗即位之前,苏轼是以一副壮志满怀的形象出现的。而熙宁四年在政治上的挫折,使苏轼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原来被用世之心弱化和遮蔽着的任性自适的一面,在外任之后开始逐渐浮现。
据苏轼自述,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3]1415。的确,苏轼的恬退心态早在出仕之初就有所显现。如嘉祐六年赴凤翔上任时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体现了他“刚出仕就恋归”的奇特心理,而名篇《和子由渑池怀旧》更是体现了年轻的苏轼对于人生意义空幻性质的认识。但这种对于人生的体悟和价值取向,因为没有遭遇到现实环境的挤压,总带有纯粹形而上的玄想性质,缺少深沉的内容。其所受的家庭教育,也令苏轼在出仕之初抱有巨大的政治热情,性格中恬退的一面,便在这用世之心的掩盖之下,一度收敛起来。而熙宁年间的政治打击,恰恰冷却了他的热情,于是“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便深刻地显现出来了。
写在赴杭上任途中的《游金山寺》,正可以反映出这种矛盾:一方面,是“有田不归如江水”;另一方面却又“我谢江神岂得已”。性格中的热烈的一面与恬退的一面,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调和,甚至还处在非我则彼的对立关系当中。热烈进取的一面遭受了挫折,宠辱偕忘的人格境界尚未完全形成,只能用恬退的一面平抚内心的失望,希求在山水游乐中得到心态的平和与休息。正如木斋所说:“苏轼的思想体系与变法具有根本性质的矛盾,这使具有范滂精神的苏轼,与变法发生了冲突。苏轼在做地方州、倅时,进一步感受到皇权与民争利的性质,于是写作了大量攻击新法、批判现实的诗作。而皇权专制的时代,又不能容忍这种狂放不羁的态度,这就使苏轼更深一步感受到不自由的痛苦。于是,归耕的主题成为这一乐段的主旋律,而且是比前期更为深沉的旋律。而归耕的不可能实现,使他更多地借助佛老的禅境和大自然的魔境,追求心灵的解脱。”[4]45-46
赴杭之初,苏轼便在给堂兄的尺牍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杭倅亦知州资历,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来若非圣主保全,则齑粉久矣。知幸!知幸!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但倅劳冗耳。[3]2526
杭州风物也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二浙处处佳山水,守官殊可乐,乡人之至此者绝少。举目无亲故,而杭又多事,时投余隙,辙出访览,亦自可卒岁也。[3]1688
苏轼甚至透露出了常住杭州的愿望:
某虽未得替,然更得于西湖过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将安往?但有着衣吃饭处,得住且住也。[3]1497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遭受政治挫折的苏轼,心态已不再如之前积极。在杭期间,大量记游、写景、宴饮诗的写作,也正可以反映他这一时期的放松心态。正是这样的心态,令苏轼真正开始了词的创作,也奠定了杭州词的基调。
苏轼之前,李煜、欧阳修等人虽有将词士大夫化的尝试,但整体上,词之一体,在人们的认识中仍是“小道”。欧阳修黜“太学体”文章,刘煇等人攻击欧阳修,就使用的是伪托作词的方法。范镇少年时见柳永填词,也惋惜“谬其用心”。因此,在熙宁四年之前,仕途顺遂的苏轼在文学上,自然不会顾及词的创作,而主要着眼于“经国之大业”的策论和诗歌。因此,苏轼的词集中,熙宁四年之前,可编年的作品总共只有两首(即《华清引》与《一斛珠·洛城春晚》。通判杭州期间,政治挫折造成的心理落差,以及西湖的迷人风光,给苏轼词的创作提供了心理和物质的条件。此时的苏轼,方始大量作词。熙宁四年,作词两首;五年,作词四首;六年,作词八首;熙宁七年,作词四十一首①从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笺注》说。。从此可以看出,在熙宁四年之前,词于苏轼不过是偶一为之,在这之后,才真正将目光转向了词的创作。学界把倅杭时期的作品统称为“杭州词”,不光具有地域意义,实际上“杭州词”作为一个整体,还反映了苏轼这一阶段的心态。
这种阶段性的心态反映在杭州词的题材和表现方式之中。
考杭州词,题材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赠妓、出游、宴饮、送迎四类②这里所说的“杭州词”,指熙宁四年十月至熙宁七年九月离杭州之前的词作,不包含赴密州任的“由杭赴密词”。。这和他倅杭期间自适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的。与前人的作品相比,苏轼词的题材的确有所扩大,此阶段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无意不可入”的特点。他的词,更多同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不再只是男子作闺音,模拟女性的口吻诉说哀愁。虽然如此,整体上看,这仍是倅杭期间内敛心态的表现:关注周围的生活,在山水和宴饮中平抚政治挫折带来的痛苦,获得心灵上的休息,同时也夹杂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在表现方式上,杭州词中,苏轼很善于根据创作的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对象,利用巧妙的联想和借代,如《双荷叶》,本是贾耘老妾名,苏轼借以作调名,且通首咏荷,却又能贴合人物。《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一首,见太守未到而两县令先来,遂有“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5]28之句,既道出了当时的情景,又将两县令比喻为方士王乔,讶其所来甚早,十分妥帖。此外又有《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用宋仁宗成句说明写作地点,《诉衷情·钱塘风景古来奇》用刘禹锡诗点明陈襄与杨绘皆诗人太守等等,不一而足。随手点化,触处成春。之所以如此,除了苏轼无与伦比的才华之外,也与倅杭期间较为轻松的心态不无关系。
总之,从手法到题材,都反映了苏轼既将词视为小道,率意为之,又利用词抒写杭州生活,为政治上的挫折提供心灵缓冲。这与苏轼的政治经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熙宁四年的外任,开启了苏轼词的创作之路。
二、熙宁七年的政局动荡与苏轼词创作心态的外扩
如前所指,苏轼外任期间,处在“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借杭州的优美风光来抚慰政治上的失意;另一方面,虽然身在地方,他的“当世之志”并没有完全湮灭。熙宁年间,苏轼写了如《吴中田妇叹》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 《山村五绝》等相当数量揭示民间疾苦、讽刺新法不便的政治诗。与亲友的尺牍中,也偶尔透露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新法的不满,如在与表叔杨君素的书信中就感叹“劣侄与时龃龉,终当舍去,相从林下”[4]1668;同友人范梦得的书信中言语则更为露骨:“近日并觉冗坌,盗贼狱讼常满,盖新法方行故也”[4]1700。这些都说明,苏轼虽然遭受了政治上的挫折,心态不如以前那样积极,但仍然强烈地关注着政治,并未完全走向“隐”的一面,而这种用世之心,联同熙宁七年政局的动荡,造成了苏轼词创作心态的变化。
熙宁七年,天下久旱,神宗诏求直言,曾布上书论吕嘉问市易之虐,引起同为变法派的吕惠卿的不满,认为曾布是在阻碍新法的推行,变法派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四月,郑侠绘流民图,且利用天变直接攻击变法,言大旱乃王安石变法造成,认为“去安石,天必雨”[1]10548。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此时流涕谓宋神宗“安石乱天下”。面对重重压力,宋神宗终于将王安石罢相,令其知江宁府。至此,熙宁政局出现了巨大的动荡。
面对王安石罢相,苏轼在诗歌中并没有直接反映,但这并不能说明苏轼对朝廷人事无所关心,相反,他对时局是密切关注着的。
王安石离开中央前,提拔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个人野心极强,他在王安石罢相后,担心王安石复来,争夺自己的权利,于是借郑侠狱牵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从此“反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1]13707。对此,苏轼诗集中有《王莽》 《董卓》二首,借古讽今,正是嘲讽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如王文诰所疏注:“是年四月,王安石罢相,荐惠卿参知政事。惠卿既得政,苟可陷安石者,无所不至。公作此二诗,正惠卿起安国狱時也。”其中《董卓》一首寓意尤为明显:
公业平时劝用儒,诸公何事起相图。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3]599
郑公业劝董卓用袁绍等人,后又反卓,苏轼以此比附王安石变法用曾布、吕惠卿等人,后遭他们的背叛。查慎行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注云:“陆务观云:王性之谓东坡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岂信车中有布乎’,盖讥介甫争市易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3]600此诗作于熙宁七年末,而吕惠卿叛王安石,起郑侠狱累及王安国,时间乃在熙宁七年十一月。可见,苏轼对朝中政治仍保持着密切的关注。那么,王安石罢相这件朝廷重要的人事变动,苏轼自然不能不知。而王安石罢相引起的政局动荡,也令苏轼词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其词中政治书写的出现。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改知密州,在去往密州上任的途中大量写词,是为“由杭赴密词”。苏轼九月从杭州出发,十二月到达密州,而在九月到十月这一个月中,作词竟达十七首之多,是苏轼一生中词创作最为密集的一个月。究其原因,乃赴密途中多与朋友饮宴。考苏轼赴密,始同杨绘(元素)、陈舜俞(令举)、张先(子野) 同舟发杭州,至湖州访李常(公择),五人又同刘述(孝叔)在松江垂虹亭上作“六客之会”;至苏州,州守王诲(规甫)开宴招待;至润州,遇孙洙(巨源)、胡宗愈(完夫)、王存(正仲)会于多景楼上;至海洲,又与曾经担任过眉州县令的陈某相会;过高邮,见孙觉(莘老)。这一路,正如苏轼到扬州后给李公择的书信中所说:
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辙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5]1497-1498
高朋佳宴,自然词情大发,原不为怪。然而,这十七首由杭赴密词中,却出现了此前未曾出现过的政治内容。如湖州所作《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一首:
不到谢公台。清风明月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秋色渐催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5]107
“旧日髯孙”乃是苏轼将前任知州孙觉比作孙权,“短李风流”则是用唐代诗人李绅比现任知州李常。根据环境中的人物巧妙地进行比附和指代,原是苏轼在倅杭期间就经常运用的手法,再次出现,显示了苏轼词早期“游戏笔墨”的成分,然而下阕笔锋一转,透露出了与杭州词不同的气息。“尽是刘郎去后栽”本为刘禹锡自郎州司马还朝后,借玄都观新栽桃花,影射朝中皆是自己外任期间提拔上来的新贵。在词中,这一句的政治意味十分明显,正指朝中变法派得势,驱逐异己,执政皆是保守派去后新得位者。在此语境下,“秋色”“黄英”就都有了政治隐喻意。这是此前的杭州词中从未出现过的。
由杭赴密词中,同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的还有《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中“天怜豪俊腰金晚”一句,《阮郎归·苏州席上作》中“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二句,《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旧交新贵音书绝”一句,《醉落魄·席上呈元素》“同是天涯伤沦落”一句,《浣溪沙·赠陈海洲。陈尝为眉令,有声》“升沉闲事莫思量”一句。而《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则甚至可以视作苏轼用词体表达对时局的态度: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5]134-135
这首词值得注意的是下阕,过片回忆弟兄二人初到汴京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甚至把致君尧舜都视作易如反掌。但接下来,苏轼没有继续实写发生的事件和心理状态,荡开一笔,道出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处事方针。这一文本的断裂,中间包含的正是熙宁外任的失落、不忿等复杂的情感聚合,因而苏轼提出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乃是针对政治挫折而发。苏轼好言,不知“稍自韬戢”,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3]363。那么面对王安石罢相,苏轼诗文中应该有所反映才是。联系这一背景,词中的“袖手何妨闲处看”,就不光是在空泛地讲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含有对新党遭遇政治挫折的嘲讽意味。
还应该看到,苏轼词中政治内容的出现,与由杭赴密途中的同游者有关系。考旅途同游者的政治属性,刘述、杨绘、李常、孙觉、胡宗愈五人,皆为熙宁三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罢出朝廷或自乞外任的御史和谏官。陈舜俞“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1]10663;王存“故与王安石厚,安石执政,数引与论事,不合”[1]10871;孙洙“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1]10422。一路上与苏轼结伴而行的,多是同苏轼一样反对变法的一派。在当时的政局之下,宴会之上,酒酣耳热之际,不免要对政治有所议论。这是造成苏轼由杭赴密词出现政治内容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以上政治感慨的出现,仍是当年朝廷政局之变所激发的。
苏轼词内容的政治化,表面来看是题材的扩展,实际上反映了创作心态的变化。如前所述,苏轼倅杭期间的词作多数是对日常生活的即时反映,虽然相比于前人的作品,显示出“无意不可入”的特点,但就词的功能而言,仍是娱乐性的、私密的,就创作心态而言,仍是内敛的。由杭赴密的途中,由于政局的动荡,再加上朋友的同声相和,苏轼遂在词中也渗入了“言志”的成分,开始把词在一定程度上当作了“言志”的工具,他的创作心态在此时向外扩展了。此前,苏轼将词划为娱乐抒写的工具,而此时,由于创作心态的转变,苏轼在词中更热烈地反映现实生活,将词在功能上提到了与诗相当的位置。可以说,由政局所激发的由杭赴密词,是他日后“诗之苗裔”等崭新的词学理论,以及“自是一家”的新型词风在创作上的先导。不久之后,当苏轼来到密州,在外扩的创作心态的指引下,那首豪放的《江城子·猎词》便横空出世了。
需要说明的是,苏轼词创作心态的外扩,与前人的创作实践、当时“破体为文”的风气、苏轼自身较为通脱的文学思想,乃至其对词体创作的熟练程度等都有关系,不只有政局动荡之一因。然而,熙宁七年的政局毕竟对苏轼的心理造成了冲击,催化了创作心态的变化,可谓是偶然之必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熙宁年间的政治局势深刻地影响了苏轼词的创作心态。他在首次遭遇政治挫折时,性格中恬退的一面令他寄情于山水宴饮,从而开启了词的创作;性格中用世的一面则令他关注着当时的政治局势,从而导致熙宁七年政局动荡时创作心态的外扩,为日后“自是一家”的苏轼词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苏轼词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熙宁政局无形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