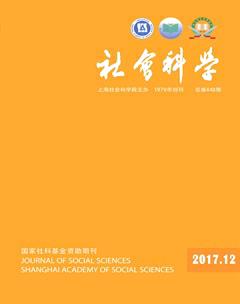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概念先行”
周怡
摘 要:“概念先行”是当前政府的“话语体系建设”倡导下涌现的社会事实。尽管每一时代都不免有顶层的制度设计,但用话语概念,尤其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话语,而不是用规章规范,去动员和唤起行动却是如今这个时代独特的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抑或观念的动员、通过意义的合法化过程,把观念下传到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抑或个体层面,的确能够获得民众的赞同,以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并指导行动。这种先于行动或镶嵌于行动过程中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我国特别有效,是因为(1)社会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文化及其人格为“概念先行”铺垫了绿色通道;(2)顶层设计中使用的民生话语、传统文化话语及新知识话语,则为夯实概念与行动、上层规划与基层响应间的一致性提供了长程的文化资源。因而,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概念先行”现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现实社会基础。
关键词:概念先行;话语体系建设;治国理政;文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05; 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062-06
作者简介:周 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
一、话语体系建设与概念先行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倡导。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增强国际话语权。那么,学理上什么是话语体系?话语(discourse),简单的字面意思是人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言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间进行日常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终其一生的“知识权力观”论述就非常重视话语与权力的分析,认为话语实际是社会权力的表演①;意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反映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②。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则指话语运用的范式;既表达说话主体的意志及其思想建构,也包括说话主体与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进行互动的整体模式。依这些学理去理解“话语体系建设”的国家政治内涵,就意味着每一个文明国家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其目标功能是:(1)对外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本土象征,在国际舞台上“说好中国故事”;(2)借用话语体系指引、规范或折射本国具体的发展道路。显然,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话语体系文本要素、以“中国梦”开启的系列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道路指示。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且完全出自“顶层设计”的标识性概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层面:
上述这些紧随“话语体系建设”之后出现的标识性概念是全新而先行的。姑且先不问概念的源头抑或理据在哪里?现实告诉我们:这些概念一经提出并传播,便顷刻成了中国人(受话人)参与治国理政的具体行动。如,“一带一路”的概念推动中国依靠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邻里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发展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及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既体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又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充分认同。又如,“智库”和“大数据”的概念,促发了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智库组织的迅猛发育和成长,催生出大数据分析技术及其“云产业”的勃勃生机。再如,在“共享经济”的概念中,有了“共享单车”这样一种分时租赁交通的新模式;也有了“共享民宿”的这种便捷经济的旅舍等等。这些由概念驱使行动的种种现象,本研究称之为“概念先行”。
很明显,“概念先行”是中国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设倡导下涌现的社会事实。相比邓小平时代用“摸着石头过河”形容改革较多源自底层百姓试错式的“边缘革命”来说,当前的许多概念是“顶层设计”的直接结果,这也是“国家治理”取代“市场分化”的象征。尽管每一时代都不免有顶层的制度设计,但用话语概念,而不是用规章规范,去动员和唤起行动却是如今这个时代独特的方面。
二、观念与行动:概念先行的理论依据
学界在处理思想观念与社会行动时,一般取两种简化模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将思想观念看作实际生活的反映;另一种是韦伯式的,将观念当作社会行动的原因。然而,这两种简化都忽略了二者互动的事实Swidler, Ann,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 No.2, 1986, pp.273-286; Vaisey, Stephen, “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4, No.6, 2009, pp.1675-1715.。如何能結合马克思和韦伯去研讨观念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困难不仅在缺乏清晰的概念来操作这种互动,还在于人类一直以来特有的对观念价值的健忘。即任何概念抑或观念一旦内化于心就会成为想当然的潜在力量去支配人的行动,并不为行动者所察觉——“观念先于行动,有如闪电先于雷声”(海涅)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被喻为闪电的观念与作为雷声的行动,不仅有先后关系,也具有互不可分的毗连关系。但现实中诸多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研究,大多侧重行动作为历史事件雷声的长程影响,而忽略支配行动的观念,即观念容易在学者的研究视线中如闪电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得揭示这种先于行动或镶嵌于行动过程中的思想观念变得十分重要,它构成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因而,这里“概念先行”的理论依据大都出自文化社会学的界说。
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有关“食物作为象征符号”的经典研究认为,日常饮食的可食与不可食性,并不以物的有用性来裁定,而是取决于物对人的意义。人对物的情感及其业已形成的观念支配着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意义不仅决定生产什么食品,也决定全球的食品市场价格。如,不食也不能生产狗肉,因为认知情感中狗为美国人心中的宠物;猪肉比牛肉便宜是因为美国人观念中牛比猪更亲近一些。这种标识性概念抑或意义符码决定了人的饮食行为。Sahlins, Marshall, “Food as Symbolic Code”,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p.94-104.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一书中,以水门事件、大屠杀、总统选举、电脑科技等一系列经验的个案研究为例,看到也强调了话语体系,尤其是深嵌人们头脑中的二元符码等无形的文化结构,对美国社会的政治事件、社会制度以及群体行动的建构和支配Alexander, C. Jeffrey,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显然,他们的研究都高度肯定了观念、概念抑或话语文本能够对人的行动产生支配抑或积极的干预作用;在因果解释链上他们置“概念”为因,“行动”为果;概念或者观念作为自变量而先于行动得到了阐释。endprint
其实,正如闪电和雷声总相伴发生那样,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是观念支配下的行动,同时,价值观念的追求一定会通过行动加以表现,观念和行动本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大凡观念总归咎为思想,研究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应该是当前中国社会话语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就涉及了支配与被支配之间如何达成“思想共识”而付诸行动的互动议题。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样,葛兰西赞同上层可以对下层阶级行使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但他认为这个上层统治权是通过赢得下层许可而获得的,即需要有下层的“赞同”;只有上层和下层达成共识的思想才可能真正组织起整个国家或社会的整合。他的分析首先将国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守夜人国家”(night-watchman state),作为一种依赖于军队、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压迫工具;另一类是“伦理国家”(ethical state),在公民形成和赢得同意中发挥教育和形塑的角色。接着,他把统治亦一分为二:一种叫控制或支配,通过使用军队、警察的暴力控制;另一种被称作霸权,为构建合法性、发展共同理念和共享价值而组织起赞同的霸权。葛兰西始终强调教育和赢得同意的霸权,而不是野蛮暴力的控制权力;因为在他看来,虽然暴力仍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稳定时期暴力控制让位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的统领作用:(1)意识形态提供给人们实践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经验,也是观念的体系,其作用是组织并整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元素,以形成霸权集团和反霸权集团。这里,霸权和反霸权是通过一系列话语建构的主体和利益群众的战略性联盟形成的。(2)意识形态植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霸权涉及意义的决策过程。人们会通过常识、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和经验;这些常识和流行文化往往成为意识形态论争的重要场所。(3)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动员及其组织起大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8; [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显然,葛兰西文化霸权观从伦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统领民众的角度,为我国新时代倡导“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理据。尽管葛兰西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而非本文论述的话语体系,但在福柯的权力知识观看来,意识形态等同于“各层次社会权力关系中具有特定后果的话语”,或可以被理解为“对政治、对任何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起凝聚和合法性作用的观念系统”[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国家通过观念系统(话语体系)向民众提供一套建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的原则[美]华特金斯·克拉姆尼克:《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章必功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回到本文关注的议题,葛兰西给当代中国“概念先行”现象所提供的理论支点可简括为:(1)“概念先行”的话语体系建设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作用;(2)概念抑或观念可以通过动员、通过意义的合法化过程,下传到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抑或个体层面,获得民众的赞同,以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及其行动;(3)在以“科学知识概念”为说服工具的互动过程中知识分子会扮演重要角色。
三、概念先行的社会文化基础
概念抑或话语先行在中国何以可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归纳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人心灵深处业已固化了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文化及其人格。在谈论中国传统的本土特征时基本有两种说法已然成为共识:一种说法认为“家国同构”塑造的家长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历来是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结构; 另一则说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就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长期执掌中国文化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结构要素的“家国同构政体”与作为文化价值要素的“儒家思想”合为一体,生成了所谓“制度化儒学”制度化儒学意指“儒学被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浓重的法家色彩的政治结构结为一体,即制度与文化的复合体”。参见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的国家治理体系。这种体系使得中国人在道德伦理上长期受威权主义顺从文化的影响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具体来说,当中国人将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组织、整合起来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血缘关系,亲代对子代的抚育中就蕴含使之服从的因素。早期的人类利用血缘关系实现初民社会统治乃属天然之事。逐渐地,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天然的恩赐由家拓展到家族及家族外群体,由宗法制度延展进今天的科层制度,复制或衍生到了国家的统治或支配模式。不少研究证实,“家”与“国”同构作为儒家社会伦理中存在的对偶现象之一Schwartz, Benjamin, “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David S. Nivison,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50-62.,长期左右着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政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中国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制度化儒学型塑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威权人格和心态。这就是,在君臣权力关系中,臣子对君主的“忠信”及顺服历来被当作重要的个人美德,而被内化于心,再付之于行动的。中国百姓习惯于顺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和安排,对国家、对单位组织具有极强的依附。改革开放后,尽管社会的主导理念已经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乎每个人都被推入相对自主的市场环境,但现实告诉我们,发生任何大小事情或任何社会问题时,国人第一时间呼吁的是“政府为啥不管”、“政府应该出面采取措施”等,基本没有主动或自主的参与意识。说到底,他们还是习惯了对政府、对国家及其组织的强烈依赖和顺从。近期一些研究也表明:政府的意识形态、政府的社会动员依旧起支配性的强作用力量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另據全球爱德曼公关公司2011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88%,位居全球第一位,之后几年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80%左右徘徊,居全球前三位。政府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力量,以及民众居高不下的政府信任,其实以两个当下的社会事实呼应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顺从权威、依附权威的深层文化特质。显然,社会成员具备这类文化特质,容易通过崇尚“‘国是‘家”、“个人应该服从集体、服从国家”的思想理念,将自上而下的新观念、新概念、新话语视作当然的制度安排而付诸实际的行动。endprint
第二,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民间流行元素。显然,由概念抑或观念组成的话语体系需要有“接地气”的民间元素才更易于产生实际的影响和秩序。话语体现民间元素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与民生需求元素相对应的路径,叫民生路径;二是与文化传统元素相对接的路径,称之为传统路径。两种路径说到底都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必要的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策略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也就是把百姓需要的、熟悉的文化資源加以整合,用定位在民生的话语体系,来为社会建设、社会整合服务。让民众深感政府的话语概念及其政策是倾向于改善百姓生活质量的明示努力,即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努力去做的一切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这样一种文化定位,一直明显出现在中国社会。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时,首先把制度建构的参照点放在“农民需要富裕,向往成为城市人”这样的民间话语层面Zhou,Yi,“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armers City in Wenzhou the Early Reform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81, No.22, 2013,pp.476-498.。又如,当前体恤民生的概念包括“打通中间(最后)一公里”、“精准扶贫”等。在“打通中间(最后)一公里”的观念下,我们看到截至2016年2月国务院取消了272项职业资格,还取消了152项中央制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在“精准扶贫”概念下,我们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此概念所做的具体阐释:“立下愚公志,心中常思百姓疾苦”(2015.3.6),“扶贫需要少搞些盆景,多搞些实惠”,“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2015.3.8),“民生工作要一诺千金,不要狗熊掰棒子”(2015.3.9)。再有,用“打赢蓝天保卫战”这样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代替了“治理污染”等学究语言。总之,概念抑或话语从国家主席直接就到了老百姓,语言上没有任何“中间商”。这样定位于民生的话语加上领袖的亲民形象显然有唤起民众积极响应的强大力量,可以使“概念先行”的行动如期达成。同样,在改革和建设的任何时期,传统文化被纳入中国话语体系的实例亦屡见不鲜。因为历史上中华民族产生过儒、释、道、墨、名、法等各家学说,涌现过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符码和习俗来动员群众,让群众感到中国的改革及其建设是“中国的”,更容易获得接受和认可。比如,作为诠释中华文明复兴的“中国梦”概念,其传导的价值观“国是家、善作魂、勤为本”,“俭养德、诚立身、孝为先、和为贵”均出自儒家典籍。而习近平2013年11月对曲阜孔府的访问,以及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典句的直接引用,如,在从严治党的论述中他用到“明制度于先,重威刑于后”出自《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典出先秦《韩非子·喻老》等等,都通过“重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向民众传递出当代中国政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强调,语义是中国人在以自己的本土文化符码解决中国的事情。本土符码的语义表达显然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第三,概念能够先于行动,还在于由概念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新知识、新技术的结合。用民间流行话语去建构话语体系所处的民粹立场,一旦被过度使用,则可能导致或加速文化世俗化的趋势[德]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在现代化发展的市场利益面前,源于商品市场发展的文化世俗化与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之间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大多数国家会通过强调复杂社会世俗化的变化来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诺言;而世俗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其中,新知识和新技术概念的提出却源于知识精英的参与和诠释。假如把“话语权”分为政治话语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学术话语权(即构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两类的话,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常见的是政治与学术话语权的两相结合抑或两相合作,更强调知识与国家治理的结合关系。“智库”的风起云涌、“大数据”的实际参与、“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等都充分反映了政治政策话语与学术研究话语的联手。比如,“供给侧”属于普通老百姓很难理解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但该概念一经提出,在供给方面就出现了简政放权、金融改革、放松管制及其国企、土地改革等政策行动,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及市场利益。再比如,“一带一路”概念是新时代中央政府在全球化市场中给出的新概念、新表述,同时也是提炼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科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即它今天的意涵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及其论证是政治文化与学术新科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们看到了新型“中欧班列火车”的启动、“新灵渠”对中亚邻国的连接、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等等。很显然这一作为中国高层推动的国家理念已经成为行动。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理念,容易被普通民众在不假思索的无意识中加以接受和认同的事实,这一点早在福柯的“知识权力观”[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里有过生动的阐发。而对中国革命、中国政治有深度关切的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ean Perry)亦看到,革命初期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身份出现在老百姓中,把他们的新理念、新知识带给乡村的上层绅士,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接受。即她看到了知识分子把教育及其知识从大学传导到民间的参与革命的过程,并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地方革命,能像中国这样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能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相对文化定位来说,裴宜理称这样的新文化传导为文化援助(cultural patronage)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培育同意”(cultivating consent)文化Rodriguez-Muniz,Michael, “Cultivating Consent: Nonstate Leaders and the Orchestration of State Leg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3, No.2, 2017, pp.385-425.,构建新文化符码和形象,并使之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其中,文化援助的手段来自新知识或新技术。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国家经过近40年的巨变,新媒体、网络支付、新金融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远超发达国家,这种创新驱动能够如此之广泛,与知识分子参与话语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用科学技术去告诉老百姓“这是科学的、实用的,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这番界说,与其革命时期传播新思想而发生的文化援助如出一辙。endprint
如果說,社会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文化及其人格为话语体系建设中“概念先行”铺垫了绿色通道,那么,顶层设计时使用民生话语、传统文化话语、知识话语,则为夯实概念与行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间的一致性提供了长程资源。因而,我国新时期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概念先行”现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现实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薛立勇)
Abstract:One emerging social fact of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precedence of conceptions. Although institutional designs from top to bottom is comm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i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current times to use discourse conceptions (especially the rank and file discourses) rather than formal regulations to mobilize individuals.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leading role of national ideology, but also the fact that the mobilization based on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cy of meaning can popularize and send ideas down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groups, or even individuals.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the mass, a society-wide “ideological consensus” is established, which subsequently directs peoples action. This type of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that are precedent to or embedded in the action process brings about societal consequences. That is because 1) the prevalent authoritarian culture and its embodiment pave the way for “conception precedence”; 2)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peopl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w knowledge that is used by the from-top-to-bottom institutional design provides long-term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ideology and action, and between top design and grass-roots resonance. Hence, the phenomenon of “conception precedence” in the new-era governance, reasonably and legitimately, has its social foundations.
Keywords: Conception Precedenc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Cultural Sociolog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