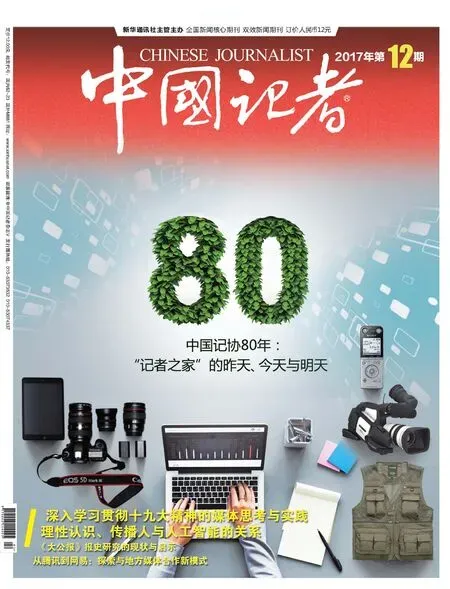“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构建新话语体系探析
□ 文/文智贤 毛 伟
一、全球话语体系与文明等级的思辨
近年来,“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概念,话语体系则可被视为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承载着话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话语体系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考量,它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在当今社会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掌握全球话语权的基础。全球“话语体系”竞争主要表现在话语体系所构建的学术话语、新闻话语、艺术话语、民间话语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方面。影响力越大、感召力越强则意味着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也意味着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地位。[1]
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西方长期占据绝对优势,这赋予了西方主流媒体强大的全球新闻话语权,通过精心设置议程议题,甚至不惜用“假新闻”的手段,在国际舆论场臆造了“伊斯兰恐怖论”“中国威胁论”等议题。西方媒体报道的偏见往往归结于多种因素,如意识形态差异、政治正确导向、国家利益驱动等。但如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沿着西方文明等级论传播和全球话语实践的发展沿革,可能会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解释国外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变化、解释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知变化,也为“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提供新的学术视角考量。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的思想理念——文明等级论[2]。“文明”一词是从英文“civilization”翻译过来的,而“civilization”这个单词是18世纪中期才提出的,特指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试图用“文明”来代表西方社会的发展成就。“文明”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词汇存在的,在其背后隐含的是对“非西方”和“野蛮”的认定,[3]以后更形成一套含有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的话语体系,经典的西方文明等级论将世界各地人群分别归为“野蛮的(savage)”“蒙昧/不开化的(barbarian)”“半开化的(halfcivilized)”“文明/服化的(civilized)”及“明达的(enlightened)”五个等级,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这个文明的等级划分趋向稳定,19世纪初,已经成为国际法、国际条约签订乃至成为西方认识世界的基础。
西方文明等级论在全球的“隐形”建立是一个过程,18世纪以前,欧洲人能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等量齐观,中国人被认为是“白人”[4],但历史的进程推动了西方人认知中文明等级的落差,到18世纪后,西方种族主义对中国人的偏见在话语实践中不断强化,中国被视为“半开化”国家,中国人的皮肤由“白”变成了黄[5],如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就将所谓“支那人”(英文Chinese本义)称为“barbarians”。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等亚洲国家被视为“半开化”国家,汉语、阿拉伯语等都被视为一种“半文明”语言[6]。“西学东渐”使得中国维新人士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将自己视为“半开化”或“半文明”,并将这种意识贯彻于各个领域的话语实践,将加入“文明”行列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文明等级论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不仅早已被西方人所内化,而且已经渗透进他国家的话语实践中,中国的文化不自信、道路不自信乃至对“一带一路”话语实践不自信都能找到“文明等级论”思维的影子。
中华民族早已有一套传统的话语体系,但近现代被外部压力和自身动力的作用下被政治无意识的文明等级论所解构,形成了向西方话语及话语体系学习、转变的趋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能一家独大控制着全球舆论场的话语权,在西方构建的世界话语体系中,其他国家文化传统形成的话语体系都“半开化”“半文明”,在向西方话语体系模仿学习的过程中,又被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不断打压或者被西方实际控制,进入了模仿和被打压的发展死循环。
二、“一带一路”全球传播的话语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战略思维,将会深刻改变现有的一些不合理、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旧秩序,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构建更加多元包容的新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四年来,国际舆论场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而我国又长期处于话语劣势,如果舆论场中的担忧和质疑得不到积极回应,则会成为传播盲点,盲点愈积愈多则会形成传播屏障,误导受众。必须厘清当前“一带一路”这一话语的传播舆论困境,才有可能优化改良,抑或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和新的传播路径。笔者对全球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调研发现,在“一带一路”全球热议的表象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话语困境:
一是海外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为对“一带一路”报道主题的单一上。海外关注点普遍集中于“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和政治影响,较少从长远角度阐述对人类发展、文化交流、文明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三同”内涵几乎没有出现在海外媒体报道中,即使是持积极态度的伊斯兰主流媒体也更多将“一带一路”简化描述成一个中国主导的投资计划或者本国与中国双边合作的计划,一些强势西方媒体则是从自身的话语体系出发对“一带一路”进行模糊化、污名化的报道解读。
二是国内外“一带一路”报道态度复杂化。从表面上看,国内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全部都在进行正面解读,但报道形式单一,很多报道内容浮于表面,官话套话等程式化报道居多,完成政治任务的正面宣传意味浓厚。伊斯兰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大多都属于正面解读,但在一些具体项目实施等微观层面的报道中表现出消极和担忧态度;这也凸显出由经济利益驱动形成的正面解读更多是一种暂时性的、协议式的认识。西方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有自己的议程和话语体系,态度既有相对中立的解读,也有对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的徘徊观望和消极隐忧。
三是国内外“一带一路”舆论场与现实脱节。这种脱节表现在新闻舆论与民间认知的脱节和新闻舆论与学术研究脱节两方面。笔者在实地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国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其实极为有限,尤其西方国家民众对于“the Belt and Road”“One Be One Road”等概念较为陌生;一些伊斯兰国家民众不熟悉“One Belt On Road”的表达方式,但却知道美国媒体创造的具有二元对立内涵的概念“China’s Silk Road”;新闻舆论与学术研究的脱节集中体现为国内外媒体在“一带一路”报道时选择学者信源时的随机性、以及普遍忽视“一带一路”的研究动态等。
四是对伊斯兰报道受到西方认知框架误导。萨义德用“Covering Islam”的语义双关“报道”与“遮蔽”之义暗讽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伊斯兰报道的偏见,而长期以来,国内舆论深受西方影响,缺少自己的议程议题,时常陷入“恐怖主义”话题陷阱,由于缺乏真正权威的解读,公众对于伊斯兰形象的认知也趋于极端化。“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众多伊斯兰国家和国内外穆斯林人民群众,而国内的穆斯林同胞大多居住生活在通向丝绸之路的重要边疆地区,伊斯兰报道关涉的不仅是“一带一路”,更影响着民族安定团结,但对于伊斯兰认识的舆论争议有扩大化的趋势。
三、“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与文明融合
参照国学大师季羡林“文化体系”的概念[7],世界文化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其中有三个都属于东方,这四个文化体系对应形成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带有强烈文明等级色彩地将伊斯兰文明视为威胁,甚至担心伊斯兰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明(中华文明)联合抗衡西方文明。实际上,在西方文明还未出现以前,三个东方文明直接已经由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交往活动,并形成了一些共同之处,到了近代,欧洲崛起,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东方的三大文明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西方文明等级意识中逐渐被归为“半开化”或者“半文明”,在这种客观历史外部环境下,东方三大文明造就的共同之处就更加突出和强烈了。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一带一路”连接欧亚大陆,“中华文明”一路向西连接“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与“欧洲文明”。从当前现实层面看,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比最高。而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形象长期遭受掌握全球话语权的西方政府、媒体、智库的妖魔化、污名化解读。在西方新闻话语实践中,伊斯兰和中国都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他们-我们”的话语建构实际上也代表着“他们”是“半文明”,“他们”是“不正确”的隐藏逻辑。中国和伊斯兰的话语体系遭受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排斥和边缘化,西方的话语主导了近代世界对于中国、对于伊斯兰的认识。不仅在新闻话语层面,在世界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上,依然由西方主导。但“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完全不同,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原则推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即蕴涵了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个蕴含中华文明包容精神的创新全球治理、重塑世界秩序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8]。
当前全球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几乎被美国一家所掌控,但客观看,美国全球话语霸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数次战争重塑世界格局及近200年的战略调整才得以建立的。这种带有侵略性和文化霸权主义色彩的话语体系已经逐渐凸显出与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相适应的征兆。“一带一路”全球传播需要构建一个人类文明融合的话语体系。从社会发展格局、话语体系现状以及文明交往历史看,“一带一路”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应当以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为切入点,在未来,还应该融合印度文明,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期,形成“中华-伊斯兰-印度”三大东方文明融合的全球新的话语体系,也将为欧洲发展带来机遇。但从现实层面考量,美国主导的话语体系及西方长期以来的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传播屏障,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文化教育领域,从宏观布局到微观突发事件,无不具备一套完整的话语霸权;此外,西方使用的英语也潜移默化地构建了一个交流屏障。
“一带一路”的传播与建设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和世界秩序,也只有一个融合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推动“一带一路”的全球传播,重塑世界秩序。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包容,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是能够团结“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9],这也是东方三大古老文明对话与融合的基础。“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将形成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作者文智贤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毛伟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
【注释】
[1] 杨鲜兰.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2):59-65.
[2] 刘禾.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14.
[3] 郭双林. 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 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35-290.
[4] 梁展. 2016. 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 刘禾.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1-162.
[5] Walter Deme. 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 Ein Beitrag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Rassentheorien[J].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92, 255(3):625-666.
[6] 程巍. 2016. 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刘禾.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1-162.
[7] 季羡林. 论东方文学——《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J]. 国外文学. 1986(4):6-27.
[8] 刘再起, 王曼莉.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以话语权和话语体系为视角[J]. 学习与实践.2016(4):68-74.
[9] 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下)[J]. 经济导刊.2016(2):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