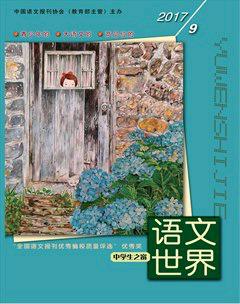生命如诗 岁月如歌
鲍学良
我的山野
“70后”的童年生活是在物资匮乏、生活清贫中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中国最早一批水电工程建设者,所以家也就随着他们,被安置在了云南罗平县离城很远的水电站工地附近。
那时的罗平农村,和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分别,春天满山满野开着油菜花,秋天各种野果累累。美丽的山村原野是我童年的乐园,馥郁的油菜花香,清甜的小草,湿润的泥土,层次丰富的山林,像血脉亲情一样令人回味、想念。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尽管很受父母哥姐的疼爱,但是由于地处偏远,父母几乎都在工地上忙碌,所以我三岁多还没照过相。在大约四岁多的一天,我偶然听到一个小伙伴在夸耀他吃到了一种叫冰棒的东西,说冰棒是多么的清凉多么的甜!从此以后,能吃到“冰棒”的愿望,就成了我一直在哥哥耳朵边念叨的话题,因为我知道只有在乡里上小学的哥哥有可能认识它,能接触到它。
那个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和平常一样,百无聊赖坐在门槛上玩,一边朝着哥哥放学回家的方向张望。远远地,我看到哥哥孤独单薄的身影像一个小黑点,移动在铺满了绿黄色油菜荚的缓坡上, 再近一些,能看到大大的斜挎书包,沉沉地坠在他的屁股上,让他走路的模样既滑稽,又很吃力。不过同以往不一样,那天哥哥的步子走得很急,一只手还是高高地举着的,神情也很自豪。距离家门还有一两百米,哥哥稚嫩的声音传来了:“弟弟……冰棒……弟弟……冰棒!”在听清楚了“冰棒”两个字后,我下意识地朝着哥哥跑去,一边跑,一边不忘紧紧盯着他手上高高举着的那根冰棒,惊喜的语调里还带着急不可耐的哭腔:“哥哥,冰棒!冰棒!”
我和哥哥坐在路边开满小小紫色龙胆花的田埂上,我捏着冰棒签,大口地吮吸那根融化得只剩下一小半的冰棒,而哥哥则一边揩汗水,一边舔流到他手掌胳膊上也许已经干了的冰棒水。因为急促地奔走,他瘦弱清秀的小脸红通通的,发丝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汗珠。哥哥开心地看着我满足地吃完了冰棒,山风吹过来,漫山遍野的油菜荚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我有生以来吃的第一根、也是最甜的一根冰棒!
装着我的念叨,上一年级的哥哥,一分一分地积攒了买冰棒的钱。
直至今日,哥哥那断断续续、稚嫩的声音还一直萦绕在耳畔,他高高举着冰棒快步行走在山野的身影,永远刻在了我心灵最深、最柔软的地方。
我的山野洒满浓浓的亲情,载满山野中自由奔跑、开心玩乐的欢声笑语,留着小伙伴集体挤着看电视的清晰记忆,生活并不因穷困而暗淡,反而让我对自然有着一份犹如对母体般的亲切。
我的家园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离开父母,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大理鹤庆上初中。这是茶马古道上一座以青山绿水和雪白美丽的银饰享誉四方的高原水乡。传说那里原本是一大片湖泊,后来飞来一群仙鹤,湖水便渐渐退去,露出了陆地,供人们繁衍生息,因此得名。水,是鹤庆的灵魂,这里湖泊星罗棋布,来自玉龙雪山腹地的清泉日夜不息,穿厅走户,给这里的人家带来温润清甜的滋养。
我并非生于斯,却在人生最美好的光景长于斯,所以对这里有着不是生地却胜似生地的深厚情感。
三年的初中生活,都是老家的伯父伯母在善待我抚养我。伯父家是一所传统的大理白族民居院落。推开大门,踏着一径光滑的青石板路,便见到照壁旁的一眼深井,井栏被时光磨洗得如儿时牵着我的祖母温暖的大手,有苍老的深痕,有时光的印记,有慈爱的味道;推开二门,是方正古朴的庭院,左手是一株几十年树龄的苹果树,年年挂果,口感脆甜,右侧种有牡丹、芍药、蔷薇、海棠、腊梅、金桂、山茶,屋檐坎上摆满兰花,这些花四时不断地轮番地开,演绎着生命轮回之美。
每年春節前,伯父总要带着我从大门开始贴春联,贴门神,一直贴到院内;大年三十,伯母领着我在大门旁给祖先敬香,献饭,这些传统的仪式,让年少的我对生活充满了敬畏。我把书桌安置在堂屋右侧的屋檐下,在这里看书,写字,听雨,观花,甚是惬意。至今,时隔多年还清晰地记得暮春、仲夏、深秋,不同季节落雨时,屋瓦滴落的雨水折射着四季不同色彩的阳光,或明或暗,或热烈或轻柔,激起泥土的不同时节的气息,带着不同的花香,弥漫到我的桌前。生命成长与自然、与四季物候如此的贴近、亲切,在我生命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求学期间,每次过年,我几乎都是元宵节未过,便辞别父母,回到鹤庆。虽然不乏伯父、伯母关爱,但难免有思念家人的离愁和想念罗平山野的孤独伤感。就在这样的境况里,我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与文字交友,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红楼梦》,读《红与黑》,当时好书难找,借书更难,同学们买不起书,就到书摊去租,两毛钱一天,为了省钱,就得赶紧看完,常常是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正是大量的文学著作,让我得以排遣内心的孤独,排解成长的困惑,并积淀下体察人生、看待生活的深厚情感和豁达态度。
而大理古城之于我,正如外婆之于我,又是一个家园的存在。
假期里回到大理古城看望外婆,是我儿时的期待。温暖的牵挂,湿润的离愁,永远牵肠挂肚。从小小的我抬头仰望城门楼上郭沫若书写的“大理”二字,到送别英年早逝的舅父的灵柩缓缓走过城门洞,到搀着外婆穿行在古老的街巷,聆听她讲述大理和她的前世今生,去感受这个民族的隐忍和担当。
多年前的大理古老,沉寂,就像文静缄默的外婆,充满神秘。于是好奇的我便去寻郭沫若的诗集,去找他的历史剧《屈原》,去读和大理有关的书,走进这座古老的小城,就像走近银发如雪、气度雍容的外婆,她深厚的人生阅历和历史风云,让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文化的情怀也更加纯粹和美好。
现在,伯父伯母已经老去,外婆……我有时间经常回乡,去街巷里走走,参加每年的祭祖,陪老家人说说话,这是我对大理这块亲情母地、文化胎盘最虔诚的感恩。
我的城市
如果说乡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温情的,到了青年时代,城市生活真正给了我身心上的历练和挫折。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举家搬迁到云南省的第二大城市曲靖。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单纯,善良,勤劳,但是由于处在经济大变革大创造时代,他们很少有精力关注到我们内心的成长,所以我们某个时期的成长注定是孤独的,甚至是叛逆的、挣扎的。
从童年时的山野寂寥到少年时的离家寄读,离离合合一直陪伴着我,去认识陌生的人事和环境,也成了令我非常敏感而害怕的事情,所以到了陌生的城市曲靖,我选择了一种沉湎于孤独的方式,不管阳光还是暴雨,我常常骑着老式自行车穿行在陌生的城市街头,看陌生的脸孔在眼前掠过。骑车累了,就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掏出书本,大声朗诵《少年游》《荆棘鸟》,或者幽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图书馆斑驳的墙壁下,读《飘》《基督山伯爵》。在陌生的城市,文学书本,是我这个孤独青年最亲近的朋友,在和它们亲近的时候,我的身心灵魂就能得到释放,得到满足。
考上大学,我来到了四时飞花的春城昆明,在这个多情的城市里读书,工作,恋爱,喜欢过齐秦脆弱的音质、张国荣绝妙的演技,还爱听女生们聊琼瑶、三毛,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喜欢《一地鸡毛》《过把瘾就死》,更喜欢的还是阅读顾城、海子的诗歌,喜欢看大部头的《白鹿原》《废都》,和所有男生一样喜欢金庸、古龙,也曾通宵看《鹿鼎记》……从青春到而立,从摇摆不定到沉淀安静,现在的我,读书,写字,备课,上课,当学生,当老师,做父亲的儿子,做儿子的父亲,从英姿飒爽到两鬓染霜,生活少了学生时代的洒脱,却多了成熟之后的温厚。很多事情可能已经释怀,已经遗忘,只有文学、艺术给予我的感受,像一张张发黄了却经典的老照片,从不泯灭,永远深刻、真切。
我的职业
奶奶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爱用粉笔在地上画小鸭子;父亲是单位的工会主席,我从小就跟着他,看他组织宣传干事去单位食堂大山墙出黑板报,我也拿着五彩的粉笔,跟着涂鸦;人生也就这样用粉笔开始表情达意;好友相聚,爱谈工作,同事们至今还经常打趣我有一次在喝醉后高声宣言:我爱教语文,我爱当老师!
从教19年,在清贫中坚守,在忙碌中收获,在做“摆渡人”职业中慢慢变老。发现过去的一切变得愈发清晰,这种清晰有一个更为具象的称谓,叫阅历——阅读带来的见识和力量,阅读带来的视野和胸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