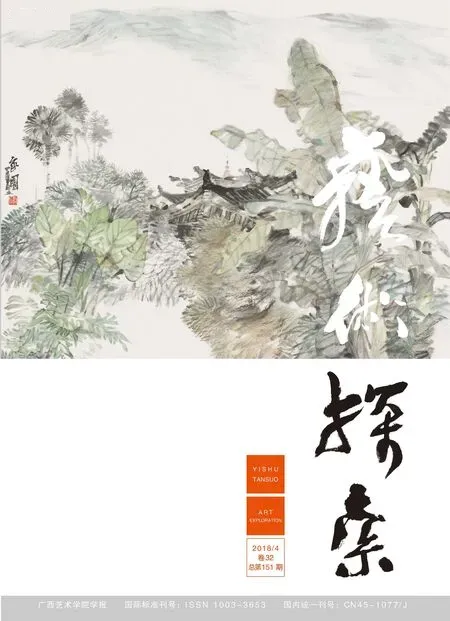艺术审美中的“身体”与“非身体化”元素
——对当下艺术创作中关于身体审美的一种反思
金丹元 张咏絮(.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00040;.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0007)
近20年来,身体审美似乎已成为一种“显学”,甚至成了一个非常时尚和流行的话题,不仅在绘画、雕塑、装置艺术乃至影视中都多有展示,甚至在理论界也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各种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直接相关的探讨。尤其是涉及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时,对“身体”的阐释更是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审美视点。受西方研究“身体”思潮的影响,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就开始了对身体的研究,首先从翻译外国著作起步,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梅洛·庞蒂等名家所涉及身体的各种说法先后被引入。而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不论是雕塑、绘画、戏曲、影视,还是充斥荧屏的各类广告,对于身体的展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单向度的“狂欢”,即对于赤裸肉身,特别是对裸体女性的关注,以及在表现欲望与人性所需联系方面的描述和论证。然而,对于作品中非身体部分的阐述却被大大弱化了,尤其是非身体的客观存在以及它所具有的隐喻功能,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这不仅对欣赏者而言在理解作品时会显得过于简单,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会因仅仅停留在画面的表层而缺乏深度。如是,在以身体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创作中,如有关裸体绘画、雕塑等,就极易出现止于裸露、肉体的表达局限,身体与非身体化元素间相互转化的关系被遮蔽了,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审美困境成了亟需我们关注和理应被格外重视的审视点。
一、“泛裸体化”时代的到来与身体消费主义
伴随着托马斯·米歇尔所言的“图像转向”的发生,以视觉图像为消费和审美主导的今天,表现人的身体美已成为各类艺术创作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对身体的书写从艺术审美到走向日常生活,进而引领时尚,成了红极当下的发展趋势。而当身体一次次得以呈现,一次次得以放大后,身体的私密性由遮蔽到敞开,又由这种敞开变成性幻想的对象,从而激活了人内在的性冲动、性需要和对性的无止境的渴求,并且这种冲动和需要也在各种艺术对身体越来越细腻的描绘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裸露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无处不在,更是成为吸引眼球所无法拒绝的刺激对象,似乎没有裸露,不见关于性器官的展示就不成其为身体审美了。于是,在当下有关身体的艺术呈现中,裸体化、情欲化和狂欢化也就成了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社会化了的消费卖点。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1世纪,中国进入泛裸体时期”[1]5,所谓的“泛裸体”是指“‘裸体’这种样式或手段被普泛使用,有艺术的也有非艺术的,甚至有的还成为一种风尚,而社会对此也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与认可”[1]5。诚然,裸体艺术自古有之,从古希腊时代起,人体就是当时雕塑艺术的主要素材,身体不仅代表了对神的崇敬,而且健硕的体格、协调的身体比例、充满力量的肌肉、优美的曲线都传达出人们对完美身体的赞美与憧憬。而在中国古代,这种有关裸体的表现大多都显得比较含蓄,有时常常还有意地遮蔽。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裸体才开始真正堂而皇之地进入到艺术和生活中来,首先在人体摄影和影视作品中初露端倪,之后,在相关的人体表演、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中也相继以运动中的裸体做出各种诱人的演示。新世纪以来,裸露身体不仅变得习以为常,而且,在艺术作品中所出现的女性裸体变得越来越精致化,也越来越具有诱惑性,其消费热点正在于“她们”的容颜、姿态和各种勾人魂魄的动作、眼神、手势,为人们提供了性刺激的参照,客观地说也达成了想象中的一次次性消费。而今天的网络艺术、网络传播又进一步使得这类性消费成为广告和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断地蔓延开来,并且在不需要出现裸露画面的广告中也不断得以强化,完全成了一种博取眼球的手段。
就影视艺术而言,裸体成为其制作和营销的噱头之一,似乎最早始见于1988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儿童不宜”的电影《寡妇村》,电影中赤裸的性爱场面对观众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张艺谋《菊豆》中偷看女人洗澡的一段影像,即男主角在偷看菊豆沐浴(而观众又随着镜头与男主角一起偷看女主角洗澡时的裸体),这组影像成了在电影审美中为满足中国观众偷窥欲的先例,也使它自身成为中国式“偷窥”的一组经典镜头。新世纪以来,《鬼子来了》《色戒》《苹果》《颐和园》《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也都因为其中有着程度不同的裸露人体的镜头而备受瞩目。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开播后,因为听说原本的“袒胸装”被剪辑了,反而引起观众的好奇,于是人们怀着各种猎奇心态,对它格外关注。而在随处可见的各类广告中,半裸半隐的女性身体的搔首弄姿不仅使裸露的趋势愈加明显,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女性作为“被看”的世俗心理,肯定了“窥视欲”的合法性。2012年,坊间传闻北京某酒吧上演了“裸体京剧”而轰动一时,其实这只是一个误传,只不过是某摄影师以戏曲造型为载体而创作的系列摄影而已。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裸体京剧/5737235?fr=aladdin。这组摄影于1996年,名为《三界,意识的三个层次:天堂,人间,地狱》的作品,现在仍能在网上搜索到某些相关图片,如《盘丝洞》《三打白骨精》《牡丹亭》《空城计》等。图中,女性丰满的乳房毫无遮掩地袒露在公众面前,在《盘丝洞》和《穆柯寨》中,更是连女性的下体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尽管是黑白画面,但依旧充满了情欲的诱惑。它也引发了网上的不少批判,认为这是为迎合媚俗的一种卖弄,是对艺术的糟蹋。在2008年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上,一尊半裸体的慈禧雕塑又引得网民热议,这尊雕塑以慈禧坐姿为造型,其右脚踩地,左脚着椅,双手分别搭在椅子扶手上,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衣服前襟全部敞开,露出了性感的乳房和私处。除了这些公共艺术的出现,“泛裸体化”时代还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私生活。明显有着行为艺术印记的,如公开的裸奔、裸体车模、裸体自拍、裸体婚纱照、裸体彩绘等相继涌现,一方面混淆了艺术与非艺术的概念,另一方面张扬着人的情欲需求和性冲动。这些对于裸露身体的狂欢式的展示,似乎一股脑儿地把国人曾禁闭的情欲都释放和宣泄了出来,似乎少了身体的裸露就不成其为艺术,就不再具有现代性特征了。对身体的狂热消费则遮蔽了非身体化元素(如作为背景或陪衬的山水、花鸟、建筑等)的审美功能和审美价值。
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当下,社会化消费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热点,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才会认为,身体才是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圈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120。这种说法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它至少印证了身体作为消费品的巨大市场潜力。但中国与西方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审美习惯与西方的历史和民族性有着很大的区别,二是艺术本身的魅力也不完全都依赖于裸体或必须仰仗对身体的演示才能产生审美愉悦。无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社会步入消费时代,改变了以往消费型社会生产决定消费的模式,恰恰相反,如今的消费正指导和制约着生产,也就是说人们想消费什么,市场就生产什么。于是,消费成为了主导,无形中也主宰着艺术的生产。在文化消费领域中,对于陌生的他者身体的神秘性和私密性的揭示触动了人的兴奋点,也刺激着人对欲望的满足。裸体常常作为性幻想或人在性幻想时的替身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当身体日益成为一种商品,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中的偶像时,对性欲的无度追求也就会随之而泛滥成灾,这似乎正在验证着鲍德里亚的说法:“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2]137-138。如是,“消费身体”就像获得了权威的支持和理论上的肯定似的越来越成为当下流行艺术的表征,而作品本身的意义却被严重忽略,乃至消解了。
二、被冷落了的非身体化元素及其表达
在当下艺术审美中,直观裸露的、情欲的“身体”似乎有着一种对现象学式的“现象即本质”的理解,但事实上往往不少无指向性的裸露却直接指向着色情。而作品中那些非身体化的艺术元素和艺术形式却被大大冷落了。这不仅不合理,有时甚至是不正常的。恰恰相反,在艺术作品中非身体化元素不仅可以加深或加强对身体所内含的意义的理解,甚至其内涵意蕴也有可能远胜于身体本身,在同一个作品中非身体化元素与身体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如果没有一丁点的非身体化元素,则纯粹的裸像究竟能说明什么,或象征何种意义,完全可能说不清楚。
“泛裸体化”时代的出现与社会变革有关,但在以艺术的名义突出或强化身体之时,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时那种莫名其妙的纯粹的肉身显现,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视觉的刺激物存在,而这种简单化的肉身的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却无从寻觅。而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包括以人体为主要审美对象的绘画、雕塑和电影(如古希腊、古罗马的裸体雕像和各个不同时代的裸体绘画)都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意义和思想,而非为裸露而裸露,为身体而身体。艺术家一定会借助裸体来表达他的观念和某种精神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身体为主要审美对象的作品中,非身体化的表现形式与非身体化元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辅助内容之一,这就如同一首优秀的交响乐或协奏曲,除了主旋律令人神往以外,它的配乐部分或第二主题也十分重要。非身体化的元素往往能起到深化身体所揭示的意义或说出身体演绎背后的意蕴。长期不受重视的非身体化元素其实在身体表达上往往还能起到衬托和映射的作用,它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是直接呈现给你什么样的视觉画面,而由它与身体的组合或浑然一体能唤起欣赏者更深层次的想象,它们所共同形成的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是非身体化元素最大的魅力所在。非身体化的表达既可以是一段优美的音乐旋律。也可以是绘画作品中背景,还可以是一段舞蹈、演员的表演和程式化的动作,等等,也就是说非身体化的艺术手段比身体本身更多样化,它的出现是为了提升身体审美,转化出一种诗化的艺术效果。
黑格尔认为:“隐喻其实也就是一种显喻,因为它把一个本身明晰的意义表现于一个和它相比拟的类似的具体现实现象。在纯粹的显喻里,真正的意义和意象是划分明确的,而在隐喻里这种划分却是隐含而不是明白说出的。”[3]127黑格尔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解释隐喻的作用的,而时至今日,“它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其他领域,涵盖图像以及虚构类的艺术表现领域,它已经被扩展为泛指各种跨越艺术表现界限的越界方法了”[4]10。这说明非身体化借由隐喻来完成了仅凭身体所不能表达的意味性,在作品中,非身体化元素与身体展示在时空中的结合会构成一系列新的画面符码,致使其意义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获得增值,从而不仅完成本义和喻义之间的转换,还能够超越画面或影像的限定,产生一种写意般的扩散视觉审美效应的功能。
“写意”原本是中国绘画的技法术语,韩玉涛先生将其定义为“小言之,这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奥赜;大言之,则是中国思维,特别是中国艺术思维的第一要义”[5]475。写意讲求的是意境之美,不以追求形似为主要目的,更注重对神似和气韵的传达。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写意既是形式也是内容,通过写意的手法,艺术家能营造出某种含蓄、虚空和具有一定隐喻性的艺术时空,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非身体化元素的转化也同样可以起到相类似的作用。如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中,导演通过对演员的表情、动作以及道具、服装的调度,使观众产生各种联想。以此让观众和演员一起进入到特定的情境与时空转换中,实现对当下现实时空的超越和想象。消费社会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强化了艺术作品的商业属性,例如,2010年,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在纽约拍出1.06亿美元的天价,再次刷新了毕加索艺术作品拍卖的最高价格。无独有偶,2015年,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画作《侧卧的裸女》以1.7亿美元价格同样在纽约拍出。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侧卧的裸女/18814233?fr=aladdin。这两幅画作都以裸体为题材,同时又都获得了极高的艺术赞誉并成为商业销售中的佼佼者。只要稍作审视就能发现,它们的成功实际上并非仅仅依靠裸体来获取人们的关注,而是通过画面中身体与非身体元素之间的转化与配合构成了有意味性的写意的艺术境界,也就是克莱夫·贝尔所言之“有意味的形式”。在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一画中,熟睡的玛丽是用简单抽象的线条勾勒而成的,脸颊和乳房的微微红晕和淡黄色的头发为人物增添了青春活力的气息,背景的嫩绿色植物和蓝色布帘,在色彩和空间上为人物形成了一道安全静谧的环境氛围。在《侧卧的裸女》中,除了裸体侧卧的女性外,其色彩搭配以及物件陈设让画面呈现出一种简洁宁静的氛围,作为底色的绯红色则暗示着由身体所引发的关于欲望和情色的诱惑,而蓝色和白色的冷色调则平衡了红色的情欲,使之和谐、优美。在这里色彩成了非身体化的艺术表现手段。试想没有这三种色彩的搭配,仅以裸体女性示人,其艺术效果和审美意蕴将大打折扣。在电影中,对身体的表达最多的类型片应该是情色片,“在银幕上展示人的性爱活动或是以引起幻想的色情景象,几乎是在电影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品的同时就开始的”②转引自阙镭《影片〈青蛇〉写意情色镜头的运用》,《艺术百家》2013年第12期,第336页。。然而对待情色镜头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如,可以是将大量赤裸身体的影像形成性爱桥段为主,也可以是以剧情为主配以少量裸露镜头,点到为止,或尽管没有床上戏,但影子、音乐、姿态的变化起到了明显的暗示作用,这些表现方式大多都以非身体化语言来传达,比之前者简单直接的性爱场面也许更耐人寻味,也可以从中生发更多的想象、联想。电影中常常用各种非身体化的物象来隐喻身体和身体所要传递的意义,在拓展观众想象和联想空间的同时,使对身体的审美上升为对文化、社会、人生的哲思。比如在韩国导演金基德的作品中,就常常用水来暗示人性中如水一样变动着的欲望和女性柔软的身体,在水袋中挣扎的金鱼暗示了女主人公无力摆脱任人宰割身体的命运。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电影中不胜枚举,在追求视觉美感的当下,这些非身体化的隐喻更深层次地传达了一个较完整的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隐喻以内在的光芒照亮了叙事,刹那间扩大了感受的范围。隐喻是影片的情绪——含义上的各个‘扭结’的浓缩物”[6]63。现代京剧《骆驼祥子》在表现两性身体缠绵交织的情节时,用一段双人舞来引导观众的想象,配以幽暗的灯光和动人的音乐旋律,舞台上诗化的表现让观众由此顿生美的遐想。此时的身体并非靠赤裸的肉身来显示,而是借助非身体化的艺术手段,使其达到一种超脱于两性交媾的更符合审美需求的灵与肉的双重结合。非身体化可以通过写意的艺术手法向身体转化,同样,身体语言也可以通过表演或恰当的手段转化出超出身体的意义和精神指向。正如黑格尔所说:“诗也可以不局限于某一艺术类型;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艺术,可以用一切艺术类型去表现一切可以纳入想象的内容。本来诗所特有的材料就是想象本身,而想象是一切艺术类型和艺术部门的共同基础。”[3]13所以,非身体化元素与身体的相互转换不仅丰富了身体艺术的表现手段,还能为观众打开想象的大门,极大地提升了以身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艺术的内涵和意蕴。
三、必须冲破被“身体”所役的审美困境
“艺术不只是认识世界,还要产生对世界的补充和一些自主的形式,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之外的东西,从而显示出自己的规律,展现个人的生活经历。但是,每一种艺术形式如果说不是被看做科学认知的替代物的话,都可以很好地被看作认识论的隐喻,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世纪,艺术形式构成的方式都反映了——以明喻或暗喻的方式对形象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当时的科学或者文化看待现实的方式。”[7]18因此,每一件艺术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深烙着时代的印记,当下艺术对于身体的热衷也折射出社会文化对它的关注,以及消费者对它的深刻影响。然而,过度地为“身体”所役,艺术也必将陷入画地为牢的窘境,呈现出身体审美的奇观化和意义生成的表层化的悖论。过分强调或任意放大纯粹由身体构建的图像,特别是任意地去表现某种性器官的诱惑,放肆地去煽动性欲的原始冲动,铺张地去渲染色情或淫荡的画面、影像等,则极易导致身体审美的意义走向庸俗、无聊和空洞化。
今天,艺术用以表征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图像化的倾向,各类艺术领地也越来越被“身体化”迅速占领,并蔓延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身体的审美可谓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在艺术审美中,身体从以往的遮蔽到现在的敞开和暴露,可以说是时代的进化使然。有学者指出这种转变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代人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身体外观的重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其次,身体的展示、暴露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最后,身体本身形成了一种文化,更有甚者,导致了某种“身体工业”的出现。对身体的关注说到底乃是视觉的欲望所致,而身体的“美学化”说穿了也就是人对身体视觉快感的苛求。[8]81在今天的中国,被视觉图像包围的受众不仅习惯了消费身体化的图像或画面,并且往往还不知疲倦地去主动找寻快餐式的、短暂的、易得的那种由肉体刺激所带来的快感体验,这种狂欢式的追求甚至成为了一种潮流,然而,过度地玩弄身体、消费身体肯定会导致意义的丧失、深度的消解和价值的扭曲。贡布里希就曾对随处可见的、被图像淹没的现象进行过批评:“以往任何时代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视觉物像的价值竟至这样如此的低廉。招贴画和广告画,连环漫画和杂志插图,把我们团团围住,纷至沓来。通过电视屏幕和电影,通过邮票和食品包装,现实世界的种种面貌被再现在我们眼前”[9]7。这不仅阐释了图像过剩且唾手可得的现状,同样也适用于说明当下裸露身体被热衷创作的情形。当下那种快餐式的图像生产和接受,则导致受众在短暂的瞬间就完成对作品的读解,而其实,往往创作者是为了吸引眼球,观众则更是一知半解,为寻找刺激而刺激。并且由于裸露身体高频次的出现也使得“裸体”变得稀松平常,神秘性逐渐丧失,受众的快感体验也随之出现边际效应。
德波所言之“奇观”,如今已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消费主义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①黄平文《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转引自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也就是说这些关于身体的奇观,一方面是被有意营造成挑逗欲望、生产快乐和满足体验的工具,另一方面那些诱人视觉的图像又反过来助推人们对其乐此不疲地进行消费。这样的奇观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看似完美的拟态环境,大众不仅认同了这一媒介环境,甚至逐渐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图像的完美,已经使我们上瘾,离开图像的生活,自我就如同枯萎的花朵失去了鲜艳与光泽,图像在培育瘾君子的同时,也使人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10]37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不遗余力地制造身体奇观并认同这一拟态环境,另一方面却又被它牢牢控制无法抽离,它成了人们走不出去的怪圈。当“身体”被奴役为一种媒体奇观之时,女性的身体也就会逐渐沦为“性客体化”①的存在。人们更注重女人的外表,身体或性身体部位,而不是她们的面孔和其他不可观察的属性(如思想、感情等)。②性客体化是指女性的身体、身体部分或性功能脱离了她本人,沦为纯粹的工具或被视为能够代表女性个体本身。在这样的图像裹挟之下,个体对于身体、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来源于图像符号,而非真实的世界。于是,“物体的图像变成了某种准主体”[11]97,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身体的认知,错把身体奇观当作真实,还会导致身体意义生成和指向的缺失。
在资本逻辑的市场中,艺术在不断向所谓的“大众化”其实是庸俗化的层面一步步妥协和就范,以此适应大众谋求操控感官体验的诉求,而这与波德莱尔定义所言之当下现代性的特点——“过度、短暂、偶然”[12]424相契合,快速、便捷、娱乐成了当下身体审美艺术运作的主要方式,以身体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各种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也必然会从高雅到走向通俗,将鉴赏转成消遣,人们似乎不在乎它是否带来艺术的熏陶与享受,更关注其个体参与体验的快感是否得到满足。周宪曾用“三个告别”总结审美文化的转向:“告别崇高,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兴起;告别悲剧,‘喜剧’时代的来临;告别诗意,‘散文时代’的来临。”[13]268于是,当以身体作为主要审美对象之时,面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快餐文化的侵袭,快感体验成为了受众追逐的主要目标。而快感体验本身就伴随着对深度意义的放逐而来,尤其是在所谓的娱乐电影中,那些只为制造裸露的视觉冲击而无意义联结的画面,已经失去了用身体来传达艺术的初衷,这必定会导致影像意义的肤浅化和平庸。
总之,尽管我们已经被图像世界所包围,尽管无处不在的身体审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我们始终不应被打着张扬人性旗号的“身体至上”“身体诱惑”困住手脚,因为身体只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对象之一,而非全部,即使是在以身体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绘画、雕塑中,也应该借助对人体的演示,不断去挖掘富有时代特征的身体的内在美,并通过这种演示,去开发出人体之美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