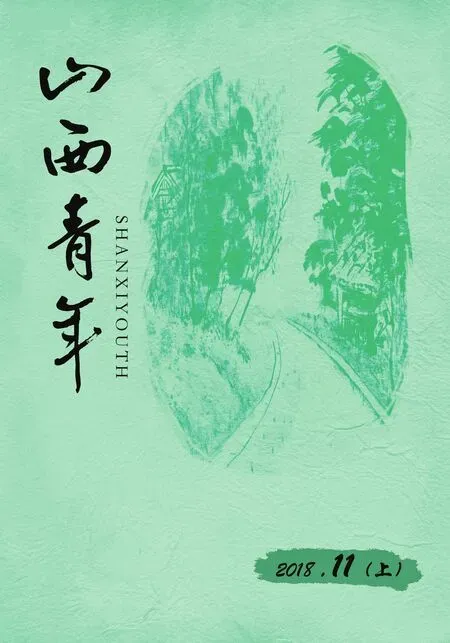从历史文献看游牧者与农耕者相似的抉择*
于 萍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近年来“炒”的很火的拉铁摩尔等人的“内亚视角”,主张站在“他者”的角度,即以游牧群体对自身的概念、方法和世界观去理解和讲述游牧与农耕的关系。对游牧者的内侵不再进行道德上的判定,而是从生存角度进行分析。然而“内亚视角”只是看到了游牧群体南侵不得已的苦衷,强调游牧者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是,游牧的困境又如何不是农耕也要面对的。翻开历史文献,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战争与和平,几乎贯穿历史发展的始终。而二者却在战和之间互相交往、互相融合,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而学界对游牧与农耕战和问题之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俯拾即是。然其多从政治角度入手而对其中的经济、人口因素有所忽略。正基于此,本文旨在前人研究之上,拾遗补阙,从游牧群体与农耕群体的经济形态入手并辅以其它影响因素,粗线条的考察与剖析了游牧者与农耕者所面临的共同抉择。即二者对于生存空间的争夺。
一、游牧社会
说起游牧社会,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天青草绿,牛羊遍野,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这样一副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但游牧生活却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惬意。牧民异常忙碌辛苦,并且经常受到一些难以预测的危险。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1]又如《汉书·匈奴传》云: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可见,自然灾害造成游牧群体财产、人员的巨大损失,破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由于游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野外放养的马匹、牛羊等牲畜是他们全部财产。当草原地区发生重大灾害时,这对游牧民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游牧群体在以游牧为主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作、狩猎、采集、贸易、掠夺等辅助性生业。而在自然灾害频发之时,游牧群体或要求扩大与农耕地区通贡贸易规模或不断南下劫掠以补充需用的不足。
(一)对外贸易
众所周知,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时常无法自给自足。因此游牧社会必须与农耕社会进行交换。其主要形式则是对外贸易。其包括朝贡和互市两方面。贸易不仅给游牧社会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而且农耕社会也从中获利。据《明史·食货四》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3]游牧者以中原地区为市场,销售其畜产品如马、牛、羊、兽皮等来换取粮食、谷物、瓷器、茶叶、丝绸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明史·黄骥传》也云:“至西域所产,惟马切边需。”[3]因农耕地区本身产马很少,且马的品种不佳,通过与游牧社会的贸易可以解决对马匹的迫切需求。而汉武帝也曾因求大宛天马不得,而贸然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
综上可知,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贸易是互利共赢的,但从长远来看游牧对农耕的依赖性却显得更大。尽管游牧者大都通过贸易互市或朝贡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但在贸易之余或贸易关系被切断之时,他们也会发动战争以掠夺的方式来解决需用不足的难题。
(二)掠夺
掠夺也是一种辅助性生业。而掠夺又可分为生计性与战略性。战略性掠夺一般采取恐吓、威胁、攻击农耕社会的手段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战略性掠夺是为生计性掠夺服务的。汉高祖白登之围后,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直到武帝初年汉匈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但匈奴经常出言不逊,破坏和约,从高后到景帝几十年间,匈奴犯边的事件多达十余次。而每次犯边之后汉朝除了象征意义的抵抗、反击之外就是源源不断地增加对匈奴的“岁赐”。《史记·匈奴列传载》载:孝文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到:“遗单于甚厚……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锦三十匹,赤綈、绿缯各四十匹。”[1]针对匈奴背弃和约“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1]的行为,孝文帝不仅没有大力惩处,反而赐予了匈奴单于更多物资。其后武帝也曾在朝会上指出,汉赂匈奴的礼物非常丰厚,但匈奴单于却“待命加嫚,侵盗亡已。”[2]进而致使“边境被害”[2]汉朝源源不断地向匈奴输送物资,但并未换来所谓的和平,匈奴仍不断内侵。可见,匈奴等游牧群体对农耕区采取的战略性掠夺,使得游牧区对农耕区形成压迫。以战争手段威胁、敲诈、勒索农耕区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
生计性掠夺即游牧群体通过对农耕地区的直接掠夺而获得物资。这是游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它有时会配合游牧的季节活动,一般发生于秋季或初冬。这是因为此时游牧民大都已完成了一年的游牧工作,兵强马壮。但草原地区在经受严重天灾之时,游牧群体南侵就可能随时发生。如《明史·世宗本纪二》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款同大塞……犯宣府……九月,俺答犯宁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春正月,把都儿寇广宁”,嘉靖二十年(1549年)“春二月壬子,俺答犯宣府”[3]等等。可见此时北方蒙古犯边不再局限于秋季或初冬,而是一年四季不间断发生。这是因为明代处于我国气候最为寒冷的小冰期,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下自然灾害频发,这也导致了北方游牧民的不断南下。
综上可知,掠夺是游牧社会的辅助性生业,即使在游牧与农耕和平交往时期,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着冲突和战争。游牧社会对农耕社会进行的掠夺,无论是战略性还是生计性的归根究底都只是人类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二、农耕社会
谈到农耕社会,首先想到的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冠带之国、礼仪之邦。但是农耕地区的实际情况也许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自然灾害不仅对游牧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在灾害面前农耕社会也无法幸免。如《汉书·五行志下》载:“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2];又如《西京杂记》也曾提到:“元封二年,大寒,……野鸟兽皆死,……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4]可见农耕社会在天灾之前也可能不堪一击。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人民的死亡。若此时恰逢游牧群体南侵,可能会导致国家动荡,王朝灭亡,明朝就是一个显例。纵观中国历史文献,从灾害造成的大量流民到揭竿而起的乱民之间,实际只是一步之遥。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时多有灾害发生。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都是在灾害背景下发生的。可见天灾会加速、加重人祸,人祸又加深了天灾所造成的后果。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曾指出,在无天灾、人祸、百姓勤恳劳作之时。普通老百姓五十岁才能着布帛缝制的衣服,七十岁才能偶尔品食肉菜,数口之家方能没有冻馁之患。可见对农耕群体来说生存也是极其不易的。农耕群体一般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的发展则表现在粮食作物单产提高和可耕种土地面积的增加。
(一)农作物的作物单产发展
在未引进红薯、玉米、花生等高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之时,从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进程之中可知,单产的提高主要取决于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的改善。即精耕细作的精细程度的提高。然而仅靠这一点并不会引起农作物产量的大度幅度提高。以黄河中下游农耕区旱地作物粟为例,汉代粟亩产约为120斤,隋唐约为140斤,北宋约为117-155斤,明清约为150-200斤。[5]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中粟的亩产只增长了30-80斤,增长率为25%-67%。可见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是极低的。相对于粮食亩产的缓慢增长,千年来中国的人口却在激增。葛剑雄先生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全国人口约为2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人口约为6000万。西汉至隋唐因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人口锐减,后随着唐王朝的建立,社会安定,人口逐渐恢复,到唐玄宗时期人口大约在8000万左右。明清两代是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明代人口约为2亿,清末人口约为4亿。[6]可见,从先秦时期到清朝,中国的人口增长了3.8亿,清末人口为先秦的20倍。
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是以算数级数率增加。[7]按照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食物的自然定律,可知生存资料增长亦必须与人口增长相平衡。因此,人口不断的增长要求农业生产有着与之同步的发展进程,依靠精耕细作所带来的农作物单产的提高,这是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百姓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延续,农耕地区的统治者多通过拓展耕地面积的方式来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治理压力。
(二)耕地面积的扩展
耕地面积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农耕王朝对外战争,开疆辟土。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经常陷于冲突之中,这其中不仅有游牧民南下掠夺中原的人口、物资,还包括中原王朝的北上反击。双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因而导致了中原地区与游牧群体在和平交往之中却掺有战争的存在。
观中国历史,在历史上被歌颂的明君圣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大都有开疆拓土之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也都因经济繁荣、疆域广阔、政治清明、文化繁荣而彪炳史册。因而开疆辟土,封狼居胥也成为了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圣主的目标。但对外扩张多被时人当做劳民伤财的行为。“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1]的观点盛行。然而疆域领土的拓展真无用吗?汉唐两代都出现过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武帝以“复九世之仇”为由,与匈奴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同时以断匈奴右臂的目的经营西域。兵连祸结、穷兵黩武导致汉朝出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的情况。因而武帝晚年下诏罪己,适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并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2]昭帝时,朝廷曾对武帝朝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讨论。有的官员认为汉匈和亲,每年给予匈奴大量的财物,但匈奴仍不断内犯。同时,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使汉朝改变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局面,国富民强。因而,武帝认为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同意对匈作战。然而,有的官员却认为武帝“苦师劳重,以略无用之地……愚窃见其亡,不睹其成。”[8]认为与匈奴的战争只是劳民伤财,征服的土地也并不适合耕种、居住,可以说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的政策是错误的。无独有偶,这样的讨论在唐太宗时也曾发生过。
唐太宗平定高昌之后,准备将高昌设为唐朝州县,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以褚遂良、魏徵为代表的大臣们却强调所谓的“华夷之辨”,认为明王应“先华夏而后夷狄……不事遐荒”[9],可以讨伐有罪的高昌王但是不能灭亡高昌国。并认为在高昌设州县之后其驻地的兵员、辎重是难以保证的而且耗费巨大,这只会加大国家的财政支出,属于“散有用而事无用”[10]的行为。
汉武帝和唐太宗在战争取得胜利之时或设立都护府或设立郡(州)县、羁縻府州对其进行统治。其目的都是巩固对北方游牧部族作战取得的成果并控制和经营西域地区。控制住西域地区就可以削弱和牵制北方游牧群体的势力,保护河西、陇右的安全,进而断其右臂。防止游牧势力对中原地区形成包围态势。并且利用新开拓的领土来充当战略缓冲地带,确保中原王朝的安全。除上文提到的政治因素外,开疆拓土还有这深刻的经济根源。
对游牧社会而言,农耕群体与游牧群体的战争可消灭游牧群体的有生力量和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据《史记·匈奴列传》载:“……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2]冒顿单于曾游牧的阴山地区,此地后成为汉帝国的领土。匈奴被迫北徙,使其游牧区域不断变小。此外,河西走廊地区,武帝前亦为匈奴所游牧。匈奴失此地后,常日夜悲痛,感叹祁连山的失去使得匈奴的六畜都无法不蕃息。游牧群体在战争中失败了,因而土地丧失,动摇了“国之根本”,实力也就衰弱了。相对而言,中原王朝疆土却得以扩张,对游牧部族就产生了绝对优势。可见,农耕王朝对游牧部族的主动出击就如蜀汉对曹魏的北伐般都是以攻为守以实现保境安民。
对农耕社会而言,封建王朝的疆域扩展活动大都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时期展开的。这是因为在王朝建立之初,因战乱、灾害、疾疫等原因造成了早期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王朝初期政治清明也使得当时的田制对百姓充分授田有一定保证,人地矛盾问题尚未显现。但是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进而使得人地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人口移动或者移民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两相平衡。而移民则需要土地,要解决因人口激增而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则必须不断向外寻求土地,发动对外战争,开疆拓土以扩大了耕地面积。中国的人口从始皇统一六国前的2000万到清末的四亿,中国的疆域也从秦朝的“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到清时的“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11]到清朝时的国土面积竟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可见,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国土面积的扩张,人口增殖是推动耕地拓展的动力。
要之,人口的滋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这一切都要求农耕民族不断地向外寻求土地,开疆辟土,以求解决人地矛盾。尽管游牧地区环境恶劣,但理论上年降水量只要在250毫米以上的地区都可进行农业生产。[12]秦朝北击匈奴,移民实边,开阴山以南之疆土。汉继秦法,以河套为根据地,开辟了陇西四郡,从此河套与河西农业区便与中原连为一起,成为主要的农耕区之一。与此同时,游牧群体南下劫掠,也必须有推力和引力,推力即游牧地已经有了无法生存下去的理由,引力即为中原地区可以为游牧民的生存提供粮食等。[13]可见无论是游牧或农耕群体其抉择最终也主要是生存空间的争夺或者说是生存本身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