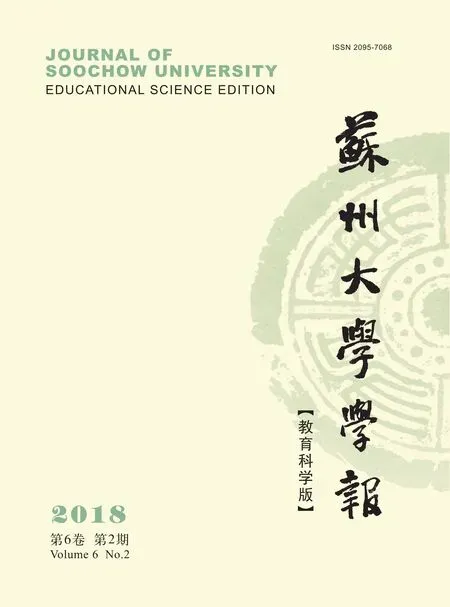共建中国心理学史料库 同创史学研究新局面*
舒 跃 育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波林(Edwin Boring)曾说过:“心理学家只有知道了心理学史,才算是功行完满。”同样地,心理学科只有形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才可能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当哲学家们在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想表达的是,是一个学科的历史在塑造本学科的当前形态。心理学史对于本学科的重要性,一方面指向心理学家们——对学科史的了解程度决定心理学家们的学术素养;另一方面则指向学科本身——我们将自己对心理学的理解,投射到对本学科历史事件的解读之中。心理学史承载着本学科的集体记忆,学术共同体正是通过这些共同的集体记忆,塑造着这门学科的“自我”和未来形态。本学科的学人们也正是通过对本学科过去的记忆的规整和重组,反思并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形象和确认自己的学人身份。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个民族如果忘记或者背叛了本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一个学科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忘记或者背叛本学科历史的学者,怎么可能成为一代宗师?一个缺乏对本学科历史总结整理的学科,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学科呢?
中国心理学界对本学科历史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初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有学者发表心理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近百年来,心理学史这个分支学科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逐渐发展过程,许多心理学史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总体而言,我国心理学史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落后。
这种落后首先表现在,我们缺乏对学科相关的史料进行有意识的保存和整理。要知道,这种有意识地对学科史料的保存和整理,是每一个心理学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责任。因为学科的发展历史,为每一位亲历者所见证,因此,完整的学科史料库的建设,必然需要尽可能多的学科建设者的参与和支持。为了让史料尽量少的遗失,仅仅依靠少数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是难以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的。国内心理学者对中国心理学史的系统整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到今天,我们对学科史料的规整,依然停留在少部分从事心理学史的研究者们的单打独斗的水平上。前几年,我自己在整理一些学者的史料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搜集史料的困难并意识到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本学科的发展。美国心理学界,从20世纪初,就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和机构,有意识地系统保存和整理学科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学者的通信、个人日记和日程表,还包括授课笔记、课程表、实验记录、仪器图样,以及学者们的照片、研究机构和研究设备的各种资料,还有各种专业组织和会议的记录资料和照片。美国心理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有意识的保存,最早可追溯到1892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之时。后来在波林的幕后推动下,由麦奇森(C. Murchison)编辑出版的《自传体心理学史》(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第一卷于1930年出版。2007年,本书的第九卷面世。当然,这部记载美国心理学发展的辉煌画卷还会继续展开。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主要由心理学家们的自传构成。自传都是个人化的,但如果大部分心理学家晚年,都能留下自传或者口述史,我们就保持了这门学科的集体记忆,这对于重建我们学科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很显然,此书的撰稿人,大多不是专门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但他们都有共同的历史使命感,那就是,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本学科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记录进入集体记忆库中——这是每一个心理学家最后的责任。
1965年,Akron大学建立了美国心理学历史档案馆。该档案馆拥有全世界最全的心理学史方面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涉及近六百名心理学家和组织,包括五万余本图书,一万五千余张照片,六千余部电影、音频或视频材料,数十万件通信、手稿、讲座笔记、测验设备及实验室设备。并且,通过美国心理学会的网站,就可以检索到各种口述历史、照片、传记、讣告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的相关资料。通过有意识地保存、整理和收集资料,美国心理学界为本学科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集体记忆库,这就为他们能在将来的任何时刻,重新反思本学科的成就及不足奠定了基础。
对比我们自己,很显然,中国心理学界还缺乏这种对学科史料有意识提交和整理的观念。尽管每隔一定的时间,中国心理学界都会对近几年或者近几十年来的学科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和反思,但往往是某些并不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术权威”在完成他们的“行政任务”,他们总结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为了让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早日摆脱被动收集和单打独斗的局面,笔者对此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中国心理学会应该尽快依托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筹备建立中国心理学史档案馆(包括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鉴于此项工作过于繁重,当然可以在全国各地区建立分馆),整理补充相关史料。同时,全国各心理学机构,都应该附设相应的心理学史档案室,并配备专门的心理学史研究人员,以存留和整理本单位自然发生的心理学史档案。与此同时,中国心理学会可呼吁我国各心理学组织(包括各级学会、各大学心理学科系和研究院所的心理学机构,包括民间的各种心理学组织)定期向就近心理学史档案馆提交各种档案的复印件和扫描件(若能提供原件更好),共同为完善本学科的集体记忆库努力。笔者自己近几年来,已经为从民国到现在西北地区心理学发展的史料,进行了有意识的收集。未来,这项工作将逐渐向全国展开。
第二,启动《中国自传体心理学史》的编撰。心理学史档案的存留和整理,不是少部分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就能完成的,这项工作需要心理学界全员参与。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缺乏主动的存留和整理,许多学界中的重大事件,当多年后,特别是这些亲历者们都离世之后,相关史料基本无从追溯。许多心理学家的生平及学术贡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缺乏对相关学者的生平进行专门和系统的整理,多年后,这些学者们在我们学科的集体记忆库中就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生疏。这在关于我国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史的编纂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许多学者,只知其名,甚至有时连确定一个人的姓名都破费周折——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百余年的心理学史,似乎只有零碎的事件,整理不出学科思想脉络的发展。我们只能看到稀疏的树木,却看不到学科之林。由于缺乏对史料的系统和主动规整,这给学科历史的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损失,可能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美国《自传体心理学史》编纂的做法,不断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每位心理学者所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工作经历。几年前,笔者就开始策划编撰一部属于中国心理学界自己的“自传体心理学史”,这项工作,现在正在逐步展开。为此,特呼吁老一辈身体健朗的心理学家们,能够有意识地以回忆录或者自传的方式,规整自己从事心理学教学、研究和推广应用的经历,能提供支撑材料比如照片或者相应的扫描件更好,这既是对自己数十年人生事业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表达对心理学科的关切和期待的难得机会。与此同时,每位心理学工作者,在平时科研和教学工作中,都要有主动保存某些必要的过程性资料的意识。
第三,通过抢救口述史的方式,补充机构档案的不足。对于由于各种原因不方便自己整理写作的心理学家,可以采取口述史的方式,来整理相关史料。笔者已于五年前开始整理西北地区早期心理学家及家人的口述资料,这个工作最近也在向全国展开,这项工作也得益于部分老一辈学者们的支持。当然,口述史可以是针对自己的,也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老师或者熟悉的心理学学者的。但整理口述史,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在这方面,许多媒体和专业组织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我们需要多向他们学习。但在口述史的整理过程中,一定要以史实的整理为主,尽量少作对当代人的评论,特别是对自己的“定论”。整理口述史,需要传播老一辈心理学家们的优秀品质和积极精神,但不要言过其实,不要将口述史作为某些人个人粉饰自己的工具。心理学家们的历史评价,将来历史自有公论。不建议学者自己去为自己做所谓的“历史定论”。另外,由于年代久远,有些记忆可能不是太可靠,史实的真伪需要鉴别,需要多方面考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整理档案,还是收集回忆录或者自传,乃至整理口述史,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都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更多的人支持和合力,特别是成立专门的机构,争取专门的经费。当然,此前许多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系统而全面的工作,还需要心理学界共同协力,将这项工作推进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为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开拓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