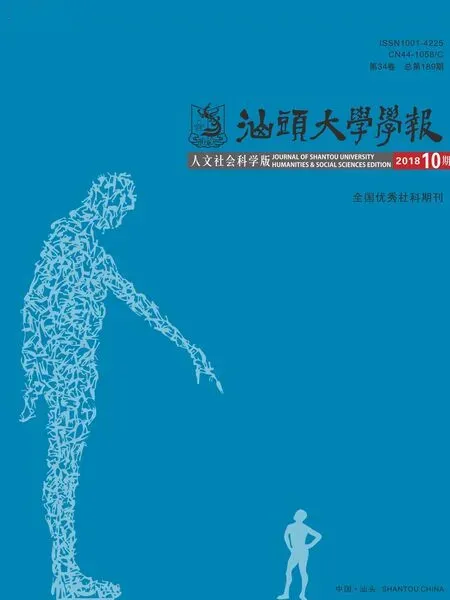俗世立人的假想与批判
——鲁迅《野草》“复仇系列”的再解读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野草》二十四篇被认为是鲁迅唯一的散文诗集。然而,事实上,《野草》里各篇未必都算得上是散文诗。鲁迅自己对《野草》文体就有不同标目,如“小品”“小感想”[1]365-366,又如“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1]469不仅如此,《野草》各篇的文本自身就呈现出了不同的文体样态,既有鲁迅式的“杂文”,也有“散文”,也有“散文诗”,也有“故事新编”和“文学剧本”,乃至于还有自嘲为“拟古的打油诗”式的“新诗”。即便是《复仇》系列的两篇,也在文体上各自不同。《复仇》(其一)总体上与其说有散文诗的味道,不如说有情景剧的色彩。《复仇(其二)》显然是故事新编,而且是《新约全书·马可福音》里的故事的“中国化”的新编。
如此说来,鲁迅对《野草》文体上的考量,事实上文体学意义的比重不是中心,战术上的布局和角色塑造才是要害,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战斗”,要有“战斗的意气”。鲁迅对文体问题并非像后人所设想的那样认真、那么规范,这当然不是因为鲁迅的文体认知不深,为学不精,而是因为鲁迅所处的时代语境和学术阶段,乃是新文学初创、现代文学在中国草创的阶段。为了知道梨子的滋味,亲口尝一尝当然要远比看一看梨子的形状更为重要。
明白鲁迅对《野草》文体上的自我把握和主见,是为了撇开文体问题的缠绕,更好地从文本本身、从作文命意的角度来理解《野草》,而不至于因为文体上的特征过于拘泥一毛一发的微言大义之辩,也不必为个别字眼陷入诸多哲学和主义的黑洞里面,进而把问题带入到玄虚的深刻追问与无妄的诗意揣摩中。因此,不必非得以“散文诗”来论《野草》,就不仅是正常、正确的,也恰恰是符合《野草》各篇自然和本然样态的。本论着意与此,以《野草》中的两篇同题文字“复仇”系列文本的细读为基础,探究这一思路的破解可能。限于篇幅,以《复仇》(其一)为中心。
一
1931年11月5日,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里对其中“难于直说”的八篇作了说明。这部分里,有《复仇》(其一),但没有《复仇(其二)》。这恰恰印证了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里所说的“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所谓“一半”,言下之意,便是还有另一半,合起来才圆通。《野草》的“复仇”系列亦如是,鲁迅仅仅解释了一半。
的确,关于《复仇(其二)》鲁迅没有文字言诠。那么,是不是因为它容易读懂、简单呢?当然不是。诚然,我们可以说,《复仇(其二)》有故事新编的性质,即“改写”。《新约全书·马可福音》里耶稣被钉十字架而后复活的故事,对于阅读鲁迅文字的读者而言,情节内容并不难解。但为何要在彼时语境里改写一则这个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呢?如果解释对象是中国人,的确也可以说没有必要,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是常态。但鲁迅是在《〈野草〉·英译本序》里对《复仇》(其一)做解释,而对《复仇(其二)》不做解释,这多少有点悖乎常情。显然,为《野草》的英文译本作序,解释的对象就是熟悉圣经故事、熟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英语世界的人群。向这一人群解释《复仇》,反而应该是有必要解释为何要“改写”《圣经》故事的。毕竟“改写”终究是有意味的。至于《复仇》(其一)固然也可以解释为何写作,但不解释也无伤大雅。
因此,倘若是外国人阅读《复仇(其二)》,所要追问的,恰恰是这个问题——为何要改写?是针对什么?用意何为?诸如此类。通俗而非易懂,这正是英语世界读者阅读《复仇(其二)》所遭遇的别致的尴尬。因此,从解释的角度而言,反而有必要加以解释。然而,鲁迅加以解释的却是《复仇》,而非《复仇(其二)》,原因是《复仇》写作的原因“难于直说”。这个逻辑多少有点出乎意外。
鲁迅解释说,《复仇》(其一)表达的是憎恶社会上围观者之多,这并不难于直说。其实,真正难于直说的是围观什么的人多?或是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突出的动辄喜好围观的现象?如果是后者,那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考索,也不是难于直说,而是难说清楚。如果是前者,那的确存在难于直说的因素,因为围观者围观的对象、事件,也许正是某一情境下的敏感事件,说清楚其实并不难,关键是一旦说出来将会由此惹上麻烦乃至罹难。因此,难于直说的关键并非说这个动作,而是直接表达内容——说真话、说实话、说大白话之后其本身所关联的现实风险,即“直”的危险。由是可以明白,因为难于直说,必然如骨鲠在喉,所以《复仇(其一)》仅仅写出了鲁迅因憎恶社会上围观者之多而作典型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而且是虚拟情景剧式的批判,是“曲”说了。
因为鲁迅写了《复仇》(其一)的初衷——“直说”某事的写作冲动未能排解,于是便有了《复仇(其二)》。遗憾的是,鲁迅仍然是不过以故事新编的方式,曲折地隔山打牛,曲说了一通了事。鲁迅在同一天连写同题的“复仇”两篇,而且同刊于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7期,自然不是一般的续作,起码也是意犹未尽之作。写完《复仇》的鲁迅意犹未尽,便有了情不自禁、顺势而为的《复仇(其二)》——颇有“故事新编”意味的“野草”。真可谓欲说还休!于是,《复仇》与《复仇(其二)》便构成《野草》里的“复仇系列”姊妹篇。只不过,鲁迅仍旧是在“曲说”,因为他是知识分子、精神界的战士,但更是本色的作家,有作家的本色。“说”——不管是曲说还是直说,“写作”,才是鲁迅的本色和呈现本色的应然所在。
鲁迅《〈野草〉·英译本序》告诉我们,打开《复仇》(其一)解读思路,就是理清其“曲说”的轨迹和艺术。这显然不是什么散文诗与否,而是鲁迅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逻辑特色。鲁迅希望在《〈野草〉·英译本序》提醒外国朋友的,是“如何读”而并非“为何写”《复仇》(其一)。这自然是英译本序文应该有的考量。如是也就明白鲁迅为什么不解释《复仇(其二)》了。因为要害就是“如何读”而并非“为何写”,强调的是“曲说的艺术”以及背后的愤怒与批判,而并非“说什么”的“奋其私智”、乃至私勇。鲁迅虽赞扬猛士,但自己并不满足于、乐于此道罢。
故而可知,曲说是艺术,但并非散文诗专有。鲁迅的文体,作为一种风格,和所有人一样,无非就是曲说与直说,这并不神秘。曲说是艺术,直说也可以是艺术。不过,鲁迅的文字魅力正是以曲说和直说的经纬交织,绚烂成文。《复仇》(其一)亦如是。《复仇》(其一)共八个自然段。开头两自然段,起语劈头就是“人的皮肤之后,大概不到半分……”,接着一段却是“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其实正是“直说”与“曲说”、真实与假设的两段,构成了下面六个自然段的“复仇新说”的前提和结论——“这样,所以……”。倘若没有这个文钮性质的“这样,所以”四个字,就没有鲁迅的《复仇》了。
二
鲁迅以“复仇”来命题,再到立论,再到展开议论,这里面的逻辑思路是什么?鲁迅在《复仇》和《复仇(其二)》里分别要表达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两篇文字的题目都是《复仇》。那么何谓“复仇”?为何命题为“复仇”?
尽管现代汉语里这两个词经常换用,但显然“复仇”不完全等于“报仇”。“复仇”更多指涉着某种基督教里的宗教情怀,强调的是仇恨的消解、平复,着意于宽恕与博爱的基督教文化。报仇则执着于仇恨本身,强调的是二者的报偿、应答与得失均衡,没有过多的文化和思想底蕴的依托。重要的是,报仇最终引发的是仇恨的连环效应,或聚变,或裂变或衰变,指向的是无边的仇恨。
注重仇恨的无法消解,还是在意仇恨的平复与宗教式的博爱宽恕,是我们理解鲁迅为何命题为“复仇”的关键。报仇的俗世味道,也许是鲁迅强调韧的战斗的底色所不愿意用的。而复仇的宗教意味与底蕴,那种无边的悠远指向,在“执着”与“破执着”的恒久上,反而有着内在的精神通联。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命题为“复仇”而非“报仇”,而且在同一天,连着进一步在《复仇(其二)》里再作一文,借《新约全书·马可福音》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改写,申说在《复仇》里未能尽兴的、意欲强调持久的战斗这一意思和相关联想。于是在世间与出世间的过渡地带,鲁迅找到了自己对“仇恨”问题的独特理解和处置态度,这也就构成了《野草》里独一无二的文本系列——复仇篇。①有学者指出鲁迅的《女吊》里的复仇理解,似乎更强调报仇。笔者认为以民俗视野来看女吊怨鬼式的形象,在鲁迅看来,所取并非报仇的痛快,而是对于事情的认真与执着精神,所谓韧的战斗。这一点恰好与《复仇》(其一)所强调的“他们俩对立着”的共存意义上“对立”精神是相通的。
那么,《复仇》(其一)究竟写什么?
长期以来的一种解释,就是鲁迅所说的,是因为“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即对路人们、围观者的复仇。事实上,这只是解释了《复仇》篇的绝大部分,即“路人们从四面奔来”之后的部分。在此之前,鲁迅设计一个“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的情境,意在引出被围观的后续情境。这固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在这句话的前面有两个虚词“这样,所以”,那又该做何解?显然,“这样”指代的是《复仇》开头的两段话,“所以”导出的是后面出现的俩人裸身捏着利刃相向的结果,进而导致被围观的结果,又进而导致围观者“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最终反转为“被围观者”围观“围观者”——“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可见,在“这样,所以”之后的文字里,鲁迅展示了一系列互为因果的情景剧,思索生命在这种连环套般的格局里的干枯与大戮。被围观者——无论是“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也罢,或是“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也罢,尽管相对于无聊的“路人们的干枯”与“无血的与大戮”而言,有“复仇”的大欢喜、飞扬、沉酣的自豪感与痛快淋漓,但其代价同样也是无谓的。对于无聊的路人们,对于以无聊为意义与追求的“路人们”,耗尽自身生命来赏鉴这种无聊,这样的俩人“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显然同样不算有多少真正的意义。正是因为这种以近乎无意义的“以死人似的眼光”来对待路人的无聊,围观与被围观,双方的实质并没有多少不同,唯一变化的不过是视角与角色的互换而已。哪怕是情节翻转,充其量也不过是享受一种居高临下的反讽与快感而已。这当然不算是“复仇”的意义,否则同样是形而下的庸俗快感——这想必也不是鲁迅所期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过是互为观看,互相围观,以虚无对付无聊,结局是没有意义的,也仍旧是无聊。而一旦堕入如此境地,以这种方式的反抗路人的围观的“复仇”,与其说是“哀其不幸”,毋宁说是“怒而争”——近乎怼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复仇”导致的最大伤害,并不是对路人、对围观者的憎恶,而是迎风而唾、唾面自干的尴尬与虚无。因为复仇者是牺牲了自己有意义的鲜活生命去对抗那些无聊的、失去了生趣生命,本想因此而求索生命的真意,但结局居然都是一样的——干枯。复仇者复仇的结果却是牺牲自我、自我干枯,与无聊着同样干枯,这样的大结局,多少显得荒诞。
仅仅以“看与被看”的模式论来解释“这样,所以”之后的部分,并不能解释鲁迅为何非要设置一个“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的情境。本来,制造吸引路人们围观的情境有非常多的可能。特意设想俩人裸身默然捏利刃相对的情境,鲁迅的这种假想意在何处?有意思的是,鲁迅在写作《复仇》的时候,只是写“有他们俩裸着全身”,但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却明确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2]由模糊笼统的“他们俩裸着全身”到“一男一女”,这里的可看性、围观热度无疑是大不一样的。然而一旦明确为“一男一女”,尽管强化了这种被围观场景的世俗趣味,却降低、淡化了这一情境本来的思想内涵。鲁迅后来的补充,道出了当初写作有意回避的部分。这也说明《复仇》这一情境创设初衷并非在于其可围观的庸俗趣味和因素,而是强调其高远的思想志趣和象征意味。也就是说,这一情境的要害,并非这俩人的性别,而是他们“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后的“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的肉体与精神的对峙、紧张状态。而无论是相爱或者相杀,俩人的对峙——“对立”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复仇”——但不是报仇,因为这种对峙的意义不在于消灭对方的肉体,而是获得精神的统一与平衡,是追求共存,在互相参照与对立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对”的目的和旨趣都是“立”,而不是“亡”和“杀”,真正的“复仇”是为了共存不是共亡,这才是鲁迅“复仇”新论的最大新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第三自然段的“这样,所以”。否则无论语意还是逻辑上,都是无法自洽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样”才能指代前面两个自然段的内容——“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但都并非肉体之欢,也不是肉体消灭的凶杀,而是“复仇”——爱恨情仇的互相依存。如此这般存在的两个人,其精神与肉体的均衡状态与本质意义的尊崇,才恰恰与路人们和“他们俩”构成的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关系是互看基础上的互灭,是无聊之上的无聊,本质上并无关系,有的只是没有意义的互相伤害。这当然也是一种复仇,不过是世俗之仇。
由此可见,《复仇》中呈现出了两种复仇图景,展示了两类复仇关系的理解境界,既指涉肉体与精神互敬互爱、和谐统一的共存,也关联着肉体与精神互害互灭、无聊对立的虚无。当然,这两种复仇关系,同样存在和适用于“我”——鲁迅——作为个体的自己。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图景,《复仇》所探问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复仇”,是世间的精神拯救,是真实人间的精神“立人”,是人文世俗的启蒙开化,而非出世间的宗教超越。尽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种思考多少有点人工制造革命的意味。没有文化上的彻底批判与刷洗,这一“立人”的就只能是“但倘若”的设想,最终堕入虚无,因为它没有自我内爆的思想战力和精神更新的内涵。
三
如何在中国文化里更生出新的精神质素,锻造出现代的精神界战士(立人),强调一种对立共存的现代人的间性关系,这正是如鲁迅这种矢志启蒙而又执着于自我反省的人时时念念于心的问题。但俗世恶趣味如此之重的中国人间,显然是难乎其难。于是,在叩问了中国文化下的人之子的“复仇”后,鲁迅意犹未尽,心绪难平,于是有了对神之子与人之子的“复仇”差异与共同之处的是非想,于是有了《复仇(其二)》,并在《复仇(其二)》末了仍旧发出慨叹——“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由此可见,鲁迅的“复仇”指向是人间的,鲁迅要的是“立人”而不是“尊神”。这才是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鲁迅式复仇情境设计的“理念”所在。和相关引导、抒论的“理念”所在。有鉴于此,《复仇》(其一)对肉体的微观赏鉴与宏观哲思,对两个裸身仇者相爱相杀、难解难分的生命“大欢喜”境界的喟叹,对围观者与复仇者之间关系的角色批判与思想翻转情怀,其如郜元宝先生所谓“精神和肉体成功的‘合作’”的见地,才能在鲁迅基于反抗、基于复仇,终于立人、终于爱人的现代理想和境界中得到解释。毕竟,“人之子”才是五四一代的孤独者们的中国式的“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3]的怕与爱。
显然,上述对《野草》里“复仇”系列的探究,事实上与散文诗与否并没有直接关联。“复仇”系列的文字事实上也并不费解,它的确有象征、高度浓缩和转折、跳跃的文本特点,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它是“散文诗”。相反,鲁迅的“复仇”系列的文字转折和逻辑关系非常严谨,提点清晰,场景的转换和过度都有明确的勾连。这甚至也是鲁迅小说文本的一个明显的特色——逻辑关联词语特别突出。本来,文本特征与文体构成关系,事实上也并不那么单一。文体之所以成为文体,自身的创作思路规定性、审美特征的独特性反而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况且鲁迅对于文体本身,并没有后人所界定的那么认真和拘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拘囿于散文诗来论《野草》的“复仇”系列,我们反而能从文本自身的朴素还原上,看到和读到了它想说和说出的东西,当然也看到了它想说而没能说出某些东西的“无奈”和“空虚”、无聊的状态。作为一个真正清醒、乃至“独醒”[4]的“人之子”的思考者,我相信,这样的非文体论导出的鲁迅《野草》解读也许会更为朴素、本真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