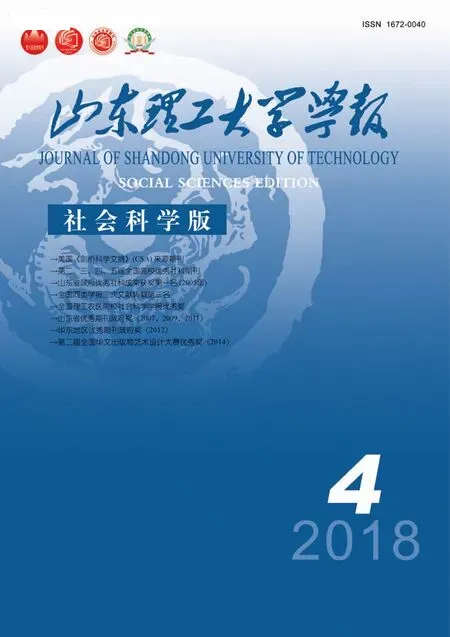论魏晋士人人格意识的演变
岳 庆 云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魏晋是“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自觉”的时代。谈及魏晋经典之作《世说新语》时,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1]210。宗白华先生强调的是:人格美的评赏是中国美学的发端。笔者认为,人格美的评赏也是魏晋士人人格意识的重要体现。学者张法曾说,“魏晋时代审美意识的成熟意味着中国审美对象结构的定型”[2]123。由此可见,魏晋士人人格意识的演变在中国士人发展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之前,士人的人格意识还处于模糊、不自觉的阶段。如《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谈及的是一种集体的、笼统的人格意识。至魏晋时代,士人的人格意识产生了向内转的趋势,以我为本,以真为贵,展开了对个体生命的审视。从历时性角度看,魏晋士人人格意识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节点:建安时期、竹林玄学以及陶渊明,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建安时期:慷慨悲壮的才性之美
春秋末期,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准确立:即“立德、立功、立言”,俗称“三不朽”。其中,“立德”排在首位,强调的是道德人格的建立。“立功”排第二,强调的是社会责任的完成;“立言”排第三,强调的是文化使命的完成。“立言”排在最后正符合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总体来说,儒家是以“德”取人的,道德人格的建立是士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首要途径。
建安时期,择士标准发生重大转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曾记载曹操的择士观:“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此处的“行”是指品德操行,“才”是指才能智慧。曹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胆推行“唯才是举”的择士标准,不再以品德操行为首要的衡量标准。这种新的择士标准把人的才能智慧推崇到空前的高度,是对儒家传统“德行第一”择士观的反叛,在人的思想解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已经给传统的“三不朽”重新排了位置,将“立功”排在首位。建安时期,这种评赏人物的新标准由政治领域逐渐延伸至其他领域,从而演变为一种时代风潮。刘劭在《人物志》序言中宣称:“智者,德之帅也。”他明确提出“智”是选才的首要标准,排在德行的前面。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干,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擅长辞赋。他曾说:“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中论·智行》)他认为历史上那些成就大业之人靠的都是智慧,不是仅有德行虚名,就能成就霸业的。
强调“才智”、淡化“德行”,是建安时期品评人物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是建安时期士人人格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在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有非常明显的呈现。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年高志远的进取之心。曹植的“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现了一个年轻人为成就霸业,视死如归的悲壮之情。由此可见,建安时期人格意识的最高追求是个体生命在展示才智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才性之美。这种对“才智”的赞赏虽仍留有儒家传统人格的印记,但也增添了一种积极进取、慷慨悲壮的人格特质。
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与王朗书》中,曹丕对“三不朽”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在曹丕看来,立德仍然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首要目标,“立言”紧随其后。而曹操重视的是“立功”“唯才是举”。笔者认为,这父子二人的不同观点源于他们不同的经历和使命。曹操作为一个开国元勋和政治家,戎马一生,志在一统天下,启用有才之人是其成就霸业的根本,因而他大力提倡“唯才是举”,将“立功”置于首位。对曹丕来说,他的首要任务不是打天下,而是守天下,需要提倡“立德”来稳固统治。除此以外,曹丕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面对生命的短暂和荣华富贵的易逝,难免会对功名利禄产生一种虚幻感,认为“立功”难以体现生命的价值,文章写作虽无事功可言,却可以名世。因而曹丕将“立言”置于“立功”之前。这表明曹丕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个体生命意识觉醒方面比曹操更进一步。
总之,建安时期淡化“德行”,强调“才智”,由重品行之美发展至重才性之美,呈现出慷慨悲壮的特质,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的重要表现;曹丕强调文章写作的不朽,是魏晋时代“文的自觉”的重要表现。这两个表现在中国士人发展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竹林玄学:幽愤逍遥的个性与自由之美
汉末以后,经学衰微,玄学兴起。玄学是对老庄思想的研究和解说,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次复兴。魏晋玄学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又提倡道家的自然观念,因而玄学家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在思想中协调儒、道之间的关系。学者李锦全曾将玄学名士分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3]98,前者以何晏、王弼、郭象等名士为代表,后者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主流派名士的贡献是对抽象的认知体系进行重组,非主流派名士则主要致力于将抽象的认知体系转化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生追求。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主流派名士虽是玄学的创立者,但他们并未对玄学理论进行现实意义的转换,因而,他们的人格意识的内涵并没有新的变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崇尚庄子的自然观念,开启了一段追求个性与自由的新旅程。
“竹林七贤”极力追求个体生命的内在体验,在放达、任诞的休闲生活中体现自己的个性。《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与嫂子亲近,有人讥笑他不懂礼数,阮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张季鹰过着快意放纵的生活,有人提醒他要顾及名声,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士人王子猷曾经借住在一处空宅子里,找人种了满院子的竹子。有人问曰:“暂住何烦尔?”王子猷答:“何可一日无此君?”对“礼”与“名”的蔑视,意味着玄学家对传统的人格意识的反叛。将兴趣爱好转化为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使之与个人的生命融为一体,这也是展示自我个性的一种方式。
竹林玄学认为内在的才性会外化于人的服饰容貌,并将人物的服饰容貌作为评判士人人格的重要依据。《世说新语·容止篇》曾专门记录士人的服饰款式,以宽大、飘逸的服饰为主;不仅注重女人的容貌,还注重男子的容貌,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美男子潘岳,他的出现往往会引起众人的围观,“莫不连手共萦之”。“魏晋士人的‘个性’不但风采独具,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反映在当时的审美文化上,就是所谓‘魏晋风度’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特征”[4]176。
除了生活中的自我个性,“竹林七贤”还追求精神自由。他们深受道家自然观念的影响,主张以精神的超脱来远离俗世,追求一种亲近自然、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阮籍在《达庄论》中提出了“至人”的人格,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又提出“大人先生”式的人格。这种“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人格,其本质是一种崇尚绝对自由的人格,是阮籍等寻求身心自由必须达到的精神境界[5]79。
“竹林七贤”的人格理想中,道德因素不再居于首要地位,但作为一种入世观念保留下来。在他们的人格建构中,对个性与自由的执着追求是一种显性存在,儒家的入世观念则是一种隐性存在。归隐山林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当建功立业的雄心湮灭在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虚伪之中时,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会浮出水面,成为他们最终的人生归宿。在这种入世与出世的两难选择中,“竹林七贤”的人格意识呈现出个性化特点。嵇康是一个敢于直面敌人的勇士,他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对抗,没有迂回徘徊;他最痛恨的是政治家的虚伪和战友的背叛,耿介、高洁的个性以及焦虑、孤独相伴终生,最后惨遭当局杀害。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面临当局的政治迫害,他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以“发言玄远”而佯狂寓世;山涛、向秀、王戎等名士最终选择放弃人格理想出来做官。
总之,“竹林七贤”崇尚老庄的自然观念,致力于玄学理论的现实意义转换,以放达、任诞的方式体现自我个性,以崇尚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建构来逃避、超越现实。然而,“竹林七贤”所追求的个性与自由只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实践与精神的空想,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生存的土壤。所以他们要忍受来自现实与理想双重的失落之苦,呈现出一种幽愤逍遥的气质。
三、陶渊明:冲淡自然的田园之美
据史载,陶渊明乃官宦子弟,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早年亦有济世志。陶渊明回忆年少的诗句:“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这说明陶渊明年少时也曾有过建功立业的志向。陶渊明给大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希望儿子“温恭朝夕,念兹在兹”。他在《责子》诗中责备儿子们懒惰、不爱读书、好玩等等,表达出一个父亲的失落之感。以上实例说明陶渊明以儒家的传统观念寄希望于儿子。而立之年,陶渊明初涉官场,官拜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作了几任小官之后,最终选择隐退,正如陶诗所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
生于东晋的陶渊明,也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十分推崇庄子的道家思想,在诗歌中多次用到“自然”一词。如《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进自然。”陶渊明还多次化用庄子的典故,如《拟古九首·其八》,陶渊明曾把“伯牙与庄周”看做自己的“相知人”。此处的“伯牙”并非实指,而是“相知人”的代名词,诗人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对庄子的赞赏。朱自清先生曾评论说:“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6]569这说明庄子的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之深。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次复兴,“回归自然”是其思想的精髓。陶渊明在这种玄学思潮的影响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的人生理想。陶渊明认为,混迹官场虽可勉强填饱肚子,建立功名,但却必须牺牲自尊与自由。为了保持人格的自然本性,实现真正的自由,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弃官归隐。竹林玄学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归隐山林,陶渊明则把“自然”这一概念引向了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归隐田园的可行性。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7]108
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创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了其独特的美学意义,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歌的创作之旅。
其一,自然风物之美。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把优美、闲适的乡村风光写进了诗歌。各种意象如山林、飞鸟、榆柳、桃李、微雨、东风等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乡村图画,以质朴清新的风格走进了陶渊明的诗歌,令人心向往之。
其二,乡村人情之美。怀着济世之志出来做官的陶渊明,非常反感那些勾心斗角、沽名钓誉的官员,也厌倦了官场生活的虚伪与黑暗。辞官归田之后,陶渊明与农夫朝夕相处,在这些粗陋的农夫身上,他发现了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简单、善良的品性及健全的人格。他很快就融入了田园生活,与这些乡村野夫农忙时一起耕种,闲暇时一起玩闹:“农务各自归,闲遐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民,见面交谈的话题也围绕着庄稼和收成:“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时分,偶有农夫不请自来,原来是得了一壶好酒上门来分享:“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当他生活窘困、难以为继时,邻居会慷慨解囊:“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田园生活免不了清苦,却也体会到了一种真挚的乡村人情之美。
其三,物我相得、恬淡自适之美。陶诗有:“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登东皋以舒啸,鸣清流而赋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谈我书”。这些诗句记录了陶渊明弃官归隐、走进田园之后的生活日常:种地采菊、打扫屋子、读书赋诗等。这些生活日常流露的是一种物我相得之情,洋溢着恬淡自适的悠然自得之情。
袁行霈先生评价说:“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8]211在陶渊明的诗歌中,真实记录了田园生活优美的自然风光、真挚的乡村人情、清贫简陋的日常生活,但整体来说,作者还是沉醉于这种恬淡自适的田园生活。
总之,与“竹林七贤”幽愤逍遥的气质相比,陶渊明追求人格理想的心态更趋平和。他曾涉足官场,也曾徘徊于官场与田园之间,但最终确立了“归隐田园”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身心的自由自在,不受外物奴役。“归隐田园使陶渊明从空间上避开了世俗社会的困扰,虚拟的桃花源亦可从意念上修正现实田园生活中的种种缺憾。”[9]44田园生活虽然清贫,却没有官场的污秽之气,陶渊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找了依托之处。东晋时代的陶渊明在官场和山林之外,找到了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呈现出一种冲淡自然的特质,为后世文人所效仿。
四、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之前,士人的人格意识还处于模糊、不自觉的阶段。与前代相比,魏晋士人的人格意识产生了向内转的趋势,展开了对个体生命的审视。魏晋士人为寻觅身心自由、排遣心灵焦虑,其人格意识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节点:建安时期、竹林玄学以及陶渊明。建安时期淡化“德行”,强调“才智”,由重品行之美发展至重才性之美,呈现出慷慨悲壮的特质,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的重要表现;曹丕强调文章写作的不朽,是魏晋时代“文的自觉”的重要表现。“竹林七贤”所追求的个性与自由只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实践与精神的空想,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生存的土壤。所以他们要忍受来自现实与理想双重的失落之苦,呈现出一种幽愤逍遥的气质。与“竹林七贤”相比,陶渊明追求人格理想的心态更趋平和。他追求一种“归隐田园”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自在,不受外物奴役。他在官场和山林之外,找到了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呈现出一种冲淡自然的特质。陶渊明在人格意识的修养上达到了魏晋时代的最高点,并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