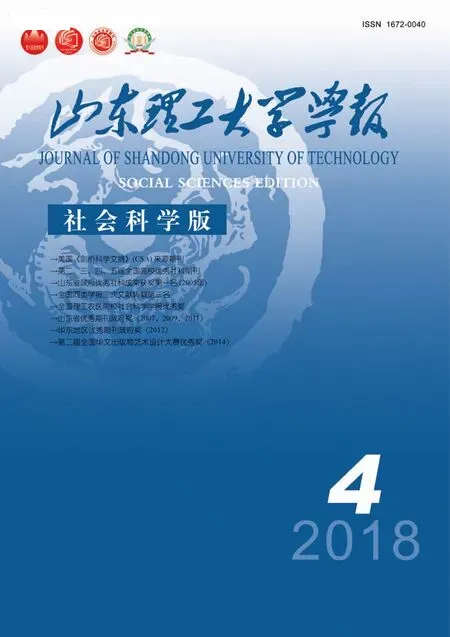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冲突下的《发条橙》解读
王 晓 华
(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一、引言
《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62)是英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安东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1917—1993) 的一部影响极广的代表作。特别是当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将这部小说于1971年搬上银幕后,《发条橙》不仅成为销量惊人的畅销书,作者本人也随之成为名人。为此,国外有关该小说的研究文章不断增加。在我国,漓江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一书,从这里人们知道了安东尼·伯吉斯及其作品《发条橙》。自此,国内有关该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时至今日,有关《发条橙》的研究文章还是比较鲜见,且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道德选择与自由意志”“反语言与反社会”“音乐与犯罪”“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困惑”“自由意志与极权社会的关系”“叙述角度” “宗教危机”等方面。再者,这些研究除极少数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高层次刊物之外,大多集中于普通刊物,学术影响力不足。本文认为,《发条橙》所反映出的,是在科学昌盛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忧思:作者立足于人本身,从人的发展角度,展开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独特思考。由此,这部文学作品便发散出浓重的哲学之思。对此,本文将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冲突的角度,对《发条橙》做出再思考。
二、《发条橙》与人文主义
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被称作20世纪中叶英国文坛的“实验现实主义小说”。在伯吉斯创作的30多部小说中,《发条橙》是其获得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尽管作者本人并不看好这部作品)。1971年著名导演库布里克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影片因其中大量的色情与暴力镜头而引发广泛争论,导致在英国遭到禁演。《发条橙》获得人们广泛关注,多是由于作品中对“恶”的描写。毋庸讳言,那一幕幕令人作呕的画面在整部作品中几乎俯拾可见。因此,阅读行为甫一开端,作品就将读者带入一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环境之中。主人公亚里克斯与其同伙彼得、乔治和丁姆,都穿着当时时兴的黑色贴体紧身服,“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嗯?”成为他们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无恶不作的开场白。在作品的第一部分,抢劫、打架、强奸、吸毒、凶杀等一幅幅暴力场景,以及夹杂着非正常的纳查奇语与说话方式,仿佛将大家带到一个黑暗的罪恶之都。在那里,每条街巷,每个公共场所、每栋民宅,都成为亚里克斯等人的寻衅闹事,并从中获得快乐的地方。他们毫无法纪观念,动辄毫无缘由地打人抢劫。比如亚里克斯伙同他人私闯民宅,对这家的男主人任意殴打,并当看他的面轮奸女主人;他们抢夺私人汽车,用完后将车推入河中;他们与另外流氓团伙血拼,并带着全身的血腥味继续作恶;他们打劫商店,打伤店主人并将收款机中的钱悉数抢走;当他们随意打伤一位老者,看到鲜血从老者身上涌出时,他们却认为“真好看”。这一切就是亚里克斯等人玩的所谓“花样”。这些“花样”既是他们自行取乐的方式,同时又是给他者施加痛苦的方式。在《发条橙》中,这些“花样”大致占据了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人们不禁要问:作者以冷静的方式,刻意描写这些罪恶的东西,其目的何在?难道仅仅就是为描写而描写吗?事实绝非如此,伯吉斯对罪恶的描写,只是表达其对当时社会环境焦虑的一种手段。依据欧洲思想发展史与伯吉斯本人的思想可以看出:《发条橙》意在揭示社会的发展,“恶”的泛滥,反向证明人文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和思潮,“人文主义”在欧洲思想史上自古有之,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注点与理论特征。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更多体现为一种人文教育,对“完整人”的全面培养的教育。这种培养目标的实现,也就体现出Humanism的内在精神。即对“人性”的培养。这一时期,“‘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1]4-5。由于文科(Liberal Arts)和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都带有(Liberal)一词,这就说明,在西方,不管是文科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包含着“自由”之义。因此,“人文”又有了在自由状态下的理想人性之义。
作为一种特指,“人文主义”主要指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即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看待外在一切的出发点,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人的个性与自由,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宽容。与此相关,人们主张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有关科学与艺术的主张。特别是要求将科学、道德与艺术三者结合起来,通过教育的手段,使之在人的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其中,古典文化的恢复,特别是古典文学即拉丁文学的重现,既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成就,也是文艺复兴这一表述的由来。作为一种思潮与理论,人文主义的形态从来就不是静止或封闭的。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主义理论形式也发生着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人文主义精神实质,即主张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性与自由,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思想,在欧洲思想史中一直得以延续。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思想,相对较少关注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其实,作为人类思想的共同成果,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同欧洲大陆思想一样,都是推动人文主义思想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譬如,都铎王朝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运动,对英国社会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对英国国家意识的建立与巩固,民族主义的觉醒,工业制造业的形成,航海业发展与海外市场的开拓,世俗政权的不断强化等,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日渐受到科学主义的挤压。于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艺术教育改变人们精神面貌,重新实现科学、艺术、宗教三者统一。这一理论主张与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观点一脉相承。所不同之处在于,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主张人文主义的实现应从文学艺术入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首先是一场文学运动。换言之,英国人文主义者认为要改变英国国民的精神状况,首先应从文学艺术开始。从19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批判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的侵蚀、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其中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理论、弗·雷·利维斯的文学批评理论、I. A. 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的文学批评颇具代表性。他们普遍认为:文学可以强化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文学对价值的关注,是通向传统的唯一精神途径。以利维斯为例,他的《伟大的传统》《英国诗歌的新方向》等著作,都昭示着他对文学传统的坚守。他认为科学技术只能造成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而只有文学才能矫正这种思想偏差,改变人们重物欲、轻精神的观念,重新唤起社会对人自身价值的关注,进而将人从物欲的泥沼中解救出来,使其摆脱沉重的物质羁绊,以轻盈的身躯飞向自由而广阔的精神世界。基于此,利维斯特别强调了文学在人文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伯吉斯本人的家庭出身对其创作也有着深刻影响。伯吉斯生于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幼深受宗教影响,并对此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天主教对现世幸福的追寻非常类似于人文主义思想对人类本位的张扬。故而,伯吉斯的宗教信仰其实进一步浸润和巩固了其人文主义思想根基。我国思想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简单认知:启蒙运动是理性横扫宗教,彻底战胜并消灭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在20世纪之前,在英国人的思想中,人的现实性与精神性、人性与神性,科学理性与天启神喻,人的世俗性与理想性,知识的探求与宗教的信仰等因素,并未完全走向对立。比如有西方哲学家认为人们不能仅仅依靠知识的力量,就能完全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有较少或肤浅的哲学知识使人的思想倾向于无神论,这是人所设想的真理和得自经验的结论;但是,继续深入地研究,又使人的精神皈依宗教”[2]292。应该说,这些哲学家有关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现着启蒙运动中理性与宗教、人文主义追求与神性主义信仰之间和谐关系。伯吉斯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及其本人的宗教背景,都决定着他在创作《发条橙》时,决非刻意为描写罪恶而进行描写。相反,其目的在于让世人理解:人的自由实现是建立在对他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对他人价值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尊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与操控,而是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关系。当一方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时,他也必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和现实的惩罚。而作品第二章对于亚里克斯受到惩罚的具体描写,便是这项人性伦理因果律的感性显现。
三、《发条橙》与科学主义
《发条橙》的第二部分描写了亚里克斯被强制改造的过程。这部分描写表达了伯吉斯对科学万能论的不同看法。在第二部分的开端之处,亚里克斯的名字已经变为6655321了。他在这个“地狱洞、人类兽园”中,“被凶残成性的看守踢打、推搡,与色迷迷的臭罪犯打交道” 已经2年[3]80(以下引文无引证出处的,均出自《发条橙》)。在这一部分中,伯吉斯借亚里克斯之口,说出了“坐牢并不是教化,一点也不是”的观点。同时,他又借狱方之口表达了同样观点:“政府再也不能墨守过时的监狱管理学理论不放了。把罪犯都圈在一起,然后坐观其变。你们就开始集中犯罪,在刑罚中犯罪。”在作者看来,对人的教化,不应该是通过限制人的自由而实现的,也不应该是通过打骂等侵犯人的尊严等方式完成的。当然,我们更不能通过所谓科学方式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在第二部分中,伯吉斯特别提及科学手段对亚里克斯改造的失败。当亚里克斯在狱中待了2年,而常规改造对其毫无起色时,狱方决定用科学手段——“路多维哥氏技术”来完成这项未竟的工作。该技术将犯人作为单纯的病人,用针剂注射的方式,扼杀掉犯人的犯罪反射神经,以此彻底割断罪犯头脑中“恶”的念头,以期达到对犯人的改造。本文不再赘述“路多维哥氏技术”的运用及其对亚里克斯造成的痛苦与伤害,而只谈论这项科技是否能真正达到为犯人祛除恶念并使之复归正常人这一目的。事实是:亚里克斯的确再没有犯罪的念头了,甚至看到罪恶的场面与描写就想呕吐。他彻底成了一个“善人”,但同时他也失去作为正常人而应具备的生存能力。特别是在一个充满暴力与邪恶的社会中,当他遇到别人对他攻击时,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作家亚里山大见到亚里克斯这个样子后,不无忧虑地说道:科学技术的成功就是将人变成毫无选择能力与权利的动物。可悲的是,这恰恰不是科学的成功而是科学的失败。经由对这项“失败的科技改造”的书写,伯吉斯诉说了他本人对20世纪欧洲“唯科学论”的失望,以及对科学技术未来发展前景的忧虑。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我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用以统治人的工具,更不是目的。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目的,而人成为手段,那人就变成了“发条橙”,即变成一个受到机器装置控制的人。这也正是作者以“发条橙”作为书名的用意。应该说,这重隐喻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展示与描写,而科技对人性的摧残与压抑,科技的局囿与限度则构成了该隐喻的深层所指。
科学与科学主义之间也可谓是同异结合。为更清楚地把握科学主义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产生与影响作一探讨。关于什么是科学,迄今尚无统一的界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科学作了不同说明,提出了自己关于科学的定义。比如“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4]1026。“科学是指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以及人们追求这种知识的活动”[5]2。尽管这些定义表述各不相同,但在强调科学是关于事物的知识体系这一问题上,却又是极其接近的。在此,我们权且不去细分这些界说,仅将其视作是一组针对“科学”所做的“家族相似”式的表达与概括。那接下来的问题是,“科学”的产生机制为何?
论及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古希腊便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阶段,因为古希腊是科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古希腊早期,哲学与科学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多来自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与研究。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就是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也就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发端。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决非单纯是为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深层目的在于自由之实现。古希腊人为了实现自由,就必须完成对外在自然事物的了解,对事物规律的揭示。因此,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言之,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手段,而人的自由与价值是最终目的。第二,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更多体现为精神性的追求,而对物质的追求相对较弱,功利性的观念不强。正如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说过: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6]45。 由此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自由的学问,是求知的学问而非功利式的学问。
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却在整体上呈分裂之势。从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确立,培根等人对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崇尚开始,人的主体性、理性或技术理性成为近代特别是现代社会两大主要问题。这两大问题哪一个是主要的,是需要首先发展的呢?很显然,当时大多数思想家倾向于把理性或技术理性看作手段,将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作为目的;同时,他们又认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于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支持与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趋对自然科学所产生功效产生了过度迷信与依恋。特别是当黑格尔将理性推至终极标准的高度后,理性或技术理性超出了作为手段的范围而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它已经由原先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然而,技术理性与人类主体性的错位却同时招致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这种冲突关系在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显现得尤为突出:在古代,尽管自然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技术理性还没有充分发展,人们时时受到强大自然力的威胁,物质财富贫乏,但人们却能从自然界中发现那诱人的诗意;而科学理性昌明的近现代,自然界却全没了诗意,露出了与人为敌的面目。这是缘于,科技理性的狂潮裹挟起了人类无尽的实践欲求,使其在凝聚科学的、实用的态度的同时,日渐疏离了那通向自由境地的审美状态。于是,自然成为人类科学和发展实践的首要对象,却不再是人类审美经验的主要来源之一;技术取代了人性,充当起了社会发展的核心焦点。进而,我们在拥抱科学主义的同时,却近乎遗失了人文主义的精髓所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与概括,科学的涵义及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哲学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系统化,并将之作为唯一的知识标准推向科学之外的其它领域。于是,首先,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走向分裂。其次,科学所体现出的技术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终极标准。最后,实证性、知识化、数字化与可操作性等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侵入人文科学,并最终成为人文科学使用的标准。“近代西方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由于近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以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7]5。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最初产生于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一切知识都应是在经验范围内的,经验之外无所谓真与假。后经罗素等人的推动,科学主义把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数理化与逻辑化,并推广运用于一切人文学科之中。于是,科学转化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8]163。当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终极方法,广泛应用于一切理论研究之中时,科学主义不仅与人文主义分道扬镳,而且日益挤压人文主义,不断将其边缘化。最终,科学主义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科学技术,成为解决现实社会中一切问题的最终手段与方案。伯吉斯在《发条橙》中,对依靠科学技术改造犯人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亚里克斯被科学技术改造后的处境,也说明科学技术永远不是万能的。
四、《发条橙》的启示:人文与科学应和谐而非对立
本文认为,伯吉斯的《发条橙》之所以声名远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者向世人证明了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统一的,而非冲突对立的。人的发展是人文与科学产生的直接动因:人文主要从价值论角度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意义;而科学主要探讨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寻找人在世界中得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前者侧重于人的内在精神,后者偏重于人的外部世界。尽管有内外之别,但两者都是围绕着人展开探索与研究的,故而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过度发展一端而放弃另一极。否则,人将成为单面的人,人本身将不再完满。这对于个体性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人类社会来讲亦复如是。当人文与科学分裂之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冲突与对立就会不断加剧。人类社会内部也充满着矛盾,社会将处于动荡之中。
萨顿在其《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中强调,科学如果离开人性或为人的意义,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科学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它是人类为了自身而不断探索的历史。如果离开了人,科学研究就会毫无意义可言。为此可以认为:读科学史,也就是读人类历史中最美好的一个方面,使我们学习到人类努力的连续性和科学与智慧的传统,从而得到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新人文主义[9]168。这就意味着科学史能使科学人性化。科学绝不是单纯的,与社会现实无关的,它总体现着人类不断探索周围环境及人自身的努力。科学史表明: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开展,总是与人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它总是证明着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自我的能力。因此,从科学史上看,人文与科学是不可分的。
如前所述,从人类思想史来看,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是一种自由的学问,一种近乎自由的探讨,其本身所包含的功利因素是单维的,即为了自身的生存。这种将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其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文与科学是密切联系的。自文艺复兴始,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科学研究自身的功利性逐渐增强,无功利性的自由探讨让位于利益的获取。这时,人文与科学之间出现裂痕。当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更多以技术的形式,呈现出实用的功利目的。实用或有用成为衡量科学存在的重要现实依据。科学所强调的理性,已经放弃对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探索,而转向以实用为目的技术。科学沦为一种实用工具。古希腊时期倡导的理性转化为一种工具理性。“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它只讲事实理性不讲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目的理性。…… 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也是胡塞尔所谓危机的表现”[7]39。爱因斯坦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道:“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10]12。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这时的科学哲学认为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而认为场域的不同,科学方法的运用也就不同),新浪漫主义对科学的批判,环保主义对科学的责难,反科学至上的浪潮开始此起彼伏。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解构,“科学终结论”的反复响起,为反思科学,重新确立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冲击下,在由知识科学观转向智慧科学观的背景下,各种观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复杂的变化。从反科学与科学相互颉颃的视角出发,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流和融合”[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