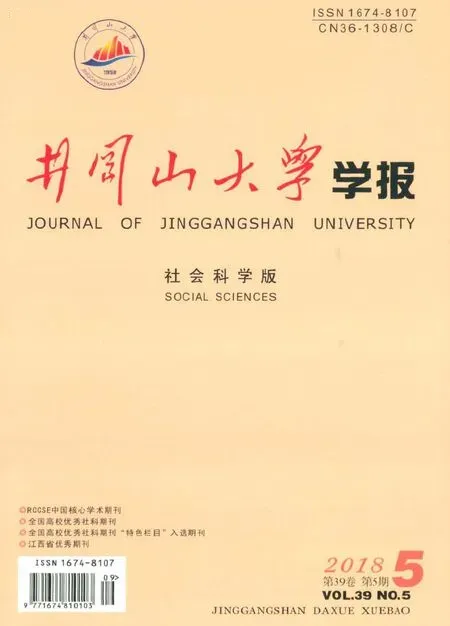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发展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
张瑞岚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政治发展理论,并由此开始在学术层面使用政治发展的概念。较之于西方政治学家,马克思更早地使用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自始至终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和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发展基本原理中所蕴涵的当代价值和智慧火花,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及政治发展的初衷
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逐渐由法国转移到德国。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逐步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1843年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登记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黑格尔哲学批评〉导言》和《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三篇文章论及了政治发展的概念。
1842年,马克思针对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自由问题撰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登记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撰写不早于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月26日写成。文中,马克思首次提及了“政治发展”:“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够资格的作者’。17世纪和18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等等以及大学的平庸作者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烦琐的咬文嚼字的学位论文站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中间。我国的著作业是由那些不够资格的作者创立的。 ”[1](P196-197)马克思认为,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和等级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下,滋生出不够资格的作者无法实现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共通共融,遂导致政治发展缓慢。换言之,德国政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人被限制了政治自由。只有人获得自由才能实现德国的政治发展。
1843年4月因《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在恩格斯、赫斯等人的支持下,又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在上面发表了三封信和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是其中的一篇。文中,马克思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囿于资产阶级立场未能超越“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社会目标,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实现“人的解放”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在涉及到政治发展一段文字中,马克思提出,如果德国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会像俄国人一样低。人是国家的基本构成单元。单纯的政治发展并不能代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等全面发展。德国革命的前景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的解放,而不仅仅是人的政治发展 (解放),否则国家依旧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同时代共进步、同发展。
几乎与马克思同一时间,恩格斯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也提到了政治发展的概念。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因从事商务移居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的21个月时间里,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就是恩格斯向民众介绍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重要著作。在文中,恩格斯以法国为例,认为政治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改革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经过怎样的政治发展形式,都必然要汇聚到共产主义。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即是实现共产主义。五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共同向世界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新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全部的奋斗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言以蔽之,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上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入阐释的。在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涵。他认为,“人的解放”将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使人自身的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并同自身相分离。[2](P46)这就意味着,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发展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最终努力使得产生于社会但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政治权力或曰公共权力)重新还归社会,不再构成超脱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条件。在以后的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不同场合直接提及政治发展概念至少达8次。①据笔者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初步统计。正如这些最开始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将政治发展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把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在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进行总体考察的时候,科学地揭示了内含其中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政治发展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也在避免做这种超前的详尽规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3](P458)“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 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4](P274)在关于政治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了关于政治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一般原理。这些思想内含于唯物史观之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和科学体系。归结起来主要有:
第一,政治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泌到密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5](P7)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满足人的向往和需求的过程。而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是人在社会中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则是一个由社会进步所逐渐积累起来的过程,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关系和各种过程相互连接、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要素随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并随人类文明进程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总有一天……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6](P198)人类文明将推动产生于社会但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重新归还社会,从而使得人与社会和谐共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社会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将以此为最终奋斗目标,政治发展同样如此。
第二,在实现最高理想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贡献在于推动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其一,政治发展的动力根源于经济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7](P591)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必然会对生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构成新的政治发展的动因。其二,政治发展的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就总体趋势而言,在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政治发展要依据经济发展不断做出调整,自觉地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政治发展应遵循经济的原则,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而不是消耗在政治发展和行政运转本身。就某一历史阶段而论,政治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加速或延缓两方面。“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4](P110)政治发展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轨迹。 当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指政治发展,笔者注)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3](P597)也就是说,当政治发展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反之,经济发展就会放缓甚至引发社会倒退。最后,政治发展的途径是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当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与环节,并可以通过政治体系的局部量变调整这种适应性的时候,政治发展会以政治改革的形式对政权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进行系统、深刻的革新。这种革新以不破坏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前提,谋求政治体制的调整与革新,提高和完善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实际效能,以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但是,当政治秩序不再具有这种历史合理性的时候,政治最终会在经济的压力下被迫做出反应。这种情况下,现有政治无论如何调整都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于是以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政治制度彻底变更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就成为政治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反应和唯一途径。
第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足以实现最高理想之后,政治发展将会走向消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中,经济特征表现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使得产生剥削阶级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将消灭;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相应地,政治上,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它的社会职能已经失去其阶级性质,政治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换言之,政治最终将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而走向消亡。对此,恩格斯断言:“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6](P597)
三、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发展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凡属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或词句,都既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又同样属于当代,具有当代价值。”[8]当前,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发展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应该是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上讲,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前,政治发展的任务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政治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阶级、国家的消失而消亡。马克思的《政治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充分论证了国家和公共权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们认为,政治是伴随阶级分裂、国家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社会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9](P563)到那时阶级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作为阶级对立不可调和产物的国家,和随国家产生而形成的政治也将自然而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阶级和国家的存在使得政治发展的任务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从现实来说,建立在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发展的任务尤为繁重。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在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取得胜利的。这样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还不够坚固,封建残余思想仍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的环节等,这些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逐步予以解决。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即使社会基本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政治上层建筑也还存在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或环节。这些方面或环节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来逐步地加以克服和解决。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它还不很完善,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现行的基本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调整和革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道路。原有体制的“硬核”部分,即政治体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体制改革等深水区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却始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0](P78)政治体制改革是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通过调整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治环节,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这种改革是以不破坏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前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我革新。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使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积极能量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通过自身发展逐步实现政治反哺经济,公共权利回归社会,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最终奔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前途。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同经济、文化等基本要素一样,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力量。在这些基本要素之中,其决定作用的依然是经济因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人们所进行的物质生产都是社会生产,因此,在这种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这种社会关系必然要反映为阶级关系,从而决定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当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整个政治结构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必须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 ”[11](P806)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的有效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改革不仅仅是政治发展的独善其身,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实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社会权利而不再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居于人和社会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言,“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12](P195)。 因此,“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12](P2542)政治发展应该不止于维持政治和行政运转,而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中,使发展的成果惠及经济、社会,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国家党、政、军、群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主要是: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设置、职责划分、机构编制不够科学,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有待完善;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群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事业单位定位、职能、效率等有待提高。这些问题,必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抓紧解决。
当前,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与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进行的7次机构改革相比,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绘就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蓝图更加系统、更加全面,不仅阐述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首要任务和重要任务,而且明确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等重要内容,对于构建简约高效的党政军群体制,推动高质量政治经济资源配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水平的一场深刻变革。可以预期,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这场深刻变革将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