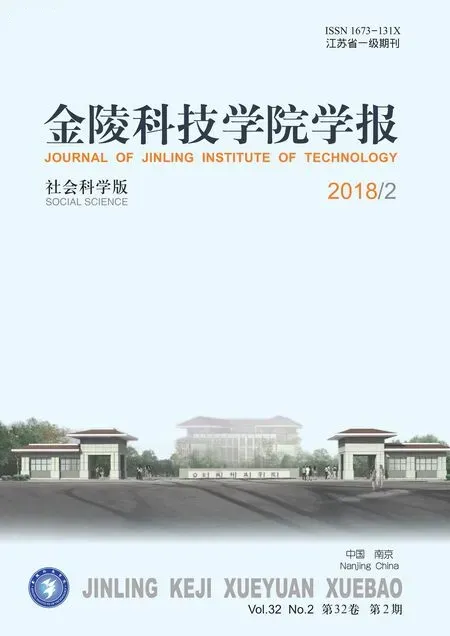农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再造
——基于河南省Z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的实践
武俊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公共文化服务”概念。《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7年,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文化领域内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时隔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日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农村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场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使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处境颇为尴尬,传统文化式微、人才流失、“撤点并校”政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等,皆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虽然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了支持的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成效却不理想。因此,有必要检视当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思路,再造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
一、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与反思
根据现有文献可知: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最显著的问题是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农民沦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他者”[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过于强调标准化、均等化,忽略了文化、族群及地域差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政策难以落地生根,形成“悬浮化”现象[2]。从本源看,缺乏视角(lackperspective)即看待与分析问题时常常过于关注不足和缺陷,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影响较大[3]。该视角指导下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者或研究者多关注如农村人口素质低下、农村文化落后、基础设施缺乏、资源不足等问题,加之多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其核心在于“送”,这虽然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但也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求错位,难以由“文化下乡”转化为“文化在乡”。农民成为文化权益的被动享受者,其作为公共文化建设主体的自主性价值却一直被忽视[4]。
文化志愿服务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人民群众自我创造、自我参与、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群众基础”[5]。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农民的主体性得以回归。因为农民更了解本土文化,对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更有话语权。本文以河南省Z村的文化志愿行动为例,解析Z村民众如何通过个体生命治理、集体增能、社区赋权来实现村落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再造。
二、河南Z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实践图景
Z村位于河南省北部山区,经济较为落后,村民比较贫困。2003年以来,为了生存村里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基本是老人和妇女,因而该村逐渐成为空心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空心村里发展出了本土的深入人心的公共文化服务,究其原因,是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有效互动的结果。
(一)外力介入——H机构的催化作用
H机构*H机构成立于1998年,其致力于社区教育,成员具有社会学、女性学、人类学、历史学背景,同时具有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长期关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多次到Z村所属的郑州市开展以“社会性别与发展”为主题的培训,并开展以推动农村妇女发展为目标的专题调研。H机构发现,Z村仍保留有传统的织布绣花手工艺技术,村中有31名中青年女性擅长此艺。郑州旅游资源丰富,如果能组织Z村妇女制作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那么既有利于中原地区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传承,又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实现经济赋权。在H机构的推动下,Z村成立了手工艺协会,致力于开发妇女手工艺品,增强妇女生存能力,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妇女参与社区事务。为了提高手工艺品设计能力,H机构邀请了香港慈善社群艺术机构的专家为手工艺协会举办工作坊,激发会员的设计灵感。手工艺协会会员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既有旅游性手工艺品、收藏性手工艺品,也有实用性手工艺品、公益性手工艺品。Z村的手工艺品开发制作先后经历了个人生产、小组生产、集体生产3个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妇女们扶助弱势群体,互助合作,共同发展,提升了合作意识,重新认识了自我价值。在村民和H机构的共同努力下,“Z村巧女”手工艺被认定为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一起制作手工艺品外,手工艺协会会员还一起编排“巧女秧歌”,使没有手工艺技术的妇女也能参与其中。“巧女秧歌”受邀参加各种乡村文化展演活动,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手工艺协会会员也逐渐成为Z村最早的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
H机构是非营利组织。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非营利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因非营利组织关注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故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容易获得弱势群体的信任与好感;因其能够深入农村,能为村民解读政策和传递信息,故其具备沟通优势;因其具有良好的工作弹性,非营利组织介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衍生出了多需求满足优势和效率优势[6]。作为外来力量,H机构将自身定位为协助者、信息提供者和资源整合者,而非指导者或服务者,他们将所开展的项目与工作嵌入村民生活及文化系统,激发并尊重村民的创造精神,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将“送文化”与“种文化”结合起来。H机构以文化为媒介介入Z村,既改善了村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又推动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同时催生了第一批本土文化服务志愿者。
(二)力量内生——Z村公共文化服务志愿力量的形成
在外来力量——H机构的推动下,手工艺协会会员成为Z村首批文化服务志愿者,会员借助手工艺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借集体的力量发声。在我国中原地区的农村,无论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上,还是在村规民约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手工艺协会会员在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逐渐增强了性别平等意识,个体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挑战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及行为。2010年,手工艺协会会员基于真实的故事,自编自导戏剧《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倡导民众改变传统观念,给予女性和女童公平的发展空间。在手工艺协会的示范和引领下,Z村先后成立了艺术协会、老年协会、常青互助会、“青青草”志愿小组,这些组织分工合作,共同建立起村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艺术协会致力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其开展的活动有三类:日常文娱活动(跳舞、唱歌等);参与节庆活动,推动民俗的变革;借助民众戏剧开展社区教育。尤其第三类活动影响较为深远。民众戏剧的编排及演出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通过戏剧表演,村民将自己的生活、心声与需求真实地呈现给观众,不仅演员在演出中能接受教育,而且观众也能获得正向影响。
老人是社区的资源和财富,老年组织是实现老有所为的载体。Z村老年协会会员凭借其威望和经验,有效推动了本村的文化建设,例如:进行社区探访,搜集社区资料,记录社区历史,使年轻一代了解自己的社区;参与调解民间纠纷,主持新式民俗事务。常青互助会的工作由手工艺协会和老年协会共同承担,其旨在促进村庄互助合作,重建守望相助的良好人际关系。常青互助会发动村民整修废弃的窑洞,打造出留存村庄记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
“青青草”志愿小组由有一定文化的中青年妇女组成。该小组针对在外求学的中小学生开展周末成长营、暑期夏令营等活动,组织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重建青少年学生与乡土的联系,使其建立起对家乡的文化自信。“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使村落失去了重要的文化空间,也给学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孩子们被迫早早离开家庭,寄宿于学校,寄宿制使孩子游离于家庭之外,导致儿童成长中家庭教育的缺位;孩子们与自然环境疏远,与乡土疏离;孩子们无视村落礼俗,渐失家乡情感和文化自信[7]。“青青草”志愿小组通过挖掘本土内生性教育资源,将孩子们的身心从“单一化的应试教育”和“单向度的城市教育”带回村落的自然场景教学中,重建其与家乡的亲密关系。
Z村文化志愿服务力量的形成,经历了从外力催化到内力聚生的过程。H机构作为外来力量介入乡村文化建设,通过社区教育和引导村民的自组织建设,引发了村民公共意识的觉醒,成为村落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形成的内在动力;村民的自组织建设使分散的个体聚合成网络,村民间的互动不断增强,个体觉醒的公共意识逐渐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力量。
三、Z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主体的再造
(一)个体生命治理
个体生命治理就是“从内心深处唤醒行动者,使其行动的力量得以复归,使其真正参与到改变自身环境的过程中,从边缘走向中心”[8]。Z村手工艺协会会员是最早的文化志愿服务骨干力量,但在村落里她们并不是“精英”,而是普通一员。她们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里做针线活,大多数人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在H机构调研Z村传统手工艺时,这些技艺超群的“巧女”被央求许久才怯怯地拿出自己的绣品。在组建手工艺协会时,曾经比较怯懦的秀*根据研究惯例,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高票当选手工艺协会会长,在工作中她逐渐变得沉着果敢。在Z村还有很多像秀一样的妇女,她们被父权、男权文化所塑形,陷入贬抑与自我贬抑怪圈。H机构介入后,其以传统手工艺为媒介,开启了Z村妇女的个体生命治理之路:通过开发手工艺品,实现经济赋权;随时随地参与式培训,促进其意识觉醒,互助合作、扶助弱势群体、共同发展等理念深入人心;公益性产品的生产,促进其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促进其主体性意识的持续增强。在这些文化活动中,Z村妇女看见了自我的力量,重建起自我形象,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治理。
(二)集体增能
集体增能即通过成员间的互助合作,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发展社会资本,提高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而增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近年来,农村居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强烈的“组织起来”的愿望并开始付诸实际行动。村民在集体交往中,通过合作与相互间的支持,获得了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正是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Z村地处山区,水源缺乏,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与男性相比,妇女获得学习以及改善生活的机会比较少。手工艺协会使Z村妇女走到一起,在制作手工艺品的互助合作中,她们不断学习、交流和思考,深刻认识到集体的力量以及平等互助、尊重支持、互利共享的重要性。通过参加手工艺协会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Z村妇女实现了集体增能,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
(三)社区赋权
我国乡村一直有守望相助的良好传统,村庄既是村民情感相系的共同体,也是他们参与村庄事务的平台,而文化建设正是村庄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村庄文化设施和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中,应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Z村有悠久的穴居文化,背靠黄土,筑窑而居。近年来,Z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村民纷纷住进宽敞明亮的平房或楼房。因此,在Z村随处可见废弃的窑洞,而这些窑洞却是Z村穴居文化的外在体现。为了留住村庄的历史记忆,建设有“温度”的乡村,同时也为了探究窑洞文化内涵,保护文化遗产,进而增强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尊重感,Z村村民、H机构、SZ大学专业设计团队在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支持下,启动了“老窑新生”建设项目,致力于打造具有Z村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项目建设采用参与式设计理念,尊重当地建筑经验,使用的建筑材料也全部是村民家里闲置的废旧材料。通过社区赋权,村民成为“老窑新生”项目建设的主体,在参与项目建设中,村民增强了对村庄的历史文化记忆。
四、结语
Z村通过个体生命治理,使村民重塑了生命并掌控了命运,使个体实现了社会价值;成员间的互助合作使社会支持网络得以构建,个体的生存发展能力获得了进一步提升,村民实现了集体增能;通过社区赋权,村民以主人的身份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社区文化建设者和文化服务志愿者。在Z村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再造过程中,H机构从推动村庄公共文化建设入手,引导村民逐渐成为村庄文化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村民在村庄事务的处理上也逐渐敢于发声,敢于付诸行动。通过外力介入和力量内生,Z村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得以再造。Z村的实践值得其他村落借鉴。现阶段,我国农村应抓住政府大力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契机,重建既尊重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村文化,再造农村文化志愿服务主体。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扶助外,还要广泛发动在地民众参与本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引导村民真正成为农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