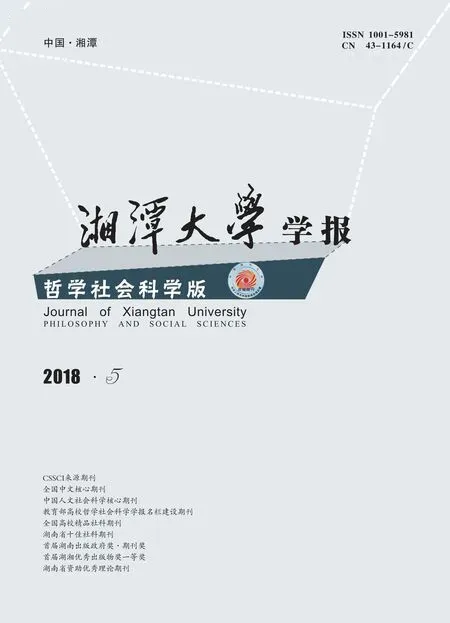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
胡慧娥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魏源一生对传统政治文化有深刻体察,其读书范围甚广,生平著述涉及经、史、子、集等诸多领域,他又深具经世情怀,其学术探究与理论思考大多会落实到政治层面,他对天道观、王道之治、法治理念以及民本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均有深入论述,有传承,亦有超越,形成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系统认知。
一、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在中国传统社会,鬼神观念亘古就有,早在商朝,“殷人尚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等理念就已载于典册,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又逐渐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或理解“天”,将“天” 的运行变化视为一种规律,及至春秋末年,自然天道观已经完全形成,其所突出和强调的就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或规律,但这种“天道观”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干预人事的职能[1]55,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以“天道”来参照人事,于政治统治中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魏源对这一理念有高度关注,他主要是从天命观、幽明观以及忧患观等三个角度来进行认知的,大致而言,魏源认为天命观、幽明观是“神道设教”的两种重要形式,而忧患意识则是尊崇“神道”、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的根本途径。
1.天命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权力自我警示
魏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天命观的政治文化内涵,一是认为天命观可以解释政权兴亡之因,二是能以此为所有在位者提供警示。
他曾用天道、天命观分析夏朝国祚短于周朝的原因,其论曰:“唐、虞均一世尚不能下逮,何况世德作求?天之报圣人者或不在是。抑或契至成汤十四世而后王,稷至太王千余岁,数十世而周始兴,兴愈迟者阼愈久。”[2]156他认为夏朝自少康以后并无贤圣之君,亦无“卜世七百年之阼”,反不如商、周者,原因不在于天之不报禹之圣功,而是天道早有安排,以使“兴愈迟者阼愈久”,尽管他申明“天道不可得闻,姑存其说”,但其“尊崇天道”的用意甚明。他又曾辑《汤誓佚文》,详细阐释汤伐夏的理由:“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罪“致天之罚……”[2]163—164。魏源认为此篇“三举天命以誓众,明誓在告天之后”,充分表明他认可汤兴夏亡是天命所归。他还以“天意”解释商朝衰亡之因,以为高宗长子先其而卒,故高宗逝后次子祖庚继立,“乃祖庚享国不永而卒,传及于祖甲,以淫乱衰国祚。此殷家兄弟世及之常,高宗所不及豫料,殆若有天意焉。……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乌乎!天胤典祀,敢不战战兢兢哉!”[2]173将商代自高宗后由盛而衰之历史迹象归之于“天意”,认为“天胤典祀”,须时刻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这是畏天命的直接体现。
魏源对周公制礼作乐之圣功极为肯定,以为周公实际是为周之合法性立言,亦是为万世王权政治立言。他说:“盖文王我师,周公所自道。然其意以为文王者,非独吾子孙之师,亦天下百世人人所宜师也。人知文王之圣而不知其所以圣。知父者莫若子,故本其继志述事之心,制为礼乐,播诸天下。若曰:吾父之化乎闺门者,固如此也;其亲贤体下,极其诚敬者,固如是也。又精揭其配天无二之德,以告天下之为人君者。若曰:我周之所以王者,盖非偶然也……”[3]5
魏源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慎终追远,尊祀文王,即是要论证周之得天下有其必然性,是文王“配天无二之德”所致。以后为人君者,若要建立巩固的政权,必须以文王之德为标准,否则其政权之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嗣王怠政”,大臣就要“咏《关雎》以讽”,如果“上不好贤”,大夫就应“弦《鹿鸣》以刺”[3]5,人君要有配天之德,才能得天下。周公制礼作乐,是为周之得天下之正立言,更是为后世人君立下祖法宪章。
除了以天命观解释政权兴亡之因外,魏源还认为“天命”可为当权者提供警示。他晚年著《元史新编》,详载元太祖成吉思汗止兵印度及不久后下“止杀”令之事,认为是受天命警示所为:“(十九年甲申,夏)帝征西军既平西契丹,将往征印度,进至北印度之铁门,遇异兽,一角,能人言,曰:‘天道好生,人主宜早还。’帝曰:‘印度乃自古神圣所降之地,今遇此,其天乎!’遂班师。……(冬十一月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帝自西域遇角端,已思止杀。至是,感五星之祥,又得耶律楚材及真人丘处机之劝,乃下诏止杀。”[4]20—22以神兽出现而止兵,是对天道有敬畏之心,以五星祥瑞而止杀,是对天命存感恩之心,可见魏源之意是借“天命”为最高王权设置一条警戒线,以防止权力滥用。魏源著述中对天命警示作用的阐发还有很多,兹不赘述。[注]如《圣武记》中载雍正第二次征厄鲁特事,誓师时“大雨如注,旌纛皆湿,识者以为不祥”,后几经波折才平定此乱,魏源对大学士张廷玉“力赞用兵”之举颇为不满,在《事功杂述》篇中仍有微词,认为“张廷玉力主出师,荐傅尔丹为帅而败,此不当进而进者”。其实借天象以示“不祥”只是幌子,内中含义则是天时人事未至,不宜出兵。参阅《魏源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8页。
魏源肯定“神道设教”之功用,并不惟就天命的最高审判来谈,他亦提到幽明的观念,即须崇祀祖先,敬畏鬼神,这也是传统社会里儒家政治文化中倡导“慎终追远”的理念,但魏源把幽明观与王教政治直接相联系,作出了比较深入的阐述。
2.幽明观:鬼神之说,阴辅王教者甚大
魏源认为天命观可以为政权合法性张目,并为统治者提供警戒,而幽明观则可使统治者常怀敬畏之心,推行仁爱之政,也能为百姓祭祖祀亲提供理念支撑,故有再三致意。
魏源曾批驳俗世所言“两不朽”之说。一则曰“儒以名教为宗”,但魏源认为“时愈古则传愈少,其与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所以名教难与天地同不朽。另一“不朽”是指子孙薪传,以为“宗庙享保,气降馨香;虚墓知哀,魂魄旁皇”,但魏源认为子孙祭祀宗庙无须就“虚墓知哀”,因为“骨肉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他将鬼神之魂气视为可以流转于天地之间的事物,则“祭祖祀亲”随地可行,而其警示作用亦当无处不在。故他又说:“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5]3魏源明确提出阴教有益于人心,能使王法不及惩罚之人,以阴教震慑之。同时他从反面批判后儒无鬼之说,认为“无鬼非圣人宗庙祭祀之教,徒使小人为恶无忌惮,……孟子辟墨,止辟其薄葬、短丧、爱无差等,而未尝一言及于明鬼、非乐、节用、止攻”。[5]4在魏源看来,儒家推崇宗庙祭祀,墨家倡言天志、明鬼,都是有深刻用意的,鬼神观念,对于政治教化不无裨益。
从魏源对天命观、幽明观的认知,可看出其不仅关注“神道”能预测吉凶祸福,更重视“神道”于是非善恶伦理观中的警示作用。然而,他并未完全局限于这种“神道”之影响,而又提出“造命”“立命”君子之说,认为命运并不能决定一切,人可以摆脱命运的安排:“命所不能拘者三,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忿山欲壑,立乎岩墙,‘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此恃命之小人,非命所拘者乎?诚知足,天不能贫;诚无求,天不能贱;诚外形骸,天不能病;诚身任天下万世,天不能绝。……命当富而一介不取,命当贵而三公不易,命当寿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匹夫确然其志,天子不能与之富,上帝不能使之寿,此立命之君子,岂命所拘者乎?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5]20—21这三种人,除第一种是“恃命之小人”,魏源给予极力批判外,其余两者均以“君子”褒之,一为“立命”之君子,一为“造命”之君子。特别是“造命”君子相信“人定胜天”,通过自身的努力,排除万难,可以扭转命运的安排,使“贫贱夭”能转为“贵富寿”,“祈天永命,造化自我”,如果得遇机缘,必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的确是天命限制不了的。
魏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天命”“幽明”等神道思想的局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除了上述对“立命君子”“造命君子”的肯定外,他还相信忠臣义士可以在承平之世执“人定胜天”之理念[6]539,所谓“天之未定则人胜天”[5]76。事实上他自己实践得更多的正是这一积极思想,加上他还时刻存有心忧天下的忧患观,所以才会在著书行事中彰显经世理念。
3.忧患观:常怀忧惧之心,何患不与天合一?
魏源对天命、幽明观念作了深入探究,主张敬畏天命、尊祀鬼神,其目的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因之,魏源大力发扬了自古就有的“忧患观”,以为常怀忧惧之心,“何患不与天合一”[5]19?他提出忧患意识必须贯注为学、为人、为治等各个方面,是对传统忧患观的进一步弘扬。
首先,魏源认为学问之道须于艰难困苦中不懈探求。他指出:“学问之道,其得之不难者,失之必易;惟艰难以得之者,斯能兢业以守之。”[5]18为学治学须有坚毅不拔、勇于探索之精神,只有勤奋刻苦,反复琢磨,才可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著《诗古微》始于道光二年(1822年)左右,至咸丰五年(1855年)还在修订[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诗古微》序后夹有一张纸笺,是魏源亲笔所写的“识语”,落款时间为咸丰五年。参阅夏剑钦:《杰出的思想家魏源》,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38页。,绵延数十年,他相信《论语》所说之为学之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治《诗经》的经验是“积久豁然,全经一贯”,“愤、悱、启、发之功也,举一反三之功也”,他能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与《毛》诗相互比照,从而“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所下功夫是可以想见的。故魏源大发感慨:“学问之道,固不可浅遇而可深逢者也。”[5]117
其次,魏源主张人生亦须常怀忧患意识,他倡言:“圣人之道,不在豪放高远,而在枯槁寂寞之中”,在“先忧后乐”之执着追求上。他认为人的忧患意识应体现在日常的德行修养中,要能耐住寂寞,于艰难困苦中亦能自得其乐。他说:君子能“耕苍莽之野,钓寂寞之滨,而乐尧、舜之道焉,故可以达,可以穷,可以夷狄患难。故颜回、禹、稷同道”,并引《诗经》语:“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他认为这就是“先忧后乐”的道理。[5]19他还强调“人必有终身之忧,而后能有不改之乐”,又说:“所忧生于所苦。不苦行险,不知居易之乐也;不苦嗜欲,不知淡泊之乐也;……君子以道为乐,则但见欲之苦焉;小人以欲为乐,则但见道之苦焉。欲求孔、颜之所乐,先求孔、颜之所苦。”[5]24魏源之意是人只有先品尝苦境、遭遇逆境,方能知晓顺境、快乐的滋味,而人若能减少欲望甚至达到无欲的境界,则能如圣人般虽处苦境,犹甘之如饴,亦会时刻有快乐自在之体验,这就是他所持君子之忧患观、苦乐观的日常体现,其实也是魏源倡导的基本人生观。
当然,魏源最关注的还是为政者须有忧患意识。他年轻时即作诗云:“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5]501认为六经是贯注忧患意识的经典。[注]此诗约作于嘉庆二十四年,时魏源26岁,参阅熊焰:《魏源年谱新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又说:“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古圣先贤发愤求学,日夜忧思,就是唯恐天下不治,“故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5]9圣人常具忧患精神,才会有紧迫感,责任感,为了求治天下,懂得珍惜时日。魏源还强调:“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思乱。……即无良之人,有不恐惧修省者乎?”战乱起,就知太平之世的难得,生病了,就知健康的重要,君子总能居安思危,虽治思乱,时刻保持警惕,如《诗经》所言:“敬天之怒,无敢戏豫。”(《诗经·大雅·板》)“人心能常如洊雷震罅之时,何患不与天合一?”[5]19对上天常怀敬畏之心,对天下常存忧患情怀,方能领略“天人合一”之境界。
以上是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天道观”的深入考察与认知,他承继了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认为尊崇天命、敬畏鬼神有助于为政,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忧患意识。他虽关注“神道设教”的政治功用,然并未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倡言“造命”君子、“立命”君子,在“天未定”时坚持“人定胜天”的理念。在此基础上,魏源进一步考察传统社会“人道设教”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提出了以德治国、重现王道之治的理念,又主张重法行法,倡导治法与治人兼备,对于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理念——民本思想,他亦有深入思考,有些理念已明显带有近代启蒙色彩,以下将分而述之。
二、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以德化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大特征,“三代之治”所以始终为世人所称颂,就在于其体现的是“王道”政治。魏源一生所追求的亦是“王道”理想之治,他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王道有近功,并对王道实施主体“圣君贤臣”的执政素养作了严密规范,其关切点基本指向当政者的道德规范与治理功效。
1.王道纯出乎道德
魏源提出:“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5]36,即认为只要内心纯出乎道德,政治意图是善,则事功无分南北,为政才可称为“王者之治”。他还说:“事功纯乎道德,……礼乐兵刑出于喜怒哀乐,……然后一怒而安天下之民。”[5]39魏源对商汤伐桀、周武伐纣等“安民”之举非常赞许,对元代、清代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之事亦无不肯定[注]魏源著《圣武记》《元史新编》,对两朝之武功盛事,尤其是建立统一政权、开疆拓土、维护边疆稳定等史事给予相当的肯定。,其中或许有为当政立言的意图,但他以为建立统一政权,结束纷争混乱的局面,使百姓重新过上安稳生活,这即是王者之德。他强调:“礼乐胜则纯乎道德,如春风之长万物而不知。……甚哉功利之殃人,而王道不可一日熄乎!……夫惟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5]43—44只有使势、利、名都以道德为纯粹的出发点,才能真正建立王者之治,也才能达到平天下的目的。魏源再三感叹“纯粹道德”对于构建王道政治的重要性,表明他对王者之德的高度重视。
2.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嘉道时期,国势渐渐由盛而衰,社会弊病丛生,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复古”“尊古”[注]如阮元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陶澍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龚自珍自称“药方只贩古时丹”,汤鹏提出“则古尚变”,说明嘉道士人“复古则古以求变”之风渐成气候。,实际上是以复古之名,行变易改革之实,以期重现王道理想之治,魏源的改革复古思想亦很强烈。
他提出王道应学古,“三代以上之天下,礼乐而已;三代以下之天下,赋役而已”,“甚哉功利之殃人,而王道不可一日熄”[5]43—44,其对三代仁治社会之赞赏由此可见。他于道光二年(1822年)在顺天乡试墨卷答“居之无倦”二句题时,曾主张为政要以古、以常:“……善为政者,始之以古,终之以古,政乃攸处;表之以常,衷之以常,政乃攸行。”[注]道光二年默深顺天乡试墨卷全文,可参阅熊焰:《魏源年谱新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0页。魏源之意是为政从始至终都要学古,才能兢兢业业,不会生倦怠之心;同时也要遵循常理、常规,依法办事,才能忠实地执行各项政令。魏源好古之意,在其《诗古微》《书古微》中亦有深刻体现,他著《诗古微》,即是要“由古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此鲁一变至道也”。[7]878著《书古微》,亦是同理,欲“阐西汉伏、孔、欧阳、夏侯之幽,使绝学复光大于世”,“鲁一变至道”。[2]111此“至道”从政治文化上讲,即指上古“王道”政治无疑。魏源所倡之“学古”,落到社会层面,其实就是看到了现实政治的弊病,而主张变易改革。他曾参与漕运、河工、盐政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实践,并撰写了大量总结改革经验的时文,在鸦片战争后他最先提出系统的“师夷”思想,充分表明了他在“学古”旗帜下对求变求新理念的具体思考。
3.王道有近功
魏源在崇德、学古的基础上又提出王道有近功说。他认为孟子严分王伯、义利之辩,并非完全摈弃功用,而是认为实行王道,自会达致富强之效,所谓“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后儒则误会孟子,不解古圣人之意,“以兵食归之五霸,讳而不言”,一味“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若此只会造就腐儒,其“无用亦同于异端”。[5]36所以,“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治民。非令下如流水之原,不可为善政;非立效如时雨之降,不可以为圣功。……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5]40这就是说,王者能审时度势,掌握大政要领,出台适时之政策,其他百事尽可付诸臣子去办理,王者“垂手拱治”可也,功效自成。他又言:“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5]36因此,魏源以为王道必然有用,王道必然有近功。
4.王道实施主体:圣君贤相
魏源既以王道仁政为统治者应有之施政纲领,又以“学古”之名,而倡改革之实,注重治理之功效,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将希望重点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强调王道实施的主体必须是圣君贤相,就是很自然的了。魏源认为人君要能成为“圣王”,大臣要能成为“贤相”,均须在四个方面锤炼行政素养,即修德、用人、勤政、善断。
如前所述,魏源首先重视人主大臣的德性修养,他说:“同言而人信,信在言前;同令而民从,从在令外。……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故行修于一乡者乡必崇,德昭于一国者国必宗,道高于一世者世必景从。”[5]7—8同样的话人们相信你,是因你已立信于民,同样的命令人们服从你,是因你早已立威于外。自身无德,即使口吐莲花,句句经典,也不会取信于世;即使一切因袭古制,也不会感动民众。故以德行于一乡,则一乡能得善治而受人崇仰,以德治理一国,则一国之人都会以你为宗,而以道行于一世者,则一世之人都会紧紧追随你。君主之德行威信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法宝。
魏源又提出:“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人主不能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否则会导致心力交瘁,而百事皆荒,如此,就需要有一批能臣干将辅佐政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魏源认为人主谦卑、宽容可以得人。“惟人君不以高危自处,而以谦卑育物为心,人人得而亲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给之。……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5]57人主能以谦卑之心待人育物,虚心求才,则人才自会接踵而出。魏源还强调人主须心胸广阔,他曾引陆贽的话赞武则天“以宽得人”,同时褒扬庆历之宽政,认为“宋庆历中培养之人材,数世用之不尽”。[5]57
人主既须着力于培养人才,同时还要善于识人、用人。识人之标准,要看其是否懂道德、知廉耻,是否能做到“大德不逾闲以为本”,还要看其是否有济人利物之心。[5]62
关于用人,魏源更有干城、腹心之辨,才臣、能臣之别,还有大猷、远猷、壮猷之异[5]52—56,总之人各有才,人主要善于发挥其长处,使人尽其才,即使是小人,魏源也认为有可取之处,他说:“天下小人不可尽诛,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止可驱策于边疆而不可用于腹心密勿之地。”[5]56不唯如此,魏源对自己最为痛恨之乡愿,在用世方面亦有两说:“有不可临大节而可佐承平之乡愿,孔光、冯道、范质,平时不失为贤相”,认为孔光、冯道、范质之流虽大节有亏,但其才可当承平之贤相。魏源认为人主要能洞烛忠奸,对于小人中有才而德稍差者,只要其能坚持道德底线,则可因才为用,将其用于边疆之地,甚或可以用为干城,人主须特别防范的是身边之有才无德之“鄙夫”[5]65,是为“毗阴之小人”[5]61,这种人只会惑主乱政,须加以远离或清除。
魏源还提出人主须“勤政”,在位者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励精图治,以“使民无事”,使天下太平,因此,“尧步、舜趋、禹驰、汤骤,世愈降则愈劳。”《诗》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是以夙夜匪懈,山甫之佐中兴;夙兴夜寐,卫武之相王室。”[5]41
魏源曾著《老子本义》,肯定黄、老“无为思想可治天下”[5]230,《默觚》中亦有文称“主好要而百事详”,言人主应抓大放小,垂拱而治,此处又言“勤政”,是否矛盾冲突呢?其实不然。黄、老“无为思想”能有治天下之效,往往是在改朝换代或历经大变之际,如魏源所言,“秦汤方燠,九州为炉,故汉初曹参、盖公沐之清风而清静以治”。而在承平日久之世,则须矫正各种荒政积习,当然只能“勤政”,否则,“以清谭清静为无事,有不转多事者乎?”[5]41终日无事,必会导致矛盾丛生,而转成“多事”之秋。
人君能做到修德、善于用人以及勤政的话,也自能具备善断之素养,所以魏源讲人主“当以达聪为独断,而不以臆决为独断也”[5]51,希望人主能善于乾纲独断,不胡乱施政,又说人主应“赏罚于众人所及见”,“令下如流水”,即“可为善政”[5]40,都是强调人君要善断如流,能赏罚分明。此点魏源在《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亦有反复说明,《圣武记》中对前期开创龙兴之圣君亲临战事、指挥若定、所向披靡之情势多有赞誉,对康、雍、乾等圣主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荡平多起叛乱之事亦颇为称许;反之,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对道光帝优柔寡断的品性颇有微词,视此为鸦片战争失败受辱的重要原因。
魏源重提王道之治,又期望圣君贤相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其承继“师儒”关注时政的政治主体性人格,也是其对政治建设仍具信心的表征,他是一位积极用世的儒者,绝非一般腐儒、庸儒可比。
三、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传统社会倡导以德治国,虽也有过短暂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但因理论上的局限性,始终未能做到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注]费孝通曾指出:在秦朝统一中国以前,确实曾有些人想要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这是受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一学派提出的体系是好的,……作为秦国宰相的商鞅试图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可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有一点小小的疏忽——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法律之内,那就是天子。这留在法律体系之外的一个人却把法家的整个体系废黜了。参阅费孝通著,赵旭东、秦志杰译:《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历史的真实情形如荀子所言: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魏源对传统法治观念有深刻的认知,有学者曾就其法治思想或法律思想作过一定的探讨[注]参阅胡峻:《魏源的法治观及其评述》,《船山学刊》2001年第3期;魏昕:《论魏源的法治思想》,《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0月;沈大明:《魏源变革清代法制的思想》,《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章平:《魏源的法律思想》,湘潭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曹文泽:《魏源的法治思想与时代价值》,《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7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魏源对法的思考,笔者以为魏源不仅有重法理念,且他主张治法与治人必须兼备。
1.法之功用:法令,治之具
首先,魏源对用法来源作了历史的探析。他认为后世是“以征伐统礼乐,……征伐胜则纯乎威力,如夏日威天下而不得不循其法”[5]43,在无法回到三代圣王之治的郡县制社会,循法而治是不得已之统治方略,亦是时代发展之必然需要。又说:“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代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5]59魏源之意是说后世在“循法而治”的统治模式下,亦有胜于三代的地方;而法治虽不如礼乐能达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效,但更符合人类社会管理之客观实情,也比较契合历史发展之要求,故能彰显“仁”与“公”。这已大致可看出魏源对法之缘起与功用的认知,他结合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阐述,既吸收了柳宗元“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论》)的学说,亦借鉴了王夫之的“郡县论”。王夫之曾言:“两端(指封建、郡县各执一端者)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8]1他认为郡县制已实行两千年之久,无人能改变之,当是“势之所趋”而理有固然。比较柳宗元、王夫之看重“用人选贤”及“势之所趋”的见解,魏源从治法的角度立说,以说明后世胜于三代,似乎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法理依据。
魏源对法之功用的阐述颇多,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序运转,必离不开法:“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5]46这句话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荀子·哀公篇》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以水比喻民众,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前者则显然是强调法及人君用法的重要性。他还说:“弓矢,中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法令,治之具也,而非所以治也。”[5]46虽然此句用意在于说明有法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但从中亦可看出魏源认为法是治国理政必不可少的工具。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撰写了多篇总结海运、盐政、河工等改革方案的文章或奏疏,就是想为各项改革善政留下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政策,其实质也就是保留新法的经验。如他编撰《淮北票盐志略》,是要“用垂法戒”,以彰显“圣天子、贤牧伯制法宜民可久可大之精意”[5]415,故并不在“专志淮北”,充分显示了他对成法制度的重视。
2.法之实行:治法与治人兼备
魏源既有重法理念,也体察到传统社会德治理念的主导作用,因而对法之具体实施,有很务实的思考,常主张治法与治人必须兼备。
魏源言:“不汲汲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5]46法之立效与否,取决于能否得其人用之。他以道光六年(1826年)的海运一事,盛赞陶澍、贺长龄等人善于除法外之弊,而使事功立现,在总结海运改革经验时亦反复强调:“苟非其人,法不虚创,功不虚施”[5]382,“苟非其人,法不虚行”[5]387,说明创法与得人必须相得益彰,才有功效。
鸦片战争后,魏源把注意力转向最紧迫的海防建设,提出了很多引领时代的思想,其中重要的理念仍是强调良法美意须与“得人”相辅相成,才能成事。如在议守时说:“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期年,亦溃之一旦。”[9]6又说:“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9]15这里可看出魏源虽重西洋之器,但更关注得人与得法。
魏源对传统法治理念有深刻的洞察,他充分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治法与治人兼备,在“弊极”之时必须应时而动,顺势而为,积极变法改革,他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人物,亦能成为与时俱进、倡言改革的思想家,应该与他这种客观冷静的法治理念关联甚密。
四、以民为本,重民富民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内涵,魏源始终关注民生民情,提出了鲜明的重民思想与富民理念,体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近代民权思想的弘扬,客观上也能促进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
1.重民思想
魏源的重民思想在上述对君主大臣之行政素养要求中已有一定体现,而他在君民平等及民心民力之作用等方面还有独到的见解,表现出非常直接的重民理念。
黄宗羲曾言:“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是说君、臣“名异而实同”,倡导君臣一心,共同为民谋福,将国家治理好,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的色彩”[10]4。魏源更进一步提出君与民应是同一地位的激进思想,他说:“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鼻息?非庶人与!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日息柅。古圣帝明王,唯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5]67将君主比作“元首”,庶民比作“鼻息”,同为身体的一部分,即指地位相同,而又强调“鼻不可一日息”,则特别指明庶民的重要性。“鼻息论”并非魏源的独创[注]冯景《鼻息说》中早已阐明类似观点,但论说较粗略。参阅冯景:《鼻息说》,《皇朝经世文编(卷九)·治体三(政本上)》,《魏源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60页。,然而他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指出帝王应与庶民息息相通,并要时刻关注民声,而非仅听言于臣。
魏源还认为所有人都是不能轻视的,而君主之产生亦无特殊之处:“人者,天地之仁也。……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尪,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5]44—45此论认为君主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所谓天子,是众人推举而产生。魏源直接将君主与普通百姓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从心理上消除君主的优越感。他说君主是“众人所积”而成,其实已暗含众人集体认可并进行监督之意,说他受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熏陶,又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已显示出一定的近代民主民权色彩,虽不中的,亦不远矣。
魏源的重民思想还体现在时刻关注民心民力之作用,具体包括民之参政议政能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方面。
魏源提出民众亦可参政议政,且在位者应虚心勤求访问,以获取多方信息与意见,才能制定出合乎时宜的决策。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是以《鹿鸣》得食而相呼,《伐木》同声而求友。”[5]35孔飞力将此解释为魏源对鹿(指臣子)与鹿之间交流的重视,也即“正确政策的产生来自于讨论,而不是来自于由上而下的某种单一的源泉,……精英阶层必须克服自己对于在公共事务上相互交换意见以及自己似乎是在组建朋党的恐惧。……君主本人则必须给予这样的讨论以应有的合法性”。[11]48—49、105孔飞力将此视为魏源提倡“文人中流”参政理念的佐证,所谓“文人中流”的精英身份只指那些获得了举人头衔的“士”,不包括精英阶层的最下端,未能惠及秀才等人。[11]39孔飞力认识到了魏源提倡参政议政的勇气与智慧,但将参政人群局限于“文人中流”则不太确切。魏源写《筹河篇》时,自称“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忍不议”?此文作于道光二十二年,时他已中举逾二十年,按孔飞力之说法,则早已是“文人中流”,又何来“下士不敢议政”?细察之,则知这仅是魏源的谦辞,故其后他又理直气壮地说:“乌忍不议?”即只要涉及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下士”亦是可以议政的。而所谓“众意参同”“同声求友”,应不仅有在士人群体中商讨之意,亦有向广大民众咨询访问之意。他多次强调《皇皇者华》之诗的作用,“为此诗者,其知治天下乎!一章曰‘周爰咨诹’,二章曰‘周爰咨谋’,三章曰‘周爰咨度’,四章曰‘周爰咨询’。”[5]35就是讲此诗赞许周天子派官员外出采风,四处探求民情民隐,从而能“治天下”。因此,魏源的用意并不仅在“文人中流”等所谓精英参政议政,他很重视古代民间采风之策,其实就是允许老百姓发声,使民情能及时上达天听。
魏源重视民众的参政作用,也对民众之自治力有一定的信心。如他在参与道光五年(1825年)漕运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就对海商的自治力高度肯定,认为此次海运“优于元代海运者有三因: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5]393—394能完全“因商用商”,摆脱官运模式,即是对海商行事的高度信任。在实行票盐制改革中,他对私人盐商亦很肯定,曾言:“盐为利薮,官为盐蠹,……以十余疲乏之纲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数省散商之财力,众擎易举?以一纲商任百十厮伙船户之侵蚀,何如众散商各自经理之核实?以纲埠店设口岸而规费无从遥制,何如散商势涣无可指索?以纲商本重势重,力不敌邻私,而反增夹带之私,何如散商本轻费轻,力足胜邻私,且化本省之私?”[5]411—412此论充分表明魏源对私商散商经营盐务的认可,比官商经营纲盐制不知高明多少,这是他通过周密调查之后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他鼓励发展民间商业的重要实践依据。
对老百姓之合力的重要作用,魏源也是有深刻认知的。他倡导民心民力可用,在论述傅鼐治苗事时曾充分肯定其重视苗民之合力,他指出傅鼐变通古屯田法,“均亩养丁,自穑自卫,……又屯苗叛产五千,俾自为镇压,永助我捍卫。”[5]252—253这种重视民力、“以苗治苗”之方,魏源很是赞赏。他还对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力量也极为关注,认为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首先必须赢得这些地区的民心,而具体策略则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如对蒙古诸部族,大体以怀柔和亲为主,又以木兰秋狝抚绥蒙古,后虽有噶尔丹叛乱,康熙“三驾亲征”,平叛后仍宽宥之,建置封王,“自是永为不侵不叛之臣”。[6]96—110对于西藏,则尊其宗教,以服其民心。“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土,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6]215—216对于回民,则认为可训练其为兵勇,化枭奸为良民。他称:“回民之仇怨狠鸷,……与厄鲁特之崇黄教、嗜劫掠何异?……诚能训练回兵入伍,驱狼戾之族为纪律之师,其力最鸷,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纥、扁和用乌喙之谊也。”[6]308以上这些均体现了他对民力的重视,当然,其中还有对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倡导。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对民心民力的关注尤其明显,言朝廷对粤民存先入之见,朝廷认为“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朝廷不信任粤民,多与民结怨,而英人反而能释还乡勇,“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6]467官府不能体察民情,善待民意,则必然失去民心,甚至使良民转为汉奸,也未可知。魏源对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新安武举人庾体群率众攻洋船事以及南海、番禺等地团勇自发组织的抗英斗争等给予了高度赞扬[6]467—468,均显示出魏源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与期待,他还明确说,在鸦片战事中,“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6]485其意即是在非常时期,应积极调用所有民心民力,共同抵抗外侮,这既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先声,亦含有人民战争的意味,他对民众合力之作用,是存有很大信心的。
魏源倡导君民平等,主张百姓有参政议政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亦有自治的能力,而民众之合力更是求得内治外安的重要因素,这些均是其重民思想的突出内涵,某些理念已有超越传统的态势,而焕发出近代启蒙色彩的光芒。魏源始终着力于了解民生民情,重视民意民力,自会时刻关注为百姓谋福祉,其落脚点即是“富民”思想。
2.富民思想
魏源针对嘉道时期国穷民困的现状,明确提出了“富民”主张。他说:“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适足损有余以益不足,……天道恶积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恶偏,则知以俭守财,乃白圭、程郑致富起家之计,非长民者训俗博施之道也。”[5]72—73
他明言“禁奢崇俭”之美政,只能用来“励上”,即约束当政者,不能“训贫”,即针对老百姓。对于普通百姓,要时时提醒其不可安于贫穷,要鼓励其多事生产,致富裕之家。魏源又言:“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5]72这表明他似已把民生置于国家根本之地位,认为富户愈多,就愈能维持国家之稳定发展,这与《史记·货殖列传》中“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之说一脉相承。魏源相信富户好行德,能为政府分担部分地方责任,而“散财任恤足为美俗仁里”[5]73,所以他并不排斥商业、开矿等致富政策,已凸显对“本富”(食)、“末富”(货)同等重视的倾向。[12]121—122针对现实的严峻问题,他甚至提出了“缓本急标”的观念,曾言:“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6]568
综合而言,魏源对天道观、王道之治、法治思想以及民本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几个核心理念均有深入的探讨与认知。他承认“天道观”作为“神道设教”的重要意义,既可为统治者政权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为当政者设置一道无形的最高警戒线;他不排斥鬼神说,认为幽明观能“阴辅王教”,有益于人心,认为王法不及惩罚之人,阴教可以震慑之;魏源对忧患观十分看重,认为常怀忧惧之心,是达到“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由此才能建立良序社会,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魏源还对传统社会的王道政治理念作了细致分析,主张王道纯出乎道德,要通过学古、变易等方略来实现王道的理想,又明确提出王道有近功说,还对“圣君贤相”的执政素养进行了具体探讨。魏源对“法”的看法并未脱离传统的“法是治理之工具”这一基本认识范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观有根本的不同,但他针对当时陋规重重、弊病丛生的现象,主张“去法外之弊”,而在“弊极不得不更”的时候,又坚决主张变法改革,他认识到了法的重大功用,结合传统人治社会的特征,提出“治法与治人兼备”的思想,在其时应是切合实际的。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民本思想亦有深刻的认知,从其著述中体现出来的重民思想、富民思想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局限,而透出近代启蒙思想的光芒,如他提倡君民平等观,相信民之参政议政能力、民之自治力等,也意识到民之合力的作用;他承继孔子“先富而后教之”(《论语·子路》)的富民思想,提出“本末皆富”甚至“缓本急标”的重商思想,对洋务运动以及后来中国的整个近代化进程应该都有深远影响。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认知与超越反思,显示了他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诚如有的学者所说,魏源思想资源体现的仍是本土性质,他虽写了《海国图志》,但其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11]3亦有人说: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连续一贯性,要远远超过为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所认识到的程度。[13]16因此探求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对于理解其本人的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化转型的问题,均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他所弘扬的诸多理念,对当今的政治文化建设亦不无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