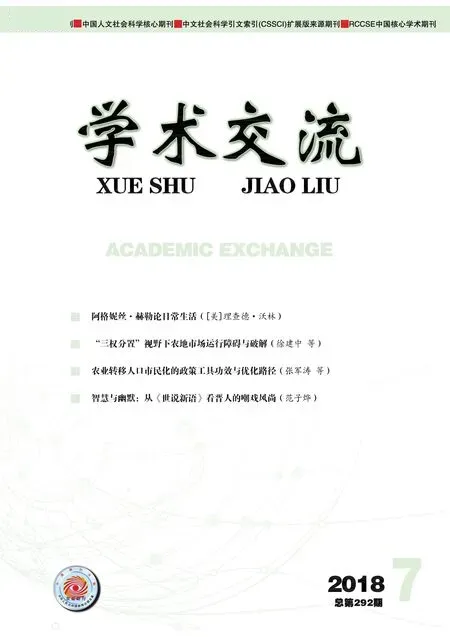中国墨学史构成分析及启示
沈传河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一、问题的提出:既然是绝学,为何还有中国墨学通史?
在学界,“墨学是绝学”大致是公认的论断。当然,这一论断是就墨学在古代的发展状况而言的。一般认为,墨学创立、兴盛于先秦,消亡于秦汉,此后长期沉寂,清代中叶以来才渐事复兴,至民国初期达到高潮。于是,墨学遂有“绝学”之称。在当代学界,颇有一些学者直接以“绝学”来界定墨学,以下略举数例:(1)孙中原《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七章标题“绝学重光待琢磨:墨学的命运和现代价值”;(2)魏洪峰《墨学何以成为绝学》(《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3)曾繁仁《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墨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史哲》1999年第6期);(4)暴庆刚《墨学之成为绝学探因——兼以儒家、道家作侧证》(《东方论坛》2002年第2期);(5)沈长云《士人与战国格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章内小标题“从‘显学’到绝学”。
当然,墨学消亡的问题在古代学界就早已有人述及。远在西汉,桓宽《盐铁论》中即有相关记载:“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1]这里说的是,先秦儒学和墨学都亡于秦朝之暴政。不过,联系当时的情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谓的“丧”,应当是指儒学、墨学在学派层面上的大体丧失,而非包括学者消亡在内的完全丧失。也就是说,秦朝建立后,部分或个别的儒者(儒家学者)、墨者(墨家学者)应当仍然是存在的,甚至其中部分士人很可能后来进入了汉代。到了东汉,王充《论衡》也有相关记载:“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2]王充从“薄葬、右鬼”说起,指出了墨学理论上存在的弊端。王充这里对墨学失传因由的推断虽然不无偏误,但他明确提及墨学“废而不传”,这一信息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即说明墨学到东汉初期已经失传消亡,当时最后一个墨者应当是在西汉消失的。孙诒让是晚清治墨大家,他认为墨学当灭绝于秦末:“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3]680“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3]707孙氏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颇大,其后的学者们大多认同这一观点。但也有部分学者,尤其是当代一些学者,则认为墨学一直延续到了汉代,在汉武帝尊儒之后才逐渐消亡。笔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墨学的消亡,历史地来看,可以分为墨家集团体制的消亡和个体墨者的完全消亡这两个层面,其中前者应出现较早,当于秦朝建立后不久即已完成,而后者应出现较晚,当于汉武帝尊儒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得以完成。不管怎么说,把墨学消亡的时间确定为秦代至西汉这段历史时期,应当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其消亡的具体时间和情形在学界难免尚有争议。
既然墨学在秦代至西汉时期就已经消亡而成为了绝学,那么在西汉以后、清代中叶墨学开始复兴之前,即中国墨学的消亡期里,就不应当再有各代墨学史,而“中国墨学通史”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对墨学史的研究,无疑是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在寻绎、探究墨学史时,对西汉以后、清代中叶以前的墨学史一般并非阙如不问,而是仍然有所述及或评论。以下略举几例以作明证:(1)清陈梦雷等人的《墨子汇考》(原为《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系历代墨学资料汇编,其选录的时限是战国至明代。其中来自宋、明、唐的资料分别有11条、8条、7条,在条目数量上居于前三位。[4]显然,编选者并没有空缺对墨学消亡期内相关墨学资料的编选。不仅如此,编选者对墨学消亡期内相关墨学资料的编选还尤其多。(2)近人陈柱于1926年著成《墨学十论》,其中第十论为“历代墨学述评”。在“历代墨学述评”中,作者对墨学消亡期的墨学[注]“墨学消亡期的墨学”,这种表述形式看似矛盾,但有了下文的阐释,就不难理解了。的述评虽然总体上较为简略,但实际上并未空缺,依然有所述评,尤其是对西晋学者鲁胜的治墨述评较多,较为详细,且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彼鲁胜者,独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怀兴微继绝之志,岂非人杰之士乎?……鲁胜书据其序则当甚可观。”[5](3)今人谭家健先生1995年有《墨子研究》一书出版,该书第十六章为“历代墨学研究述略”。在这个“中国墨学史简编”中,作者同样没有置墨学消亡期内的墨学于不顾,而是依次对其作了比较详细的编述,其中对宋、明等时期的墨学所述尤详。值得注意的是,谭先生在这里使用的是“墨学研究”一语。(4)迄今为止,对中国墨学史研究最为深广、所取得的成就最大的,当数山东大学郑杰文先生。作为郑先生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墨学通史》于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86万字。该书以“通史”命名,通贯古今,旁征博引,对中国墨学史进行了全面深入而又具体详尽的梳理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未明确界分出中国墨学的消亡期,更未将这一时期的墨学空缺而不予撰述,而是对其同样作了比较详尽的编述与批评,尤其是对东汉、明代等时期的墨学。一般认为,魏晋至宋元自然是属于中国墨学的消亡期;但《中国墨学通史》第四章的标题即为“魏晋至宋元间墨学的流传”,且该章内容占了72页之多,显然述之也较详细。郑杰文先生认为:“魏晋至宋元1100余年间,墨学流传进入长久的低谷阶段,但仍传播不绝。”[6]226
以上两方面的内容,显然存在着矛盾冲突,问题也就自然产生:既然墨学已经消亡而成为绝学,出现了漫长的消亡期,那为何还有消亡期内的历代墨学?为何还有“中国墨学通史”?
二、中国墨学史构成分析:两类墨学与两类墨学史
(一)两类墨学
“墨学”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概念,以至于学界很少有人对其专门加以界说和探究。而当加以界说时,人们一般把“墨学”界定为墨子或墨家的学说。但就学界的现实情况而言,所用“墨学”的含义却并非如此单一。据笔者考察和辨析,在当下学界,“墨学”一般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墨家的学说及其学术活动,二是指对墨家及其学说的研究。也就是说,统观古今,被称为“墨学”的学术活动实际上应当被区分为以上两类。或者说,“墨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上面所讲,前者为狭义的,后者则属于广义的“墨学”。如果说第一类墨学应首先被称为“墨学”的话,那么第二类墨学,确切地说,就应当被称为“对墨学的研究”。[注]当然,这里其实是还可以衍分出第三类墨学的,确切地说,它应该称为“对于对墨学的研究的研究”。这类墨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例如后人对清人治墨的研究、对墨学史的研究等。如果不作严格区分,这第三类墨学也可与第二类墨学合为一类。“对墨学的研究”即学界一般所说的“墨学研究”,甚至也包括“对于对墨学的研究的研究”。学界有时为了称谓的方便,会把“对墨学的研究”省称为“墨学研究”,甚至进一步省称为“墨学”。例如谭家健先生《墨子研究》一书的第十六章,该章标题为“历代墨学研究述略”,而其下各节均省以“墨学”为题,分别为“第一节 秦汉至宋明墨学”“第二节 清代墨学”“第三节 现代墨学”“第四节 当代墨学”“第五节 海外墨学”。[7]值得注意和肯定的是,谭先生在这里显然对“墨学(墨家之学)”和“墨学研究”作了大致的区分,故该章撇开先秦墨学(墨家之学)不谈,而是直接从秦汉时期的墨学研究谈起。当然,中国的墨学研究是可以、也是应该追溯到先秦的。在先秦,除了墨学(墨家之学)的创立和发展之外,学界对墨学(墨家之学)的研究与批评也几乎同时展开,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皆存有一些相关研究内容。上述两类墨学,虽然都可以称为“墨学”,但实际上是不同的,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淆。
上述两类墨学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主体不同。第一类墨学的研究主体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人”(墨者),所以此类墨学可称为“墨家墨学”,省称“墨学”;而第二类墨学的研究主体一般则是学界里面墨家之外的一些学人,所以,此类墨学可称为“非墨家墨学”,它实际上是对墨家墨学的研究,故可相应地省称为“墨学研究”。(2)研究对象不同。第一类墨学主要以当时的社会人生、军事斗争、学术文化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重点在治世、修身、节俭、名辩、城防、技艺等方面展开研究;而第二类墨学则主要以墨家的著述、思想学说以及墨者的活动、行事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以墨子其人与《墨子》一书为研究重点。
以上对两类墨学的区分,是有一定的价值意义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墨学本身就是墨家在与其他学派的对话与辩争中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将他者的学术批评也引入墨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研究墨学、认识墨学,乃至发展墨学。(2)对两类墨学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解读分析中国墨学史,理出两类墨学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墨学是否曾经消亡等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分析与判断——这方面的问题下文将详有阐释,此不赘述。
上述两类墨学,如上所说,是可以分别称为“墨家墨学”“非墨家墨学”的,但这种称谓不仅难免有费解之嫌,而且似乎与现代学术语言有所不合,故笔者认为,还是分别以“墨学(墨家之学)”“墨学研究”来指称为好。这样的称谓,也正好能够契合本文的写作缘由与目的,即鉴于学界在使用“墨学”这一概念时存在含混不清的情况,笔者欲将墨家学派意义上的墨学与一般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墨学区分开来。现实地来讲,学界肯定有人已经将“墨学(墨家之学)”与“墨学研究”加以区分,只是尚未成为共识和通行做法而已,笔者于此所为,意在将这种做法明确化、具体化,进而使之能够普遍化。与“墨学(墨家之学)”“墨学研究”相对应,它们的研究主体就分别为墨者(墨家学者)和墨学研究者,这二者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也值得我们注意,其主要有:有不少墨学研究者其实不是墨者;部分墨学研究者可以转化为准墨者甚或墨者;墨者、墨学研究者这两种身份可以统一在一个个体身上。
(二)两类墨学史
既然中国的墨学应当区分为墨家之学和一般的墨学研究,那么,中国墨学史自然也就应当相应地区分为二,即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或者说,跟墨学一样,中国的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狭义的、广义的两类,其中狭义的墨学史即指中国墨家学术的发展史,而广义的墨学史则还包括一般学者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也就是说,中国墨学史其实是由墨家学术发展史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这两类墨学史共同构成的。这两类墨学史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有二:(1)历史主体不同。墨家学术发展史的历史主体是墨家学者,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的历史主体则是一般的墨学研究者。相比之下,后一研究群体的学者数量应当远远大于前者。(2)历史发展的动机不同。墨家学术发展的动机,是基于墨家本位立场,继承发展墨家学说,积极扩大其社会影响;而一般学者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其动机往往是基于学术史研究的本位立场,研究和批评墨家学术及其各个具体方面,从而服务于当时的思想学术建设。
中国墨学史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由于儒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对立,对墨学史的研究就具有了更大的价值意义。笔者认为,对两类墨学史进行区分是必要的,是有一定的价值意义的:(1)这是具体深入地研究墨学史的前提。此前的墨学史研究,往往只从整体上着眼,缺少分析,缺少深入探究。“两类墨学史”的提出,对于打破这种研究格局,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分类考察,深入探究,能够更加真实细致地反映墨学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从而为解决与墨学消亡、复兴乃至发展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基于史实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墨家的学术发展史确实是比较短暂的。墨家之学虽然在先秦一度十分兴盛,被誉为“世之显学”,但是秦汉专制政权的确立,使其很快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先是墨家组织的失却,尔后是最后一批墨者的消失,最终使得墨家之学失传,墨家的学术发展于此止息。清代中叶以降,虽然墨学逐渐再度兴盛起来,至民国初年形成新的墨学高潮,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复兴的墨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古代墨家学术的研究,而墨家自身学术复兴的成分并不多。之所以这样说,理由主要有二:(1)现实地讲,这一时期,新的墨家学人(新墨者)并没有真正地或较多地出现,更不用说新的墨家学派的形成和出现。在此期间,虽然不乏一些倾心于墨学、推崇墨学的学者,如汪中、俞正燮、孙诒让、梁启超等人,但严格地说来,这些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准新墨者”。即使其中有些人可以被视作真正的新墨者,这一类人在数量上也应该是很少的。既然缺少新墨者,没有出现新的墨家学派,那么墨家自身学术的复兴自然也就不好谈起。(2)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这一时期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墨学的社会影响也日趋扩大,但其实,墨家学术的核心——墨家学说并没有获得多少创新与发展,“新的墨家思想”基本上无从谈起。这种状况的存在,也正是笔者不愿把上述汪中等人视为真正的新墨者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墨学研究的知识体系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墨家自身的价值体系其实并未获得多少创新与发展。
相比之下,学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则是绵延不断的。先秦时期,墨学是在与其他学派,尤其是儒家的辩争中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先秦墨家创立和发展自家学说的同时,其他学派,尤其是儒家对墨家学术也多有关注,多有批评,这客观上构成了另外的第二条线索,即学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可以省称为“墨学研究史”),其中先秦阶段可以省称为“先秦墨学研究史”。这条线索与原本的第一条线索——先秦墨家的学术发展史(也可省称为先秦墨学史)虽然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却是明显不同的。这两条线索内外相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一起构成了广义的先秦墨学史。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墨家、墨者的逐步消亡,第一条线索后来就彻底中断了,中断发生的时间应当是在西汉中后期。但第二条线索却并未随之而中断,对此,郑杰文先生用“衰而不振,然亦引用不绝”[6]185来描述当时的情形。第二条线索为什么能够不中断,而得以继续呢?原因应当很简单,那就是:虽然墨家、墨者完全消亡了,但他们所著的书籍、所创立的学说及其影响等却依然存在,这使得非墨家的学者对墨家学术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在墨家、墨者消亡的时间里,墨学作为一种活的价值体系虽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死的知识体系却依然存在,尽管这一知识体系在历史的变迁中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损失。出于对自身学术地位的维护,封建社会的诸多学派,尤其是儒家,多对墨学采取批评、排斥的态度。为了更好地批评和排斥墨学,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大的学者,势必要对墨学有所了解,有所研究,以便能够抓住其要害而予以批判和攻击。这是进行学术辩争的基本需要。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儒家辟墨,就其实际情况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悖论。例如,身为大儒的朱熹也持辟墨的态度,但他的辟墨不再是孟子式的主观攻击,而是代之以诸多冷静而精深的学理分析。[6]278-289比如,朱熹在批评墨家“兼爱”思想的时候说:“墨子之心本是恻隐,孟子推其弊,到得无父处,这个便是‘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8]试想一下,如果朱熹对墨学完全辟除,没有什么了解和研究,那么这些精深的学理分析何以成为可能?因此,上述第二条线索,即“墨学研究史”,大致始于战国,贯穿于秦汉以下诸代历史,其间未曾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也就是中国对墨家学术的历代研究史,或省称为中国历代墨学研究史。郑杰文先生的《中国墨学通史》一书对之阐述甚详,可资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第二条线索是有一个兴衰起伏之变化的,总的说来是两端(战国至两汉,明清至今)兴盛高起,中间(魏晋至元代)衰落低伏,这从《中国墨学通史》中各代墨学研究史所占篇幅上很容易看出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意义上的“墨学”应当分为两类,即墨家之学(墨学)和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前者是原发性的,后者则是继发性的。与两类“墨学”相对应,总体意义上的中国“墨学史”也应当分为两类,即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和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两相对比,前者是比较短暂的、曾经中断了的,而后者则是十分长久的,中间未曾中断、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因此,整个中国墨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部中国墨学研究史,而中国墨家学术发展史在其中只占有较小的比重。今人撰写中国墨学史,固然可以将两类墨学史合写,但在其中应当作出明确的区分和说明。
说到这里,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自然就可以得到理解或回答了。(1)上文提及“墨学消亡期的墨学”。对于这一貌似矛盾的表述形式,应当这样理解:前一“墨学”是指狭义的墨学,即墨家之学,而后一“墨学”则包括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属于广义的墨学。汉代以降,虽然墨家、墨者消亡了,墨家学术发展史中断了,但学界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却仍在继续,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并未中断。(2)本文第一部分即提出问题:既然是绝学,为何还有“中国墨学通史”?对于这一问题,至此也不难回答了。墨家、墨者消亡了,墨家学术发展史中断了,故称墨学为“绝学”,应当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一如上文所述,虽然墨家、墨者消亡了,墨家学术发展史中断了,但墨学研究者(对墨家之学进行研究的非墨家学者)却仍然存在,延续不断,这客观上形成了第二类墨学史,即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因而,就中国墨学史的总体而言,称之为“中国墨学通史”自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墨学虽然是绝学,但并不否定中国墨学通史的存在。但若具体分析起来看,则应当这样说:中国没有一部墨家学术发展通史,但有一部对墨家学术的研究通史,可省称为“中国墨学研究通史”。
三、中国墨学的灭绝与复兴问题
(一)中国墨学是否曾经灭绝或消亡?
这貌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用“是”或“否”就可以回答;但其实不然。
这里先基于上文的分析论述,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如上文所述,墨学可以分为两类。如果问题中所说的“墨学”指的是第一类墨学,那么对这个问题可以作肯定的回答,因为西汉以降,墨家、墨者终究是消亡了,墨家学术发展史因而也就出现了长期的中断。而如果问题中所说的“墨学”指的是第二类墨学,那么对这个问题自然就应当作否定的回答,因为如上文所述,从战国至今,学界(墨家除外)对墨家之学的研究是一直延续不断的,中间并未出现中断,从而才形成了绵延不断的第二类墨学史,即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
但上面的分析和回答其实仍然不够,因为墨学(墨家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它有诸多的构成方面,就不同的构成方面加以判断,对上述问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回答。整个墨学(墨家之学),大致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构成方面,即学人、著述、学说、精神,而其中后两个构成方面显然更具有核心意义。上段对“中国墨学是否曾经灭绝或消亡”所作的肯定回答,是就墨学(墨家之学)的第一个构成方面而言的,即就墨家在学人传承方面出现了中断而言,中国墨学(墨家之学)出现过灭绝或消亡。而就后三个方面分别而言,则都可以得出中国墨学(墨家之学)并未灭绝或消亡的结论。迄今为止,墨家的著述和学说都依然存在(尽管确切地讲来都只是部分地保存至今),具体可详,无须赘说。墨家消亡之时,墨家的诸多精神因素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多为其他学派或教派(主要是儒学和道教)所承续,从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甚至传承至今。当代学者如郑杰文、秦彦士、范学辉等人,对此问题皆有所研究,其相关著述可资参考。其中,郑杰文《墨学对早期道教的影响》(2005年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秦彦士《从董仲舒看汉代儒墨合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范学辉《从公孙弘看汉代齐学与墨学的融合》(《管子学刊》1996年第4期)等文的代表性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如果从对墨家思想和精神的传承这个角度看,同样可以得出“墨学未曾灭绝或消亡”的结论。有一个学术事实也可有力地证明中国墨家之学其实并未完全消亡,这一学术事实即是墨家消亡期间儒家对墨学的持续不断的辟除。如果墨家之学在墨家消亡期里真的是完全消亡了,那么儒家在此期间的持续不断的辟墨就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荒唐。
值得欣慰的是,当代学界并未完全为“绝学”之论所蔽,真知灼见也时有出现。今试举几例:(1)孙以楷拟著《中国墨学史》,其第四章中的一个小标题拟为“墨家学派的消亡与墨学不绝”[9]。可惜该书未成,此标题也只能有目无文,使人难得其详。但从该标题不难看出,在墨学是否消亡的问题上,孙先生已将“墨家学派”与“墨学”分而论之,同时指出“墨家学派的消亡”与“墨学不绝”,确属高明之见,值得学习,后来学者可以沿此思路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2)钱永生认为:“秦汉以来,儒学独尊,墨学衰微。……或儒墨相用,或依附道教,在主流思想与民间信仰之间,墨学不绝如缕。”[10]钱先生确认了墨学自秦汉以来的“衰微”态势,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否认墨学的流传,而是用“不绝如缕”来加以形容。(3)金鑫认为:“秦汉之后墨学成为‘绝’学,并非完全绝迹。墨学从未在任何一个朝代中绝迹,只因墨家学派不再、墨学系统不再、墨者行为不再,故以为‘绝’。”[11]此语同样是在强调,墨学在秦汉之后虽然有“绝学”之名,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断绝。
(二)中国近世墨学复兴的水平如何?
这里所谓“近世墨学”,是指清代中叶至20世纪前半期的墨学。
中国近世墨学发展复兴的状况如何,可从梁启超和栾调甫的相关论述中获得一个大致的了解。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清人治墨总结道:“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然非承卢、毕、孙、王、苏、俞之后,恐亦未易得此也。仲容于《修身》、《亲士》、《当染》诸篇,能辨其伪,则眼光远出诸家上了。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12]梁氏于此举要以梳理,依次列举了清代的治墨大家卢文弨、毕沅、孙星衍、王念孙、苏时学、俞樾等。其中,梁氏对孙诒让的论述最多,肯定最多,评价最高。栾调甫在其《二十年来之墨学》一文中对民国初二十年的墨学发展论述道:“独至晚近二十年中,家传户诵,几如往日之读经。而其抑扬儒墨之谈,亦尽破除圣门道统之见。……原此三端,遂以造成二十年来墨学春苗勃发之势。”[13]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世墨学复兴发展的高潮期,栾氏对此期墨学的盛况作了很好的论述。
目前学界对近世墨学的复兴,尤其是晚清民初墨学的复兴,一般都有很高或较高的肯定和评价,其言外之意即是说,这一时期墨学复兴的水平是很高或比较高的。但笔者认为,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这一问题应当尚有值得分析和商榷的地方。我们可以基于上文“两类墨学”的说法,对此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说明。就第二类墨学而言,中国近世墨学的发展确实是空前的,在对《墨子》文本的校理、对儒家辟墨的反拨、对墨学义理的阐发、对墨学社会文化价值的应用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就是说,若从墨学研究(对墨家之学的研究)的视角来看,近世墨学复兴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若就第一类墨学而言,中国近世墨学的复兴确实又不容乐观,不可高估,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在中国近世墨学的复兴中,墨家自身学术复兴发展的成分确实不多,取得的成就也不大,并未达到多么高的学术水平。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1)清人以朴学方法治墨,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并有其学术必要性,其学术成就也不容否认,然而,客观上,对墨学义理研究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墨家学术在理论上的自我突破与创新。(2)晚清以降,社会发展波折动荡,人们对于墨学,更多的是去发掘和使用其工具价值,以服务于时势演进,这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墨学(墨家之学)自身的内在价值,忽略了对墨学(墨家之学)本身的反思、超越与发展,使其新的理论形态无从明确形成,“新墨学”(新的墨家之学)只能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期待。(3)古老的墨学(墨家之学)缺少发展,缺少与时俱进,它不会直接成为近世学术文化演进的目标或目标之一。在新的墨学(墨家之学)理论没有明确形成的情况下,新的墨者也就不可能真正(较多地)出现,新的墨家学派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近世的墨学复兴中,第一类墨学即墨家之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复兴和发展,墨家之学复兴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此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两类墨学之中,第一类在先、在内,第二类在后、在外,第一类墨学更具核心意义,更为重要;因此,在中国近世墨学复兴中,由于第一类墨学复兴的水平较低,所以即使第二类墨学复兴的水平很高,我们在作总体审视的时候,也仍不能认为近世墨学复兴的水平很高或较高。
——释德扬法师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