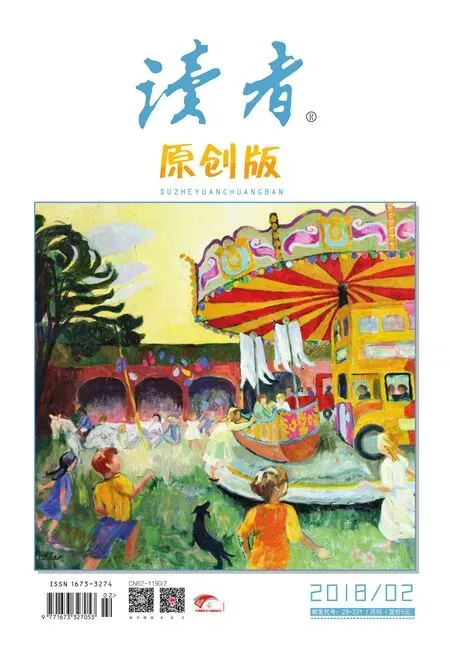妈妈的花式劝食
文 | 肖 遥

一
周末去妈妈家。对于“去妈妈家”这件事,我和我姐都怀有一样的心情—如果妈妈不使劲地劝人吃饭,那就完美了。
就连我小姨,妈妈的亲妹妹,一说到她姐姐劝人吃饭的事情,都哭笑不得。
我们成年以后,陆续离开了家,爸妈也搬进了新居。小姨去参观新居,吃完妈妈做的晚饭,撑得几乎走不动路了,但是还是得走,得消化呀,于是走了十几站路回家的小姨,一路走一路吐……
没办法,如果不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是很难抵御我妈的花式劝食的。
跟我爸比,我妈的厨艺稍逊,但是我妈很会买食材,总是拣全市场最新鲜的水果、蔬菜买,捎带买很多核桃、瓜子、麻花、蚕豆……当这些好吃的一股脑地堆在桌子上时,你就会放松警惕,这个抓一把、那个抓一把,等到吃饭时已经有八分饱了。然后主餐上桌,热气腾腾,一般人很难抵御这种新鲜食材的诱惑。重点是,当你吃到极限的时候,妈妈会不失时机地递过来一块煎饼:“就剩一个了,给咱解决掉。”你一想,一个煎饼而已,吃了!若不吃,妈妈会说得更恳切:“你们不吃完,我和你爸得吃一周的剩饭。”
你吃煎饼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削苹果了,当你咽下最后一口煎饼,一块苹果已经递到了你手里。你若稍有难色,妈妈就会说:“苹果是帮助消化的。”打消顾虑,吃!苹果还没吃完,梨已经削好在盘子里等着了,吃了苹果不吃梨,对梨也不公平,继续吃……
在妈妈家,你会发现,无论你走到哪里,食物都如影随形。吸取小姨吃吐的教训,我吃完最后一块梨后赶紧离开餐桌,然后发现,姐姐和姐夫早就跑了。可是,不论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在书桌前看书,或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都有一盘刚刚切好的白兰瓜摆在眼前。
二
现代人总喜欢用幼年时遭受的创伤来解释遇到的人生问题,人对某件事情极其执迷,多半是小时候在这件事上吃过苦或吃过亏。父母小的时候,食物是匮乏的,这可能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曾经对于吃的极度渴望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成了这样—爱你就劝你多吃。可是,对我们来说,过于丰盛的食物,过于殷切的劝食,会使得吃饭这件愉快的事变得令人避之不及。
其实我一直有种不厚道的揣测:因为我妈妈对自己的厨艺并不自信,所以她需要一再确认。
这事儿还得扯到我爸。我爸是个非常利索、爱干净的男人,尤其擅长做菜,可他却不是个“暖男”;相反,他脾气急躁,因为自己做得好,就看不上我妈做的。我妈不论是炒菜、蒸馒头,还是熬稀饭,都会被我爸挑刺儿、批评。我妈这人内心清高,不受重话,我爸的那种态度,导致我妈的厨艺在最应该提升的阶段没有提升。通往厨房的路,对我妈来说,其实是一条畏途。但是家里来了人,又不得不下厨,因此,她只好用劝食来掩盖自己的不确定感—担心自己做得不好,怠慢了对方。
不得不说,有些能力是天生的。
比如我大舅妈就很擅长做厨房里的事。每到过年,大舅妈家一拨一拨地来人,大舅妈就做一大盆粉蒸肉,蒸很多馒头和包子,再熬一大锅粥。来一拨人,切一盘卤牛肉、一盘肉冻,馏一碗粉蒸肉,炒一盘莲藕或土豆丝,从亲戚进门到亲戚坐好,大舅妈一边跟他们寒暄着,一边四菜一汤已经端上来了。我们小孩子饿了就跟着吃一点儿,不饿就跑得没影儿了,这种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的感觉在我家是无法体会到的。
而我的婆婆,一个农村家庭主妇,尽管只会做简单的饭食,但很会说场面上的应酬话,听她说得一套一套的,你反而不好意思放开了吃。比如她说:“也不会做啥可口的,你们就凑合吃点儿吧。”这时你就得说:“已经很丰盛了!谢谢妈!不要再弄菜了,您也过来一起吃吧……”于是,在这样的餐桌上,吃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你首先得接得住她的话。自从吃过婆家的饭之后,我才变成了一个坐在饭桌上却并不是为了吃饭的成年人。
三
每一家吃饭时的气氛,其实都反映出了这家人的日常生活氛围。
我家吃饭时的气氛是怎样的呢?我妈这种知识分子,说她是“老少女”也好,“公主病”也罢,生活一直没有逼着她学会看眉高眼低,也没虐得她必须学着运筹帷幄。她既不像我大舅妈那样,家里总有一大群人进进出出、吃吃喝喝,被锻炼得似有三头六臂;也不像我婆婆那样能说会道,即便你只喝她一口茶,她也会让你觉得你喝到的是全天下最美味、最来之不易的茶。
我小时候,家里一来人,妈妈就手忙脚乱。直到现在,我最害怕的事就是进厨房,确切地说,是进有我妈的厨房—看着我妈惊慌失措地把菜扔进锅里,热油刺啦一声响,不知为何,我总能清楚地从她的动作里看出怨恨,怨恨我还没长大、笨手笨脚、帮不上忙、到处添乱……她忙活焦躁地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则觉得自己仿佛被放在火上炙烤。
厨房是我们的禁地,无论你是想帮忙,还是想探看一下今天吃啥,刚一踏进厨房,就会被我妈赶出来。我大舅妈也会把闲杂人等从厨房里往外赶,但即便是赶人,大舅妈也会表现出一种“不需要帮忙”“就等着吃好的吧”的自信。而我妈,她表现出来的是气急败坏,好像每个进厨房的人都是去围观她出丑的。
大舅妈让你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知道一会儿可以心安理得地吃饭,想吃多少吃多少,吃不完大舅妈也有办法。我妈把你往外赶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害怕,因为一会儿的就餐时间保准不会好过—全吃完了她会紧张,暗暗责备自己准备不足;吃不完的话,她会气呼呼地指挥你把剩菜吃完,否则就对不起她的辛劳。
成年以后,我下定决心闯一闯妈妈的厨房。我妈的第一反应果然是:“别催!马上就好!”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来帮忙。”我妈几乎是恼羞成怒地说:“不需要帮忙!出去!”我说:“我来吧,你出去!”其实,我还想说:“你要么不做,放着我来,要么就心平气和地做,别吹胡子瞪眼睛的。”但是这些心里话我肯定不能说,母女相处时间长了,堆积了太多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彼此即便不说话,一个表情也能激怒对方,外人看着根本不是事儿的事,在亲人之间反而会勾起新仇旧恨。
听我那么说,我妈的腔调都变了:“我的厨房我为啥要出去!”我俩近乎激烈地冲突后,妈妈出去了,但是特别生气。我也很生气—你的厨房你要善待它啊,你的领地你要爱护它啊,你的食物你要珍视它啊,你的孩子你要温和地对待她啊。可是你呢?厨房好像是令人讨厌的办公室,有机会就逃,可别人来占领你又要霸占住;食物好像是垃圾,千辛万苦地做好了,却总是让大家“赶紧处理了”;孩子就更别提了,我们童年时的吃饭时间,基本上是在“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和“吃不完把头割下来灌”的台词中度过的。
姐姐说,有一件事她总也忘不了。一年夏天,她游完泳回来买了一根冰棍,刚准备放进嘴里,妈妈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也不知道给大人吃一口。”她顿时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姐姐知道,就算把冰棍递给妈妈,妈妈肯定也不会吃。多年以后,姐姐跟妈妈还是不能好好聊天儿。
四
劝食之所以让人排斥,就是因为这“劝”里除了爱还有其他东西—逼你产生内疚的感觉和对你的怨言。这些,都使得这爱变得不纯粹了。这世上大多数的事都可以掺水分,唯有爱不可以,掺了水分的爱,即便是孩子也能感觉得到,而且越是年龄小越敏感。
长年累月地做饭、带孩子,对我妈来说一直是件辛苦的事。完成以后,那些使她受苦的人,都不免成为她迁怒的对象,她的恼怒是不自觉的,她甚至不清楚这怒气从何而来。这怒气或许源自她明明不喜欢做饭、做家务,可是她有两个孩子,尽管力不从心,也不得不按照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好妈妈”的模板做下去。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拧巴的状况。我们成年以后,每次一获悉我们要回去,她就会平均每半个小时一个电话地询问—“你们走到哪里了”“还有多长时间到家”……等我们到了以后,她却不见踪影,打来电话说:“我跟你某某阿姨出去了,钥匙在窗台上,菜在冰箱里,你们自己弄吃的吧。”等我们快离开时,她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或者我们到了以后,发现家里有一群他们的老同学或老朋友。平时他们两个自己在家时为啥不呼朋唤友,非要在家庭聚会时间招待朋友和同学?我估计这很有可能还是和食物有关。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就采购了一大堆食材,和面的时候一想:“和得太多了,算了,再叫些人来‘解决’吧。”人多了食物又不够了,那就再做一锅米饭:“哎哟,好像又弄多了,那就把XXX也叫来。刚好熬一锅羊肉汤,把冬天没吃完的羊肉给‘解决’了。”妈妈很喜欢用“解决”这个词来劝食,就好像我们吃的不是美食,而是垃圾,得赶紧打扫了,解决了。
可是,无论是人还是食物,不用心对待,简单粗暴地“解决”或“打扫”,只会越解决问题越多,越打扫越会变成一团乱麻。
这也许是因为,在妈妈出生、成长的年代,没有所谓的“生活美学”,大多数人对待生活,与其说是粗暴,不如说是随性。如今,我们和妈妈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她转发的《是中国人就转起来》《20种千万不要碰的食物》之类的文章,我们只能装作没看见,不然呢?我们需要她操心的事越来越少,她能告诫我们的就只有“吃好喝好”了,不然呢?
尽管我们都还怀有对彼此的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