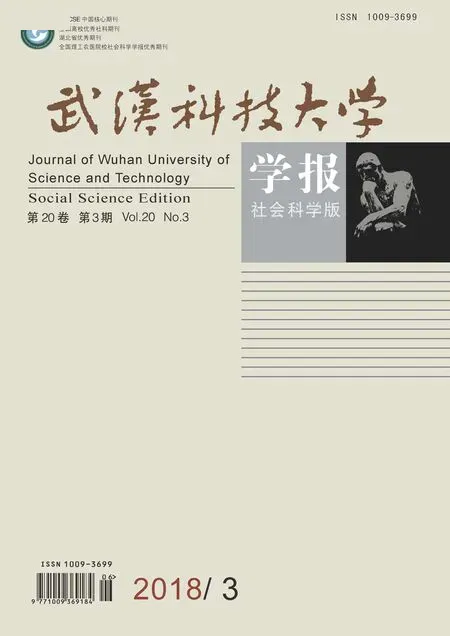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国外世界公民教育研究
周 金 华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于“世界公民”的探讨,可以用“微微弱弱和断断续续”来形容,对于公民教育研究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的民主理论与公民身份问题上。而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公民以及世界公民教育逐渐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世界公民教育给予了高度关注,该组织隶属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提交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该报告指出:“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的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1]鉴于此,本文依据相关文献,对新世纪以来国外世界公民教育的目标、焦点和路径等进行梳理,以期对正在推进的我国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一、新世纪以来国外世界公民教育概况
进入新世纪,“9·11”事件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贫困、不平等、不公正等现象与恐怖主义活动之间的关联,加深了人们对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理解。奥德丽·奥斯勒(Audrey Osler)和克里·文森特(Kerry Vincent)在《公民身份和全球教育的挑战》一书中写道:“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及其后果强化了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教育青年人准备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需要。这个袭击的规模和震撼程度使得青年人(和成年人)感到脆弱和无力。其回响不仅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被感受到了,而且在全世界的地方性社区也被感受到了。”[2]4-5美国教育思想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延续她在《培养人性》这本著作中的思想,并对世界范围内公民教育中的弊端与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努斯鲍姆认为,不仅仅是看得见的危机,隐性的危机更为可怕,“我们正处在一场全球性危机中,它规模浩大,极为严重……我所说的危机尚未被大多数人察觉,如同癌症;对民主自治的未来,这场危机最终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教育危机”[3],这里的教育危机,指的是拼命追求国家利润的教育。加拿大政治理论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在“多元文化公民权”的框架下探讨了世界公民教育问题,他把它命名为“多元文化教育”[4]序xiii。
2002年7月17~21日,在意大利的贝拉吉奥(Bellagio)举行了“多元文化民族和国家中的族群多样性和公民教育”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论坛,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和公民教育专家能够认识与设计一种推进在民族和国家内所有群体参与、尊重并保持各自文化差异的公民教育相关议题。2014年6月24~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主题为“全球公民教育”欧洲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始于新的教育”口号。一些关于世界公民教育的国际合作也在展开,日本、加拿大两国2000~2001年进行关于世界公民责任的调研[5];2006~2009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开展第三次公民教育调查,即“国际公民与公民素养教育研究”,与此同时,一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加入到世界公民教育活动之中。2013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国际共识,全球公民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无论是在地方层面上还是全球层面上都能从事和承担积极角色,以应对全球性挑战,最终成为一个更公正、更和平、更宽容、更安全和可持续世界的贡献者。
世界公民教育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世界公民教育相关文献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迅速增长,进入新世纪以后稳步增长且进入深化阶段,最近8年的相关专著数量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
二、新世纪以来国外关于世界公民教育目标的建构
世界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开展世界公民教育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上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同化”策略,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所有群体分享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同化论策略的实质在于,它包含着由强势族群所设计的旨在促进自己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公民教育目标,剔除其他少数群体的文化特征。世界公民教育目标的制定,开始针对的就是这种同化论策略。但与此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族群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不平等地位,他们进而团结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世界的族群复兴运动兴起的大背景,其中,发端于民权运动的美国族群复兴运动影响最大。在族群复兴运动的冲击下,公民教育的同化论策略就愈来愈面临着诸多难题,这迫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对公民教育的目标进行重新界定。
世界公民教育的提倡者对于目标的建构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视角:
第一,世界文化共存的视角。这种视角,基于对过去冷战时期两极对峙的深刻记忆,特别是基于对“9·11”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反思的结果。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指出:“对西方而言是普世性的,对他者而言就是帝国主义。”[6]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如何能够和平共存成为世界公民教育的最为重要视角,体现在知识目标上,包括对于世界多样性和相互依赖的了解、对于和平与冲突的知识性理解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了解;体现在能力目标上,包括尊重他人和事物的能力、合作和冲突解决的能力;体现在态度与价值观上,包括对同情的理解、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承诺以及珍视和尊重多样性等。“道德世界主义”可视为该视角的同盟军,帕瑞克(Bhikhu Parekh)认为,基于共同人性,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性相互依赖,我们不仅对于我们的公民伙伴具有特别责任,我们也对于我们的人类伙伴具有责任,包括不妨害他们福祉并且在能力范围内有责任加以推进,作为公民,我们应当充分考虑这些职责来定义我们的集体福祉[7]。
第二,应对当前“危机”的视角。这里的“危机”,既包括教育本身存在的危机,更包括那些并非依靠一个国家能够得到解决的全球性危机。玛莎·努斯鲍姆认为当前“全球性的教育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如果说努斯鲍姆指出的危机是隐形危机的话,那么,还有更为紧迫需要及时加以处理和应对的显性危机,如生态环境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为应对危机,世界公民教育目标就必须做出相应变革,如果说纠偏当前风靡世界的“盈利导向”教育的措施是加强人文教育,那么,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则必须加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教育,使受教育者关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一般认为,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是蕴蓄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从根本上应对和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在文化体系上理解世界上的族群、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在情感和态度上珍视和尊重多样性,在行动上促进相互之间的包容与和谐,在发展上要注重全球公平正义等问题。
第三,国家建构的视角。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国家内部日益增加的族群、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多样性正迫使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现存的公民身份和民族性概念。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国家必须围绕一系列他们认同的民主价值观来整合不同的族群,这就需要进行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传统的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必须补充一些“世界主义”的要素,即进行世界公民的知识、能力和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总体而言,对于许多西方国家而言,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捍卫和巩固自由民主制度,巩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确保他们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竞争中优势地位。
由于切入视角的不同,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世界公民教育目标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只是对所强调内容的排列组合和取舍的侧重有所差异。奥斯勒和文森特从价值、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进行界定,世界公民教育“旨在通过促进能够实现民主、发展和人权的价值、态度和行为来建构一种全球性和平文化”“为青年人和成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一起生活做准备”[2]1。
根据以上视角,归纳他们对世界公民教育诉求,我们可以从认知、能力、态度和价值观这几个方面来对近年来国外教育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世界公民教育目标进行概括。
世界公民教育的认知目标主要包括:第一,了解并理解世界上的族群、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多样性。当今世界存在着600多个语言群体和5000多个族群,同时还存有众多的文化、宗教群体,了解并理解彼此的不同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前提。第二,全球化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依赖和影响正在日益加深。“9·11”事件表明,单个国家谁也不能处理好一些世界性的重大问题,诸如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第三,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第四,和平与冲突相关教育,了解世界上冲突发生的原因,探讨促进和平的办法与途径。第五,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受众理解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消弭冲突、进行合作、关系和谐的重要前提。
认知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能力才能达成。这些能力目标包括:第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欧美教育界比较强调批判性思考,鼓励受教育者提出探索性问题,然后寻找答案,检验各种主张和论据,并判定其中要点的优劣。第二,有效讨论的能力。上述认知目标需要个体公民之间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对话,甚至慎思明辨方能达成共识。第三,挑战非正义和不平等的能力,也就是对于现实中遇到的非正义和不平等能够进行有效地挑战。第四,尊重他人和事物的能力。第五,合作和冲突解决的能力,即能够与伙伴公民或者非伙伴公民进行合作,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冲突。
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包括:第一,认同与自尊。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文化和价值认同。第二,同情。对于他者遭受苦难、不幸能够给予理解、关怀。第三,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承诺。从思想到行为致力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第四,珍视和尊重多样性。将文化、族群多样性看作是人类繁荣的保证。第五,关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资源环境日益趋紧的约束。
三、新世纪国外世界公民教育的焦点——多元文化教育
在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一般指的是,公众对于作为不同共同体的移民和少数群体的接受。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在语言、文化、社会行为上不同于主流人群,他们常常具有自己的社团和内部结构。多元文化主义也暗示,这些群体的成员在共同体中享有与主流人群平等的权利,而无需放弃他们自己的多样性,但他们常常需要认同特定、原属主流社会的关键价值。在西方社会,多元文化这个术语被以不同方式加以运用。史蒂芬·卡斯特(Stephen Castles)认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多元文化是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运用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本身就是广义的世界公民教育[4]18-48。
西方社会多元文化教育产生的背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族群复兴运动强烈地挑战了公民身份的同化论和生物学观念。美国的族群运动发端于民权运动,其反响遍及全世界。一些西方国家的原居民和少数族群,诸如美国的墨西哥裔、英国的黑人、加拿大的亚裔等,要求把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语言纳入国家文化并且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课程体系。这些群体也呼吁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对于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需要进行更多回应。原居民、少数族群和移民群体除了争取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也要求进行结构性变革以减少歧视、贫穷和妨碍他们成为社会完全成员的其他障碍。
多元文化教育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多元文化内容和性质角度,詹姆斯.A.班克斯(James A. Banks)将多元文化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承认文化多样性;其二,社会平等[4]3-16。从多元文化教育涉及的地域范围角度,金里卡把多元文化教育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在民族和国家的背景下多族群和多种族国家为促进国家的统一、团结所采取和运作的多元文化教育策略,该维度被称为国内维度;其二,超出民族和国家范围的多元文化教育,即跨国公民身份问题,特别是在移民群体范围内,尊重差异,尊重移民群体的亚族群身份,部分涉及到尊重移民群体与来源国维持密切联系的愿望[4]序Ⅴ-Ⅷ。这种教育过程的意图性后果是培养适应文化差异并且能够在范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成功生活的个体,像传统的多元文化教育一样,它寻求挑战传统价值观教育的陈词滥调和种种偏见,扩展人们的视野及促进人们进行文化间互动的能力。从正式的法律层面来理解这一点,这可能涉及到接受多重公民身份的理想,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它涉及到接受移民“跨国主义”的观念,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主义。
将班克斯与金里卡的分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多样性承认维度和社会平等维度应该都属于“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强调需要学习和尊重那些与我们共享一个国家共同体的不同族群的整全历史、认同和文化,把它作为使国家变得更正义和更具包容性的教育方式。而“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则主张学习国际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有影响力国际语言和文化,把它作为促进一个人在全球化世界取得成功的经济机会和文化资本,它针对和回应的问题有:一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国际竞争力;二是在跨国、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和平相处和合作。昂格(Aibwa Ong)认为,这种从国内多元文化向世界主义多元文化的转换是被一种新的跨国移民的欲望所点燃,他们持有一种强烈的与国家公民身份观念断裂了的工具主义的教育观[4]50-52。
主张“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的一些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关键点在于培养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世界公民教育应当帮助来自不同文化、种族、族群、语言和宗教地区的人批判地了解和审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忠诚,它在赋予受教育者维系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忠诚和认同选择的同时,也承认其他文化和认同选择。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要调整和修改学校课程,以便使它能够反映构成整个社会的各个不同族群的文化以及来自不同地方人们的文化。正如古特曼(Amy Gutmann)所指出的,民主的教育是以平等、宽容和承认为特征的。他认为:“忽略少数者受压迫和他们贡献社会的方式,不仅仅是不尊重那些文化,更为根本的是,不尊重那些认同这些文化的个体。民主社会应该平等尊重作为公共平等的个体,而不是群体,但是,不尊重一些群体传达的是不尊重认同那些群体的个体。”[4]80
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教育,实际上是希望公民教育的课程和项目应当帮助受教育者获得文化、国家、全球认同与忠诚之间的微妙平衡,即公民教育帮助受教育者获得不仅使他们能够适应他们自己所在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的态度、知识和能力,也能够理解和同情其他国家、地区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够适应世界共同体。应当产生对于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深思熟虑和清晰的认同,应当具有清晰的全球认同和对于自己在世界共同体中扮演角色的深度理解。同时,受教育者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和国家是怎样影响其他国家的以及国际事件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文化的、国家的和全球性认同与忠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对于公民来说,既具有一致之处,又有一些需要加以审慎处理的微妙差异。
“多元文化”之所以会成为西方世界公民教育的焦点内容,其原因纷繁复杂,但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西方国家国内由于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凸显,少数族群对于权利和正义的诉求需要得到回应;二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不同文化、宗教之间由于互不理解或者理解不充分导致的冲突需要得到化解;三是西方国家设想通过世界公民教育的实施,继续保持他们在世界上各个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
多元文化教育有时也以其他名目出现,并补充一些重要内容,如奥斯勒和文森特运用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丹麦以及荷兰的案例考察在世界公民教育方面机构和政府提供的支持情况。他们把世界公民教育定义为:“全球教育包括使年轻人和成年人准备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生活在一起的策略、政策和计划。它建立在合作、非暴力、尊重人权和文化多样性、民主和宽容的原则之上。它以在教育方法上基于人权以及鼓励批判性思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社会正义关怀为标志。学习者受鼓励将本地、区域和世界性议题相联系,以及应对不平等。”[2]2奥斯勒和文森特认为和平教育、人权教育和民主教育应该是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世界公民教育实施的路径
对于国外世界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考察,可以从主体、课程、过程以及评估等方面进行。世界公民教育实施主体的层次直接反映了世界公民教育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过程和效果。一般而言,世界公民教育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国家、学校、公民社团以及国际组织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相关文件充当着风向标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现有的世界治理和国际关系框架下,国家是世界公民教育最为重要的实施主体。即便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所提出的世界公民教育纲领,也需要得到国家机构的有力支持才能得到落实,国家的政策更是直接决定了公民教育落实和公民社团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所制定的有关文件具有纲领性作用,许多国家都结合本国国情参照执行,以培养受教育者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其中,核心能力:①对全球性议题、发展趋势的理解,对于关键性价值,诸如和平、人权、多样性、正义、民主、关爱、非歧视、宽容的理解和尊重;②批判性、创造性、创新性思考,解决问题和做决定的认知能力;③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进行互动交流的人际间交往能力和态度;④发起和从事前瞻性行动的行为能力[8]。联合国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反映了“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对世界公民教育的新认识。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国家层面对于世界公民教育日益重视,特别是美国,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认识,而且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美国人重新认识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重新进行战略调整。200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编制并发布了《美国教育部2002~2007 年战略规划》,该规划特别强调教育与国家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及反恐战略中的“利益”之间的联系。在加拿大,多种形式的世界公民教育已经融入了学校教育。威尔士政府将世界公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嵌入到教育教学各项活动之中,政府为高等教育提供包括财政在内的各种支持。
具体而言,西方国家世界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设显性课程。国家的重视,为学校和公民社团进行各种形式的世界公民教育提供了稳定的动力。关于世界公民教育的课程,各国的通行做法,一般是分年龄分阶段对公民进行世界公民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与态度教育。澳大利亚的世界公民教育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特色,其课程大纲作出如下安排:①意图。澳大利亚的“公民学”和“公民资格”作为义务教育课程,要求发展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能力和品性。②课程组织。澳大利亚课程大纲把“公民学”和“公民资格”划分成两条互相关联的线——知识与理解、技能,世界公民教育的因素渗透其中。③课程内容。“公民学”和“公民资格”从3岁就开始学习相关内容,诸如相互联系的世界、全球污染、气候变迁等议题逐渐介绍给学习者[9]。课程大纲为学校和教师提供了指导方针,规范了世界公民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必要内容。
第二,使学习者在亲身实践和体验多元文化中形成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多国家都注重在实践中开展教学活动,经常性组织学习者参观考察政府机关、历史博物馆和艺术馆等,使学习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还强调讨论的重要,经常性组织学习者开展讨论,并往往从一些地方性议题逐渐扩展到全球性议题,帮助学习者把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全球议题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学习者提高批判性思维和交流能力;再就是充分利用媒体,关注有关“冲突”议题,研究不同视角下的观点,增强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三,鼓励跨国学习交流。近几年,美国高等教育改变过去单纯注重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单一战略,逐渐转向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本国学生出国学习的新政,美国大学越来越多与外国教育机构建立学术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加大学生交换与师资交流力度。明尼苏达大学的霍恩(Aaron S.Horn)和弗莱(Gerald W.Fry)提出了通过到国外学习来促进世界公民教育等措施。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海外留学奖助委员会在2005 年11 月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全球竞争与国家的需要——百万人海外留学”计划,旨在通过塑造世界公民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第四,世界公民教育的实施遵循“学习-思考-行动”的流程。学习就是探讨一些“重大”议题,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并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思考就是批判地考察我们可以对议题做什么,并且把它与价值观和世界观联系起来;行动就是作为积极的全球公民(或个体或集体)针对议题所采取的做法。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西方国家将大学生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重点人群。美国许多大学都将“世界公民”教育列为艺术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并围绕“世界公民”教育课程实施的需要设立了一系列训练和评价标准。
第五,对世界公民教育实施评估。这在世界范围内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新颖的课题,威尔士、加拿大和荷兰等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相对而言,威尔士的“审查高等教育大学可持续性课程工具”评估体系比较完善。该评估体系对所有本科教学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进行系统的课程审查,通过为可持续性课程的内容打分来对所学课程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课程内容则划分成“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或“跨学科的”等主题,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评估含有可持续课程内容的比例以及这些内容是否强调了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迁、贫困和多样性等问题。这种方法论不仅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内容之间的“平衡”,而且由于选项设置提供了有深度的单元或细节内容,从而使得评估也较为深入。当然,这样的评估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如审查评估只能反映课程提供的内容如何,但是不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要真正全面准确地评估世界公民教育的效果还需要其他的补充性评估。
五、结语
如果说冷战终结使得世界公民教育在上个世纪末得以复兴,那么“9·11”事件则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公民教育在全球范围向纵深拓展的重要催化剂。对于世界公民教育的讨论,发端于政治理论界,但其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却在教育界。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为了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有利位置,为了多元文化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欧美许多国家进行了不同形式世界公民教育的探索。
在目标建构上,为世界公民教育所制订的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平、社会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目标,都是当今世界全球化迅猛发展、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环境危机凸显、冲突频繁的大背景下亟需提倡的,这是世界走向和平、安宁的必要条件。一些国家应对危机的工具主义视角需要加以矫正,应该确立真诚的世界共存的视角。该视角的确立,需要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政府和公民彻底放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真诚面对国家关系历史和现实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切实负担起应有的责任,平等对待世界其他族群和文化。
多元文化教育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重视,但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潮,即便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由于它对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形成挑战,在广泛传播和渗透的同时,能否有效达成其目标也值得怀疑。文化承认维度和社会平等维度触动了西方社会主流群体的传统利益和价值观,受到抵制是必然的。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培养超越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目标,与主流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冲突,如何使受教育者在族群文化、国家、全球认同与忠诚之间保持微妙平衡,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
近年来,在世界公民教育的实施上,国家作为主导者通过制定政策、配置资源等方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很多西方国家在赢利导向牵引下的所谓“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工具主义做法会损害教育的整体效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对于域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世界公民教育的探讨,总结他们在教育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在实践中推进的世界公民教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相互理解、合作与包容,世界公民教育是达成该目标的重要环节。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利益、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载入联合国文件,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向纵深推进,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培养中国公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和素养,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是我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
[1] 联合国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34-35.
[2] AudreyOsler,KerryVincent.Citizenshipandthechallengeofglobaleducation[M].London:Trentham Books,2002.
[3] 玛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M].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
[4] James A. Banks. 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global perspectives[M].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2004.
[5] George H. W. Richardson, David Blades.培养全球观:日、加学生对于世界公民责任问题的看法[J].比较教育研究,2002(S1):237-243.
[6] 奥特弗利德·赫费.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M].沈国琴,尤岚岚,励洁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57.
[7] Bhikhu Parekh.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 citizenship[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29 (1):3-17.
[8] UNESCO.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an emerging perspective[EB/OL].[2017-09-05].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41/224115E.pdf.
[9] MurrayPrint.Aglobalcitizenshipperspectivethro-ugh a school curriculum[M]//R.Reynolds, D. Bradbery,J.Brown,et al.Contesting and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Global Education.Rotterdam:Sense Publishers, 2015:18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