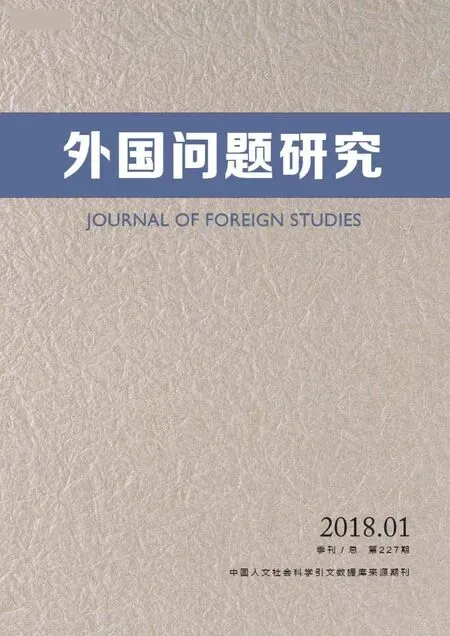语言学与思想史双重视域下解读荻生徂徕《译文筌蹄》
张 妍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荻生徂徕(1666—1728),姓物部氏,字茂卿,号徂徕,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古文辞学将日本的古学推向了顶峰,是江户思想史研究中难以绕开的人物。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围绕着荻生徂徕及其古文辞学展开了研究,研究成果可谓是车载斗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徂徕学”研究。①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子安宣邦:《徂徠学講義》,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谱考》,東京:平凡社,1984年;岩橋遵成:《徂徠研究》,東京:名著刊行会,1969年;野口武彦:《荻生徂徠:江戸のドン·キホーテ》,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田原嗣郎:《徂徠学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今中寛司:《徂徠学の史的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2年;高橋博巳:《江戶のバロック:徂徠学の周辺》,東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小島康敬:《徂徠学と反徂徠》,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 年;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等等。然而,其中关于徂徕的首部著作《译文筌蹄》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则略显单薄,因此,本文从语言学视域下深入解读徂徕对“和汉”两种语言所作的转换工作,进而从思想史的视域下探讨《译文筌蹄》与后来古文辞学形成的关联脉络。
一、荻生徂徕的启蒙教育与《译文筌蹄》的问世
与江户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徂徕早年的独特启蒙教育对其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至深且巨:一是其父荻生方庵对他“口授笔受”的“书记”训练,一是跟随其父的南总流放经历,这两段经历与《译文筌蹄》的问世紧密相关。
徂徕在《译文筌蹄·卷首题言》中叙述道:“七八岁时,先大夫命予录其日间行事,或朝府、或客来、说何事、作何事,及风雨阴晴,家人琐细事,皆录,每夜临卧,必口授笔受,予十一二时,既能自读书,未尝受句读,盖由此故。”*荻生徂徠:《譯文筌蹄》,《荻生徂徠全集》(第5巻),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年,第20頁。这意味着,徂徕在未接受正式启蒙教育之前,先受到其父方庵的“书记”训练,运用汉文书写是当时社会的风气,徂徕每日所记日常之事皆以汉文书写,这种训练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徂徕能在未学句读的情况下已能独自读书。也就是说,徂徕最先接受的教育不是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朱子学说教,这是徂徕与其他学者的主要不同处之一,而这一特殊训练对《译文筌蹄》的写成以及古文辞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吉川幸次郎在《徂徕学案》中高度评价了徂徕的这一经历,认为:“徂徕后期古文辞学的最初萌芽可追忆于此。不单是对于言语,徂徕以自身的体验来把握学术态度也根源于此。”*吉川幸次郎:《徂徠学案》,《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73 年,第641頁。
如果说“口授笔受”的“书记”训练是徂徕写成《译文筌蹄》的第一个诱因,那么,“南总流放”的经历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十二岁前后,徂徕在林凤冈门下学习朱子学,但时间不长,他因父亲获罪于德川纲吉而全家被流放于上总国本能村,即“南总”。徂徕在《送冈仲锡徙常序》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流放经历:“余幼从先大夫,逊于南总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诸侯所不国,君子是以弗居,乃田农樵牧海蜑民之与处,性好读书,书无可借,无朋友亲戚之驩者,十有二年矣。当此时,心甚悲以为不幸也。然不染都人之俗,而娴外州民间之事,以此读书,所得皆解,如身亲践,及后遇赦得还,乃与都人士学者相难切,寡陋之学,或能发一识,时出其右,由是遂窃虚誉于海内者,南总之力也。假使予有天幸,而生不离都下,何以能尔,亦唯得为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尝谓南总沐惠广恩者,为多于藩邸接见时,为是故也。”*荻生徂徠:《送岡仲锡徙常序》,《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3巻),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第114頁。其中的“藩邸接见”是指柳泽吉保对徂徕的知遇之恩,对此,有学者曾言道:“徂徕为天下之徂徕,实因柳泽吉保的勃兴而由其所拔擢是最大的因由……他被柳泽氏所识,正所谓蛟龙得云,他的天禀之才能于此得到无遗憾地发挥。”*岩橋遵成:《徂徠研究》,東京:關書院,1934年,第119頁。
然而,在徂徕看来,他后来之所以名扬海内,全靠南总之力,甚至超过了“藩邸接见时”,这在徂徕的著作中多次有所述及,可见其对徂徕的重要意义。那么,“南总”的哪些经历对徂徕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根据《送冈仲锡徙常序》所载可知,徂徕长期与田农樵牧海蜑之民相处,深刻体会到了“民情”,这是从书中难以直接领悟到的内容,为后来徂徕从政后处理“道入弃亲”事件提供了参考;然在这一期间,徂徕所读之书虽只有《大学谚解》一书,但从书名可知,该书为朱子学著作无疑。故可说,徂徕早年是受到朱子学启蒙而开悟的。徂徕在南总期间的读书未受到正规的“世师讲说”教育,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说教,同时,也不受“江户都人之俗”的影响,完全是自己揣摩、体悟而读书,尤其是基于“民情”的读书法使其把读书和实践紧密结合,进一步领悟到了书中的内涵。所以,徂徕在二十五岁时因父亲被赦免而回到江户之后,发现南总期间的读书心得与江户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主要与当时盛行的教育方法格格不入。而且,回到江户之后的徂徕又陷入生存危机,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收徒讲学,*原念齋等:《先哲叢談》,東京:有朋堂書店,1928年。但其教授学生的方法完全是徂徕自身体悟出来的新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徂徕将这一新教法的主要内容口授出来,后经僧天教与吉臣笔录而成之,此即《译文筌蹄》。
二、《译文筌蹄》对日本传统“汉文讲授法”的批判
从《译文筌蹄》的书名来看,“筌蹄”二字出自《庄子·杂篇·外物》,即:“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其中的“筌蹄”常被用来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意味着,徂徕以“筌蹄”作为书名是在强调“译文”的手段或工具,而其中的“译文”显然是指“中文”翻译成“日文”。其中,《译文筌蹄》凸显的内容正是徂徕对传统汉文“翻译法”和“讲授法”的批判、质疑以及否定。
在江户之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可谓是源远流长,甚至日本语言文字的形成也与汉语的影响密切相关,从中国唐代开始,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将汉字及汉语引入日语之中,丰富了日语的内容。重要的是,日本人在学习汉文的过程中为更彻底地吸收、理解中国文化,创造了一种独到的中日文“翻译法”——“训读”。按照“训读”的方法,并不是把全部汉文直接翻译成日语,它是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却不使用汉语的读音而是采用日语的读音,但由于日文的语序与中文的语序完全不同,所以,“训读”法在保留了汉文句子成分的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日语助词,并在汉字旁边标注训点来改变语序以及提示读音。*沢田総清:《漢文教授法概説》,東京:芳文堂,1937年,第131—149頁。从平安时代开始,历经镰仓、室町时代,日本人主要以“训读”方法研习汉文文献,并持续到江户时代,以《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为例,日语训读之后为:“人(ひと)の始(はじ)め、性(せい)本(もと)善(ぜん)。性(せい)相(あひ)近(ちか)し、習(ならひ)相(あひ)遠(とほ)し。”*磯村少苟:《三字経訓読及精解:評註》,東京:黄石洞書院,1935年,第2頁。在今天看来,“训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翻译,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汉日”翻译,一方面它保留了所译语言(汉语)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又有日语的内容。然从语言学视域来看,日本人之所以使用“训读”的方法与中日语言的差别密切相关。从中国语言发展史考察,当时中国盛行的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的语法性特征较弱,并大量使用省略句式,且缺少助词,而日语则与之明显不同,助词极为丰富,这就促使“训读”方式的产生,也就是说,“训读”方式的出现以及能在日本盛行了一千多年正是日本人利用了汉语的不足而发挥了日语的优势,为日本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日语独立性的特征却并不明显,反而使两种语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然而,对徂徕而言,由于长期的南总流放,使他少年时代未接受这种“训读”教育,所以,他回到江户之后对“训读”的教育方式极不适应,并在收徒教学过程中对“训读”及当时盛行的讲学方法产生了质疑,认为,汉语和日语是两种语言体系,日汉差异犹如日语和荷兰语的差异,即是“训读”采用了颠倒顺序(回环之读)的翻译法,虽有可通之处,但实为牵强附会之举。*荻生徂徠:《譯文筌蹄》,第19—20頁。因此,徂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主流教育的“十大弊端”的根源正是“训读”方法,因为经过“训读”之后的“汉语”,已不再是“汉语”的真面目,而是“似是而非”的日语。重要的是,讲师通过“训读”法来阅读中国儒学经典,完全是凭借“己意”来理解,事实上已背离了儒学典籍的本旨,况且,他们又将自己所理解的内容教给学生,而学生所学的内容完全来自讲师讲授,不是“读书”而是“听书”,所学内容更是错上加错。所以说,徂徕从语言学的角度不只意识到汉语和日语的差别,更是指出了“和训”法所造成的弊端,非但对汉语学习和阅读中国儒学经典无所裨益,反而抹杀了日语的意涵,因此,徂徕提出了新的解读方法。
三、《译文筌蹄》的新译法及其与古文辞学的内在关联
在《译文筌蹄》中,徂徕在指出“和训”弊端的同时,更是提出了新的学习汉文的方法,其直言道:“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荻生徂徠:《譯文筌蹄》,第19—20頁。
这意味着,徂徕认为学习汉文新方法的第一步即为“崎阳之学”,所谓“崎阳之学”是指日本长崎之人所通用的学习汉语的方法。如众所知,江户日本虽采取了锁国政策,但保留长崎一地与中国、荷兰保持贸易往来。因此,长崎人懂得汉语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可不是通过“训读”来学习汉语,而是直接将汉语翻译成通俗日本语,所以,徂徕对这一简单的做法极为赞同。紧接着,徂徕认为,初学汉语者不宜先学的中国儒学经典,应学习汉语的日常用语,并使用汉语的发音而不采用日语的读音,然后再把汉语翻译成日本的俚语(民间非正式、较口语化的语句),在此基础上,才能较容易地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摆脱“和训”之法对汉语学习的束缚,否则将事倍功半。
同时,徂徕特别强调这一“译以日本俚语”的方法对于“和训”的优越性,在他看来,“和训”出自古代搢绅先生之手,他们务捡雅言,简去鄙俚,使用的语言词汇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而俗语、俚语则不同,它们平易而近于人情,用此而翻译中华文字,能使人不生奇特之想,不生卑劣之心,更贴近中华圣者之道:“而谓圣经贤传,皆吾分内事,左骚庄迁,都不佶屈,遂与历代古人,交臂晤言,尚论千载者,亦由是可至也。是译之一字,利益不尠,孰谓吾好奇也哉!”*荻生徂徠:《譯文筌蹄》,第18頁。所以,在《译文筌蹄》中,徂徕收录了二千多个常用汉字,将意义相近的汉字列为一组,如“闲静靖恬寂寞寥阒舒徐谧”、“动摇撼荡”、“安宁康逸泰休绥妥易晏保”等,先用日语俗语解之,然后再引用中国经史子集的内容进一步补充说明,例如,对于“闲”字,译作“ひま”、“むだ”,并引唐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来进一步解释“闲”字。又如“撼”字,译为“ゆるがす”,《诗经》“无感我帨”中的“感”实为“撼”的古字通用。所以说,徂徕的翻译法使汉字的字义更加通俗易懂,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典籍的学习与理解程度。
很明显,徂徕的翻译法在日本语言学史具有重要意义,且对日本人学习汉语有极大的裨益,对此,有学者指出:“徂徕思考的不仅仅是语句文本的翻译,而是如何实现跨文化、扩文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极富前瞻性。”*刘芳亮:《荻生徂徕的翻译思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然而,徂徕的这一“新方法”在江户日本却没有盛行起来,多半被其弟子们所继承,究其原因,与“和训”在日本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密切相关,而徂徕提出采用“汉语发音”的主张,与日本传统的做法格格不入,最终难以推广。但是,跳出语言学的局限,从思想史的脉络考察,《译文筌蹄》的成书对徂徕“古文辞学”形成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以往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以学术分期的方式探讨徂徕“古文辞学”形成的时间,吉川幸次郎认为,徂徕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为古文辞学者。*吉川幸次郎:《徂徠学案》,1973 年。今中宽司在《徂徠学の史的研究》中,以徂徕四十四岁写成《蘐园随笔》为古文辞学开始的标志。*今中寛司:《徂徠学の史的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2年。韩东育及董灏智在研究中皆以徂徕写成《读荀子》一书作为古文辞学的开端。*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董灏智:《儒学经典结构的形成及其在近世日本的变迁》,博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这些说法对徂徕古文辞学的形成标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对此不再赘言,而是特别强调《译文筌蹄》与“古文辞学”的内在关联。
如前所述,“南总流放经历”对徂徕的影响至深且巨,这自是毋庸讳言,但南总归来后写成的《译文筌蹄》虽未直接促成徂徕的学术转型,却更加坚定了徂徕对汉语的认识,并积极使用他的汉语学习法来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典籍,并继续批判“和训”方法,甚至指出,江户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最大失误正是以“和训”阅读中国宋儒的著作,进而曲解了“圣人之道”。他说道:“此方读字,有音,有和训。和训又与和歌语俚语不同,而以音读之,大觉高远艰深,远于人情,以和训读之,乃觉其平易,近于人情,更换以俚语,愈益平易,同一字而其殊如此者,皆声响所使,不啻此焉,如华人于其言语,亦皆义由音响而殊也。此方学者,误会圣贤之言,皆多此累。予近学华音,识彼方俗语,而后所见愈转平易,由此推之,仁斋所误亦未免此耳。”*荻生徂徠:《蘐園隨筆》(巻2),《日本儒林叢書》(第7巻),東京:鳳出版株式会社,1978年,第26頁。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徂徕在发现语言有“和汉”差异的基础之上,更意识到汉语也有“古今”之别,江户日本所学的汉语并不是汉语的本来面目,而是宋代的汉语,更为重要的是,徂徕由此意识到,宋儒所提倡的儒学亦非孔子儒学的原旨,而是宋人添加、改造的。所以,先秦儒学才是真正的儒学,三代以下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同时,徂徕“古文辞学”中非常重要的“人情论”特征亦在《译文筌蹄》中初见端倪,他言道:“予读三代以前书,人情世态,如合符契。以此人情世态作此语言,更何难解之有也……”*荻生徂徠:《譯文筌蹄》,第17—18頁。所以说,《译文筌蹄》对徂徕“古文辞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从比较语言学的视域考察,《译文筌蹄》的语言学特征是极为明显的,但是,《译文筌蹄》的学术价值不只局限在语言学的范畴之内。徂徕“古文辞学”的端倪已暗含其中,这对江户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从语言学与思想史的双重视域下解读《译文筌蹄》,无疑更接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