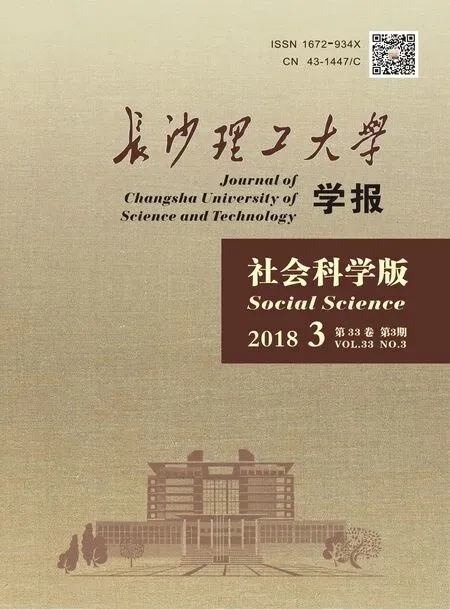技术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兼评易显飞《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当代社会研究》
车 辕,陈浩凯
(1.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2.长沙理工大学 科研部,湖南 长沙 410114)
工具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意味着“技术”成为了人们同周遭世界打交道的中介和方式,人类进化的历史与技术发展的历史交融在一起。人类并不与周围世界直接接触,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在文化上是以语言、技术和艺术为中介的[1]。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术具有“生产、生育和造成”的意思,在他看来,“质料”本身是被动的,是没有灵性和活力的材料,是一种“潜能”;而这种潜能如果要成为现实,就必须获得“形式”;质料获得形式之后,也就成为了“技术制品”。基于此,透过技术这种现象,我们能够领悟到人的本质。进入到工业社会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技术垄断”这一新的难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甚至成为了技术统治的“奴隶”。面对如此的情形,哲学家弗洛姆发出震耳发聩的声音:“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一切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2]因此,如何反思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解决技术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就关乎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走向。易显飞教授等著的《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当代社会研究》(以下简称为《创新》)一书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刻地阐述与论证。
一、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
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本身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肢体。”[3]这也就说,人们不再像动物一样,通过肉体和器官直接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借助于劳动资料将自己身上的自然力以活动的方式传导到自然物质之上,而自然物质也就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人所需要的、满足人的价值的物质形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劳动资料也就体现为“技术”。在对技术的诸多定义中,取得较大共识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是人同自然界打交道的一种中介方式和手段。劳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大工业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同样,我们也可以将工业“替代”为技术,认为技术的历史和技术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创新》一书也敏锐地分析了中国和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上产生区别的原因,指出中西方在是否追求对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作出理论解释上背道而驰,而这恰恰是人类能否跨越“自然技术阶段”迈向“现代科学技术阶段”的分水岭。古代中国人擅长经验思维,技术的使用是在经验活动之中总结出来的,对于技术本身日用而不知,并没有对之进行自觉的理论性思考。而西方受到古希腊文明理性精神的影响,对于技术的运作机理有着追根溯源的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验性的思维方式虽然使得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产生,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的经验性思维方式完全一无是处,毕竟,它孕育了整个古代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中国丰碑。而且,随着西方世界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人们在工业社会之后开始大规模、深层次地征服与改造自然,自然生态开始严重失衡与日益恶化,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这正是技术理性思维不断膨胀,反过来控制作为主体的人所造成的恶果。而中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形成的是敬畏自然、追求和谐的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观念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可见,当代“技术问题”或“技术与社会”问题的求解,似乎都要从中国古代那里去寻求智慧。
二、作为异化状态的“技术垄断”
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跨入到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和技术开始走出最初的混沌状态,逐渐从社会母体中分离开来,并逐步摆脱社会的控制,独立性愈来愈强。美国思想家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技术垄断”。在“技术垄断”的状态下,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资源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文化的不断丧失和道德水平的逐渐下降。“技术垄断”带来的危机不仅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人类价值和道德的堙灭。与这一判断相呼应,《创新》一书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相应描述:“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为日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埋下了祸根;农田变城市的极度扩展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高节奏、强竞争的生活加重了人的心理负担和生理不适,人们的心灵家园逐渐荒芜;人际交往中的‘金钱至上’和‘物质主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远,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厚重,人们逐渐囚禁在自己所打造的物质囚牢里”[4](P123)。
由于出现了技术“控制”人的状况,因此人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有时并没有“体现”自己的本质。正像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异化的状态描述的那样:“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马克思指出,在中世纪,虽然工匠们完全被其所从事的工作所占据了,但是他们对于其工作保有兴趣并且对于工作的技术非常熟练,甚至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艺术性,因此工匠的技艺也就展现出了个人的技术和才能,他们在工作中也就获得了满足和肯定,这个过程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朴素结合。然而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工人与自己的工作是相分离的,他们对之也并不关心,这是因为不是工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工人,人成为了技术的“奴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每个工人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动,表面看上去有了自己选择工作的“自由”,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可以被替代的“零件”,他们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了,而是被“同质化”了,人们也就失去了其独一无二性和不可被取代的价值。在这样一种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是相向而行,而是渐行渐远。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技术的膨胀对于自然无外乎变成了一场浩劫,影响了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一现状,哲学家罗尔斯顿开始猛烈攻击“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伦理学的旗帜,强调自然界本身的“内在价值”。实际上,真正的人本主义从不贬低自然的价值,恰恰相反,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与人类成为休戚与共的统一体。自然界哺育了人类,人类都是从自然的“子宫”之中孕育而生的,但当人类用技术的手段来侵占与欺凌自然时,自然与人天然的母子关系就被亵渎了,这也是“技术垄断”所带来的生态道德上的紊乱。
对于上述问题,《创新》一书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虽然给现代人创造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期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这种控制使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4](P176)技术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手段或者一种人类活动,然而现代技术却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全新的东西。现代技术的本质已经脱离了满足人的需要的这一素朴范围,而变得与人的负相关性与日俱增,其本质变成将万事万物优化配置成为越来越高效率的纯工具。也就是说,人已经不是目的了,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最优排序”,纯粹为此而已。
三、对于技术的审视和反思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理性和经济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构架统治了当今的我们,这种框架使得人和事物都被限定在特定的技术需要之上。比如一个现代大型客机,从它的技术本质上来理解,并不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对象,而是运输系统中一个灵活而高效的齿轮而已;与之相类似,我们也不是使用运输系统的主体,而不过是被运输系统用来“填满”飞机而已。在这种技术视野之下,之前人们所设定的一些最终目的,比如服务于上帝、社会、同胞或者自身也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了。这样一来,人反而成为了被使用的“资源”。海德格尔所担心的是对于存在的技术化理解而导致的人类危机,而非具体的技术手段所带来的毁灭。由此,海德格尔区分了技术所导致的当下问题,包括生态破坏、消费主义等,以及如果靠技术来解决所有问题所导致的毁灭性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并不是反对技术,而是说只有当技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且跳出技术思维的框架,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之进行审视和反思。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技术制品的形成过程中,有四个“因”共同作用,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提供的是材料基质,形式决定了事物的本质,这种形式是通过人赋予事物的质料的,也就使事物从潜能变为现实。制作者用形式去加工质料,制作者也就成为技术制品的动力因。而目的因就是制作者为何去制作技术制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目的因”是最重要的和最权威的。技术目的可以分为为了生活所必需的“实用性”目的,以及不是为了生活所必需的“非实用性”目的。即是说,技术不仅仅满足的是人的物质性需求,而且还满足的是人的精神性需求。虽然技术目的各有不同,但是最终都指向的是最高的“善”。马克思也强调,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带有人的自觉的目的性[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反倒要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基础和前提,生态文明并非回到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6]“经济学家们便将生产功能解释为技术变迁或技术创新表征,生产动能曲线运动就是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7]实际上,对于上述关于技术的反思或审视,《创新》一书也强调,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有自觉的目的作为引导,技术和人性是无法割裂开来的,技术使用情境的建构依赖于使用者整体人性中真、善、美的支撑,人人都具有同情和恻隐之心,都在渴望着美丽而干净、快乐而充实的生活图景。因此,要实现“以人为本”和技术创新的人性化,由原来的纯“工具理性”的经济化技术创新转向充满“价值理性”的生态化技术创新。作者基于技术的反思或审视,从价值与伦理观、文化观、教育观、技术社会观等方面,构建了解决技术创新价值危机,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也唯有如此,技术创新方能真正实现“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2]。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它的魅力取决于它与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创新》一书,技术哲学是其写作构思的理论基础之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走出了“书斋哲学”,紧密联系经济、人文、生态、法治、创新型国家等现实问题来探究技术创新,体现了作者关注现实的情怀。但是,作者又不局限于此,而是通过探究这些现实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带有的普遍性问题,当对这些普遍性问题进行学理反思时,其研究的哲学特性又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Petran Kockelkoren,Inside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5:151.
[2]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9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2.
[4]易显飞.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当代社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4.
[6]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J].哲学动态,2016(1):47.
[7]李三虎.论创新行动的表征性和非表征性[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