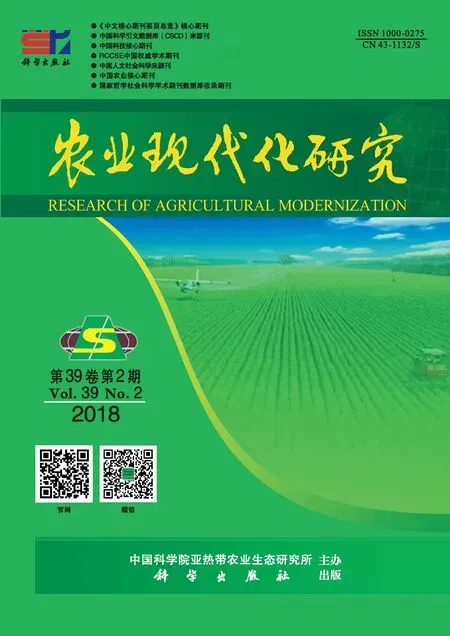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分析
——基于10省(自治区)奶农的调查
吴强,沙鸣,张园园,孙世民*
(1.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00)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原奶生产国。第七届中国奶业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奶牛存栏1 507万头,原奶产量3 755万t,比2010年分别增长了6.13%和5.02%。奶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者的饮食结构和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奶农质量控制行为不够规范,导致“药物残留超标”、“添加违禁物品”等事件时有发生,既影响着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又严重制约着中国乳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何应对乳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学者和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亟待解决。国内外乳品质量控制的经验表明[1-3],优化乳品供应链中各主体行为、改善主体间合作关系和发挥乳品供应链“自组织”作用,是解决中国乳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作为乳品供应链的源头,奶农关于质量控制的认知水平与行为特征将直接影响奶牛健康状况和原奶质量安全,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物使用、疫病防控、档案记录和动物福利等方面。Shaw等[4]分析了密歇根州的兽医、奶农和乳品加工企业对激素的认知、态度和行为。Dernburg等[5]调查并评估了法国奶农对奶牛诊疗记录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对抗生素使用的记录情况,并建议改善奶农的档案记录行为,应侧重于教育和奖励。Sorge等[6]对加拿大238家奶农的牛结核病控制程序执行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加强与奶农的沟通与交流能够改善奶农疫病防控行为。Jones等[7]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奶农抗菌药物使用态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奶农使用抗菌药物的意愿与社会的引导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并建议管理者向咨询机构尤其是与奶农频繁接触的兽医普及抗菌药物的科学使用及经济做法。Cardoso等[8]研究发现奶农普遍认为产量比犊牛的福利更重要,故乳品企业及相关专业人员应向奶农普及动物福利的重要性和科学做法。Jones等[9]的研究发现欧洲奶农改善奶牛健康状况的目的是获得更高的产奶量、良好的繁育能力、较高的效益和工作满意度。Kayitsinga等[10]基于美国东部1 700家奶农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该地区奶牛乳房炎治疗行为选择状况,并认为奶牛乳房炎诊疗记录行为需进一步规范。
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奶农质量安全行为和原奶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李红和常春华[11]基于内蒙古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奶农饲养行为、消毒行为和挤奶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技术指导、对食品安全知识的了解对奶农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钟真[12]对内蒙古奶牛养殖业的调查研究表明:散养模式下原奶质量安全水平主要受卫生环境、疫病防治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王莉和刘洋[13]基于内蒙古等地的调研数据分析认为,生鲜乳收购价格、土地与劳动力资源禀赋、资金支持是影响奶农养殖规模、养殖模式和机械化水平的主要因素。芦丽静等[1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证明了养殖小区模式下奶农质量安全行为(包括饲料购买、疫病防治、牛舍消毒等)与受教育年限、对检测指标的熟悉程度、政府监管力度和生鲜乳价格显著相关。刘明月等[15]研究发现,疫情认知对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有显著影响。吴强等[16]对全国10个省份的奶农质量控制行为实施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奶农的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质量控制行为。
综上可知,国内外相关学者已从某一侧面或地区对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关键问题开展了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较为领先且深入,但因奶牛养殖业发展程度、农户自身素质、监管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待检验。国内奶牛养殖业起步较晚,故有关原奶质量控制的研究与实践明显滞后,且涉及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的关键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文综合借鉴国内外研究思路,根据国内奶牛养殖特点及原奶质量安全属性,拟从供应链视角,基于认知行为理论[17-18],采用10省(自治区)569家奶农的问卷调查,从投入品质量控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环境质量控制和质量协同控制等4个维度8个方面分析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关系,明确质量控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纠偏措施,旨在为提高中国乳品质量提供现实参考与借鉴。
1 理论分析框架
奶农质量控制行为就是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并依据相关标准和规定,实施的相应质量安全管理活动[19]。认知行为理论从内在的认知和外在的行为两个方面来帮助决策者实现目标,其主要观点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就要首先改变人的认知。
参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高产乳牛饲养管理规范》强调的关键控制点,结合原奶质量的形成过程[20]和已有研究成果[11-16,21],本文将从投入品质量控制(奶牛、饲料、兽药和饲喂用水)、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原奶质量标准、设施配置、疫病防控和养殖档案建设)、环境质量控制(饲养环境和行为福利)和质量协同控制(合作协调)等4个维度分析奶农质量控制的认知与行为。
良好的投入品认知,即熟悉奶牛品种、饲料与兽药、饲喂用水的标准,能够指导奶牛、饲料以及兽药的采购行为,并且规范奶农的用水行为,以期获得产奶能力高、遗传性状好的奶牛,保证饲料的营养和兽药的疗效,维护原奶的理化和微生物指标。奶农只有充分理解原奶质量标准,才能科学和正确地选择质量标准,进而采取良好质量控制行为,维护原奶感官、理化和微生物指标。良好的设施配置认知,主要是指了解设施配置标准并能熟练掌握饲料加工技术,能够确保饲料加工、挤奶与冷贮等必要设施的完备性,提高饲料的营养性和适口性,改善奶牛的动物福利。良好的疫病防控认知,主要是指熟知常见疫病的传播途径和疫病防控要点,进而有针对性地预防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做到科学防疫。良好的养殖档案建设标准认知,能够提升养殖档案建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确保质量安全问题的精准追溯。良好的饲养环境标准认知能够改善奶农的选址、消毒、绿化和灭鼠灭蝇行为,进而避免疫病的交叉感染和细菌的滋生。良好的行为福利标准认知,能够促进奶农改善舍内环境条件,满足奶牛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健康和舒适需求。只有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才能积极主动地与乳品加工企业共同维护原奶质量安全。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图1)。

图1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由山东农业大学三农省情调研中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于2016年1—3月(寒假期间)实地调查获得,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56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29%。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奶牛养殖环节存在的问题,此次调研区域选择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共选取了10个省(自治区),除了湖南、青海和广西之外其余7个省份均属主产区,其中河北、黑龙江和山东属于东部地区,河南、内蒙古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广西、陕西、青海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问卷详细情况见表1和表2。
569名受访者中,男性占77.50%,年龄在30~50岁占62.92%,初中及以上学历占79.96%,从事奶牛养殖行业4年以上的占79.44%。此次调查地区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而且主产省份较多,受访者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从业时间较长,对奶牛饲养管理较为熟悉,易于把握和理解问卷内容,因此问卷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可信度较高。

表1 受访奶农的行政区域分布情况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3 奶农质量控制认知分析
3.1 投入品质量控制认知
投入品质量控制认知主要是指奶农对于奶牛(包括种牛)、饲料、兽药、饲喂用水等投入品的质量或使用标准的了解程度。奶牛生物学特性表明,奶牛、饲料、兽药、饲喂用水质量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原奶质量。调查表明,受访者对投入品质量或使用标准的了解程度堪忧,569家受访奶农中,27.42%的对中国荷斯坦奶牛标准表示“熟悉”,25.66%的对饲料质量标准“熟悉”,仅有25.49%的对用药标准表示“熟悉”,只有22.32%的对饲喂用水标准表示“熟悉”(表3)。可见,受访奶农对于上述投入品标准的认识很不理想,极易导致奶牛饲料营养配比的失衡以及兽药的误用甚至滥用,尚需相关部门加强对标准内容的普及。

表2 受访奶农所在地区与饲养方式分布情况Table 2 Region and feeding patterns of respondents

表3 受访者对投入品质量或使用标准的了解程度(%)Table 3 Quality or use standard recognition of respondents on the inputs (%)
3.2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认知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认知主要是指奶农对原奶生产过程中相关标准的了解程度和技术掌握水平,主要包括原奶质量标准认知、设施配置标准认知、疫病防控认知和养殖档案认知。
1)原奶质量标准认知。原奶质量标准是原奶验收的重要依据,认识与理解原奶质量标准是原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的前提条件。调查发现,569家受访奶农中,仅有63.44%的对原奶质量标准“熟悉”或“比较熟悉”。实践中,这种低水平的认知状况导致奶农的执行标准不够统一。
2)设施配置标准认知。调查显示,569家受访奶农中,25.31%的熟悉牛场设施配置标准,35.85%的比较熟悉,26.89%的有所了解。综上可知,受访奶农对牛场设施配置标准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不利于牛场设备的准确购置与使用。
饲料加工技术认知。精饲料具有营养含量高、粗纤维含量低、消化率高等优点,青粗饲料则有来源广、成本低的优势,但很多奶农对精、粗饲料加工技术并不熟悉,137家选择“有所了解”,46家选择“听说过”,28家选择“不知道”。由此可见,受访奶农对饲料加工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状况整体较差,不利于饲料质量风险的把控。
3)疫病防控认知。对常见疫病及其传播途径的深入了解有利于从源头切断传染源,更好地采取有针对性的防疫措施。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口蹄疫和乳房炎等常见奶牛疾病的熟知度普遍较好,对其熟悉或较熟悉的比例分别为89.46%和72.23%。569位受访者认为疫病传播途径主要有4种,其被选(可多选)比例依次是“蚊蝇和老鼠”(76.45%)、“病死牛”(66.08%)、“外来种公牛或母牛”(64.32%)和“外来人员”(38.49%)。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奶农仅仅了解常见疾病及其传播途径远远不够,疫病防控技术要点的掌握更为关键。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常见奶牛疫病防控技术,569位受访者中,64.15%的表示“熟悉”或“比较熟悉”,26.01%的只是“有所了解”,而7.38%的仅仅“听说过”,2.46%的甚至“不知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疫病防控越来越受到奶农的重视,但乳房炎等常见疫病的发病率却居高不下的原因。
4)养殖档案认知。调查显示,关于养殖档案的标准,569家受访者中,55.54%的表示熟悉或比较熟悉,35.68%的只是停留在了解层面或听说过,甚至有8.78%的没听说过;关于耳标的佩戴方式,37.96%的表示熟悉,33.74%的比较熟悉,16.34%的有所了解,11.96%的仅听说过甚至不知道。
3.3 环境质量控制认知
环境质量控制认知主要是指奶农对饲养环境标准和行为福利标准的了解程度。
1)饲养环境认知。良好的饲养环境认知是奶农实施场区选择与规划、灭鼠、杀毒和绿化等行为的基础。调查表明,受访者对于饲养环境标准或要求的认知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熟悉”和“比较熟悉”被选的比例分别为27.24%和34.8%。可见,奶农饲养环境标准认知有待提高,强化奶农对各项环境指标内容、含义及其作用等基本知识的学习尤为必要。
2)行为福利认知。行为福利即保证动物表达天性的自由,被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以及与同类伙伴在一起。良好的行为福利条件对于提高奶牛健康水平与原奶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始,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陆续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与执行。调查显示,仅有47.45%的受访奶农熟悉或较熟悉行为福利标准或要求,29.35%的表示有所了解,23.20%的仅仅听说过甚至不知道。
3.4 质量协同控制认知
奶农的质量协同控制主要是指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协调关系,共同保障原奶质量。质量协同控制认知主要是指奶农对合作的重要性、动机和原因的认知。与乳品加工企业合作能够弱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提升奶农生产优质原奶的能力,保障乳品供应链安全稳定地运行。这一点在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86.82%的受访奶农认同“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能够提高原奶和乳品质量”;建立合作关系的受访者出于以下6个动机(可多选),“获得更高的牛奶销售价格”被选比例最高(78.04%),其次是“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获得高质量的奶牛和饲料”与“获得奶牛饲养管理技术”,最后是“减少奶牛养殖风险”(55.69%)和“获得资金支持或贷款担保”(46.11%)。关于不合作的原因主要有4个,其被选比例依次是“缺乏对乳品加工企业的了解”(44.12%)、“合作门槛高”(26.47%)、“当地没有乳品加工企业”(23.53%)和“建立合作关系没有好处”(5.88%)(表4)。

表4 受访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动机以及不合作原因(多选)Table 4 Cooperative motives and non-cooperation reasons between respondents and dairy processing enterprises(multiple choice)
4 奶农质量控制行为分析
4.1 投入品质量控制行为
投入品质量控制行为主要是指奶农关于奶牛品种、饲料和兽药、饲喂用水的选购与使用行为。
1)奶牛采购行为。优良的奶牛品种和正规的采购渠道对提高奶牛产奶能力、改良遗传性状具有重要作用。荷斯坦奶牛具有产奶量高、品质好的优点。调查发现,569家受访奶农中,91.74%的选用荷斯坦奶牛,另有8.26%的选用娟姗牛和爱尔夏牛。奶牛采购渠道主要有6种方式(表5),其中162家从国外繁育场购、113家在本地繁育场购买、102家自繁自养、75家在本地集贸市场购买、66家在乳品加工企业购买、51家通过合作社购买。可见,超过3/5的养殖场户的奶牛来源于专业的繁育场或自繁自养,采购渠道稳定且集中,有利于保障奶牛(包括种牛)质量。

表5 受访者关于投入品采购与使用情况Table 5 Inputs purchase and use of respondents
结合前文对投入品认知的分析可知,受访奶农对品种的认知水平不够理想,但其品种选育行为较为规范。可能的原因是对奶牛品种的认识与了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这对于养殖场户来说有一定困难,而其品种选育行为主要受行业内专业人士的引导,荷斯坦奶牛产奶能力和遗传性状优良,故91.74%的奶农选择该品种;在购买渠道的选择上,奶农更多依靠的是“口碑”,因此,其在购买渠道上比较集中和稳定。
2)饲料和兽药采购与使用行为。营养全面的饲料和高效低毒的兽药是保证奶牛健康和原奶质量安全的关键因素。在国家鼓励发展“种养结合”模式的形势下,有38.84%的受访奶农兼种饲草,但大多数区域的受访者受土地资源和资金成本的约束,只能从农户或市场购买饲草(61.16%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选项)。进一步调查发现,仅有48.68%的受访者对饲草进行农药残留检测,饲草质量安全存隐患。安全可靠的兽药采购渠道和规范科学的兽药使用行为有利于保证兽药使用效果。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兽药来源渠道主要有6种,其被选比例依次是“兽医开方并带来”(39.72%)、“兽医开方,去指定药店购买”(26.89%)、“兽医开方,自由购买”(14.24%)、“养牛合作社统一购买”(10.54%)、“不需开方,自由购买”(5.45%)、“乳品加工企业提供”(3.16%)。由此可见,饲料和兽药采购渠道较为分散,“乳品加工企业提供”被选比例较低,说明乳品加工企业未能发挥其支持与服务作用,不利于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和投入品质量的把控。
结合前文对饲料标准认知的分析可知,饲料标准认知状况与饲料安全行为不够一致,主要是因为受访者对农药残留有一定了解,但对农药残留检测等技术的掌握有限,故受访者对饲料的评价仅限于感官指标。受访者对兽药标准熟悉度较低,故其兽药采购行为还不够科学,采购方式和渠道不够规范,极易导致兽药的误用甚至滥用。
3)饲喂用水使用行为。水源被污染会致使奶牛饮用水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用水行为不规范易导致饲喂设备的清洗不彻底,留下安全隐患,危害奶牛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原奶的理化指标。对569家奶农的调查显示,282家使用自来水,221家使用深井水,66家使用池塘和库河水(表5),但进行用水监测的仅有297家;在饲喂设备清洗方面,52.37%的只是简单用清水冲洗,只有47.63%的采用消毒剂加清水的方式处理。可见,受访者的用水行为不够规范,不利于奶牛疫病的防控。受访者的用水行为不够规范,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用水标准内容主要由理化和微生物指标构成,这就意味着受访者很难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故其用水行为自然不够规范;其二,过半的受访场户地处中、西部,中、西部水资源本身就比较短缺,故受访者只能就近取水。
4.2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行为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行为主要包括原奶质量标准执行、设施配置的选择与使用、疫病防控和养殖档案建设等行为。
1)原奶质量标准执行状况。原奶质量标准的选择与执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原奶的质量等级。调查结果表明,569家受访奶农中,31.63%的执行国家标准(GB 19301—2010),13.71%的执行行业标准,12.3%的执行企业标准,20.91%的执行地方标准,9.14%的执行国外标准,还有12.3%的没有明确标准,标准选择较为分散。
对原奶质量标准认知与行为的分析表明,受访者关于原奶质量标准的认知水平较低、选择行为不够规范。究其原因,目前我国的乳品质量安全标准在时效性、完整性和协调性方面较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之间存在着交叉、矛盾和重复,重要的标准短缺,标准的前期研究也较为薄弱,监管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故奶农对标准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不高,且难以统一执行,将会造成原奶质量安全不一致的隐患。
2)设施配置的选择与使用行为。科学的设施配置标准和正确的设施配置选择与使用行为是实现标准化养殖的基础,是提升奶质的重要手段。
饲料加工设备的选择行为。营养全面、适口性好的饲料对于保障奶牛单产水平与原奶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调查显示,在饲料加工设备/设施选择上(可多选),饲草粉碎机(56.94%的受访者拥有该设备,下同)和铡草机(55.01%)的使用较普遍,其次是全混合日料搅拌机(54.54%)、青贮料切碎机(37.79%)和青贮窖(33.74%),颗粒饲料机(27.94%)和氨化池(14.59%)的使用明显较少。可见,受访奶农在饲料加工设备选择与使用方面存在明显的行为缺陷和安全漏洞,亟待改善。
挤奶与原奶冷贮设备的选择行为。关于挤奶方式的调查显示,5.05%的受访者依然沿袭传统的手工挤奶方式,另有37.05%的利用公共奶站的机械化设备进行挤奶,57.9%的自建奶站并采用机械化设备挤奶;此外,仅有87.49%的受访者拥有原奶冷贮设备。由此可见,牛场机械化挤奶程度较高,有利于原奶质量的保证和奶牛动物福利的提升,但原奶冷贮设备的使用仍不够普遍。
对设施配置认知与行为的分析表明,受访者对设施配置的标准和饲料加工技术的认知均不够理想,直接导致了先进冷贮和饲料加工设备选择与使用的匮乏,事实上,冷贮设备和饲料加工设备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较高,也是限制先进设备购入的原因。
3)疫病防控行为。本次调查主要涉及疫病防控程序建立、免疫、消毒与健康检查、疫病诊疗与病死牛处理等方面的行为。
疫病防控程序的建立。疫病防控程序是奶农科学防疫的前提和保障,为保证奶牛健康,养殖场户应根据当地疫病流行状况以及奶牛自身抗病能力制定完备的疫病防控程序。然而调查表明,仅有62.57%受访奶农具备健全的疫病防控程序(表6),这与疫病防控技术的掌握水平是相一致的。

表6 受访者关于疫病防控的状况Table 6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espondents
免疫、消毒与健康检查行为。及时免疫、定期消毒以及严格检查饲养员健康状况能够有效预防区域多发性奶牛疫病的发生和蔓延。调查数据表明,对于新购入的奶牛,569家受访奶农中,320家进行相关疫病检疫,257家进行隔离观察1~2月,333家进行驱虫,339家对牛体进行消毒,340家注射疫苗;由于受访奶农对人畜共患疫病的了解不深,疫病传播途径中“外来人员”被选的比例最低(仅为38.49%),故仅有136家对饲养员的健康状况进行定期地强制性检查。可见,受访者的免疫、消毒和健康检查行为尚需进一步规范。
疫病诊疗与病死牛处理行为。正确及时地对病牛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够有效遏制疾病蔓延。调查发现,当奶牛出现病情时,九成以上的受访奶农聘请专业兽医或到兽医院和合作社就诊,仅有7.91%的凭借自身经验诊治,有利于保证诊治效果;但在病死牛的处理上尚不规范,569家受访奶农中,有24.95%的选择“死前卖掉”,还有5.45%的选择“加工后出售或食用”,是明显的食品安全隐患。
对疫病防控认知与行为的分析表明:受访者对于常见疫病的认识好于其传播途径,对于疫病传播途径了解程度又好于疫病防控技术要点的掌握程度,其中疫病传播途径中“外来人员”被选的比例最低(仅为38.49%),故仅有136家对饲养员的健康状况进行定期地强制性检查,疫病防控技术要点的掌握不够理想,故受访者在病死牛处理上的行为有待规范。因此,对于疫病防控来说,找到疫病频发的深层原因是关键,普及疫病防控的技术要点是改善奶牛养殖场户奶农疫病防控行为的切实路径。
4)养殖档案建设行为。养殖档案主要记录奶牛饲养过程中的关键信息,是建立原奶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手段。调查显示,569名受访奶农中,有396户建立了养殖档案,主要记录饲料、药品、繁育、免疫和生产等关键信息,但其中83.89%的能够详细或较详细记录以上内容,53.01%的能够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奶牛标识是实现可追溯生产管理与食品安全追溯的重要载体,较为常见的个体标记方式是佩戴耳标,而调查表明,给奶牛佩戴耳标的受访者占样本总数的77.50%,该比例与耳标的佩戴方式的认知状况相吻合,但其中只有45.69%的会经常更新耳标内容。综上可知,受访奶农在档案信息记录详细程度和准确性方面稍显不足,奶牛标识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但在耳标维护与更新方面存在提升空间。
对养殖档案认知与行为的分析表明,受访者对于养殖档案建设标准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殖档案建设行为,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仍有欠缺,能够详细、准确记录信息的受访者占比不高,耳标内容更新行为不够规范,故应着重普及养殖档案的具体内容与相关操作,完善奶农的认知体系。
4.3 环境质量控制行为
良好的饲养环境条件是改善动物福利、保证奶牛健康和原奶质量的关键因素。
1)场址选择行为。奶牛养殖场址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位置与环境、地势与水位、水源与水质、用电与交通等因素。569家受访奶农的场址,17.95%的位于庭院内,24.43%的在村内,20.05%的在村外,只有37.57%的远离村庄。由此可见,受访者对环境标准的认知与场址选择行为不够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受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约束,选址行为不够科学,故人畜同院等传统饲养方式依然存在。这种不科学的场址选择易引起奶牛疫病的交叉感染,诱发原奶质量安全问题,应尽快从政策、法规、技术和标准等层面上加以解决。
2)环境卫生维护行为。规范科学的消毒、绿化和灭鼠灭蝇行为有利于消灭外界环境中的病原体,有效防止病菌进入和疫病的爆发。然而,对牛舍内消毒频率的调查发现,569家受访奶农中,只有68.89%的会定时消毒;绿化方面亦有所欠缺,仅有35.33%的经常对奶牛场内外进行绿化;对灭蝇灭鼠频率的调查显示,69.60%的选择“经常”,26.36%的选择“偶尔”,4.04%的选择“从不”(表7)。综上可知,在舍内消毒、环境绿化和消灭虫害等关键环节上,受访奶农把关不严,存在着明显的疫病传播和细菌滋生安全隐患。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人力成本的上涨以及养殖利润的下滑使得受访者在原奶质量间接影响因素的把关上有所松懈。

表7 受访者对饲养环境维护状况(%)Table 7 Feeding environment maintenance of respondents (%)
3)舍内环境条件改善行为。在实践中,超六成的受访奶农能够对奶牛进行分群饲养,但分别有超一成和两成的受访者不能保证牛舍的良好通风和干燥卫生,四成左右的牛场(舍)没有朝阳、降噪和适当空间等条件,近三成的牛场(舍)没有运动场(表8)。综上可知,奶农在分群饲养、舍内通风、降噪、运动场建设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仍有提升空间。

表8 受访者动物福利条件改善行为Table 8 Improving animal welfare conditions of respondents
以上对行为福利认知与行为的分析表明,行为福利的认知和实施状况比较一致,但均不够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行为福利标准的理念传播与实践均明显滞后,绝大多数奶农对行为福利观念缺乏认同和深入了解,同时,目前奶牛养殖业还处于“保本”的边缘,因此,受访者改善舍内环境条件的动力不足。
4.4 质量协同控制行为
奶农的质量协同控制主要表现为与乳品加工企业订立购销合同,接受其监管与服务,为其提供详实的奶牛养殖档案信息和日常质检报告。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保证乳品质量的前提和基础。调查表明,已有88.05%的受访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了生产或销售合作关系,其中88.54%的愿意接受乳品加工企业的监管和服务,86.07%的愿意分享养殖档案信息,91.64%的愿意分享原奶质量检测报告,进一步印证了合作认知对合作行为的作用。仍有68家受访奶农未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受访者对合作的必要性和目的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故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状况整体较好,未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受访者占比较低,能够有效发挥供应链内部约束作用,协同保障原奶质量,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益;相互了解程度与合作能力是影响双方合作意愿与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而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双方合作的深层次因素。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研究表明,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对原奶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受访者的质量控制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行为,即奶农良好的认知能够促进良好质量控制行为的实施。总体来看,受访者的质量控制认知水平还不够理想,质量控制行为仍不够规范,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善,而认知能力差、专业技能低、标准不够统一和信息不对称是阻碍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提高的主要原因。
本文对奶农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现状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能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我国地域辽阔,奶牛养殖较为分散,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奶业产业链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开展不同养殖区域和不同养殖模式下奶农的质量控制认知与行为的调查,深入分析奶农质量控制的“短板”及其产生原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后续的研究重点。
5.2 政策建议
1)拓宽认知渠道,提高奶农的认知水平。利用广播、手机、电视、读物和互联网相关传播媒介,既要大力宣传先进养殖理念和相关标准要求,又要着重开展对典型养殖场户的参观学习,提高奶农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要发挥示范养殖场户“以点带面”的作用,引导周边奶农积极开展质量控制行为活动。
2)加强奶农培训,增强奶农质量控制行为能力。在奶农认知改善的基础上,政府相关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亟需开展配套的培训工作,如投入品检测技术、疫病防控技术、养殖档案维护技术等,进一步提高奶农实施质量控制行为能力以及操作的熟练程度。
3)增进合作程度,弱化信息的不对称性。作为乳品供应链的核心,乳品加工企业应加大对合作伙伴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并且及时准确地向奶农反馈原奶入厂检测报告及市场消费和价格等信息,促进相互了解与信息共享,不断改善合作效果,提高质量协同控制的层次和水平。
4)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奖惩机制。政府部门和乳业企业应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建立科学、统一的原奶质量标准体系;职能监管部门应明确职能划分,从关键影响因素出发,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做到“有据可依,违规必究”,敦促奶农不断改进自身的质量控制行为。
参考文献:
[1] Lankveld J M G. Quality, safety and value optimisation of the milk supply chain in rapidity evolv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markets (OPTIMILK)[R]. Leerstoelgroep Productontwerpen en Kwaliteitskunde, 2004.
[2] 慕永利, 徐贤浩. 我国乳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问题探讨[J].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6(12): 16-17.Mu Y L, Xu X H. Discussion on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of dairy supply chain in China[J]. Food and Nutrition in China,2006(12): 16-17.
[3] 吴强, 孙世民. 国外乳制品供应链质量控制策略与启示[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2015(4): 67-70.Wu Q, Sun S M.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and revelation of foreign dairy supply chain[J].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5(4): 67-70.
[4] Shaw J R, Mather E C, Noel M M.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large animal veterinarians,dairy farmers, and dairy processors in Michigan on bovine somatotropi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1992, 201(4): 548-550.
[5] Dernburg A, Fabre J M, Philippe S, et al. A study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French dairy farmers toward the farm register[J].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2007, 90(4):1767-1774.
[6] Sorge U S, Kelton D F, Lissemore K D, et al. Attitudes of Canadian dairy farmers toward a voluntary Johne’s disease control program[J].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2010, 93(4): 1491-1499.
[7] Jones P J, Marier E, Tranter R B,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dairy farmers’ attitudes towards antimicrobial medicine usage in cattle in England and Wales[J].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 2015,121(1): 30-40.
[8] Cardoso C S, Keyserlingk M A, Hotzel M J, et al. Trading off animal welfare and production goals: Brazilian dairy farmers’perspectives on calf dehorning[J]. Livestock Science, 2016,187(2): 102-108.
[9] Jones P J, Sok J, Tranter R B, et al. Assessing, and understanding,European organic dairy farmers’ intentions to improve herd health[J].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 2016, 133(8): 84-96.
[10] Kayitsinga J, Schewe R L, Contreras G A, et al.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of clinical mastiti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The influence of dairy farmers’ mastitis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behavior and attitudes[J].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2017, 100(2):1388-1407.
[11] 李红, 常春华. 奶牛养殖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2(10): 73-78.Li H, Chang C H.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quality and safety behavior of dairy farmer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2(10): 73-78.
[12] 钟真. 为什么家庭式散养条件下原奶质量安全水平不高——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调查报告[J]. 中国乳业, 2012(8): 12-15.Zhong Z. Why is the quality of raw milk quality not high in family type from a survey of the Hohhot in Inner Mongolia[J]. China Dairy, 2012(8): 12-15.
[13] 王莉, 刘洋. 奶农生产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 2012, 48(6): 28-31.Wang L, Liu 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duction behavior of dairy farmers[J]. Journal of China Animal Husbandry, 2012, 48(6): 28-31.
[14] 芦丽静, 焦莉莉, 孙永珍. 养殖小区模式下奶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 2016, 52(4): 14-19.Lu L J, Jiao L L, Sun Y Z.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afe production behavior of dairy farmers in the farming community[J]. Journal of China Animal Husbandry, 2016, 52(4):14-19.
[15] 刘明月, 陆迁, 张淑霞. 不同模式养殖户禽流感疫病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363 份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6, 17(2): 22-28.Liu M Y, Lu Q, Zhang S X. Farmer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different feeding way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63 free-range farmers and scale breeding farmers[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6, 17(2): 22-28.
[16] 吴强, 张园园, 孙世民. 基于Logit-ISM模型的奶农全面质量控制行为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3): 53-58.Wu Q, Zhang Y Y, Sun S 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airy farmers implementation will of total quality control behavior based on the Logit-ISM Model[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7(3): 53-58.
[17] 张亚旭, 周晓林. 认知心理学[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1.Zhang Y X, Zhou X L. Cognitive Psychology[M]. Changchun:Jilin Education Press, 2001.
[18] 李岩梅, 刘长江, 李纾. 认知、动机、情感因素对谈判行为的影响[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3): 511-517.Li Y M, Liu C J, Li S. Negotiation behavior: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issues in cold and hot perspective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15(3): 511-517.
[19] 尤建新, 武小军, 邵鲁宁, 等. 质量管理理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You J X, Wu X J, Shao L N, et 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20] 王福兆. 乳牛学[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Wang F Z. Dairy Science[M].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5.
[21] 吴强, 孙世民. 论供应链环境下奶牛养殖场户的质量控制行为[J]. 科技和产业, 2016(4): 78-82.Wu Q, Sun S M. Study on quality control behavior of dairy farms and farmers in supply chain[J].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016(4):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