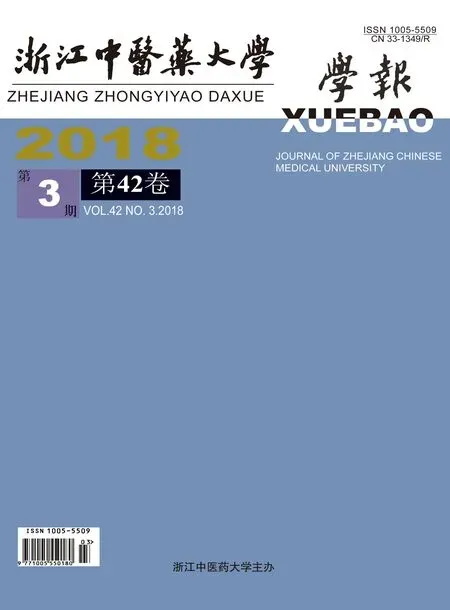张志聪对“戊癸合化”应用的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岳阳临床医学院 上海 201203
清代钱塘医家张志聪,精于经典,集前人之成,融《黄帝内经》于《伤寒论》,善以运气学说中的三阴三阳规律解读《伤寒》六经。除发挥伤寒六经气化理论之外,张志聪用运气中的“戊癸合化”分析《内经》《伤寒》,独具特色。该论虽未完备,但其经典互参、理论共通的方法,可为中医理论创新和各家学说研究提供新思路。
1 理论基础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十天干的五行属性恰与五行相生顺序相符。《素问》运气七篇中,又根据天文现象提出“甲己化土,乙庚化金……戊癸化火”的天干五行对应方式。其具体区别如下。

表1 中医基础理论的天干五行对应

表2 运气学说的天干五行对应
对于存在两种天干与五行的对应模式,《素问·五运行大论》的解释是:“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认为五运的对应顺序为“天之阴阳”,与“人之阴阳”不同,不能按照“数理变化”推求。该理恰如先后天八卦之不同:自周文王后天八卦发明以来,在具体应用中,不论医卜均合以后天八卦,而非伏羲先天八卦。在汉文化中,天地人三和,应用于人仍当合以人之阴阳。因此十天干在中医的应用中,除运气推算外,基本等同于脏腑的代名词,如提及甲木即指胆,丁火即指心。
宋朝虽推崇运气,但传世文献远不如明清丰富,难考其详。至金元时,诸家对《内经》《伤寒》多有发挥,经典互参,互为注解。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药物配伍即结合《内经》药物性味理论。该时期医家解读经典,以经典为本,而又不拘于原文,别具一格。对于运气角度的天干与五行的对应,李东垣在解读《伤寒》中芍药、甘草配伍时即有发挥。认为,芍药甘草酸甘化阴,即因甲己化土[1]。清末张锡纯对此给出更详细的解读:滋阴药多不健脾,而健脾药多不滋阴。如《伤寒论》太阴病篇言:“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即认为芍药滋阴,而不能补益中焦。但芍药甘草配伍,滋阴且健脾,则是因甲己化土可补中,酸甘化阴可滋阴[2]。
2 张志聪应用
之所以张志聪屡用戊癸合化解读经典,盖因五行理论较少直接联系胃、肾二脏。历来为诸家称道的《素问·水热穴论》“肾者,胃之关也”一条,而今也被证明“胃”为“谓”的通假字。而戊癸对应脏腑胃、肾,又可对应六经之阳明、少阴,故可解读《伤寒》中六经之间的关系,也可解读《内经》中之胃肾关系。张志聪对戊癸合化的发挥可分为以下五类[3]。
2.1 胃肾先后天互资 张志聪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胃为后天之本,肾藏之精与胃化之水谷精微可以互化:肾精上行与阳明相合,即为戊癸合而化火,可运化水谷精微以生肾精。反之,若肾精受损,不能与阳明戊土合化,则不利于进食[4]135。此外,水液代谢中,水入中焦,还需要下焦之气上升合化,即戊癸相合,而后才能上输于肺[4]221-222。
注解《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中“阴阳合血气始生”一句时,张氏又指出肾、胃与气、血、脉的关系:肾为生气的本原,阳明戊土为生血气的脏腑,因此血脉的形成有赖于肾、胃的共同作用“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而血乃成”[4]239。该段又可与张氏解读《金匮要略》“少阴负趺阳为顺”一节互参:脉始于少阴、生于趺阳,少阴在下而阳明在上,少阴上合而负于趺阳则为戊癸相合,可使脉气有根,因而为顺证[4]271。
2.2 戊癸合化,少阴得阳明太过而致病 对于《伤寒》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句,自林亿以后,多以为“表”“里”二字颠倒或表里俱热之误,但也不乏直解者。如宋代许叔微,以白虎汤能除伤寒中暍,认为该句病机为表热里寒[5]66。此处张志聪的解读更倾向于认为原文无误,但病机当为“表里俱热”。张氏引平脉篇论“阴阳和合为滑脉”,指出:阳为太阳表热,阴为少阴里寒。因戊癸化火,少阴得阳明而化热。故始寒后为表里俱热[4]669。又《伤寒》192条:“阳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戢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现代医家多认为该病病机为太阳欲转阳明,发汗则可愈,而张志聪以“戊癸合化”论具体解读其中症状,以骨节疼属少阴,又引平脉篇“翕奄沉名曰……沉为纯阴,翕为正阳”指出,症见“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属阳明,认为少阴、阳明证同见,即戊癸合化所致[4]673。上两类分析,均以“戊癸合化而见阳证”为病机,并结合脉象作为佐证。关于伤寒戊癸合化见热证的相关论述,还可见于张志聪对《素问·逆调论篇》“阴虚阳盛者遇风寒而愈热”的分析:阴虚阳盛为少阴虚、阳明盛,戊癸相合因而见阳证[4]139。
2.3 戊癸不得合化,少阴不得阳明而致病 论《伤寒》中炙甘草汤证之结代脉,张志聪从肾、胃、心三者与脉的关系进行阐述:“夫血脉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胃,主于手少阴心。”张氏认为,若少阴不得阳明、太阳之热化,戊癸不得合化,则少阴之阴气“结于中”,故见结代之脉。该段有两处需要注意:其一,少阴需得阳明、太阳热。少阴得阳明之热,可见手足温、利止等症;少阴得太阳之热,可见不恶寒、发热。其二,脉与心、胃、肾密切相关。心主血脉,无需多言。至于胃、肾与心,如前文所述,张志聪认为“少阴趺阳为脉生始之根”[4]271。此外,心、肾均为少阴,少阴与太阳互为表里。因而从六经气化角度可认为,炙甘草汤证病在少阴,病机为少阴不与阳明、太阳相合,影响气血推动,导致血脉凝结。
2.4 戊癸合化,少阴阳明相合而病愈 《伤寒》288条论少阴病预后:“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一般认为,少阴病内虚而寒,纯阴而无阳,故难治;少阴病阳气未绝,故可愈。张志聪解读为,少阴得阳明之热,戊癸合化故病愈。参考条文中“利自止”属手足阳明经之症状,可见用“戊癸合化”在解读部分《伤寒》条文时,对于诸多细致的症状,较之单纯的“阴阳”“五行”,更具优势[4]692。与该段相似的论述,又见于《素问·通评虚实论篇》论水肿病人症状、预后一节中。张氏认为,水肿病人形体满而尺脉涩,是因为肾主水,肾又与少阴相应,见于尺部。水邪阻遏少阴正气上升,因而尺部脉涩。若少阴得以上行而与阳明相合,为戊癸合化,为“从则生”,即少阴之气来复。上述两节注释,均以病在少阴,少阴与阳明相合则病愈。前者重在少阴得阳明之热,后者重在少阴之气上行与阳明相合[4]119。
2.5 症治 戊癸合化之论可用于分析症状、推测病机,分析药性,指导治疗。在具体应用中,张志聪多以胃肾关系对应戊癸。在《侣山堂类辩》中记载其自患“胃脘痈”一案,在用药外敷后,见胃脘部起一毒气,行入左肾之中[4]1084-1085。虽然腑病入脏为难治,但张志聪认为该现象为“戊癸相合”,并非病情加重。该案仅解读一现象,临床应用价值较小。相较之下,其对“呃逆”的解读更有实用性。对于呃逆,一般病机分析多考虑胃气上逆,而张志聪则认为该证为胃气与肾相合,为戊癸相合。其分析《宣明五气篇》“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即言:“胃之逆气下并于肾,则为恐。盖肾于胃,戊癸相合也,哕、呃逆也。”[4]103因此,在治疗呃逆时,可考虑胃、肾,或者阳明经、少阴经同治。如《灵枢·口问篇》中“哕逆,补手太阴、泻足少阴”之论,即考虑到治少阴以治呃逆。对于与呃逆同属胃气上逆所致的呕吐,也可考虑相似治法。如《灵枢·杂病》中“心痛引腰脊,欲呕,取足少阴”一句,张志聪分析其病机为“肾与胃戊癸合化,心痛引腰脊而欲呕者,肾气上逆而为心痛也”[4]479-480,因而从足少阴经治。
就治疗胃肾相关疾病而言,“戊癸合化”蕴含了补肾以补胃的思想。《得配本草》分析肉豆蔻与补骨脂配伍:二药分别补阳明、少阴,可使戊癸相合化火,从而运化水谷。[6]该配伍并非首创。如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收入“二神圆”,即为肉豆蔻、补骨脂,补肾以治疗脾胃虚弱之纳差。[5]100但戊癸合化运化水谷的论述,当是受张志聪学术观点影响。该论与《侣山堂类辩》分析半夏异曲同工:因半夏生于夏之半,为阳最盛之后阴气初起之时,因而张志聪认为其有启一阴之气——少阴的功效,半夏又入阳明经,与戊土相应;戊癸合而化火,因而半夏能助脾胃运化水谷[4]1080。
3 总结分析
3.1 应用特点 张志聪对于戊癸合化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内容:(1)重视胃肾作为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的互生关系。(2)重视少阴、阳明对水液代谢、水谷运化的共同作用。(3)脉的形成需要阳明少阴生化气血、协调运作,因而脉象可佐证戊癸合化所致之病。(4)在注解《伤寒》中所用到的“戊癸合化”,均可概括为“少阴是否得阳明热化”:少阴得阳明太过则见热证;少阴不得阳明热化则见寒证;少阴阳明合化则病愈。(5)在具体应用中,戊癸的对应,多以六经为纲,推衍至脏腑,结合《内经》之论而推至气血,综合性较强,但总不离《内经》《伤寒》。
然而,若要将该理论更系统地应用于释读脏腑关系、六经关系以及方药,仍需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对戊癸合化有所发挥,但对丙辛化水、丁壬化木等鲜有研究,这使该论缺少系统性。其二,就戊癸化火而言,从六经气化角度分析,当更明确地区分少阴化火是受太阳、阳明还是少阴君火本身的影响;从脏腑角度分析,需要区别胃肾、脾肾关系。
3.2 对后世影响 张志聪之后,陈修园、黄元御等医家对其医论甚为推崇。陈修园《医学三字经》言“大作者,推钱塘”,即盛赞钱塘张志聪、高世栻之学。其《伤寒医诀串解》将阳明病分为阳明本证、自受证、转属证、能食不能食证等[9]1051,其中对寒冷燥热证的分析,很明显是对张志聪“戊癸合化”的继承发展:表热为阳明戊土不能下合少阴癸水,里寒为少阴癸水不能上合阳明戊土,下利清谷为戊癸不合而下焦生阳不升(不得化火)[9]1052。黄元御分析《伤寒》多见六经相合、不合之论,概出于此。至于胃肾关系的具体应用,后世亦不乏发挥。清代陈士铎即认为“补肾必须补胃”,用四君子加陈皮、泽泻、车前子治疗小便艰涩[7]。现代刘沈林教授治疗胃癌时发现,若从胃治疗效不佳,则需从肾治。如其运用《温病条辨》增液汤中生地黄、麦冬配伍思想,即同时联用补胃阴、肾阴之药,运用干姜、附子配伍,即同用温补胃、肾之药,又常佐以济生肾气丸治胃癌[8]。
3.3 启示 张志聪在解读《伤寒》时,善于以经释经,这不仅能让人深入地认识《内经》《伤寒》,更是一种理论创新。如其将《伤寒》六经与运气之三阴三阳相联系,很大程度地发展了《伤寒》六经气化理论。理论融合,这正是中医理论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源头。如魏晋至唐多重视五行为纲(如《辅行诀》《中藏经》),金元医家大量融合六气(如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脏腑经络(如张元素《医学启源》),才有了金元时期医学理论的繁荣发展。在千年的融合过程后,现在的中医理论体系,已包含了阴阳、五行、八卦、三阴三阳、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不同分类方法。正因为有不同理论的融合,才有现在多角度看待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中医理论。
很多学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和《内经》《伤寒》的理论,已经难以再有创新。检索各类书籍也可发现,中医经典相关研究之作已然汗牛充栋,浩瀚如海。但仅仅参考张志聪对《伤寒》的注解就可发现,用今人的眼睛看前人的世界,中医经典中仍有很多未能解释清楚而有待深入研究以期使之系统化的理论。就创新而言,将各家的理论与经典相融合,就能获得无尽的创造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年顺.李东垣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35.
[2]张锡纯.屡试屡效方[M].刘观涛,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39-40.
[3]张如青.“肾者,胃之关也”质疑[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4(4):6-8.
[4]郑林.张志聪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5]刘景超,李具双.许叔微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6]严洁.得配本草[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68.
[7]郭巧德,林晓辉,胡灵敏.陈士铎论“胃为肾之关”[J].江苏中医药,2011,43(8):83.
[8]胡玥,刘沈林.刘沈林教授“胃肾同治”理论探讨及其在胃癌中的应用[J].西部中医药,2015,26(10):72-74.
[9]林慧光.陈修园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读《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