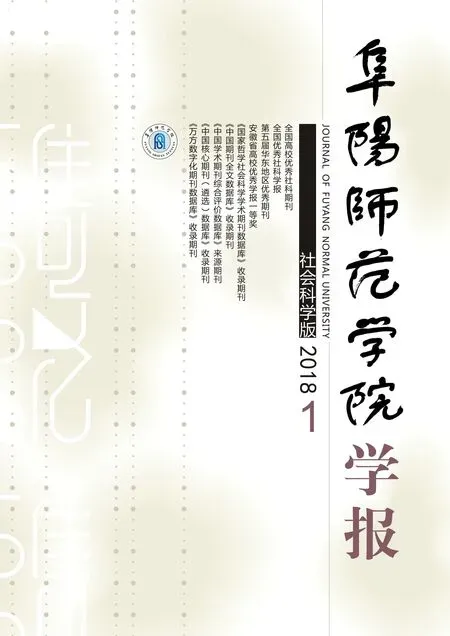地域和西方文化融合视野下的现代皖籍作家——以李霁野、苏雪林、方令孺为中心
张 文
地域和西方文化融合视野下的现代皖籍作家——以李霁野、苏雪林、方令孺为中心
张 文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皖籍作家在传承地域文化和吸纳西方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考察皖西北作家李霁野、皖南作家苏雪林、皖中作家方令孺的创作,可以清晰地窥见作品中呈现的安徽地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其中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桐城文化三个方面,西方文化主要体现在19世纪英国文艺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这可为进一步研究现代皖籍作家及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提供翔实的史料。
地域;西方;李霁野;苏雪林;方令孺
20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学在新与旧、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与交汇中除旧布新,皖籍作家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有力的步伐,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每一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不可小觑的印迹。以蒋光慈、李霁野、韦丛芜、韦素园等为代表的皖西北作家群,以胡适、刘延陵、苏雪林、汪静之等为中心的皖南作家群,以朱湘、方令孺、方玮德、方然等为核心的皖中作家群,都具有文化传承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他们的作品既呈现鲜明的安徽地域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和现代气息。众所周知,一种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其影响力将会渗透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的创作旨趣无不受地域文化的浸润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个性。“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1]从霍邱、徽州、桐城走出去的作家群,有着浓厚的安徽文化情结,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地域文化基因十分突显。与此同时,他们在新文化的语境下,为推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成熟,曾不遗余力地竞相借鉴并吸纳域外文化。本文拟以皖西北李霁野、皖南苏雪林、皖中方令孺为中心,分别考察他们作品中所呈现的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桐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展现地域和西方文化融合视野下现代皖籍作家的创作风貌和精神品格。
一、李霁野作品中淮河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
淮河文化区的皖西北作家除蒋光慈外,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等都是未名社成员,出生地都在霍邱叶集。由于近现代西方文化对地处相对偏僻的皖西北霍邱、金寨等地影响和侵入较小,生长在这一地区的现代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基本都处在十分闭塞的文化环境中,对当地的古文化遗风有着深切的感受。尽管他们后来走出封闭偏远的乡镇,接受西方文明思想的传播,但他们幼时乡间的生活体验以及古老文化的深刻记忆,无不在他们的精神品格和作品表现形式上留下印痕。李霁野(1904-1997),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其散文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他以娴熟的笔致描写霍邱特有的地域风情,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古老皖西北大别山麓乡村历史的窗口。童心、亲情和爱情是其经常涉笔的主题。“童心”构成了他浓烈的回归意识,散文《谈渔猎》中对乡村垂钓的每一个细节的描写,以及表兄捉鹌鹑的每一个动作的刻画,无不表现出作者几经生活磨砺之后仍拥有一颗童心,忘情地描写着儿时家乡的快乐时光。描写亲情、爱情的散文情真意切,令人荡气回肠。《童年的天使》中描写其姑表姐跟母亲学一针一线纳袜底、鞋底,以及伏在灶火前为小伙伴们烧烤玉米棒的情景,文中使用了霍邱方言来称赞表姐,她“性情善良温和,说话声音低柔,举止比较缓慢,所以从小我们就用方言称呼她‘肉姐’,肉就是缓慢的意思。该她做的事情,她总从从容容地把它做好”[2]324。1928年发表于《未名》半月刊的散文《生底漫画》中,他深情回顾祖母、外祖母和母亲的音容笑貌,描述儿时夏夜“倾听祖母说‘牛郎和织女’,母亲说八哥等小故事”[3]22的快乐时光。在《纪念我的两位姑母》里,他又颇爱倾听大姑母“时时带出有趣的民谣似的韵语”[2]329。散文《春晖记》中他回忆母亲教孩子们唱:“轱辘馍,咸菜汤,不吃不吃又添上。”[2]329以及月下散步时母亲教唱儿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花篓”[3]297和“月姥姥,黄巴巴,小孩子,要吃妈”[2]444的情景。李霁野1982年创作了一首《妻诞辰有赠》献给妻子:五十年来我们同甘共苦,∕半个世纪同走险路坦途;∕有时候我们忧心忡忡,∕有时候我们眉飞色舞。∥你好像考帕的挚友玛丽,∕你是我理想的终生伴侣;∕你好像彭斯钟情的安德森,∕我们相谅相爱,两情依依[4]。李霁野思乡怀旧的抒情散文,文风朴实、自然亲切。他笔下的皖西乡土风情,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李霁野善于将西方文学与乡土风情融合在作品中,因十分偏爱英国随笔(essay),又加上鲁迅先生鼓励他多读英国名家作品,故其散文娓娓叙谈中带着蕴藉的乡愁,留有自然亲切的英伦随笔印痕。在追忆母亲、姑表姐和妻子的散文里,他总会引用英国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脍炙人口的诗句,表达对亲人们的挚爱和怀念,感人至深。威廉·考帕是18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其作品以描绘乡村生活、歌颂田园乐趣和赞美和睦人际关系为主,以《收到母亲的画像》《致玛丽》等诗歌闻名。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他与19世纪初华兹华斯相呼应。1936年12月李霁野在天津时创作了散文《听雁》,文中母亲的容貌又使他想起考帕的诗句:Time has but half succeeded in his theft— ∕ Thy self remov’d,thy power to sooth me left (时光老人只做成了半个小偷— ∕ 你失去了,你慰安我的力量他却不曾偷走)。他感慨亲情的温暖和关爱始终铭刻在心[3]67。文中还曾多次引用考帕的诗句:“悲苦的已经被时间洗去伤痛……欢乐的却又渗进了一些淡淡而无刺痛的忧伤。”[3]64他甚至希望在墓碑上刻考帕的两行诗作为表姐的墓志铭:胸怀纯净有如溪水明镜,∕ 在她脸上反映出上天的形影[2]325-326。爱情诗《妻诞辰有赠》第二节中,霁野以两位英国著名诗人彭斯和考帕的浪漫爱情自比,表达诗人对相濡以沫妻子的一片深情。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是苏格兰农民诗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先驱之一,以爱情诗《约翰·安德森我的爱人》()和《我的爱就像红红的玫瑰》()著称。考帕曾作《致玛丽》()献给爱妻玛丽·恩温。
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不仅表现在霁野思乡抒怀的作品中,而且更多地渗透于表达人生信念的散文和文学评论里。自春秋以来,淮河流域是老庄道家思想的源头。植根于淮河文化,李霁野的人生观必然受到老庄淡泊无为、守静蹈虚思想的濡染。他一生淡薄名利,热爱自然,热衷艺术。1945年在散文《试谈人生》中,他十分赞同19世纪英国诗人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对于生和死所持的态度,在文中大段引用并翻译兰多的诗歌: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1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5]53.他认为我们应该持诗中所阐明的人生态度: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斗。∕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我在生命的火前温暖我的双手;∕一旦生命的火消沉,我愿悄然长逝[5]53-54。李霁野借英国诗人兰多75岁时的人生总结,表达出自己超然物外、磊落旷达的胸怀,同时也呼吁青年人专心致志热爱大自然,追求艺术的真谛。不难看出霁野的人生观既体现了老子“圣人之道,为而不争”[6]的处世之道,又传达了庄子顺应自然的思想。由此,淮河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一起渗透在他的散文创作中。霁野另一篇文学评论东西方文化思想的融汇尤为突出。1933年在《女师学院期刊》上发表《现代英国诗人》一文,评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威廉·戴维斯(W.H.Davies诗歌《闲暇》(),他认为“Davies不仅凭了诗的技巧,也凭了成熟的天才和丰富的经验,给我们表现出这样的‘深’来”[7]3。What is this life if,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 No time to stand beneath the boughs, ∕And stare as long as sheep and cows. ∥ No time to see, in broad daylight,∕ Streams full of stars, like skies at night. ∥No time to wait till her mouth can∕enrich that smile her eyes began[7]2-3. 戴维斯在诗中希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多花时间去驻足观赏草地上的羊群和牛群、倒影在溪流中的星星,欣赏佳人红唇轻启时盈盈动人的笑眸。诗风清新、自然、质朴,字里行间充溢着一份远离尘嚣的恬淡,一种与自然合一的惬意,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霁野的中西文化融合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还渗透在精神品格中。地处豫皖苏交界的淮河文化与黄河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相互渗透。楚文化是构成淮河文化的主体,楚人弘扬祖先“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精神,传承延续下来的楚地民风,培育了皖西北作家认真严谨、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从霍邱叶集走出的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在鲁迅坚韧精神的浸渍下,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里又增添了求真务实、默默奉献的高贵品格。他们不畏艰难,以“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8]组建未名社。他们传承楚文化精神,在革命事业中锤炼出高贵人格。李霁野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文学翻译事业上。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翻译种类繁多,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抒情诗、文艺理论批评,字数高达500万。1946-1949年间,翻译英国吉辛散文集《四季随笔》、英国19世纪末斯蒂文森中篇小说《化身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翻译界达到了高峰。1977-1980年间,已80高龄的他,仍译出100多首莎士比亚、彭斯、布朗宁、济慈、雪莱等英国抒情诗。此外,他花10多年时间先后修订40万字的旧版译著《简爱》,1935年被列入《世界文库》,翻译出版200多首英国抒情诗《妙意曲》,并选编出版《李霁野文集》共14卷。茅盾先生在接到李先生《简·爱自传》的原稿时感叹道:“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9]因在外国文学翻译贡献突出,1995年李霁野与巴金、冰心等著名文学翻译家同获“彩虹翻译奖”。李霁野坚韧品质的塑成是楚文化基因和西方文学影响因子的复合体。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19世纪英国著名散文家,他酝酿了近10年,写了两年多才完成散文集《亨利·赖柯拉夫特私人札记》()即《四季随笔》。李霁野十分推崇乔治·吉辛,不仅仅因为喜爱他的散文,更对他勤奋的工作态度倍加赞赏,曾表示自己一生别无他愿,只希望能够如乔治·吉辛那样“工作到死掉之一日”[10]。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 1812-1889)是维多利亚中后期著名诗人,李霁野在散文《试谈人生》中,通过引用勃朗宁的诗句,表达出自己对吃苦耐劳精神的推崇和赞扬:Be our joys three-parts pain!∕Strive, and hold cheap the strain. 不敢深味人间苦的人,也不敢深味人间的快乐。人间苦是净化我们生活的火焰[11]。
二、苏雪林作品中的徽州情结和西化色彩
徽州文化对皖南作家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自然景物描写上。苏雪林(1897-1999)对皖南山水的情怀,主要体现在描绘黄山风景的散文中。在《掷钵庵消夏记》中,她用优美的语句描绘了黄山的雄伟与灵秀:“云巢以下,松树大皆十围,丛生危峰顶上,密密重重,苍翠可爱。黄山属于红土层,大小峰峦,色皆作深紫,覆以浓青老绿的松林,色调之美,给人以‘凝厚’‘沉雄’的感觉,好象宇宙的生命力磅礴郁结成此大山,非常旺盛,但又非常灵秀。”[12]351另一篇散文《黄海游踪》描写了黄山的云烟“时时飘入我的梦境”[13]173,并感叹“天公于黄山的布置,已将天地问灵秀环奇之气发泄殆尽。……想不到我们黄山三日之游,饱览世间罕有的美景,最后还看到四海门这样伟丽的景光,等于观剧,这是一幕声容并茂的压轴;等于聆乐,这是一阕高唱入云的终奏;等于读文章,这是一个笔力万钧的收煞。啊,黄山,你太教人满意了。”[13]182在她98岁高龄时,《苏雪林山水》画册在台湾出版,收录的75幅山水画竟全是描绘黄山风光和岭下苏村,其中《黄海壮观》等黄山图,大气磅礴,表达了先生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游子思乡的情怀。除了描写黄山,苏雪林在小说中还描写徽州建筑,尤其是家乡古老的祠堂。在小说《棘心》中,苏雪林描述她的家乡:“在万山之中,风景本来清绝,但村人为迷信风水之故,无端筑上许多高墙和照壁,和自然的景物隔离。”[13]216因宋代理学家朱熹十分重视宗族伦理,其撰修和编纂的《家礼》和《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对徽州宗族族规家法的构建影响深远,尊祖敬宗、恪守孝道成为徽州人的重要传统习俗,宗祠是徽州宗法制度最重要的载体。她在《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一文中描绘道:“在我故乡那个地名‘岭下’的乡村,苏姓族人聚族而居,已历数百年。村中有一座祖宗祠堂,建筑之壮丽为全村之冠,祠中供奉着苏氏历代祖宗的牌位,每年冬至前夕为阖族祭祖之日,牲醴极其丰盛,直到元宵过后,祭礼始告完毕。”[14]祠堂文化将族规和礼仪深深根植在徽州人的灵魂深处。
苏雪林的徽州情结,还表现在作品中对贤母孝妇的书写。苏雪林自幼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徽州式封建家庭,母亲的品行对其影响颇深。她称赞其母“身体强健,吃苦耐劳,禀性又温良诚实”[15]6。对母亲的治家本领她也十分敬佩,苏母“若仅有德而无才, 也不足为贵。难得她天生有一种才干,善于治家”[15]12。苏雪林自认为《棘心》是自传体小说,在《自序》中,描述了主人公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这一徽州地方贤母孝妇的典范,作者认为杜老夫人的人格十分完美、纯粹,其行谊可以一个“忠”字概括。总体而言,苏雪林对母亲的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孝道。在《棘心》中,作者借醒秋之口再三说:“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16]162可见,徽州地区的孝道已深深植入其骨髓。
在徽州文化浸润的同时,苏雪林还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西化色彩浓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唯美主义思想。《棘心》将母爱与上帝神圣之爱合二为一,西化色彩非常浓厚。她认为基督教的神“无尽慈祥,无穷宽大,抚慰人的疾苦,象父亲对于儿女一样的”[12]119。有神的爱护,“从前的悲苦,都已忘怀,象重新获着一个生命了”[12]119。其散文集《绿天》就以《创世纪》伊甸园故事开篇,抒发作者对亚当夏娃式自由生活的渴望和向往,文中高度颂扬以母爱、自然、童心为核心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在散文《当我老了的时候》中描写死亡时,她表示希望有“一个安宁静谧的环境”[13]277,“一间光线柔和的屋子里,瓶中有花,壁上有画……灵魂早洗涤清洁了,一切也更无遗憾,就这样让我徐徐化去,像晨曦里一滴露水的蒸发”[13]278。于静谧安宁中通向上帝的理想归宿,基督教色彩浓郁。
苏雪林受19世纪末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颇深。被誉为“才子和戏剧家”[17]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19世纪爱尔兰著名作家和戏剧家,西方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他主张艺术应享有独立自由的空间,不应受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其唯美思想及其戏剧在中国现代剧坛备受瞩目。创作于1893年的独幕剧《莎乐美》()借用《圣经》中的故事情节,表达出王尔德关于“美”与“爱”、“罪”与“爱”的唯美思想,1929年该剧由“南国社”搬上中国舞台,上海、南京等地反响颇大。苏雪林在其早年文艺评论《我所爱读的书》中,就表明对西方戏剧十分青睐,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梅特灵克的《青鸟》、王尔德的《莎乐美》”[12]607,并在文中直言“我爱唯美文学”[12]606。她不仅喜爱《莎乐美》,而且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竭力借鉴和模仿。长篇小说《棘心》通过主人公醒秋对“王尔德之才”[16]94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王尔德的敬仰和推崇。1935年刊发在《文学》月刊上的三幕剧《鸠那罗的眼睛》的题记中,她直接引用王尔德《莎乐美》的一句名言:“唉,你总是不许我亲你的嘴,约翰,好!现在我可要亲它了。”[18]她在《鸠那罗的眼睛》中模仿王尔德借用《圣经》故事,化用印度阿输迦太子鸠那罗与王后爱与复仇的古老传说,辞藻华丽凄美,异域色彩浓厚,堪称东方版的《莎乐美》。欧洲汉学家 M· Calik 认为苏雪林的《鸠那罗的眼睛》在艺术上超过了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e) 的《莎乐美》[19],而且因其文字美丽哀婉,完全冲淡了剧中不道德的气氛。苏雪林接受唯美主义影响,还表现在对词汇和色彩的注重,其另一部剧《玫瑰与春》充满自然唯美的色彩。“微风动处,碎金似的光波,在绿茵上荡漾不定,浑如碧流间泛着许多瞻波伽花瓣。从树梢头望过去,穿了白衣的云儿,像仙子似的,携著手在蔚蓝天空里结队徐行。又像一群绵羊,离开了牧人,在新鲜的空气里,沐浴着阳光,自由自在地吃草。”[16]335文中运用唯美色彩,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的渴望。其散文《小小银翅蝶的故事》充溢着梦幻美丽的色彩:“我们蝴蝶的生命,全部都是美妙轻婉的诗,便是遇到痛苦,也应当有哀艳的文字。我以后要将我的情爱,托之于芙蓉寂寞的轻红,幽兰啼露之眼,更托之于死去的银白色月光,消散了桃色的云,幻灭的春梦,春神竖琴断弦上所流出的哀调。”[20]作者借小银翅蝶之口道出自己的人生观和生存方式。
三、方令孺散文中桐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
方令孺(1896-1976),桐城籍现代著名散文家、新月诗人。早年深受桐城文化的熏染,桐城勺园是其散文经常涉笔的风雅之地。勺园是其父方守敦起居、读书、作画之地,也是她与桐城文人吟咏唱和之处。祖父方宗诚也常在园中的凌寒亭与翘楚姚永朴、房秩五唱和。方令孺和其弟方孝岳、侄子方玮德、方管(舒芜)的童年无不受到这座园子里的春风沐浴,诗礼浸染。在散文《忆江南》里,令孺饱含深情地描述故乡的庭园:“每一片石、每一条径、每一棵古树、每一个残缺浓荫的门,都和父亲的风仪连合着,我想到父亲,就联想到那些醇雅的情景。”[21]85儿时的乐园,在她看来,顿生无限的亲切和甜蜜的感觉。庭院中的凌寒亭最能透出勺园的雅致,方守敬在亭子里收藏了一些书画碑帖。在散文名篇《琅琊山游记》中,令孺描写勺园的景致:“我小时候住在故乡老屋里,屋的四周墙上长满薜萝,每当春夏之交,满墙盖着郁郁苍苍的绿叶,又从门头上蒙络交翳的倒挂下来,我就喜欢,恍惚觉得自己是住在山洞里。”[22]方令孺创作的散文文笔雅致清新,章法细腻有序,令孺《琅琊山游记》与姚鼐《登泰山记》中的登顶远眺文笔神似,如出一辙。姚鼐这样描写登高远眺的情景:“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23]令孺借鉴姚鼐的笔法,将登上琅琊山最高峰南山峰的景致呈现出来,文中写道:“等走到山顶的时候,精神就完全不同了。眼前豁然开朗,山峦从这里倒退下去,重重叠叠像波涛又像莲花似的在我们脚下起伏。山影慢慢淡下去,渐渐沉没,化合到一片白茫茫的云气中。云气的底下又看见一滩滩明亮的白水,……只仿佛是一片湖泽展开在眼前。”[24]远处的田野和山峰,与白茫茫的云气融化为一体,云雾缭绕,恍若仙境。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令孺散文中桐城文派的遗风余韵。
方令孺赴美留学期间(1923-1929)专心研读西方文学,并十分注重吸纳西方文化养料,不难看出其散文都有西方文学尤其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投影。从《琅琊山游记》中的一段夜景描写,可以看出她借鉴并模仿19世纪末英国著名散文家史蒂文森(R.L.Stevenson,1850-1894) 的表现手法。《松林中的一夜》是史蒂文森游记散文《驱驴旅行记》(,1879)中的一个片段,主要写作者在法国旅行期间,从布内玛尔出发去攀登洛泽尔山,露宿松林一夜的见闻与感受。该文以细腻的文笔,描写了从黄昏到次日清晨大自然的静美,表现了露宿大自然所体验到的生活乐趣。“屋檐下的夜晚寂静单调,而在户外,我就过得轻松愉快了。有繁星、露水和花香陪伴,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对禁闭在墙壁和窗栏间的人们来说,夜晚似乎是暂时的死亡;而对露宿野外的人而言,夜晚却是轻快而富有生机的安眠。整个晚上他听到大自然深沉而自由的呼吸声,……睁开惺忪的双眼,看着美丽的还未消退殆尽的夜色。”[25]方令孺在《琅琊山游记》中把高山深壑夜间的幽静描写得十分细致入微:“山中的夜是多么静!我睡在窗下木榻上……好像沉到一个极深的古井底下。一切的山峰,一切的树木都在月下寂寂的直立着,连虫鸟的翅膀都不听见有一声瑟缩。世界是在原始之前吗?还是在毁灭了以后呢?”[21]77接着描写次日天亮以后的心情:“树上有各种的鸟在那儿争喧,世界又回复了它美丽的现实。我为贪恋山中的景物,不敢多眠,……这古木苍岩已够教我心醉。”[21]78二人描写的山林夜色以及游人的愉悦心情笔法相近。此外,她还恰到好处地引用英国作家的经典语录,通常直引英文原文。在游记散文《去日本看红叶》,她直接引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英文诗句:“And this gray spirit yearning in desire , To follow knowledge, 1ike a sinking star, Beyond the utmost bound of human thought”[26]38,表达了作者要做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现代人的愿望:“要像Tennyson写 Ulysses一样,到老雄心都不死。”[26]38
综上所述,皖西北、皖南、皖中作家李霁野、苏雪林、方令孺的作品既呈现了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桐城文化的地域特征,又融合了西方基督教文化思想和19世纪英国文艺思想,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现代皖籍作家为了促进中国新文学不断成熟与发展,在不遗余力继承安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接受并融合域外文化思想,他们的创作风貌和继承并创新的精神品格,可为深入研究皖籍作家与英国文学的关联以及中西汇通的创作风格提供一个范例。
[1]董楚平,金永平.中国文化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018
[2]李霁野.李霁野文集:第2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李霁野.李霁野文集:第1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4]李霁野.李霁野文集:第3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44
[5]李霁野.给少男少女[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6]老子.道德经[M].李若水,译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303
[7]李霁野.现代英国诗人[J].女师学院期刊,1933(1):2-3
[8]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集[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254.
[9]王秉钦.李霁野“直译”《简·爱》[N].天津日报,2011-03-13(07).
[1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4:22.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散文选 (1918-1949):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79.
[12]沈晖.苏雪林选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3]苏雪林.当我老了的时候[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14]沈辉.苏雪林文集:第2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5.
[15]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16]沈辉.苏雪林文集:第1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17]薛雯.颓废之美:颓废主义文学的发生、流变及特征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188
[18]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外国独幕剧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196.
[19]严家炎. 问学集 严家炎自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139.
[20]林呐,徐柏容,郑法清.苏雪林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04:53
[21]李季农.桐城现代名家文选[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
[22]方令孺.方令孺散文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9.
[23]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54.
[24]方铭,王达敏.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51.
[25]史蒂文森.史蒂文森游记选[M]. 钱佩瑶,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236.
[26]龙渊,高松年.方令孺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Contemporary Anhui Writers as Viewed from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Centering on Li Jiye, Su Xuelin, Fang Lingru
ZHANG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hui writ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absorbing western culture. Study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Li Jiye from northwest of Anhui province, Su Xuelin from south of Anhui province and Fang Lingru from central section of Anhui province, the organic fusion between Anhui reg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can be seen clearly. Regional culture includes the culture of Huaihe River, Huizhou and Tongcheng, while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ry thoughts and Christianity are embodied in western culture, which will provide an example for further studying Anhui writers’ creative style of blending the western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spiritual character.
region; west; Li Jiye; Su Xuelin; Fang Lingru
2017-09-2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安徽作家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AHSKY2015D122);教育部英语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美学视域下朱光潜翻译思想与治学特色研究”(SK2016A0569)。
张文(1966- ),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1.06
I206.6
A
1004-4310(2018)01-0031-06
——论苏雪林早期的文学批评
——苏雪林与袁昌英、凌叔华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