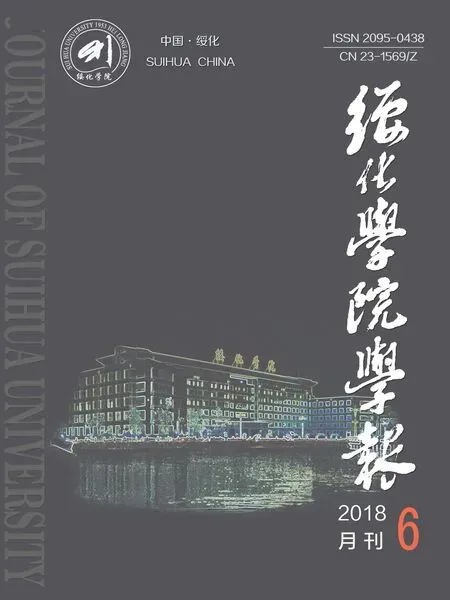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
王康辉
(安徽大学法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终身监禁制度在我国刑法典中已经正式确立。从立法之初该制度备受争议,甚至有学者强烈反对该制度入刑。但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终身监禁是利大于弊。当然,该制度的实施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析。为此,本文拟从终身监禁的法律定性为出发点,对该制度的具体司法适用予以明确,以期对终身监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一、终身监禁的法律定性
一项新的制度如何在法律上精准的定性是司法机关正确理解和运用该制度的前提条件。终身监禁不是刑法上独立的刑种已是刑法学界的共识,因为一个独立刑种的设立在形式上需要总则予以确定,实质上要在分则的具体罪名上有普遍适用的功效。但该制度的法律性质在刑法学界却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就针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要的梳理。
观点一:终身监禁制度是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有学者认为,“终身监禁”不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而是在执行“无期徒刑”这一刑罚过程中适用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方法,当然,这种执行方式依照现行刑法仅适用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
笔者认为,终身监禁制度既不是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也不是“中间刑罚”,更不属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从法条的逻辑结构上讲,终身监禁以死缓的启动为前提,是死缓的一种特殊执行方式。理由如下:
第一,终身监禁不依附于无期徒刑的执行,无期徒刑只是终身监禁的执行效果。被告人因为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缓,司法机关根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是否自愿悔罪等量刑情节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实行终身监禁。若适用终身监禁,被告人在2年的考验期结束后,没有故意犯罪或者重大立功行为,死缓的处罚减为无期徒刑,并且不得减刑假释。终身监禁的效果就是剥夺被告人的终身自由,这样的效果在表面上理解确实是因为执行无期徒刑而导致的,但是无期徒刑只是死缓考验期满后的执行结果之一,除了会出现无期徒刑的结果之外,还可能存在死刑立即执行或者25年有期徒刑的情形。假如被告人直接被判处无期徒刑,依照刑法第383条是根本不能产生终身监禁的效果。所以从根源上讲,终身监禁只能是死缓的执行方式而并非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
第二,关于中间刑罚的概念,黄京平按照其应有的含义进行了阐释,但是刑法学界关于“中间刑罚”的还未达成统一见解。死刑刑罚的执行按照其严厉程度可以分为死刑立即执行、终身监禁的死缓、限制减刑的死缓、一般的死缓。终身监禁的严厉程度的确位于死刑立即执行与限制减刑的死缓之间,但不能用“中间刑罚”这一固有名词来定性,否则就具有成为独立刑种的嫌疑。张明楷也认为如果使用中间刑罚这个概念,实际上把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的死缓割裂开来,将两者视为相对独立的刑种,进而得出终身监禁是中间刑罚的结论,而这样结论明显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5](P79)
第三,“死刑替代措施”可以理解为在没有死刑的条件下,寻求一种可以达到与死刑效果相当的措施来代替死刑。“替代”应有“取代、替换”之意。但目前《刑法修正案(九)》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增设终身监禁的同时并没有把该罪的死刑刑罚废除。被告人所犯罪刑达到死刑的量刑标准理应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而非可以用终身刑来代替。这两种刑罚虽然都属于死刑的范畴,但是导致一生一死的结果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如果对于被告人处以死刑过于苛刻,被判死缓又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可以对于被告人实施终身监禁,这时仍然不能说是死刑替代措施,因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根本没有达到死刑的标准,何来死刑替代一说?
第四,黎宏持有的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表述不够准确。死刑的执行方法只有两种,即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将终身监禁定性于死刑执行方式,并且不同于现有的死缓措施,那么从字面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死刑的执行方法有三种,即死刑立即执行、一般的死缓、不得减刑假释的死缓,且这三种方式相互独立。但是,从法条表述来看,终身监禁的启动仍然是依附于死缓的实施。所以,把终身监禁定性为死缓的执行方式比较准确,只是终身监禁在死缓的具体实施方式上比较特殊而已。依照笔者的观点,死缓依据执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可以减刑假释的死缓(一般的死缓);第二是限制减刑的死缓;第三是不得减刑假释的死缓(终身监禁的死缓)。
二、终身监禁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对于修正后的第383条第四款能否适用于生效前所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成为了首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基于保障人权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考虑,在刑法溯及力上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只有新法比旧法更有利于被告人时才可以适用新法,否则应当对于被告人适用旧法。那么,终身监禁制度是否更加有利于被告人不仅要从制度本身考察,而且还要结合修正后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从宽处罚情节进行综合判断,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第一,从立法机关设置终身监禁的意图来看,认为因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基于慎用死刑和防止犯罪分子因过度减刑而逃避刑罚的考虑,适用终身监禁,可以做到罪刑相一致。[6]如上述所言,终身监禁的严厉程度在一般的死缓之上又在死刑立即执行之下。一方面,终身监禁可以针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判处死缓又偏轻,适用终身监禁能做到罪刑相适应的被告人;另一方面,根据“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也可适用终身监禁。但是被告人单纯被判处死缓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是绝对不能适用终身监禁的。总的来说,在立法原意上该制度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根据旧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可以适用新法规定的终身监禁。从这个角度看,适用终身监禁是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的。
第二,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修正案中得到了提高。立法机关将定罪量刑标准从原有的固定具体数额修改为较为开放的概括式数额。在死刑的适用标准上,将过去的“十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司法机关针对概括式数额的标准在总结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基础上再制定出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当然,司法解释中关于概括式数额的标准也只是定位在一定的范围区间,并不会精确到具体的数额,这样的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会更容易操作,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正义。比如在2016年最高院与最高检出台的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可以明确看到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足2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足300万元的,应当认定“数额巨大”。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据最新的定罪量刑标准,明显可以看出较大幅度的提高了贪污受贿犯罪适死刑适用标准,符合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第三,修正案扩大了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情形。依照第383条第三款之规定,相比较修正案之前,立法机关把从宽处罚的情节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提示。该规定一方面不仅将酌定的量刑情节设定成法定量刑情节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予以法定化,另一方面把从宽处罚的情节涵盖了第一款的所有情形的贪污贿赂犯罪,甚至是可以判处死刑的最为严重的情形。依据司法实践的总结,从宽处罚情节存在于大量的贪污受贿案件中,而且被告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宽大处理。所以依据修正前的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适用了修正后的第三款从宽处罚规定,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一般的死缓。
综上所述,修正后的贪污贿赂的定罪量刑标准总体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终身监禁制度主要是针对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设立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全部适用修正后的新法,应当有所区别:如果被告人依据修正前的刑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可以根据修正后的新法适用终身监禁,此时新法具有溯及力;除此之外,新法则无溯及力。
三、终身监禁与重大立功规定
(一)死缓考验期内适用重大立功。终身监禁的启动依附于死缓的实施已是不争的事实。被告人即使被判处终身监禁,根据考验期内罪犯的表现,也将会出现不同的执行结果:故意犯罪的,死刑立即执行;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25年有期徒刑;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所以从最终的执行结果来看被告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不必然会产生“牢底坐穿”的效果。终身监禁以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为前提,假如被告人因为重大立功直接减为有期徒刑,那么终身监禁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此时就可以阻却终身监禁。有学者认为适用重大立功使得被告人逃脱终身监禁的刑罚,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无期徒刑是死缓的执行效果之一,既然立法者的表述是“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那么就已经把因重大立功而减为有期徒刑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大多是利益集团的共同犯罪,适用重大立功则有利于被告人积极主动地揭发他人犯罪、提供犯罪线索,使司法机关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二)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不适用重大立功。有学者认为,在死缓考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又因重大立功而减为有期徒刑的,同样可以阻却终身监禁。理由为:第一,刑法分则规定的终身监禁并不是刑法总则关于减刑的例外规定;第二,死缓考验期间的重大立功与无期徒刑期间的重大立功,只是发生时间与所处阶段不同,但重大立功的内涵与基本性质应当具有一致性。[2](P102)笔者认为,一旦终身监禁的实施条件成就,在无期徒刑阶段是不能适用重大立功。首先,要对法条进行法律解释,文理解释应当是众多解释方法中的首选。从法条表述来看,“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在前,“终身监禁”在后,依照正常的逻辑顺序,两者应该有明显先后顺序。且“不得减刑、假释”是对于“终身监禁”的解释和强调。假如无期徒刑阶段还可以因重大立功而获得减刑,那么立法机关何必增设“终身监禁”一词,以示其特殊性与严厉性。其次,刑法分则相对于总则而言有例外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分则的规定。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的不得减刑假释本身就是对于刑法第78条关于缓刑的特殊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最后,终身监禁已经是对于应当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的宽大处罚,并且在死缓期间给予了被告人获得减刑的机会,倘若在无期徒刑还可以减刑,这必会使“终身监禁”一词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其实质的功效。
四、终身监禁是否应扩大适用范围
(一)适用于存在死刑的犯罪中符合我国减少、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趋势。在如今高呼废除死刑、限制死刑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形成一系列死刑替代的刑罚措施是我国学者所追求的目标。终身监禁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新制度,是否能起到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还有待商榷。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周光权认为,法律这样规定实际上是将终身监禁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替代措施看待,而不适用于原本应判处死缓的人,从而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适用。[7]而张明楷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终身刑是侵害人格尊严、比死刑更为残酷的惩罚方法,不应该成为死刑的替代措施,故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8]首先,笔者对于死刑的态度是减少、限制死刑适用,但应当保留必要的死刑罪名,比如严重的人身犯罪、公共安全犯罪与社会秩序犯罪。在保留死刑的刑法框架内,终身监禁无法发挥着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但是,这项制度的出台却可以在判处罪犯死刑偏重,死缓偏轻的情况下扩大到其他保留死刑罪名中予以适用,以致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率,在这方面是符合当前“少杀、慎杀”的立法趋势。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立法机关增设贪污贿赂犯罪的终身监禁的同时并无意要把该罪名的死刑废除,那么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取舍适用还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死刑适用的集中领域在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对于贪污贿赂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少之又少。如果该项制度的适用只是仅仅停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而没有被扩大到其他罪名,那么这对于减少、限制死刑的法治进程的推动作用还是非常微弱的。
(二)适用严重的暴力犯罪更能体现罪责相一致,发挥特殊预防的功效。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果。财富的积累已经不是困扰我国发展的重大难题,人民越来越关注的是人格权、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利如何更充分的实现。相应的在法益保护位阶上,人身权益的保护应当高于财产权益的保护。贪污贿赂犯罪不仅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而且还严重地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从本质上讲,贪污贿赂犯罪更多的属于经济犯罪。而严重的暴力犯罪侵犯的是人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人格权等人身权利。目前看来,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规定了如此严厉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而严重的暴力犯罪在刑法第50条与81条更多体现的是限制减刑和不得假释。可见利益位阶在前的法益保护程度明显低于位阶在后的保护程度,使两者在整个刑罚体系中显得罪责刑不协调。只有将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严重的暴力犯罪,才能更好体现罪责相一致,突显刑法对于人身权利的特殊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具有特殊的身份性。被判处死缓甚至是最轻微的管制或者拘役刑罚都会导致犯罪分子终身失去公职身份。即使回归社会,也不可能再进行贪污贿赂犯罪。因此,终身监禁无法发挥对于该犯罪的特殊预防效果。但是某些重大的暴力犯罪,特别是由于严重的人格扭曲、变态心理导致的人身犯罪,犯罪分子出狱后再犯的可能性极高。除非是将其肉体消灭,否则一般的刑罚对于该犯罪分子的特殊预防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只有将其终身监禁,才能使其再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实现社会的安定。
(三)总体看来有利于改善我国“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体系。我国的死刑依据执行方式可以分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于“严打”的刑事政策考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率比较高。近些年为了贯彻保障人权的原则,对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掌控的非常严格,大多数应当被判死刑的,最终都适用了死缓。死缓虽然属于死刑的执行方式,但是大多数罪犯被判死缓后,经过两年的考验期后都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5年的有期徒刑,因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且情节严重而被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少之又少。因此,死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入生刑系列。即便是直接判为无期徒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总是会通过减刑、假释的方式使得实际执行期限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执行效果实在差强人意。反观我国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我国共有46个死刑罪名。不仅在公共安全犯罪、人身犯罪、社会秩序犯罪中存在大量死刑,甚至是经济秩序犯罪、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经济犯罪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死刑,可以说死刑罪名章章可见(除第九章的渎职犯罪)。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罚体系结构不甚合理,即生刑偏轻,死刑偏重。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终身监禁的出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刑罚体系上的缺陷。如果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基于“少杀、慎杀”的原则,可以采取终身监禁措施,留住犯罪人的生命,体现了刑法宽大的精神。但是如果犯罪人被判处普通的死缓太轻,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那么对于犯罪人苛以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也正是加重了犯罪人刑罚的严厉性。可以说,终身监禁制度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应孕而生。
[1]黄明儒,项婷婷.论《刑法修正案(九)》“终身监禁”的性质[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21.
[2]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98-102.
[3]黄永维,袁登明.《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J].法律适用,2016(3):37.
[4]黎宏.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J].法商研究,2016(3):23-24.
[5]张明楷.终身监禁的性质与适用[J].现代法学,2017(3):79-81.
[6]乔晓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EB/OL].中国人大网,2015-8-24.
[7]徐日丹.“数额较大”如何起步?“死刑立即执行”如何适用?[N].检察日报,2016-4-19(3).
[8]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J].法学研究,200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