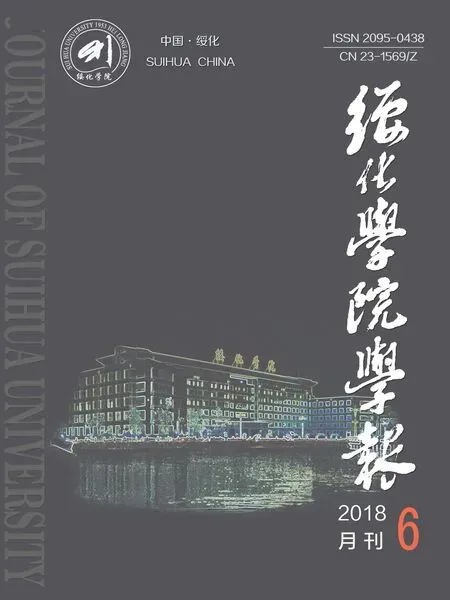乡关何处:城市化语境下的乡土文学创作走向
寇国庆 倪相群
(1.蚌埠学院;2.蚌埠第一中学 安徽蚌埠 233030)
最早给乡土文学下定义的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显然,鲁迅所指的这一类作家的创作多与故乡的乡土情感相关。
其实,从创作者来看,是从外围俯视乡土,以文人、知识分子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乡土,把乡土作为批判亦或颂扬传统文化;或是寄托人性的乌托邦,还是政治风向的试验场,这些创作中的“乡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早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就已经暴露出的问题,茅盾就指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真正的乡土创作不应该用旁观者的视野,用猎奇、俯视的眼光来看待乡土、乡村、乡民对乡土文学创作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时代巨变语境中的乡土文学
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古典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过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造就了传统乡土社会加速瓦解,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宗法的、血缘的、地缘的纽带日益松散,就像马克思所讲的那样,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一急剧的时代变迁给乡土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考查他们精神、情感上的困惑、纠结、探索,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记录与追问。
建国前后,赵树理、柳青围绕农村、农业、农民的生存发展而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品生动鲜活地记录了社会变迁,文革时期浩然的创作尽管多有诟病,也不失时代风云的折射。
20世纪80年代,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多以改革时代为背景,描绘时代巨大变迁中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情感变化,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既有时代阵痛下的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的怀恋,也有作者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思考。贾平凹早期围绕底层乡民的“商州系列”着力于宏大背景下描述社会转型时期人性的变化,新时期以后的《秦腔》《带灯》等长篇小说,关注当下时代巨变给传统乡土社会带来的精神与情感方面的震撼。而另外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则以他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白鹿原》探究民族秘史。当代河南作家多以中原大地为血缘纽带,这其中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李洱的创作有着浓重的“乡土”情节,在表现内容与手法上也进行了创新与探索。刘震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对“故乡”探索的系列作品《故乡到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既有对当下的乡村社会时代巨变下的利益冲突与情感纠葛的展示,也有对乡土社会孤独个体生命体验的洞察。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在《受活》《丁庄梦》等一系列作品中,虚构各种超现实的荒诞故事强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读者哭笑不得,情节荒唐夸张,带有滑稽剧色彩,折射了现实中乡村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李佩甫90年代以后的《羊的门》《李氏家族》描绘了厚重乡土文化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性的幽暗与现实权谋。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再现了的农村基层竞选中基层干部的人性所遭受的扭曲与痛苦。河南的优秀作家还很多,厚重的中原文化给了他们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也使他们的作品更能够展现当下乡土社会的真实。山东作家莫言用他的一系列关于高密乡的历史与现实的言说,描绘了一个神秘、野性的故乡。张炜对九月大地的深情拥抱,在在展示大地的博大与多情。另外,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葛水平的《喊山》、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等等揭示了北方乡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民们生活的原始残酷与坚韧执着。
二、现代语境下乡土文学存在的问题
不容置疑,在新的世纪,城市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城乡距离拉大,市民与农民在物质财富有着明显的差距,因此,许多乡土小说着重描绘了农民在物质财富落差下的心态失衡,以及进城脱离乡土进城后一段适应期间的艰难。这些作品有: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吴玄的《发廊》、林白的《去往银角》、巴桥的《阿瑶》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文明相对于乡村文明来说,给了农民给多的回馈、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自由。如果看不到这些进步的方向,一味地谴责城市文明,显然缺乏历史意识。
描绘乡村权力的暴虐在很多作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对于乡村的政治建设、民主建设都有着借鉴意义,然而,如果看不到乡村政治建设、民主建设的进步,显然不能够真实地表现乡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系列、刘庆邦的《家园何处》、陈应松的《神鹫过境》、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杜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和女人》都描写了乡村政治权力建设中出现的弊病。此外,这类作品还有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尚志的《海选村长》、梁晓声的《民选》、曹征路的《豆选事件》、陈中华的《七月黄》、荆永鸣的《老家》等等,描述了剔除乡村旧有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势力的艰难。燕华君的《麦子长在田里》、向本贵的《泥泞的村路》、阎连科的《白猪毛黑猪毛》、秦人的《谁是谁的爷》艾伟的《田园童话》、张继的《清白的红生》等等描绘了乡村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所遭受道德伤害,从而揭示乡土社会、乡土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亟需改造的必要性。
当下的中国“城市化”造就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文明的挤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业已影响和渗透到乡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20世纪代以后,市场化、城市化加快,在这样的化语境下,重新审视乡土文学创作,批判对乡土、乡村、乡民错误的情感认知,才能够为乡土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建议。
对于乡土、乡村的衰败,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人文知识分子显然会有更多的怀恋,进而对现代文明持更为苛刻的情感态度,上个世纪30、40年的沈从文可以是个代表。沈从文心仪的是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乡土。在1942年他为《长河》所写“题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地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接下来,他慨叹:“‘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3]城市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给人造成了很多不适应,有很多不足,如果一味地加以否定,显然是带上了有色眼镜。
还有一些作家,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把乡土、乡村、乡民赋予过多的道德色彩,这也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指出,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将人与土地连接起来凸显出来的民粹意识,这种意识源于旧俄时期的民粹主义的“土地性——人民性——道德性”[4]的思维方式在我国知识分子里同样具有广泛的市场,张炜的道德体系的建构在既通纯洁“血缘”的同时,又接上了“人民”的“地气”。《古船》中隋抱朴最后明白的道理就是“要紧的是和镇上的人在一起。……老隋家人多少年来错就错在没和镇上的人在一起”。在张炜的审美理想中,“人民”成为一种理想的尺度。“说到奖赏就不能不想到‘人民’,不是抽象的想,而是具体地、真切实在地想。一个作家的劳动帮助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或后来时代的人民,他应该由喜悦到兴奋到忘情,获得无边的快乐。”[5]乡土、乡村、乡民并不必然在道德方面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乡土文学作家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利于乡土文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建设。其实我们更应该在现代都市中发现未来意义,“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出的各种新型的人格。”[6]
三、乡关何处——乡土文学的追问
尽管乡土社会可能已渐行渐远,乡土文学也逐渐失去土壤,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语境下,乡土文学的未来必须是处理好乡土、乡村、乡民与城市关系的问题。
确实,在城市化、市场化语境下,传统的乡土正在遭受现代城乡文明的挤压,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乡土农业文明怀恋的人文知识分子作家来说,现实对情感的冲击肯定是巨大的。当然,作家可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留下历史发展的感性记忆,正如贾平凹所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7]作家们注定要把这急剧变化的时代变迁与情感激荡记录下来。由此,贾平凹在《秦腔》中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8]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称为“乡土叙事的终结”。贾平凹运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9]贾平凹以极大的激情记录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秦川文化的秦腔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做的应对与抗争。
对于作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摆脱先入为主地对城市做出的单一的道德判断,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紧紧地拥抱大地,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新疆作家刘亮程在广漠的西北土地上,感受到大自然、大地,体味大地与乡土的恒久绵长,因此有学者曾经感叹:“10年前我读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认为在乡土的广度、深度和细部上都充溢着生命感,大地——乡土上的人,牲畜和庄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乡土仍在,这就是永恒的力量,就是永恒。”[10]余秋雨的文化乡土创作同样也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有益探索,在散文《信客》《夜航船》《牌坊》《老屋窗口》《酒公墓》中有童年度过的青葱回忆,乡亲们艰辛的谋生和对故乡的眷恋,《乡关何处》则挖掘故乡渊源的文化价值。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描绘了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在远去,在高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今天的乡村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乡土文明作为文化记忆与审美理想可能仍然对中国人当下生活与未来愿景产生深层的重要影响,仍将是中国悠久文化的根基,但乡土社会秩序与乡土文明最终也许只是会成为我们不变的乡愁。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53:78.
[2]茅盾.关于乡土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3.
[3]沈从文.长河题记[N].重庆《大公报》“战线”副刊971期(1943-4-23).
[4]刘小枫.圣灵降临的的叙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07.
[5]张炜.心上的痕迹,绿色的遥思[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22.
[6][美]R·E.帕克等、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
[7]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28.
[8]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9]周媛,贾平凹.我要为故乡树块碑[N].西安晚报,2005-02-23.
[10]李伯勇.植根大地写作的精神向度——关于“大地写作”的话题[N].文艺报,2012-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