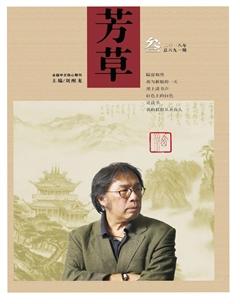中国新诗百年高端访谈
一 国外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翻译与评价
吴投文:能不能再谈一下西方国家的读者对中国现代新诗的了解和评价?
西川:他们对中国新诗一般来说不了解。但中国当代的少数几个诗人,国外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我有一个朋友,加拿大诗人、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蒂姆·柳本,在加拿大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谈到我、翟永明和欧阳江河。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曾经在美国《信仰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谈于坚和我。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并不低。蒂姆甚至说,我们几个干的活就相当于当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那几位诗人对俄罗斯的意义。问题是,这样的评价通过我的嘴传递回国内,人家就觉得你在瞎吹。很多我在国外碰到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讲,因为当时边上也没有别人。但我知道人家对我是一个什么态度。比如说,一九九五年,我去荷兰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才三十多岁。在我朗诵完之后,英国威尔士女诗人、获得过英国女王金质诗歌奖章的吉莲·克拉克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世界诗歌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听了你的朗诵,我知道你就是世界诗歌的希望。”诗歌节组织前来的各国诗人们乘船游览鹿特丹,有一位荷兰盲诗人正好坐我边上。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中国诗人,叫西川。他说:“我知道你,那天我听了你的朗诵,整个诗歌节只有我们两人可以交谈。”
吴投文:他们还是有预见性的。
西川:不是预见性,当时我已经写出了《致敬》之类的作品,我在那儿读的就是《致敬》中的几章,当然,也讀了别的。
吴投文:国外对中国诗歌的翻译质量,你觉得怎么样?
西川:我诗歌的英文译者很棒,他中文名字叫柯夏智。他因为翻译我的书获得了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的两个大奖之一的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
吴投文: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目前中国翻译国外的诗歌很多,但国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不多。
西川:其实也很多,只不过没有弄出什么声响来。我刚才给你看的光是英文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都多少本了,王屏编的、张洱编的、明迪编的、王清平编的、托尼,巴恩斯通编的、杨炼编的……我没数过,这还是仅限于英语出版的当代中国诗选。法语的尚德兰、意大利语的鲍夏兰、德语的顾彬、西班牙语的明雷、俄语的邓月娘(娜塔莉亚·阿扎洛娃,俄语名字)、日语的田原、葡萄牙语的姚风、斯洛文尼亚语的施派拉,奥伯斯塔尔等,都翻译编辑出版过当代中国诗选。翻了不少。
吴投文:据你的了解,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有没有什么差异?有哪些国家对中国当代诗歌翻译得多一点,哪些国家翻译得少一点?
西川:各个国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不同的译者之间有差异。每一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背景,每一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趣味。比如,有的译者本身就喜欢很精致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的法语译者,她不太适合翻译我的东西,她更适合翻译北岛的东西。像我的英文译者和西班牙文译者就非常好。总体上说,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诗歌算多一些。
吴投文:现在中国诗歌被翻译成外文,存在什么误读没有?
西川:误读永远都有。别说别人对咱们有误读,咱们对人家也有误读,咱们对自己都有误读。误读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吴投文:中国诗歌翻译成外文,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西川:中国当代很多诗人都希望自己的诗歌被翻译成外文,但是,翻译成外文以后基本上处于无效状态。没有什么用,只能说是被翻译了,可翻译成外文也无法为你赢得世界的尊重、国外同行的赞扬。所以,这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写作观念上的问题。如果你自己的写作观念既不独特,也不充满创造力,而就是写点诗,就是对生活有点怨言有点伤感——这些东西对诗人个人来讲,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世界文学的进程有什么意义?很多人的诗是没有意义的,在中文都没有意义,就更不要说翻译成外文了。
吴投文:关于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同人的评价差异比较大。
西川:不是评价。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国外究竟怎样评价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只有几个名字,一个是北岛、一个是杨炼、一个是顾城,往后是比如多多、于坚、欧阳江河、翟永明、我。我们在世界上真正赢得同行认同的并不是所谓的“诉苦文学”,你也可以不诉苦。
吴投文:你认为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诗歌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西川: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中国诗人在国际上的处境?……哦,中国的诗人们,包括中国的小说家们算在一块儿,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没有同行。哪一个作家、诗人在国外赢得过哪个国家诗人、作家的高度赞扬?不是看哪个国家是否有新闻报道你,是要看什么时候国外那些真正有身份的作家是否出来表扬你,就像我们的作家都在表扬博尔赫斯。另外,花钱买来的赞扬不算,通过商量、交换来的赞扬也不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语言问题:中国绝大多数作家诗人讲不了外语。第二个问题: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总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这种情况在东欧更严重些。
吴投文:中国目前在国外被翻译最多的诗人是哪几位?
西川:北岛是最多的,像杨炼、顾城、多多、舒婷等都被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
吴投文:我注意到了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朦胧诗之后的中国当代诗歌,基本上都是翻译诗。
西川:他的原话是“经过双重翻译的外国诗”。这是说北岛,在他的文章《何谓“世界诗歌”》里说的。
吴投文:实际上,也涉及到了中国其他诗人,他觉得似曾相识。
西川:宇文所安是个学者。做中国古典文学的。其学术研究令人敬佩。但他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他认为台湾的杨牧是个大诗人,能够中西结合。这是他的判断。但我也可以给你引述点儿国外作家对我诗歌的看法:我新方向的那本集子,译者柯夏智为它干了好几年,反复修改。我就觉得新方向有可能不愿意出我这本书了,也许人家觉得我不够格,新方向的眼光太高了。后来,我就给他们出版社的一个人(著名作家)写了封信,说你实话跟我讲,我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你们出版社出书?那个作家给我回信说:“我当然认为你应该跟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们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你要是按照宇文所安的说法我哪配,当然他说的也不是我。我写的诗跟朦胧诗很不一样。美国汉学家陆敬思和莫楷都认为我的诗正在摆脱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双重束缚。陆敬思在他的《创造性辩证法与中国当代诗歌对新形式的追求》一文中说我“正在重铸当代中国的文学表达”。他这篇文章的译文很快会在《诗书画》杂志上登出来。
吴投文:目前有很多汉学家从事中国新诗研究,比如顾彬、柯雷等人,你如何看待汉学家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否符合中国新诗的实际情况?
西川:柯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尽管他曾经在荷兰被称作“摇滚教授”。他在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的时候,有他的学术背景。顾彬、柯雷两人的区别在哪儿呢?柯雷是一个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他追踪的是诗歌现象,中国诗歌发生了什么,中国当代的时代变迁形成了什么样的诗歌?顾彬关心的不是晚近发生的诗歌现象,他是从他的德国文化背景来讨论,他关心的是有什么好诗,有没有好的作家。他们两人虽然都是汉学家,但是他们的学术背景不一样,他们的研究重点也不一样,讨论的问题也不一样,得出的看法和结论也不一样。
吴投文:顾彬说,相对于小说,诗歌实际上更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成就,中国的诗歌在世界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了。他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如何看待?
西川:顾彬这么说的时候,你得知道顾彬在德语世界中是个什么位置,他是以一个作家的面貌出现,还是主要以一个汉学家的面貌出现?当然,他也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者,他又是一个汉学家,又是一个诗人。他对德国的文学界肯定是了解的,所以他才这么说,我想他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中国的诗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达到了国际水平,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大多数中国诗人肯定不在这个行列里。所以,当顾彬说中國的诗歌达到国际水平的时候,他指的是几个人,像北岛、多多、杨炼,还有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他一定指的是这么几个人。当然,他有时也提到我,谢谢他——提不提到我其实无所谓。
吴投文:哦!
西川:顾彬是德国人(又跟奥地利关系密切),他在研究汉学之前是研究神学的,所以他特别要求文学的精神性。他认为中国的小说没有这种精神性,中国的小说都是传奇,都是故事。他认为中国的小说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把中国的小说与德国的小说比,可能就会觉得中国的小说有些问题。当然,他对中国小说的看法我也不完全同意,比如他对于莫言的看法。我曾经对顾彬说过我对莫言的看法,我说你有偏颇。顾彬并不是我的译者,我在德国有另外的译者,尽管我们也熟,也有一些交流。说到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地位,汉学家的看法只是一方面,我有很多汉学家朋友,除此之外,我直接认识一些国外的作家、诗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我也知道。说起来又有意思了。我以前也说过,了解中国诗歌的外国诗人没有那么多,但只要他们了解中国诗歌,就会对中国诗歌有比较高的评价。但他们给出比较高评价的对象,也是几个人,不是所有的人。
吴投文: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人?
西川:甚至比那几个人还少。刚才我说的是顾彬的看法。因为顾彬跟这些人打交道,他退休以后就生活在中国。在国外,有些人不跟这些人打交道,像美国纽约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艾略特·温伯格,他说起中国当代文学来,会说到北岛、顾城和西川;艾略特是小布什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全世界最著名的三个批判小布什的知识分子之一。另一位是印度得过布克奖的阿伦达蒂·罗伊,就是写《卑微的神灵》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如果换成美国语言派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我曾经与他一起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朗诵,在我用英文朗诵了《开花》之后,他不得不临场改换本来准备好的朗诵内容——他说起中国文学,一定会提到车前子。澳大利亚诗人、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员约翰,金塞拉也会提到车前子,当然也会提到我。要是英国诗人,像W·N·赫伯特、帕斯卡尔·佩蒂特,他们一定一天到晚地说“炼,炼”——杨炼。而像阿根廷获得过二〇一〇年西班牙文学批评奖的青年小说家、诗人,也是波拉尼奥的好友的安德列斯·纽曼——他的《世纪旅人》已经翻译成了中文;我在西班牙碰到过他——我们的记者问他了不了解中国文学,他说了解—部分,说了几个中国作家的名字,李白、苏轼、西川。这个你在中国的网上都能找到。
吴投文:我们新诗研究者看不到这些,没有这个条件。……说到当代诗歌的翻译,好像朦胧诗人们被翻译得更多些。那么你们这一代诗人作品的翻译情况呢?请具体谈谈国外对你诗歌的翻译。
西川:好多话我没法自己说,你自己判断吧。刚才我提到我的作品发表在《巴黎评论》上,出版我英文诗集的出版社是纽约的新方向出版社。这是美国顶级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国外,内行人不在乎你出没出过一本还是几本书,人家首先看你是哪个出版社出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曾有美国诗人问我我的出版社是哪家,我说是新方向,对方立即表示他听了都起鸡皮疙瘩。
二 以国际视角回看中国新诗
吴投文:说实在话,国内做诗歌批评的人对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影响了解有限。
西川:不光是这个问题。我去年十月份与咱们一个批评家一起去美国,曾经在阿肯色州一座当代美术馆里与几个美国诗人一起做朗诵,听众没有太多人,但参加活动的美国诗人都不赖。其中包括出任过美国诗人协会主席的施家彰、白萱华、语言派诗人汉克,雷泽、批评家斯蒂芬·弗莱德曼等。他们都是做先锋实验的诗人和关注先锋实验的批评家。咱们的批评家自己并不写诗,就在现场朗诵了卞之琳、穆旦的诗,就是中国诗歌批评界、大学中文系里特捧的几个人。我就觉得在那个现场,朗读这样的诗人的作品特别不对头。
吴投文:对穆旦,你与欧阳江河好像批评得比较厉害?
西川:不是厉害。穆旦在他那一拨人里算好的了。穆旦在中国为什么重要呢?原因之一是穆旦有中国表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原因之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后,穆旦他们是所谓现代主义诗歌信条的实践者。但是在穆旦身上,你感受不到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的创造力和思想深度。五四以来中国诗人的写作实绩其实一直挺弱的。当然,穆旦比文艺青年们好。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穆旦问题》,我在文章里说,穆旦因为分量足够,我才这么认真讨论他,他如果不够分量,我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对于不好的诗人我要么不提,要么就只会说好—一所有你不愿意认真讨论的人,你都说好,就省事。但是,穆旦由于他重要,我才认真讨论他的诗里面有什么问题。
吴投文:你认为批评家的创造力到底是指什么呢?
西川:能够鉴别人所鉴不出的东西,不能全是套话,不能全是用现成的概念来套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居然一个新词都发明不出来,那還做什么批评?诗人们向前走,而批评家们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看住自己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学来的那些概念。
吴投文:但是,目前在诗歌批评界内部,批评家对诗人同样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观察当代诗歌的。
西川:他可能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但是,他那套知识系统全是别人提供的,是从国外学来的,从他的导师那儿学来的,他自己发明了什么?
吴投文: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很多诗人对当前的诗歌批评不满意,实际上有很多的诗歌批评家在追踪当下诗歌的变化,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西川:他们是在追踪。但却是用一种老眼光追踪。他们也需要打开他们自己。他们也需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别说诗歌批评家了,干哪一行都需要有才华,有没有才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谈吐都会显露自己的才华,不打开可能性的讨论就是没有才华的讨论。咱们撇开诗歌这一块。譬如,有多少人在研究历史,但是你一旦读傅斯年,你就会发现傅斯年才华横溢,他就能够看到历史当中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你看另外一个人写的历史著作,你就觉得没劲,全是罗列一些事实,顶多能够找到一些文献一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尘封的文献就已经不错了。即使像历史研究,咱们都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谁是有才华的,谁是没有才华的。不是说只有诗人需要才华,干什么都需要有才华,连挣钱都需要有才华。比尔·盖茨挣那么多钱,因为他有才华。批评家不能成为诗歌写作推进的绊脚石。有些人就是在充当绊脚石的角色。
吴投文:我也对目前的诗歌批评感到困惑,目前的诗歌批评确实和当下诗歌的发展不是保持同步。但是,这种研究上的时间差距似乎也有某种合理性,很多东西需要时间来沉淀。
西川: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不是批评家认为自己是合理的,诗人也觉得自己是合理的,大诗人也觉得自己是合理的,小诗人也觉得自己是合理的,教授们觉得自己是合理的,博士生们也觉得自己是合理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那么如何尽量客观一点地说话呢,我们就需要坐标了。比如说,你对诗歌做出的批评力度,与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相比,与海伦·文德勒相比,与玛卓瑞·坡劳夫相比,与伊格尔顿相比,达没达到他们那种力度?左派、右派、保守、激进,都可以,看你的批评力度。伊格尔顿是怎么做文学批评的?伊格尔顿不断涌现出新鲜的观点,不断地有发现,哪个中国的批评家达到过这种状态?没有。你看一个批评家的行文就能够看出来,他的批评行文中有没有激情——个别人的批评里我也读到这种激情——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如果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我就认了,问题是我知道国外批评家是怎么做的。实际上,好多东西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我坦率地讲吧,我在学术界有很多朋友,人家根本瞧不上咱们的诗歌批评,这真让我窝火。人家跟我讲,为什么我们不读中国当代诗歌,因为你们没有好的批评。这是学术界其他领域做学术研究的人跟我讲的。
吴投文:这倒是一个警醒。
西川:这不是一年两年了,多少年都是这个样子。几十年不进步。还有就是,诗歌界内部有一个小江湖,谁的身份高一点,谁的身份低÷点,老师是谁,后进者是谁,分得很清楚。同样是学术界,你去政治学研究领域去看一看,去历史学研究领域去看一看,甚至也可以去经济学研究领域去看一看,人家都做成什么样了?只有诗歌批评是这个样子,从不拿自己和别的领域的学者做任何比较。
吴投文:我也注意到了,现在有不少诗人,自己同时又是批评家。
西川:因为没办法,有什么办法?只好自己出来说话。
吴投文:你如何看待社会公众对当代新诗的质疑?如何看待先锋诗歌的读者问题?
西川:这个问题我在别的访谈里也回答过了。我说,社会公众对当代诗歌的质疑是出自他的知识结构,他们的诗歌知识结构不外乎由三种东西构成的:一个是唐诗宋词,他把对唐诗宋词的理解拿来套在中国当代诗歌头上;第二个是老苏联传下来的“积极浪漫主义”,这也是一种看待诗歌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里面也包括了革命文学。很多人就守着这三种知识,就是这样一个知识结构,这样,他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就不会有好的看法。因为中国当代诗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框架。
吴投文:对。经常有人对当代新诗进行指责,有人说看不懂,有人认为新诗无意义,有人认为新诗和中国的古典诗词成就相比相差太大,没有继承中国的诗歌传统。
西川:我谈了很多次了。你看我马上要出版的《唐诗的读法》,包括我刚在一月三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面有大段文字讨论这个问题。你要是觉得中国新诗不好,我就跟你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也比那些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不会少吧,我不能说更深刻,至少是更独特的。
吴投文:还可能更全面一些。你在中央美院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
西川:嗯,我给本科生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给研究生上“中国当代文化研究”课。
吴投文:这两门课差别很大啊!
西川:都是关于中国的,而且我觉得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有历史逻辑上的关联。你看,讲“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时,我会讲到中国历史,许多当代问题会直接牵扯到中国古代文化。
吴投文:你讲“中国古代文学”有什么重点没有?主要讲哪些作家?
西川:我用的课本是林庚的《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但是我的课基本上是对林庚的批判,我觉得他书写得太抒情了,有时候挺矫情。而且由于成书早,许多这个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都没能被包括在其中。我自己最关心的几个重点,一个是战国诸子,这是我用力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唐代诗歌也是我感兴趣的部分。
吴投文:你对唐诗讲得多吗?
西川:我就讲到唐代为止,从中国文学的开始讲到唐代,我讲唐诗的方法可能跟别人也不太一样。
吴投文:你是采取什么方法呢?
西川:就是我对唐诗的认识与别人不一样,比如对李白、杜甫的看法。你是不是已经看了我的《唐诗的读法》?
吴投文:我还没来得及全看,就是在网上下载了一些片段看了。你的看法与林庚先生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吗?
西川:我跟好多人对唐诗的看法都不同。中国古代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死的,它必须是活的东西。比如说,讲杜甫大家都会讲到安史之乱,但是,我立刻问你安史之乱死了多少万人?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前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七五四年的总人口数大概是五千三百万到五千六百万之间——那时只有户的统计没有人口的统——整个安史之乱死了两千多万不到三千万人,死了一半人,这才出了一个杜甫。你要是不讲到这个份上,杜甫究竟为什么会出现?怎么唐诗到杜甫就转向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向?与安史之乱死了多少人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文学史一般不会讲到这一点,只是提到安史之乱,提到杜甫怎样颠沛流离——那颠沛流离到什么程度,他每天看见多少死尸等,这些都没人讲。也没人把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水岭来讲,也没人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到这个时候的转向——儒家传道系统彻底取代传经系统。做文学史研究的人不借助社会学、思想史的角度来展开工作,真正的历史就不能被带入,大家讲的都只是从文学到文学的东西。讲文学只是从文本出发,只是分析诗写得如何好,这没有太多的意义。我在《唐诗的读法》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唐代诗人是怎么写诗的?你别光说唐代诗人伟大,他们究竟是怎么写的?我们写诗的人都知道,不是随时都有灵感,我经常长时间没有灵感。而那个时候,参加个宴会或者送别,你都会写诗,可要是没有灵感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有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我在《唐诗的读法》里提到了,它记录在日本人空海法师的《文镜秘府论》这本书里,那里边有关于唐代诗人怎么写作的记载。
吴投文:他们随身带着韵书?
西川:那不叫韵书,叫“随身卷子”。他们身边是有参考书的,使用随身卷子就能写诗。我们现在管唐诗叫“类型化的写作”,就不是我们现在写的新诗。因为是一种类型化的东西,用一本参考书现场就能编出一点儿东西来。
吴投文:我前段时间看《杜甫诗选》,觉得杜甫确实有时代造就的一面,他是一位和时代现实紧密相连的诗人,他的诗里面表现了自身的真切感受。但是,这在李白身上是不是一样的,两人有什么区别没有?
西川:李白、杜甫、韩愈、王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唐诗选,我把它叫作“安静的人名排列”,王维之后排李白,李白之后再排谁?高适或者刘方平或者岑参。但是,真正回到唐代,你会发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之间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到今天,我们已经模糊了。我在文章里面专门提到了韩愈,韩愈在今天都已经排不进唐朝的前几位诗人的行列了。但是在宋代,苏辙说“唐诗当推韩杜”——宋代最棒的唐代诗人是韩愈和杜甫,韩愈甚至排在前头。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热爱韩愈。韩愈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之前的“桐城派”。现在写古诗的人写的都不是真正的古诗,我跟写古诗的人说,你们别吓唬我,你们根本就不会写古诗,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文化准备是写词的,就你读的那点古文够你写个曲儿,写个词,但写不了古诗。因为写古诗需要的文化准备是经史子集,你没读过就别跟我谈古诗。这种传统一直到桐城派都有,但到五四运动一下翻过来了。
吴投文:你对中国古代文学做了这么久的研究,这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具体的影响?
西川:中国古代诗歌对我的影响肯定有,但那都在我的血液中了。我读了那么多,你要说没影响,那肯定不对。但真要说起影响来,我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受到的影响不仅来自诗歌,也来自散文,来自战汉诸子,来自绘画。我马上要写一篇关于北宋山水画的文章,材料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古代诗歌的影响肯定有。但我觉得一个当代诗人努力变成古代诗人的影子,这是陈词滥调,这么讨论诗歌就没劲。对我来讲,这不能满足我的智力要求。所以,你说我受到过李白的影响吗?我受到过,我年轻时读《李太白全集》,一半内容我都是朗读着读下来的。但问题是,我们这么谈李白对我的影响,没有意義。
吴投文: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在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有很多博士、教授也读不懂诗歌,中文系的学生绝大部分不读诗,也读不懂诗歌。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大学教师,感到非常尴尬。
西川: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因为当代诗歌是正在进行中的东西,还没有成为“知识”。所有已经过去的东西对这些学者来说就是知识了。比如说,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觉得自己挺牛的,觉得自己研究的是冰心,那是一门学问。当代诗歌,他不觉得这就是知识。当代新诗还没有“晋升”到知识的阶段。好多大学里研究新诗的老师,都遇到同样的麻烦。大概是二〇一五年,我去湛江的广东岭南师范学院做了一个演讲,讲完以后,那里的张德明教授特别感慨,他说我的那场演讲让他感觉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尊严的。中国当代文学背后的文化思想、文学趣味、创造力的展开方式、它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由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当代性,那些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哪懂?
吴投文:哦,像我们的知识结构就比较有限。
西川:诗歌界有一些人,诗人群里也有一些人,他们把诗歌的门槛拉得特别低,人人都可以进来,自由进出,他们就以为诗歌的门槛是特别低的。
吴投文:是的。有时我在外面参加学术会议,同样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有些人对新诗的了解就非常有限,他们对当代新诗的评价不仅比较低,而且对新诗也充满误会,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
西川: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讲——就说是西川说的——中国是当代世界诗歌写作最活跃的四个地区之一。这四个地区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北美,一个是东欧,一个就是中国。这四个地区的诗歌写作是非常活跃的。东欧诗歌是由不同的小语种构成的,要是东欧不同的小语种不能算成一个语种,把它除外,就是中文+西班牙语和英语是当下最活跃的诗歌语言。那些人如果认识不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好处,那我只能说他们有问题,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没有真正的国际视野,没有一个广度,也没有历史的纵深度。
吴投文: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量的博士和教授读不懂新诗,这种隋况非常奇怪。
西川:我也不要求人人读诗。诗歌如果人人都读懂了,那就成了怪事。汪国真的诗人人都能读懂,刚去世的余光中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人可以接受的,还有台湾的席慕蓉。诗人和诗人太不一样了。人人都知道李白,大众最熟悉的就是《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李白诗里面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就是摊给那些真正理解诗歌的人去体味的东西了。同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诗歌。
吴投文: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很多,可以说与新诗旗鼓相当,甚至还要多,我身边就有很多写旧体诗的人。
西川:一定比写新诗的人还多。
吴投文: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西川:首先人家喜欢写点诗,我觉得那挺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也不用说人家。但是,我想提醒他们,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已经提醒过了,他们写的所谓旧诗不是真正的古体诗,他们大多数人,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他们的知识储备、文化贮备都不是用来写诗的。他们的文化贮备是用来写词的。中国古诗背后的知识储备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是经史子集。所有中国现在写古体诗的人,你问他们,经史子集读了多少?一般人可能读过点《论语》《孟子》,但是大量的文献他们都没有读过。基本上他们对古文的了解是《古文观止》,对古诗的了解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构成了他们的古代文化趣味。他们能写点儿古体诗,合辙押韵,但平仄谁不会啊?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我张嘴就来,谁不会?这没有难度。而且他们喜欢用一些古词,而那些古词在古代可能就是陈词滥调了。到了今天,由于古汉语已经死掉了,他们就觉得这全是精华。现在中国好多写古体诗的人,以为他们在写古体诗,但其实他们写的充其量就是“诗化的詞”。如果你想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古体诗写作者,你就得重回经史子集,重回进士文化。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要多少代人的工夫才能回去,而且,回得去回不去,我就不知道了。
吴投文:一个诗人不是一个时代,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判断出来的,要在长久的历史时间中逐步阐释。可能与目前中国的文化环境也有关系。很多研究者对世界诗坛确实缺乏了解。对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国内诗歌研究者确实都不太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目前你在北师大的工作状态。
西川:我刚到北师大,还没开始上课,到下学期才开始。
吴投文:目前的写作有什么计划没有?
西川:不用什么计划,我一直都在写。当然大部分我在写的东西不是诗歌。诗歌也在写。我根本忙不过来。我最近在给一个杂志准备四十页的稿子,一直都没闲着,都在干活。
(责任编辑: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