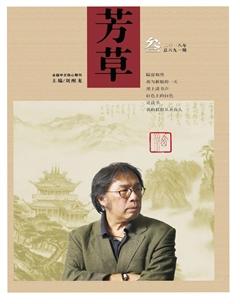喻之之:文学是爱的语言
汤天勇:喻主席好啊!(笑)你看你现在也是作协领导了,相关的事务和活动也定会多起来,它给你的写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喻之之:汤老师好,我是领导吗?一直没觉得呀,我现在的工作关系仍然在教育局,级别是一般科员,从这个硬标准来说,我不是领导,但我又担负了文联主席这一项职责,算不算矛盾呢?但不管怎么说,我实在没觉得自己是领导呀。
影响当然有,两方面的,积极和消极的。消极的影响是事务繁忙,身在运行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随着核心运转起来,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突击任务,对于写作会有所打断,想要一气呵成地完成某些短篇,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了。但今年过年,我躲在远方完成了一个短篇,并且编辑觉得质量还不错,还是很高兴的。
积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遇到的困难,见到的各式人等,特别是人性的复杂和幽微都不是当初可以想象的。人生只是一场旅程,生活给予了我们什么,都坦然接受,然后带着欣喜的心情去发现,并记录,可能就是我想做的事。
汤天勇:洞悉到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其实对写作本身而言帮助很大的。作家访谈,一般都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写作动机,也即为什么写作?之于作家,一般或可隐藏,或可进行艺术化处理,或可坦诚相告。我之所以如此饶舌,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坦诚自己的写作动机。
喻之之:记得我在《迷失的夏天》这本书的序言里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叫《文学是爱的语言》。提到一件童年往事,就是亲人去世,自己很害怕死亡,从而想通过写作来延长生命的愿望,因为作家的生命会消亡,但优秀的作品却会永存。这就是我最初也是最真的写作动机,但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当我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者乡村的泥土小路,看到劳作的人民、欢喜的孩童,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爱来,多年前甚至我在滠水公园的河堤上散步时,看到县城的万家灯火时,我想到那每一个小小的窗口,都住了一家人,他们有多少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他们有勤劳善良,也有小聪明、小狡黠,然而他们不过是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不济,也只不过是想自己比别人过得好一点点,我顿时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要拥抱那些房子的感觉,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很高很大的巨人,像拥抱一个孩子一样的拥抱那些小區,并摈膜它们的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所有的爱必须找一个出口,那就是写作,那时候,我才开始写作,但我知道,假以时日,我一定会是个优秀的作家,不因为任何别的,就因为胸中涌动的这股爱。
汤天勇:“文学是爱的语言”我很欣赏,起码从字面上理解我感觉到一股暖意融融。你喜欢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其实有部分作家一旦写作思维枯竭时,很聪明地找寻到一个前辈作家做榜样,汲取创作灵感,你会么,或者说你的灵感取自何处?
喻之之:我喜欢的作家很多,有一些是会反复阅读的,比如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奥兹、赫拉巴尔,中国的有汪曾祺,也曾反复阅读《红楼梦》,但我一直是个执拗的笨人,不会也不愿意走任何捷径。到现阶段为止,我的所有灵感都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和人民的感动,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对生活敏感和敏锐的心,生活中时常有人和事触动我。
汤天勇:写作来源于生活,不假。有时候,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颇为微妙。你的作品已有不少评论家予以关注,你会认真看他们的评论么?他们的阐释与读解是否能够切近你的意图?你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
喻之之:有些会认真看,有些浏览一下。有些评论家确实能通过作品洞悉你的创作思路和内心,但有些评论家只是作品在他的主观意识中引起的反应,他并没有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动机。如果机缘巧合,碰巧看到了评论我的文章,我会看一看,一笑而过吧。我认为跟评论家聊天比看评论收获更大。(笑)
汤天勇:聊天比评论写作更为开放,交流碰撞中就不定就会火花四溅。大江健三郎说,“好作家都有其自身的风格意识。”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在写作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显示出一定的风格趋向与识见。你写作至今,是否也会考虑自己的写作风格?
喻之之:好的作家当然都应该有他的风格,有时候风格是有意识建立的,有时候是自然形成的,我更欣赏后者。目前,我并没有考虑建立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还在不断地尝试,尝试真正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现在的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次切割原石的过程,怎样切割、从哪个角度切割,才能得到最完整、最宝贵的玉石,这是我目前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我在等待,等待这个不断阅读、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而且,我相信这样形成的风格更适合自己,也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天赋。
汤天勇: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有预设的想法,比如让小说中的人物附带着某种倾向?
喻之之:嗯嗯,有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打算,草蛇灰线,让他沿着某种思路前进,有时候则是让人物自然生长,可能写着写着,人物就活起来了,要求自己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这时候我要做的呢,只是顺着事物的内在逻辑来就是了。
汤天勇:小说集《十一分爱》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二〇一二年卷”,在丛书总序中,袁鹰先生说,“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并表明入选丛书的“文学之星”系“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是经过“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的。这次入选虽不如娱乐造星那么轰烈,但多少也是一种荣耀。尤其是入选者而言,似乎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喻之之:这个要感谢《芳草》主编刘醒龙老师的推荐,确实是一种荣誉,他会让你更早地进入编辑和评论家的视野,获得更多的关注,但之后的路还是靠个人走,有些“星”们发展得很好,比如孙频、甫跃辉,有些早已不写了,庆幸的是我还在路上,而且我相信自己会背负着这种荣誉带来的压力,越写越好。至于压力问题,因为我也常常自己给自己压力,所以外在的压力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汤天勇:风景在作家的笔下大致呈现三个不同的修辞承载:真实关系的承载、心灵状态的承载与意义延伸的承载。三者没有逻辑层次上的高低之别,都是作者修辞策略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尤其是时下很多作家似乎不屑于风景描写了。你有个特点,喜欢写风景。你引入风景,是为了凸显人与事的真实性,是为了抒情达意之需要,还是赋予某种隐喻性功能?
喻之之:我只能说这三者都有。我喜爱风景描写,它能为作品带来诗意,也能衬托或反映人物心境,甚至像你所说的,表达某种隐喻。风景就是流动的画面,我想读者喜欢说我的作品画面感很强,这跟我喜欢描写风景有某种关联吧。现在有很多批评家已经开始批判现代作家不描写风景了,比如孟繁华老师,听过他一个讲座,讲《三国演义》,他不仅对其中的风景描写大加赞赏,还用风景来比喻三国,他称东吴是锦绣江南,魏是雄阔曹魏,蜀是英雄刘蜀,您看,这里面就有两国是用地理特征来命名的,有时候,一个地方的风景是可以代表某种内在气质的。你看东欧的作品,看《日瓦戈医生》、看《爱与黑暗的故事》,看马尔克斯,我们的四大名著,风景描写多好啊,把各地的山川风物通过风景描写表现出来,丰富了人物形象,丰富了作品内涵,也带给读者阅读的享受。当你回顾这样经典的作品时,就会再次默认风景描写的重要性了,这就是广博的作品和“小”的作品的高下之分了。
汤天勇:诚然,阅读风景就是一种享受。八〇后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并且用之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俨然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了。但你的创作实质上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路数。并且,你的笔触是面向大地,面向社会,面向现实中人。我就纳闷,作为八〇后作家,你既不与青春写作关联,也不愿意附庸于现代主义文学,反而热衷写实?
喻之之:八〇后的作家,最小的也快三十了,青春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印迹,但我们也过早地与社会碰撞了,比如高房价、一毕业即失业,包括现在已成家的八〇后面对父母的医疗、子女的教育等等问题,任何一个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我认为,如果一味地写青春,不和现实相关联,就容易流于无病呻吟。至于说选择哪种表现形式,我想这也和湖北本土强大的现实主义土壤有关,方方老师、刘醒龙老师、池莉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現实主义的范本。马尔克斯也是现实主义写作呀,人们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他说,不,就是现实主义,这就是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您也说得很对,我的写作是面向大地,面向社会,面向现实,这主要跟我的创作动力有关,前面谈过。另外,我觉得耍哪个门派的武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招制敌,不然,都是花拳绣腿。您说呢?
汤天勇:对啊,“八〇后”也谈了好久了,晃眼也就“人到中年”。当然,你的现实主义论实际上是一种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从代际划分来看,你是湖北文坛八〇后作家群体的代表性作家,就创作实绩来看,湖北八〇后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面临着“突围”的问题,尤其是五〇后、六〇后作家雄踞文坛三十年,无论是知名度、学界关注度都是“笼盖四野”的,并且他们大多又是走的现实主义路子。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喻之之:惭愧惭愧,除了我自己,实在不敢代表谁。湖北的五〇后、六〇后作家的确实力非常强,前面提到的这几位老师都写了一辈子,作家靠作品说话,人们对他们的尊敬,都是靠他们点灯熬夜一个字一个字码字码出来的,我们要想超越他们,并非易事,首先得向他们学习,尊敬老师,向老师学习,取长补短,写好自己的作品,做好自己的本分,这就是我给自己的定位。
汤天勇:就你的小说涉及的题材范围来看,都市、乡镇和农村都有;就主人公职业来看,白领、教师、记者、大学生、商贩、农民、医生、市民等等,你写作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稳定几个题材范围,比如都市女性之类的,这种题材对于你这样生活在武汉的女作家而言似乎优势更为明显。你也知道,写作触角伸得越远,它对写作者的知识储备与写作素养的要求越高。你写作时是基于何种考虑?
喻之之:的确是这样,写不同的题材对写作者的知识储备和写作素养都是考验,但我不想写固定题材的作品,老写那几个题材的作品,也是挺没劲的。每一种职业在写之前,我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解行业信息、职业特点,和选取最能表现他们特征的角度进行切入。除了挂职锻炼,我也常去医院、菜场、乡镇体验生活,写《映秀之恋》时,我特地搭军车去过映秀,并在汉旺做过一段时间的志愿者。我自己以前当老师,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写起教育来,还会去乡村小学体验生活,因为这些年农村变化很大,现在的情形和前几年大不相同了,要想抓住时代的命脉,就必须与时代共振。
我也说过,自己的小说是要“给苦难以温暖”,要对这个时代的每一种艰难感同身受,要像一只苍凉的小手拂过那些残缺的、不完美的人生,因此,我必须写大众,不是写某一个群体的大众,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芸芸众生——有知识有地位的众生,没钱没权的众生,卑微的众生,趾高气扬的众生……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芸芸众生。
一个好的长篇,涉及的绝不止一两种职业,多的甚至达到几十种,像我国的四大名著,涉及的职业多达百种,而人物类型,更是千差万别,也正是因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么多独特的人物形象,才成为不朽的名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做好各方面的知识储备,也是为自己将来写长篇打下基础。
汤天勇:你目前的小说,似乎每篇都有点沉重,人物显得有些无力和顿挫,有社会的因素,有自然的因素,有他人的因素,也有自我的因素。你就不想写写美好?
喻之之:还好吧,我的小说应该不算很沉重。
幸福的人生大抵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不同,我更希望给苦难以温暖。而我写苦难,并不仅仅是沉醉在苦难之中,而是写苦难状态下人的生存状态,写各种善良坚韧的人冲破苦难的过程,从这个程度上来讲,还是写入,写人性。
当然,我的作品也有写美好的,而更多的是经历苦痛后的云破月来吧。
汤天勇:当然,你很多小说的结尾,还是为我们保留了一点希望。这大概与你的写作初心有关吧?
喻之之:嗯嗯。汤老师所言极是。苦难是茧,但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能破茧而出,而其中,帮助他们破茧而出的就是人生的温暖,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有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基于这一点,我的小说应该是温暖的小说。
汤天勇:这与你的“文学是爱的语言”相关联的。在你心中,好小说有什么标准么?你最满意自己的哪篇作品?为什么?
喻之之:如果要称得上好的小说,那就是立意、结构、语言、人物、情节都好的小说,或者说是骨骼、脉络、血肉、灵魂都好的小说。比如说,像《礼拜二午睡时刻》《圣女》《搭车游戏》《露茜卡和巴芙琳娜》《受戒》都是我膜拜的好的小说,——但可惜都不是我写的。(笑)
实在惭愧,我自己没有很满意的小说,有一些小说在某一两点上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但也有一些地方还不够。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自己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但就是笔力达不到,我在这一状态下已经徘徊了好久,有一点点竹笋在破土而出的感觉,下一篇吧,加油!
汤天勇:我们常说十分爱,十二分的爱都可,你的中篇小说《十一分爱》,为何取名“十一分爱”?
喻之之:在汉语中,“十”和“十二”都表示多的意思,那么十一,表示的是比“十”多一分,就是比多更多的意思,——就是很用力很用力地爱,如丁霁心的爱:但又比“十二”少一分,就是比多少一分的意思,——如李敖的诗,别人的爱那么多,我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这就是我要取的双重意思。
汤天勇:《十一分爱》和《映秀之恋》后,你有两个变化(我也不晓得是否准确啊):一是从写作的技术来看,《十一分爱》你采用对位叙述,叙事进程中现实与过去穿插进行,《映秀之恋》也将背景延长放大。二是,这两部作品关注的是爱情,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内心私语和精神世界,而后来的作品写爱情少了,写作的面也铺得更广。我想问下,你是否有着一种刻意的写作转型?如果有,是什么动因促使的?
喻之之:没有刻意转型,现在我手上的小说,就题材分,也是一个爱情小说,但当然不仅仅是写爱情。我本身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比较感兴趣的人,就像很多作家读书时都偏科,但我读书时不偏科,而且理化还不错,记得有一次还拿过全校的物理竞赛第一名。我想,这或多或少地投射到写作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阅读量的提升,以及更多的思考,写作面必然会铺得更广,现阶段思考的社会问题比较多,也许,等我想清楚一些,或许会有好作品问世。
汤天勇:《十一分爱》中,曾子麦与一个已婚男子坚守着他们的爱情,丁霁心通过不停地换男朋友慰藉灵魂,她们不敢追求真正属于她们的爱情与婚姻,一直处于逃避状态。其实,她们两人之所以如此,都有一个家庭的因素。所以,她们身上的张力既体现在逃避,也是在寻求平衡与稳定。另外两个女孩,佩佩和表姐,他们也想生活安定。但是,表姐夫外遇不说而且亲手杀死了情妇,无可避免地逃脱不了牢狱之灾:佩佩看似追逐的爱情有了结果,可她也知道大刘喜欢的是曾子麦,爱情的大厦也是摇摇欲坠。这样看来,不管是逃避,还是寻找稳定,她们始终无法逃离精神之困。那“爱”的出路在哪里?
喻之之:爱情的出路在阮七七那里。(笑)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连自己的爱情出口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幫天下的女性朋友们找到答案呢?有大数据统计,现阶段的单身青年达两亿人,两亿,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其中包括未婚、未恋和离异状态的年轻人,他们的爱情出口在哪里呢?再看古今中外的小说,涉及爱情的不少,但似乎很少有完美的结局,比如宝黛之恋,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不得不说,也是人幽的悲剧;再看《安娜·卡列尼娜》,女主最后卧轨自杀了;《茶花女》女主角玛格丽特先天不足(贫穷和肺病)让他们一再错过;《洛丽塔》男主和女主年龄、身份、地位、心智悬殊(甚至还有点乱伦),根本够不上爱情;而《耻》,肉欲的成分多过爱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根本没有把女性当人看待(随时当作礼物和诱饵送来送去);《西游记》更好笑,凡是貌美如花的,不是妖精就是神仙,除了女儿国国王,神仙又不能爱,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爱情……倒是咱们金庸大侠的笔下,有许多完美的爱情,比如郭靖和黄蓉,这一对组合基本上没经历什么磨难,有误解也迅速化解,从一开始甜蜜到最后;还有小龙女和杨过,这对神雕侠侣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最后终于笑傲江湖了。所以说,爱情的出口在金庸大侠那里。(拱手三拜)
汤天勇:金大侠给你提供了一个爱情乌托邦。还是这部小说啊,你好像没有把笔墨当作匕首无情地掷向男性啊,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可取或可谅之处啊,据此判断,好像你不是一个常言道的女性主义作家吧?
喻之之:嗯嗯,那当然不能无情地掷向男性啊,我们的爱情还指望着跟他们共同完成呢。据说女性比男性早进化五十万年,所以男同胞没有女性完美是正常的,也有心理学家说,女性要把男性当成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是玩笑,我想我的态度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关,在生活中,我并不是一个纯女性思维的人,比较中性,也很懂得换位思考,所以我不会一棒子把男同胞打死。因此,我虽然是女性,也写女性,但绝不是单纯的女性主义作家。
汤天勇:《映秀之恋》也是爱情小说,不过你将爱情升华的地域放置在汶川大地震这个背景之中,爱情就不能说是“欲”的问题了,而是与“死”与“大义”相联系。你当时为何这么构思故事?
喻之之:写《映秀之恋》的目的不是写爱情,是写八〇后的成长。八〇后是比较特殊的一代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且出生之初正逢改革开放,这些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不少八〇后娇生惯养,我们也习惯被人们这么批评,我们也正是在这种批评下长大。二〇〇八年,第一批八〇后已参加工作数年,那特殊的一年,不论是在大地震中,还是在随后的奥运会中,八〇后都有耀眼表现,因此我想把映秀地震作为一个节点,来写八〇后的成长,是基于此,才设计了这么一对恋人,这么一段恋爱关系。其实我的好多小说都是这样,包括你前面谈到的苦难压抑等等,那些都是外在的皮,而真正的内核是冲破这些压力的人、人性的力量和温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