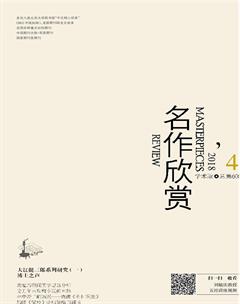西方诗学概念述要
吴涛
摘 要:自亚里士多德以“诗学”为题讨论史诗与悲剧起,“诗学”作为一个文论术语在批评话语中经历了概念的扩充和变迁。以差异和影响为标准,在诗学概念发展过程中有所建树的文论家以施泰格尔、雅各布森、卡勒和迈纳为代表。本文追溯了诗学概念的提出、沿袭和发展,介绍了以上主要文论家对诗学概念的界定和贡献。
关键词:诗学 施泰格尔 雅各布森 卡勒 迈纳
在讨论西方诗学概念时,不可不提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诗学一词的英文解释是“Treatment of the Art of Poetry”,即“诗歌艺术专论”。亚里士多德对诗学的讨论主要基于戏剧而不是诗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厄尔·迈纳(Earl Miner)教授在《比较诗学——文学理论跨文化论集》(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90)一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两个显著特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是,虽然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名字——荷马是与叙事诗和史诗联系在一起的,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却是基于戏剧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述了史诗和悲剧理论,以此建立的艺术理论是其逻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艺术理论观点十分现代。亚里士多德从舞台造型艺术和某些诗歌音乐形式中看出彼此的相似之处,并从中发现了他们的共同元素模仿(imitation)。模仿即对人文和生命的描绘,“人类做了什么和遭受了什么”,虽然这一术语在他《诗学》的很多地方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还在《诗学》中提到很多涉及美学的理念,他对艺术的简短专论引人注目。《诗学》是现存第一本致力于文学批评的著作,也确实是第一篇关于广泛美学的专论。20世纪关于艺术的道德观看法逐步失势,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应该是自发的,一件艺术品可能就是一件很好的艺术,甚至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而道德和政治只会对艺术有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确实说过诗歌中的正确标准与伦理学中的并不相同,他完全不赞同诗人没有道德责任的理念,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美学理论中是不存在的。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诗人的看法,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诗作时既不会受到神灵感召,也不能自我表现。亚里士多德抛弃把诗人看作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的浪漫主义观点。他认为诗人只是技艺工匠,在希腊语中“poiesis”的字面意思就是“制作”。亚里士多德《诗学》著作的翻译权威卢卡斯(D. W. Lucas)教授认为,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几乎不提天才或灵感,他也不关注神话中的宗教和道德含义,因为他不想让这些因素影响到受过教育的成年民众。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是一系列讲义笔记,由两部分组成,分别论及悲剧和喜剧。遗憾的是涉及喜剧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已遗失。《诗学》中大部分内容似乎在对戏剧观众而非剧作家说话,后面几章内容才对剧作家剧情构造、选择展现的人物性格特征等提出具体的技术性的实用建议。《诗学》重点论述了戏剧和史诗的技巧,集中探讨的艺术形式是悲剧。亚里士多德讲述了如何构建一部完美戏剧和史诗,成功制定出有关戏剧艺术的首批伟大原则。这些戏剧逻辑规则即使是当代最富冒险精神的剧作家都不容忽视和忘记。《诗学》从一开始就以教授写诗技艺为己任,确定范本并从中提取规则以作为评判后世创作之准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实是属于范本规则的诗学。
瑞士苏黎世大学埃米尔·施泰格尔(Emile Staiger)是当今文学研究界重要的诗学研究学者。施泰格尔诗学研究的代表作是《诗学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 der Poetik,1939),在这部著作中他对诗学概念的理解糅合于对诗作三分的理解中。他认为历史上对诗作的三分法是有根据的,只是不能用抒情作品、叙事作品和戏剧作品作为类的名称,而必须改用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他用回忆、呈现和紧张概括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的本质。施泰格尔认为纯抒情式的、纯叙述式的、纯戏剧式的诗作是不存在的,一切诗作皆“杂”。而“杂”并非是诗作的缺陷,因为几乎一切诗作都参与了这三类,只是参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这就造成诗作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施泰格尔的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三个类的概念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语言行为方式,其代表的语言要素分别是音节、词和句,代表了语言的感性表达阶段、直观表达阶段和概念思维表达阶段,这正是人的本质组成的三个重要领域:感情、图像和逻辑。
施泰格尔主张以文学类型学代替文学分类学,对强调学问教养、范本规则、做诗技艺、模仿范本为灵魂的亚里士多德范本规范诗学提出批评。施泰格尔认为“诗人在创作诗作时应创造性地将个人新的风格融入已有风格的程序化‘纯模仿中,以形成一种杂合诗学”,“倘若以范本和从中提出的规则为准绳,那么,唯有符合这标准的诗作方可称之为‘纯。但这种‘纯的观念实际上是在提倡对已有风格的程序化模仿,并扼杀任何创新。而‘杂的观念反倒为‘创造精神的发挥辨明了理由”。施泰格尔对诗学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具体诗作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对诗学的很多看法与赫尔德、歌德和席勒对诗学的认识有共通之处。施泰格尔并没有完全背弃西方亚里士多德模仿诗学的传统,他对西方的类型理论提出挑战,倡导树立新的极端分裂革命诗学模式,以尊重詩人的创作精神,对西方诗学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美国语言学界对诗学概念做出权威界定的是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雅各布森认为诗学是“在语言信息这一总的背景和在诗这个具体背景下,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1987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雅各布森的一部重要著作《文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Literature,1987),这部著作的第七章收录了他著名的论文《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cs and Poetics,1987)。雅各布森在这篇论文中提出诗学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使言语信息成为艺术品”。雅各布森认为诗歌是语言艺术,其规则限于作为全球语言行为科学的语言学范围内。但有学者认为他的论点并不正确,因为假如诗歌是语言艺术,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应在美学范围而不在科学范围内。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只是对客观能够证实的假设的经验性证实程序。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现象,而文学研究的对象却是从该对象本身形式结构产生的相互主观的意义和价值。雅各布森主要从语言学角度来谈论诗学。他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方还有两位著名学者从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角度论及诗学概念,他們是乔纳森·卡勒和厄尔·迈纳。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在《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997)一书中他将诗学定义为通过描述传统和阅读,试图对文学效果的解释。卡勒认为诗学始于被证实的意义和效果并探寻其如何获得这样的意义和效果。譬如小说中是什么使一个段落具有讽刺意义,什么使我们对一个特别的角色报以同情,为什么一首诗结尾部分含义模糊等。卡勒还比较了诗学和阐释学的不同,认为阐释学始于文本并探寻文本的意义,寻求发现对文本新的更好的解释。阐释学模型来源于法律和宗教领域,人们在这些领域寻求对权威法律文本和神圣宗教文本的解释,以决定采取怎样的行动。卡勒认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更偏爱阐释学而非诗学,原因在于人们总体上对文学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去探究文学的功能,而更想知道文学作品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东西到底是什么。诗学不要求我们知道一部作品的意义,它的任务是解释我们可证实的效果,例如,一个结局比另一个结局更成功,一首诗中意象的融合颇具意义,而在另一首诗中这样的融合却没有意义。此外,诗学关键在于为读者如何解释文学作品做出描述。卡勒在此将诗学与阐释学区分开。简单地说,阐释学关注文本的意义,而诗学更多关注文本的不同元素如何聚在一起并对读者产生某种效果。卡勒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研究》(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1975)。
厄尔·迈纳(Earl Miner)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著名教授,在其名著《比较诗学——文学理论跨文化论集》中,他将诗学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迈纳指出两种不同的普遍性诗学体系,其中之一在实践上是隐含不露的,这种诗学属于所有视文学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一种独特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另一种是清晰的原创或基础诗学,这种诗学只见于某些文化,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找不到。诗学的存在所需的对于文学独特性的假定涉及的就不是一个“黑洞”,而是由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共同构成的“群星”。迈纳认为当文学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实践基础上加以界定时,一种独特的诗学便会出现,正如亚里士多德从戏剧方面定义文学时建立的西方诗学。由于戏剧是人在舞台上动作的再现,亚里士多德把文学看作是对人类行为生活的一种模仿。与卡勒不同,迈纳主要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及诗学概念。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 and D.W. Lucas.Poetic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xiii.
[2]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Aristotle.On the Art of Poet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9: vii.
[4] Aristotle.Poe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x.
[5] 埃米尔·施泰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
[6] Roman Jakobson. Questions De Poétique[M].Paris:Seuil,1973:486.
[7] Roman Jakobson. Language in Literatur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63.
[8]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