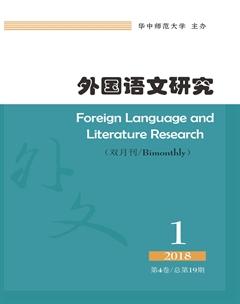告别布卢姆斯伯里:朱利安·贝尔中国之行隐在的文化政治
内容摘要:以后殖民文化批判为视角,本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现代主义诗人朱利安·贝尔中国之行隐在的文化政治。朱利安·贝尔中国之行引申出英国文化自我与中国文化自我的跨文化双向旅行,最终促使他在经历跨文化心理疏离之后开始审视、批判布卢姆斯伯里自由主义传统。这表征了在英国布卢姆斯伯里现代主义精英群体内在的价值分裂——从自由主义向激进左翼政治的否定式裂变——过程中,中国所发挥的独特酵母式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朱利安·贝尔;布卢姆斯伯里;中国之行;隐在的文化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BWW0009)。
作者简介:陶家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小说、西方文论和后殖民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latent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travel to China by British Modernist poet Julian Bell in the 193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ies. Julian Bells travel to China initiates transcultural voyage-out and voyage-in between British Cultural Self and Chinese Cultural Self,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his gaze at and critique of Bloomsbury liberal tradition after experiencing transcultural psychological distancing. This is symptomatic of the internal value split-up of British Modernist elite group Bloomsbury, a negating implosion process from liberalism to Left politics in which China plays a unique catalytic role.
Key words: Julian Bell; Bloomsbury; travel to China; latent cultural politics
Author: Tao Jiaju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novel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E-mail: taojiajun@bfsu.edu.cn
朱利安·貝尔(Julian Bell)1937年7月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牺牲,一年之后,霍伽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弟弟昆丁·贝尔(Quentin Bell)编辑的《朱利安·贝尔:论文、诗歌和信件》,其中收录有他的82封信件、14首诗歌、3篇公开信形式的论文。1966年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William Abrahams)以朱利安·贝尔和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为研究对象的《到前线去: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路》问世。1991年,伦敦索斯比拍卖行将朱利安·贝尔写给凌叔华的信件拍卖给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收藏馆(Berg Collectio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现代档案馆也收藏有朱利安·贝尔的档案。帕特丽夏·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以朱利安·贝尔与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著作《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卢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在2003年问世。2012年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斯推出了新研究成果《朱利安·贝尔:从布卢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这些材料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带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印迹,指向朱利安·贝尔以及围绕他编织成的多样世界。在帕特丽夏·劳伦斯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的男女爱恋关系被阐释为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小组与中国的新月社、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发生关系的支点。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在《朱利安·贝尔:从布卢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中偏重于探讨朱利安生活中与女性的性爱关系以及他的性心理结构特征。这样凌叔华就被放置在与其他女性同等的位置,尽管他与凌叔华的爱情有其独特的扣人心弦的激情和浪漫。而关于他的性心理特征,这两位学者既强调了瓦妮莎·贝尔的母爱对朱利安个体性心理成熟的妨碍,也肯定了朱利安性心理中暴露癖、多性恋、放荡等特征。例如他们从朱利安不断寻找、需要情妇的习惯中发现:“所有的事情共同促使他成了浪荡子:他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坚持一种‘对爱的性放纵观点”(Stansky,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7)。又例如他们特别强调朱利安在武汉期间从开始与凌叔华的爱恋关系发展到后期同时与凌叔华、英尼斯·杰克逊(Innes Jackson)等的多角性爱关系。他们的有力证据是朱利安的自白:
我开始厌倦了做爱,但是就是不可能放弃。像英尼斯甚至S这类女性——这些不得不在感情上需严肃对待、照顾、小心的女性——不再是我的茶杯了。只是令人感到糟糕的是,我从与英尼斯的相处中体会到,我确实有勾引有知识、有审美品味女人的天赋。谁又能摈弃这样的天赋而不用呢?嗨,走着瞧。(Stansky,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235)
这种过度的性阐释打上了当代西方理论思维的价值烙印,遮蔽了朱利安·贝尔中国之行更应被肯定的后殖民文化政治意义。因此我们深入分析他的中国之行隐在的文化政治的两个纬度——跨文化的双向旅行、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跨文化审视和批判。借以重新认识朱利安·贝尔在摆脱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羁绊、构建中国与英国之间逆向的跨文化关系中的积极主动以及他的激进政治观点,揭示布卢姆斯伯里这一20世纪上半叶英国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知识群体的文化和政治局限。
一、跨文化的双向旅行
1934年5月朱利安·贝尔开始向“剑桥任命委员会”提出在远东的中国或日本谋求大学教职的申请。约翰·谢帕德(John Sheppard)和梅纳德·凯因斯(Maynard Keynes)为他写推荐信;罗杰·弗莱的妹妹玛杰里·弗莱(Margery Fry)通过中国的朋友为他疏通关系。1935年7月16日,朱利安收到中国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英语教授的聘任通知。按照合同规定,他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英语教授任期为两年,第一年为试用期,教授《文学批评》和《现代英国文学选读》,年薪800英镑。
1935年8月29日,朱利安·贝尔在法国马赛搭乘日本客轮“伏见丸井”号,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布卢姆斯伯里小组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他的太平洋航程。他途经斯里兰卡的科隆坡时,列奥纳德·伍尔芙的朋友、代理总督用隆重的礼仪欢迎他,为他提供奢华的生活条件。途经香港时,列奥纳德·伍尔芙的妹妹在总督府设午宴招待他,陪他游览参观香港市容。1936年1月朱利安利用寒假从武汉到北京游览。受朋友所托,他拜访了正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阿克顿不仅设晚宴专门招待他和正寓居于北京的英国旅行作家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而且陪同他和凌叔华拜访了画家齐白石。1936年12月他决定前往西班牙,投身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正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教育的I. A. 瑞查兹(I. A. Richards)专门写信劝阻他:“别去西班牙参战。我当然崇拜任何这样做的人,非常崇拜,就像有人羡慕某类犬一样。但是结果却与行为和代价名不符实,哪怕连不会算计的动物也能看出这一点——无论于你、英国、世界亦或是未来都是如此”(Richards 98-99)。
以朱利安为连接点的这张布卢姆斯伯里小组人际关系网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在印度洋、太平洋、中国编织的脱胎于殖民传教、殖民贸易、殖民行政管理、殖民文化传播的网络;第二个基础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成长的英国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基于此,在武汉大学期间,朱利安·贝尔构建了以他自己、凌叔华和叶君健为核心的新的文学、思想和情感网络,并积极地将凌叔华和叶君健引荐给弗吉尼亚·伍尔芙、瓦妮莎·贝尔、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刊物《新作品》的主编约翰·莱曼等,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推向英国,或者说是国际现代主义文学舞台。
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联系始于朱利安·贝尔的牵线搭桥。她能跻身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得益于朱利安的亲人瓦妮莎·贝尔、弗吉尼亚·伍尔芙因对朱利安的爱和思念而衍生出的对她的关爱和帮助。1936年2月瓦妮莎通过朱利安转赠给凌叔华一幅她自己的水彩画。这年5月16日朱利安到武汉汉口的邮局给瓦妮莎寄去凌叔华和她女儿的照片以及他收集的中国古董的照片。8月底他结束了到四川的旅行(从武汉出发,途径湖南、长江三峡、重庆、成都、雅安、西藏东部地区),然后从成都乘飞机到北京与凌叔华会合,同时寄给远在英国的亲人一套四川人喝盖碗茶的瓷器茶具。凌叔华在北京专门为朱利安的妹妹安吉莉卡买下一套被保存了四十年的满族贵妇穿的宫廷服装。这些绘画、照片、茶具、服装、首饰用形象可感知的物的方式逆向传达了细腻、生动、鲜活的情感和友谊。
朱利安帮助凌叔华将她写的两个短篇故事翻译成英文。《关键是什么》(英译名是“Whats the Point of It”)发表在英文月刊《天下》1936年8月第3卷第1期上;《诗人变疯了》(英译名是“A Poet Goes Mad”)发表在《天下》1937年4月第4卷第4期上。此外朱利安還将与凌叔华合译的、她写的三个故事寄给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作家兼出版商大卫·伽尼特(David Garnett)。伽尼特将英译稿转给瓦妮莎后,她试图将这些故事发表在颇负盛名的文学月刊《伦敦水星》(The London Mercury)上。1953年凌叔华的英文版作品《古韵》由列奥纳多·伍尔芙掌控的霍伽斯出版社出版。凌叔华自己绘插图,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同性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作序。
通过朱利安·贝尔,凌叔华与瓦妮萨、弗吉尼亚形成了情感共鸣。朱利安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后,瓦妮萨与凌叔华之间经常信件往来。在1939年9月16日给凌叔华的信中,瓦妮莎写道:“我觉得他的去世使你与我之间的某种联系成为可能。如果他还活着也许我们之间不会这样。因此让我们竭力维护它,亲爱的苏”(Berg Collection)。在1939年12月5日给凌叔华的信中,瓦妮莎更动情地写道:“我仍爱你,如果我的爱能对你有任何帮助,你知道你拥有这份爱。……在任何情况下请尽可能保持乐观,我知道朱利安会告诉你同样的话”(Berg Collection)。这种情感共鸣是两位深爱着朱利安的女人对死者的共同悲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阴霾中两个女人甚至她们所属的群体相互之间爱的慰籍。
1938年春凌叔华在阅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后开始了俩人之间的通信。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38年4月5日给凌叔华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我知道你甚至有比我们更多的理由悲伤,因此任何建议一定显得极其愚蠢。……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创作,但是朱利安经常写信告诉我,且想让我看看你的部分作品。他还说你曾有过非常有趣的生活经历。其实我们曾讨论过——我想是在信中——你尝试用英文写出你的生活经历。(Woolf 221)
在稍后的4月22日下午凌叔华在武汉大学见到了到中国采访的英国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和作家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她专门托伊修伍德转送给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颗象牙雕成的头颅。直到这一年的7月27日伊修伍德才将凌叔华的礼物送到弗吉尼亚·伍尔芙手中。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给凌叔华的全部信件中,最具跨文化文学创作价值的无疑是1938年10月15日的信。在这封信中,弗吉尼亚从跨文化的角度深度阐释了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风格、修辞、文化意蕴等诗学问题。
我终于读到了你寄给我的这一章……现在我写信想说我非常喜欢它。我认为它很有吸引力。……我发现那些比喻奇特且有诗意。……请继续写下去;放开、自由地写;不必介意你是怎样直接地将汉语翻译成英文。事实上我愿建议你尽你所能在风格和意思上尽可能贴近汉语。尽量如你喜欢的那样多描写生活、房屋、家具的自然细节。始终像你面向中国读者写作那样来创作。如果在某种程度上由英国本土人士来梳理文法,我认为应尽可能保留汉语味道,使之对英语读者来说既能懂又奇特。(Woolf 290)
弗吉尼亚指出了跨文化创作的真谛:通过诗学技巧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原文化和原语言的滋味。
叶君健是朱利安·贝尔在武汉大学的学生,是除凌叔华之外他与之建立深厚私人友谊的第二个中国青年知识份子。朱利安像帮助扶持凌叔华那样帮助叶君健。他特意把叶君健的作品推荐给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刊物《新作品》的主编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因此《新作品》1937年刊载了叶君健的短篇小说《王德胜从军记》以及他的三篇翻译作品——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白平阶的《在中缅公路上》。
1944年叶君健受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赴英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宣传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在宣传演讲间歇,利用周末回伦敦休息的时间,乘火车去英国南部苏塞克斯的小镇查尔斯顿,与朱利安·贝尔的母亲瓦妮莎·贝尔团聚。因此他有缘进入由瓦妮莎·贝尔、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梅纳德·凯恩斯、列奥纳德·伍尔芙等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大轰炸的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核心中坚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叶君健从伦敦迁到剑桥去住,一边上课一边从事写作。他续上与朱利安·贝尔的妹妹安吉莉卡和妹夫大卫·伽尼特的友谊,经常在下午骑车去拜访住在剑桥郊区的他们。
到了20世纪80年代,间隔了几十年的通信联系后,叶君健趁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演讲的方便,重走当年去查尔斯顿的老路,拜访住在那里的昆汀·贝尔和夫人安妮·奥利维尔(Anne Olivier)。睹物思人,透过当年的老房子、他们夫妇收集整理的文稿,他又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再次发生情感和精神交流。因此他从昆汀·贝尔身上发现:
这也可以说,他继承了以卡尔斯登为中心那一小批文艺家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既表现在他的创作上,也表现在他的工作纪律上。他既烧瓷器,又作雕刻,还要整理佛吉妮娅的手稿和遗物,自己又要研究美术史和理论,他要作的事太多。……这事实上也是他老一代人的工作方式,是那小批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中间所形成的传统。昆定保持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给20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增添了光辉,但现在已经成了历史。(叶君健,《叶君健全集》76)
只不过与弟弟昆汀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朱利安选择了一条跨文化远行、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并为之英勇献身的道路,告别布卢姆斯伯里,告别布卢姆斯伯里传统。
如前所论,我们必须将朱利安·贝尔的中国之行放在大英帝国殖民文化和地理版图上。这样我们不仅能从他的中国之行主动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发掘出他挣脱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影响的努力,而且发现他跨越文化帝国主义的束缚、摆脱帝国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无畏精神。这不仅表征为他与凌叔华、叶君健建立起的情感认同纽带,而且更直观地表现为他到中国后对在华西方殖民者的鲜明批判立场。1936年春叶君健陪伴朱利安·贝尔去四川旅行。他们到了四川泸定桥附近的一家天主教堂住宿。面对神父对叶君健的傲慢无礼,朱利安气愤地拒绝了神父给他提供的優待。“‘用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的朋友,他说,‘也是对我的侮辱,我不能忍受,让他见鬼去吧!”(叶君健,《叶君健全集》371)
如果说朱利安·贝尔积极主动地将凌叔华和叶君健推荐给布卢姆斯伯里圈子,这是他主导的以凌叔华和叶君健为被动角色的跨文化互动,那么凌叔华和叶君健在朱利安牺牲后自觉地推动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联系并用鲜明的中国主题、中国风格进行的文学创作则是从跨文化发声的层面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政治介入。因此朱利安的努力和来自中国的两位作家的努力共同形成了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论的后殖民文化政治的“顺向航行”(殖民作家从帝国中心到边缘的旅程)与“逆向航行”(后殖民作家从边缘到帝国中心的旅程)两个层面。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朱利安·贝尔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反叛和颠覆,而这一切都隐藏在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背后。这种颠覆因他而开始,却在凌叔华和叶君健的文学发声政治中走向中国自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再现。
叶君健的英文作品面向英国和西方读者大众,运用独特的文学表征手法,以现代中国的红色革命和民族自由独立为主题,以乡土中国为背景,以草根阶层农民为历史主体,向西方讲述真实的中国、真正的中国、凤凰涅槃的中国。这些血脉偾张、家国情愫浓郁的英文作品包括:1938年在《新作品》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王得胜从军记》、1945年岁末在英国《读者文摘》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冬天狂想曲》、1946年秋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无知的与被遗忘的》、1947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村》、1948年春出版的长篇童话小说《雁南飞》。《王得胜从军记》和《冬天狂想曲》都被收入《无知的与被遗忘的》。20世纪80年代《山村》的后两部《旷野》和《远程》英文版在英国出版。《无知的与被遗忘的》出版当月被英国出版界的“书会”(Book Society)评为推荐书之一。《山村》出版当月被“书会”评为最佳作品。
在回忆录中,叶君健解释了自己20世纪40年代的英文创作动机。在《无知的与被遗忘的》这部短篇小说集“所涉及的人物大都是一些贫苦无知的农民和手艺人,及其他类型的贫苦劳动群众。事实上他们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是他们传宗接代,延续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叶君健,《叶君健全集》473-474)。而他创作《山村》的原因是:“我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中及与英国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存在着许多误解……描绘出一个较生动的在中国农村所发展起来的革命图景,使读者能从中真正体会出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其实际意义”(叶君健,《叶君健全集》475-477)。这一回忆反映出叶君健两部在英国有影响的作品的题材和价值取向。放大到国际跨文化框架中去,这两部作品表现的题材具有鲜明的中国发声特征——中国的文化、民俗、人情世故;中国以农民和农村为根基的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和生命;中国劳苦大众反法西斯的顽强和牺牲、反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和独立之路。
二、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跨文化审视和批判
与朱利安牵动、推动的中英跨文化双向旅行平行,却被批评界忽略的是越过文化边界的他在中国期间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独特审视和批判。不仅在表现言说的话语形式上,而且在自我的批判主体性建构上,他实现了对布卢姆斯伯里小组这一英国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神圣文化家族的反思和反叛。这无疑与他积极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在武汉大学一年零三个多月的英国文学教学是朱利安到中国后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进行审视的独特方式。1935年10月5日抵达武汉大学后的第三天,他就开始了教学工作。与聘任合同不同,他原定教授的两门课变成了《莎士比亚》、《写作》和《现代文学》三门课;原定年薪减少到700英镑。开始时,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是美妙、善良且乐于助人。“大学里的人们像极了剑桥人,非常友好、随和、乐于交际。我们都住在散落在山坡上的房子里,邻居之间经常串门,像随意的剑桥生活方式那样”(Bell,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43)。
在1936年秋季学期的课程《现代文学:1890年-1914年》中,他讲解的英国现代作家包括: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茹坡特·布鲁克斯(Rupert Brooks)、豪斯曼(Housman)、威尔斯(Wells)、萧伯纳(Bernard Shaw)、塞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937年春季学期的课程《现代文学:1914年-1936年》中,除了讲授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集中向学生传输的是剑桥实用批评学派和布卢姆斯伯里小组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他选取的英国现代主义人物包括:I. A. 瑞查兹(I. A. Richards)、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拉姆塞(Frank P. Ramsay)、穆尔(G. E. Moore)、G. L. 迪金森(G. L. Dickinson)、梅納德·凯因斯、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杰·弗莱、弗吉尼亚·伍尔芙。
随着教学重心转到他最熟悉的实用批评学派和布卢姆斯伯里小组,他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以及布卢姆斯伯里传统进行反思。在1936年1月10日给弟弟昆丁·贝尔的信中,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简直是“一种奇怪的主张”(Bell,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72)。到了这一年的5月份,他进一步认定中国历史传统中不存在牢固的智识(而非单纯的浪漫感伤)文学。因此尽管他们真诚、勤劳、忍耐,但是却缺乏理性、智识、观念传统。他们从英国文学中接受的只不过是二流作家的二流文学,如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罗斯金(John Ruskin)。他的中国学生尽管知识面广,记忆力好,能大量地背诵唐代诗歌,能在作文中尽情宣泄浪漫情怀,但是却不能进行抽象、大胆的理性思考。
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学传统中强烈的感性、浪漫、情感和柔美的批判最终使他转而批判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精神象征人物之一G. L. 迪金森。在1936年5月22日给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信中,他就毫不客气地批驳过迪金森。他认为迪金森之所以钟情于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的柔和与多情善感,是因为他被压抑的情感的迸发。而所有这些温情、阴柔、平和的人性都不足以强硬、坚实、冷峻到使他和人类抵抗,遏制日益迫近的战争和暴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情感浓烈、追求挚爱的凌叔华面前,他为什么会发出困惑和疲倦的哀鸣:“我从来没有发现人心中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我太厌倦感情了——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感情。这并非意味着我没有感情。……我如今真正、真诚地相信:我认为友谊比爱情更适合我”(Stansky,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209)。
朱利安在中国期间的书信体散文和论说文既是他对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探索,又是他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批判方式的创新。他最早在诗歌创作领域显露才华。1927年秋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专业,两年后转到英语专业。1929年1月开始,他连续在剑桥大学学生文学刊物《冒险》(The Venture)上发表诗作。1月份《蛾》刊登在《冒险》第二期上;4月份《冬季运动:一首正式的颂歌》刊登在《冒险》第四期上。在《冒险》的最后一期上他登出了自己的诗论文章《略论诗的晦涩》。1930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冬季运动》正式出版。1935年11月、12月,刚到中国一个多月的他就在英文刊物《天下》上连续发表了7首诗作:《形而上的慰籍》、《向马拉美致敬》、《伦敦》、《红脚鹬》、《形而上的泛神论者》、《尾声》和《帕斯卡尔》。1936年1月,他与凌叔华在北京度寒假期间,他的新诗集《为冬季而作》由霍伽斯出版社出版。
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斯认为,早在1929年春朱利安实际上就已在剑桥确立了自己的诗人声誉。“他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了,他自己、他的朋友乃至剑桥都这么认为。在与朋友的谈话中诗歌也许是最重要的话题。此外他在学生会也是个人物。他加入了使徒社。他还是个运动好手”(Stansky,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68)。此外还得加上:他是一个论说文作者。他在诗歌、散文和论说文方面的才华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它们在不同的境遇中成为他表述自我情感和思想的手段。
无论从马赛登上驶往中国的船还是从香港登上回欧洲的船,在往返于西方与中国的航程中,在中国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朱利安用手中的笔写下的主要是三篇公开信式的批判文章以及与亲人和朋友之间大量的信件。他尝试用崭新的方式来尽情地展露并保存在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书信体和论说文体来言说自己日渐成熟、逐渐独立并最终与布卢姆斯伯里传统彻底告别的情感、思想和政治生命。因此中国之行不仅促成了朱利安现代主义文学表述方式和风格的骤变,而且使他的个体生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新生。他最终挣脱了母亲、长辈、朋友乃至整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对他的情感、思想和政治羁绊。
对于他那些自成一体的大量书信,批评家们从中获取到与自己批评阐释的主观意图吻合的不同证据材料。但是除却那些有关私人两性情感、有关中国各地的见闻、对中国风景的审美凝视之外,朱利安不断强化、日趋强烈的反法西斯决心和左派政治意识无疑遭到根本性的忽略。开始时他关注的是中国国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以及远东地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战争,接着他就密切关注着欧洲的局势。在1936年4月13日给瓦妮莎的信中,他就大胆预测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走向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避免:
至于希特勒——从你和弗吉尼亚写信谈论这个话题的方式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紧迫的问题。……但是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他如此丧心病狂,他就不会被吓住——那么对我而言似乎无论从社会主义还是和平主义的角度看克莱夫都是对的。……就目前而言,如果制裁的结果必将导致战争,那么整个左派都举起了爱国主义的大旗。(Bell,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105)
到了1936年10月,他对欧洲局势的判断更使他坚定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决心,也促使他选择了一条与布卢姆斯伯里的自由主义乃至和平主义不同的激进道路。在10月22日给简·西蒙·布斯(Jane Simone Bussy)的信中,他写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政治是如此糟糕——如此糟糕以至于我根本不可能为共产党或自由派而气恼——虽然我不再能理解自由派或和平主义者们。……根本不存在任何和平的希望,无论是民族还是国际意义上,只有在战斗与屈服之间作出抉择。(Bell,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165)
在一个强权政治主宰的时代,自由主义信奉的价值观和坚持的操守已经无济于事,弱不负重。诗歌充其量使人充满了感伤和悲哀。这种向务实、行动的政治的转变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参加西班牙内战,为反法西斯的自由事业而战斗。在1937年1月7日离开武汉前夕的信中,他这样为自己辩护:“不可能让其他人去为自己信仰的事业战斗而自己却拒绝去冒險。……如果我不去,耻辱感将一辈子烙在我心中。……发现民主、自由主义就像老年人贪婪守财一样令人厌恶”(Bell,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184)。
三、结论
对于朱利安的叛逆行为,对于他的冒险心理和对左翼激进革命的向往,最好的证明就是他1935年9月26日刚从欧洲到中国、途径香港时写的、预先托好友在他为革命而牺牲的状况下转给他母亲瓦妮萨的两封信:一封信是他如果得了绝症或意外死亡时需要朋友寄给他母亲的;另一封信是如果他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而遭受不幸时需要朋友寄给他母亲的。他告诉瓦妮萨:“这样如果你听说我坐船船翻了或者卷入战争或暴乱,记住这是我应该选择的那种结局”(Bell,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196-7)。因此经历了中国之行的心路历程、摆脱了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羁绊之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和为自由献出宝贵的生命,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信仰之路,是他告别布卢姆斯伯里后义无反顾的自觉选择。朱利安中国之行引发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意图非常鲜明。1937年1月,在从中国回欧洲的旅途中他写了文章《战争与和平:给E. M. 福斯特的信》,朱利安名义上写给福斯特的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与福斯特和迪金森这两位英国现代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的批判性对话。他与迪金森、福斯特、瓦妮萨、弗吉尼亚乃至布卢姆斯伯里传统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和态度。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要么认为世界建立在稳固坚实的基础之上,要么认为人性的良好意愿能指引社会不断完善进步。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过程和必然性,认为决定世界变化的力量并不是人的意愿,而是客观的物质和社会力量。因此迪金森宣扬的自由主义,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信奉的和平主义,事实上是政治浪漫主义。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上的国际联盟凭借的仅仅是理性和善良,而不是以坚强的实力为后盾。他们无视这样一种现实,即:除了少数善良、理智的人之外,整个世界充斥着愚蠢、习惯、贪婪以及眼里只有利益的大国和实力阶级。他认为,自由主义政治的致命伤就是对实力和权力的忽视,就是对权力的真正来源的无知。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自由主义在英国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在战争和贫穷面前,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仍幻想靠同情、理性和善良来保护自己。
朱利安引发的跨文化双向旅行在空间意义上表征了作为帝国自我代表的朱利安与文化自我的疏离,与中国他者的认同;表征了作为中国文化自我代表的凌叔华和叶君健在与英国乃至西方他者交流对话过程中,在全新的文化思想氛围中,在世界文学场域中,走向文化自觉并向西方文化他者言说中国的转变。朱利安对布卢姆斯伯里传统的审视和批判在思想意义上表征了英国现代主义精英内在的价值分裂——从自由主义向激进左翼政治的否定式裂变。但是这种思想的超越是因为他的中国之行来促成并实现的。换言之,舍去朱利安的中国之行,他的生命轨迹将走上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苦难的中国,革命的中国,柔情似水的中国,发挥了独特的酵母式的能动作用。这是后殖民意义上更微妙但却影响至深的文化政治——有别于后殖民抵抗和颠覆的消解政治。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ell, Julian. 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8.
Bell, Vanessa. Selected Letters of Vanessa Bell. Ed. Regina Marl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Berg Collect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Charleston Papers, Modern Archives,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Julian Bell Papers, Modern Archives,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Laurence, Patricia.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3.
Richards, I. A. Selected Letters of I. A. Richards. Ed. John Constab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Stansky, Peter, and William Abrahams. Journey to the Frontier: Julian Bell & John Cornford: Their Lives and the 1930s. London: Constable, 1966.
---.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2.
Woolf, Virginia.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IV: 1936-194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叶君健:《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Ye Junjian. Europe in Retrospect. Beijing: Jiuzhou Press, 1997.]
——:《葉君健全集》第十七卷散文卷(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Complete Works of Ye Junjian. Vol.17:Prose (2). Beijing: Tsinghua UP, 2010.]
责任编辑:何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