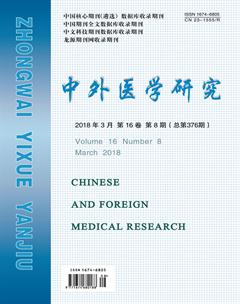基于代谢组学探讨中医药防治痛风的研究思考
顾雯靓 牛晓亚
【摘要】 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生化基础的临床常见病。基于代谢组学可以构建该病的生物标志物评价体系,并对中草药治疗该病的机制做出生理病理学阐释。然而在痛风中医证候生物标志物的建立、代谢组学相关动物模型的选择及中药提取物相关临床研究这三方面仍需研究思考。
【关键词】 代谢组学; 中医临床; 痛风
doi:10.14033/j.cnki.cfmr.2018.8.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8)08-0182-03
Study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out in TCM Based on Metabonomics/GU Wenliang,NIU Xiaoya.//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8,16(8):182-184
【Abstract】 Gout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with hyperuricemia as its biochemical basis.Based on metabonomics,we can construct a biomarker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is disease,and make a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However,there are still three aspect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CM Syndromes of gout,the establishment of biomarkers,the selection of animal models related to metabonomics and the related clinical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s.
【Key words】 Metabonomic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out
First-authors address:General Hospital of Civil Aviation,Beijing 100020,China
代謝组学作为后基因时代新兴起的一门学科,因其能够全面反映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变化及药理机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各个系统的疾病研究。痛风是由单钠尿酸盐(MSU)沉积所致的晶体相关性关节病,与嘌呤代谢紊乱、尿酸排泄过少相关。因此本文通过论述代谢组学的优势,分析痛风的发病机制,对中医防治痛风的临床研究方向做出思考。
1 代谢组学及其研究优势
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对外源性物质刺激、环境变化、遗传修饰所做出的所有代谢应答全貌及动态变化过程的一门学科,与现代分析技术、生物信息学、化学计量学、统计学存在交叉关系,归属分子生物学范畴。研究对象即小分子代谢产物(相对分子质量<1 000)。研究核心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对生物体全部细胞小分子代谢产物的定量分析,侧重于机体代谢产物组成、特性、变化规律的研究,注重寻找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标记物和指纹信息,从而分析生物细胞代谢产物的全貌。因此对比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脂组学、药物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的研究结果能够反映疾病生理病理中生物标志物的全面变化,有效地反映出中草药干预所达到的分子生物信息改变,更适合中医临床研究的应用,这是其他组学所不能相比的[1-2]。
1.1 代谢组学符合整体观念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构建出中医特色理论整体观,内涵为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与外界环境构成一个整体。依据整体观理论指导临床要“见微知著”,注重“三因制宜”。而代谢组学所研究的生物体液可以直接反应人体病理生理状态,放大基因与蛋白表达的细小变化,从而达到见微知著的目的[3]。同时代谢组学可以比较同种疾病不同人群或相同疾病人群在不同时节的代谢产物图谱及其动态变化,进而研究生物体系代谢网络的特征性改变,因此,代谢组学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动态性,这与中医整体观理论不谋而合[4]。
1.2 代谢组学符合辨证论治
中医强调“视其外应,知其内脏,则知所病”,意在说明医者透过患者症状,可推测其体内可能产生的病理生理变化,从而对患者综合诊治。辨证论治便是有效的诊疗手段。辨证是中医根据望、闻、问、切获得的资料,分析判断疾病本质的过程。而疾病导致机体生理病理的过程变化,最终均会引起代谢产物发生相应的改变。所以基于代谢组学,临床通过对病变患者的代谢产物分析,并与正常人的代谢产物比较,可发现疾病一定时间内代谢产物及代谢轨迹所发生的改变及变化规律,摸索疾病发生的生物标志物,探究机体内代谢物表达的终端信息,进而反映并解决中医证候所关注的生物体内的变化问题,对中医证型临床生物标志物的量化确定、疾病本质的阐释,以及并发症的早期预警均有重要意义。这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5]。
2 痛风的发病机制探讨
2013年《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中明确指出痛风的生化基础是高尿酸血症。目前公认的尿酸产生过多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2.1 尿酸异常堆积
尿酸增加异常包括内源性代谢和外源性食物摄入两方面,前者占80%,后者占20%。内源性代谢路径是细胞内的核酸通过水解成多种核苷酸,三磷酸腺苷是其中一种单核苷酸。三磷酸腺苷在磷酸核糖焦磷酸合成酶(PRPP)的作用下分解为磷酸核糖焦磷酸,再通过磷酸核糖酰胺转移酶分解为磷酸核糖胺,磷酸核糖胺在腺苷琥珀酸裂解酶的作用下可生成次黄嘌呤核苷酸(IMP),继而通过嘌呤核苷磷酸化酶生成次黄嘌呤,最后通过黄嘌呤氯化酶(XOD)生成尿酸[6]。
当人体内的尿酸超过饱和度时,逐渐可激活尿酸盐结晶,尿酸盐结晶的启动、扩大并维持炎症引发的关节疼痛称为痛风。需要注意的是人体内的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分化情况决定了尿酸盐结晶是否会触发炎症反应。在痛风发作的急性期,未分化的单核细胞可诱发典型的溶酶体溶解,继而诱导一系列炎症因子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IL-1β)、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环氧化酶2(COX-2)。可见单核细胞在刺激痛风急性发作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上述这些炎症因子可进一步触发中性粒细胞趋化蛋白1(MCP-1)引起中性粒细胞涌入,这是痛风炎症反应的核心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白介素8(IL-8)与中性粒细胞的涌入最为密切,因此中和IL-8或其受体为痛风的治疗提供了可能的靶位[7-8]。
外源性食物摄入途径是食物中的核蛋白在胃酸的作用下分解为核酸及蛋白质。其中核酸受胰核酸酶的影响分解为核苷酸,进而再由胰、肠核苷酸酶分解为核苷及磷酸,核苷再由核苷酶分解为碱基和戊糖,碱基中的嘌呤和嘧啶再被分解排出体外。因此食物摄入的嘌呤较少被利用,尿酸的产生大部分还是由于机体自身代谢异常造成。
2.2 尿酸排泄减少
尿酸主要由肾脏排出,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过多导致尿酸排泄减少,这是高尿酸血症的主要分子基础[9]。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是由不同的转运蛋白完成的,有机阴离子转运体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尿酸盐阴离子交换器(URAT1)、有机阴离子转运器4(OAT4)。
URAT1的基因编码是SLC22A12,已证实SLC22A12基因与尿酸代谢存在相关性。因为URAT1的转运驱动力是由肾小管管腔内尿酸和有机阴离子交换促成的,所以URAT1与有机阴离子有很高的亲和力,也正是在与有机阴离子的交换过程中尿酸重吸收增加。故研究与URAT1有亲和力的药物,减少其与有机阴离子的交换,可减少尿酸的重吸收,这也是目前抗痛风药物研究的重要靶点及热点。另外OAT4的基因变异也证实与痛风病关系密切[10]。
3 代谢组学在中医防治痛风的研究方向
痛风可属中医痹证范畴,病位在四肢关节,病因与过食肥膏厚腻密切相关。已有因子分析证实痛风的病理因素以痰湿热为主,治法以清热、利湿、化痰为主要,临床常用方剂有四妙丸、上下通用方、防己黄芪汤、涤痰汤、归芍痛风饮、虎藤汤等[11-14]。目前中医药相关代谢组学防治痛风的研究主要围绕中药提取物对主要生物标志物的干预进行。如任丽等[15]通过应用虎杖提取物对大鼠痛风模型的干预发现,虎杖提取物能够降低大鼠血清中尿酸(UA)和黄嘌呤氯化酶(XOD)的水平。吴杲等[16]也发现虎杖苷对于抑制尿酸基因URAT1具有明显的浓度依赖性。王璐等[17]研究发现萆薢总皂苷通过抑制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ALP3)炎性体的装配与激活,达到抑制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1β、IL-18)的目的,从而起到防治痛风的作用。但是由于痛风诊断及辨证的生物标志物体系仍未完善、动物模型的代谢产物动态变化仍未完全清楚,中药提取物的临床试验较少,故研究方向的思考是防治的重点。
3.1 痛风中医证候生物标志物的建立
代谢组学对中医证候的本质研究一直为热点[18]。赵铁等[19]采用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技术对湿热证痛风患者29例进行代谢组学研究发现:与正常组相比,湿热证痛风患者血清中的α-羟基丁酸、磷酸、甘露糖明显升高,乙醇胺明显下降。最终得出结论,湿热证痛风患者的血清生物标志物可能是α-羟基丁酸、磷酸、甘露糖及乙醇胺。汪海校[20]运用核磁共振(NMR)代谢组学方法,对脾虚证痛风患者的粪便样品进行代谢组学研究,结果发现丁酸、丙酸、乙醇、谷氨酰胺、牛磺酸、葡萄糖、异亮氨酸、亮氨酸、甘氨酸为脾虚型痛风的生物标志物。牛晓曼等[21]运用核磁共振氢谱(1H-NMR)方法,将脾虚证痛风患者和健康人群的粪便上清均进行代谢组学检测,更进一步发现对于正常人,痛风脾虚证患者粪便上清中的生物标志物变化特点是丁酸、丙酸、甘氨酸含量减少,乙醇、谷氨酰胺、牛磺酸、葡萄糖、异亮氨酸、亮氨酸含量增多。但是痛风的临床证型可有湿热痹阻证、寒湿痹阻证、痰瘀痹阻证、肝肾阴虚证之分。因此证候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应进一步扩大证型范围,并对动态变化做出进一步细致的描述[22]。
3.2 痛风动物模型代谢组学的研究深入
目前痛风的动物模型主要有三种类型:痛风急性关节炎动物模型、痛风性结节肿动物模型及高尿酸血症动物模型。朱洪远等[23]通过应用高效液相色谱(LC/MS)技术,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模型尿液中的生物标志物进行代谢组学研究,并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解析发现:通过代谢组学研究得到的大鼠代谢轨迹变化能够很好地反映大鼠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生发展过程,为痛风性关节炎动物模型的建立提供良好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目前仍不清楚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尿酸生成过多及排泄减少的比例是多少,而且实际上很多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并不会发展成痛风,所以用非灵长类动物模型模拟人类的疾病,并不能成功复制发病机制,也很难表现出与人相似的表现,因此痛风的动物模型仍是研究重点[24]。尤其对于中医研究中的动物模型,既要满足西医诊断,又要满足中医辨证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两年国外有研究表明,树鼩、家蚕都是未来很有前景的痛风代谢组学研究模型。树鼩的脑体比是所有动物中最高的(包括人类),且发病机制与人类接近,用来模拟人类疾病更具有临床意义。而家蚕的嘌呤代谢最终产物也是尿酸,与人类一样,所以可以作为痛风药物的评估模型[25-27]。
3.3 痛风相关中药提取物临床研究的完善
中医药治疗痛风以“个体化”“灵活多变”为优势特点,但是存在服用不方便、不良反应不清楚、缺少临床复发率的观察、长期疗效不明确等缺点。因此中草药提取物防治痛风的机制研究是未来代谢组学的重点[28]。刘树民等[29]采用尿酸钠(MSU)诱导出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模型,再通过应用超高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UPLC-TOF-MS)结合模式探讨穿山龙提取物对其的代谢组学干预途径,结果发现穿山龙提取物能够影响嘌呤代谢,大体路径是通过调节嘌呤代谢中的脱氧尿苷(dG)、肌苷、次黄嘌呤、脱氧腺苷酸(dAMP)及磷酸腺苷(AMP)水平,最终达到抑制大鼠体内尿酸水平合成的目的。徐娇[30]通过应用红外光谱技术(FT-IR)、核磁共振技术(NMR)得到月腺大戟乙醇提取物,并发现该物质的高剂量(100 mg/kg)能够改善由氧氰酸钾建立小鼠高尿酸血症模型中血清、肝脏的尿酸含量,同时还可能显著降低肝脏中黄嘌呤氧化酶(XOD)的水平,肾组织切片显示肾小管上皮细胞结构松散,部分细胞脱落,未见不可逆病变。陈娜[31]通过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秦皮甲素、延胡索乙素进行含量测定,建立痛风胶囊的质量标准,并将秦皮甲素(C15H16O9)、延胡索乙素(C9H8O4)确定为痛风胶囊的质量草案。再将该药干预由次黄嘌呤腹腔注射造成的小鼠高尿酸血症模型,发现可以明显降低血尿酸(UA)水平。Bin Han等[32]应用核磁共振(NMR)技术发现虎杖60 g、桂枝10 g混合提取获得的0.7 μg/ml泵提取物对大鼠痛风性关节炎的关节肿胀和炎症细胞浸润的抑制作用明显,主要是通过抑制TNF-α、IL-1、NF-κB p65蛋白的表达和滑膜组织实现的。同时还发现对于尿酸钠(MSU)引起大鼠痛风的病理生理变化途径与能量代谢、氨基酸代谢及肠道微生物代谢失调相关,而虎杖桂枝的泵提取物对于这些代谢紊乱具有保护作用。李贞景[33]运用分光光度法對香椿叶总黄酮提取物含量进行测定,最终发现乙酸乙酯萃取物能够抑制黄嘌呤氧化酶(XO)的活性,再应用氯嗪酸钾造成小鼠高尿酸血症模型,发现香椿叶总黄酮提取物能够降低小鼠体内尿酸水平,同时还能使尿酸水平恢复至正常范围内。
实际临床中痛风患者常以痛风发作,继而服用药物,出现肝肾功能损害,停用药物,出现痛风再次发作加重这样的恶性循环为表现[34]。所以中药提取物的临床规范研究,毒副作用评价是未来研究方向。使中草药提取物防治痛风的代谢组学研究更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及前瞻性。
随着核磁共振技术等科技发展,代谢组学已广泛用于临床疾病诊断、分子生理病理学、基因功能组学等多个领域。痛风的发生是在代谢产物层面的。人体模式识别受体(PRR)的突变,导致炎症小体(TNF-α、IL-1β、IL-6、IL-8等)的活化和慢性炎症的增加,是慢性关节炎的基本病理。所以阻断PRR信号通路上的靶细胞因子是治疗关节炎的基本途径,也是慢性风湿免疫系统的治疗方向。综上所述,充分运用代谢组学,可以有效、全面地获取痛风疾病大量代谢产物信息,从而找出中药干预更有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周爱儒.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3.
[2]虞萌,黄家恺,巴俊强,等.生物标志物的筛查方法及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17,23(5):867-871.
[3]李小科,叶永安,杜宏波.代谢组学方法在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研究中应用的思考[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6,26(1):60-62,65.
[4]牛玲玲,牛俊奇.代谢组学在肝脏疾病的应用进展[J].中华肝脏病杂志,2012,20(8):634-635.
[5]李先娜,董辉,孙晖.代谢组学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应用[J].中医药信息,2016,33(5):114-117.
[6]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共识专家组.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J].中华内科杂志,2017,56(3):235-248.
[7]廖光惠.痛风的发病机制与治疗研究进展[J].中外医学研究,2017,15(8):161-163.
[8] John H KIippeI,John H Stone,LesIie J Crofford.风湿病概要[M].第1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1-232.
[9]张蓓,孙玉萍,姚华.hURAT1、SLC2A9、ABCG2与高尿酸血症、痛风的关系及临床意义[J].医学综述,2013,19(2):216-218.
[10]沈小莉,张廷剑,刘瞳,等.痛风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业,2016,25(9):1-5.
[11]吴文静,王世东,周鑫,等.基于因子分析的痛风病病机研究[J].世界中医药,2013,8(5):491-494.
[12]孙晶,于永军,陈宝忠.中医药治疗痛风病的研究进展[J].中医药信息,2016,33(5):126-129.
[13]佟颖,文慧丽,李一平,等.痛风及高尿酸血症近年来的中医治疗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5,4(11):66-69.
[14]向黎黎,熊辉,陆小龙,等.中药治疗痛风用药规律的文献研究[J].中医正骨,2015,27(12):46-49.
[15]任丽,欧水平,陈灵,等.虎杖提取物及其有效部位的大鼠抗痛风性关节炎试验[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6(19):111-115.
[16]吴杲,吴汉斌,蒋红.虎杖苷的降尿酸作用及其机制研究[J].药学学报,2014,49(12):1739-1742.
[17]王璐,那莎,陈光亮.萆薢总皂苷对大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NALP3炎性体信号通路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通报,2017,33(3):354-360.
[18]颜凤蛟,葛惠男.代谢组学在中医证型本质研究中的应用进展[J].山西中医,2014,30(1):58-59.
[19]赵铁,殷婷婷,张英泽,等.基于代谢组学的强直性脊柱炎和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证共性特征研究[J].中医杂志,2013,54(7):592-596.
[20]汪梅姣.基于粪便上清代谢组学及基因组学探讨脾虚型痛风的生物学特征[D].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2013.
[21]牛晓曼,汪梅姣,何志兴,等.基于粪代谢组学的痛风脾虚证实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8):3071-3075.
[22]廖婷,费洪新,张英博,等.中医药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J].黑龙江科学,2016,7(6):22-23.
[23]朱洪远,肖锦,刘羽洁,等.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模型尿液的代謝组学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41(4):660-663.
[24]周京国.痛风的动物模型与模式动物[J].中华风湿病学杂志,2017,21(7):433-435.
[25] Pan X H,Zhu L,Yao X,et al.Development of a tree shrew metabolic syndrome model and use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treatment[J].Cytotechnology,2016,68(6):2449-2467.
[26] Zhou L,Li H,Hao F,et al.Developmental changes for the hemolymph metabolome of silkworm (Bombyx mori L)[J].J Proteome Res,2015,14(5):2331-2347.
[27] Li Y,Wang X,Chen Q,et al.Metabolomics analysis of the larval head of the silkworm,bombyx mori[J].Int J Mol Sci,2016,17(9):E1460.
[28]吴蕊,王镁.痛风的中医治疗现状[J].山西医药杂志,2015,44(6):662-664.
[29]刘树民,张宁,于栋华,等.穿山龙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肝脏代谢组学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7,42(10):1971-1978.
[30]徐娇.月腺大戟的化学成分及抗痛风活性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4.
[31]陈娜.痛风胶囊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09.
[32] Bin Han,Huizhu Huang.Therapeutic Eff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Herb Pair,Huzhang and Guizhi,on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Induced Gouty Arthritis in Rats Revealed by Anti-Inflammatory Assessments and NMR-Based Metabonomics[J].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2016,16(2):1-12.
[33]李贞景.香椿叶总黄酮的提取及其降血尿酸的研究[D].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08.
[34]李明,黄传兵.中医药治疗痛风的临床研究进展[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9(5):547-550.
(收稿日期:201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