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问养成的角度读《童书业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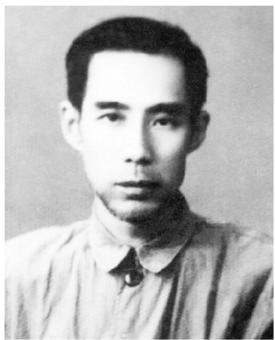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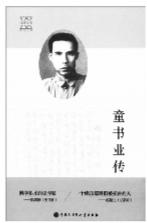
张彤
童书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许多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春秋史、《左传》、瓷器史、绘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为学界所推崇。童先生的生命历程虽然只有不足六十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又往往对做学问十分不利,但因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凡涉猎过的领域,都有所建树。而这些学术领域的跨度极大,除了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经济史研究等相关领域外,甚至还包括心理学与精神病研究,可谓学术奇才。他的师长如顾颉刚先生、吕思勉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史学巨擘,同辈交往的亦多为有建树的一流学者,近读《童书业传》(童教英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1月版),仿佛重温了二十世纪中叶学界的风云际会。也让我这个学术圈外的70后对那一代学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的学术高峰心生悬想。
童书业先生的身世经历与学术道路均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因而近年来不少关于童先生的文章都对那些所谓的“传奇故事”十分关注。而我总觉得,对于一位学者的人生道路的解读,总是应该把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创建放在第一位的,即便是探究其人生经历,也应该是为了解开他的学术思想服务,否则,岂非本末倒置?这本《童书业传》因作者本人亦是历史学者,所以始终都贯穿着一条学术思想探究的线索,这应该是这本《童书业传》中最关键的“营养”——一部学者的传记,应该令读者产生向学之心吧!
童书业出身官宦之家,他的获知方式是纯旧式教育:10岁便开始学《左传》,此后便是《礼记》《书经》《易经》《尔雅》等。童书业对所学经典大都背诵如流,便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中打下基础。童先生有天生超过常人的记忆力,即便是自己不喜欢的学科,接触一段时间也能掌握。他17岁时被迫学习会计学,虽一向不知钱为何物,对会计之学深恶痛绝,却也能掌握会计事务所的业务。1935年,童书业结识明史专家吴晗,两人相谈甚欢,他便开始涉足明史,所发表的明史论文,在几十年后仍然有学者在引用。套用现代语汇,童书业惊人的学习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童书业的学术成果称得上丰繁,虽然生命历经许多的曲折与苦难,但只要能安放得下一张书桌,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就像泉水一样汩汩而出。钱穆先生曾说,一个学者的学术与学者本身的实际人生密不可分,“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从前我只知道在文学研究中,要对作家的文学文本与人生文本做同等重要的研究,才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心灵世界,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居然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也是此前未曾意识到的。对童书业先生这样一位奇人来说,这种方式确乎是适用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学术成果是建立在少年时打下的根基,熟读古籍对中国文化学养烂熟于心,是一切的基础,而天生性格里所带有的敏感与专注,则与这学养相互成就。学问之道,虽然繁复,最终的道理却往往又十分简单明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从何处假设,从何处起疑,就往往看一个人的学养与资质了。与童书业有过学问交往的人,往往会为他“巧妙起疑,周密断案”所折服,这应该就是一个学者的天资与学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童书业传》中可见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童书业仅凭毛公鼎的文法,就推断出它的年代为周宣王时代制作,而在几十年后为冶金研究所人员所验证(见《童书业传》29页);童书业从《茶余客话》六种版本的细微不同处起疑郎窑作者不是连《清史稿》都认定的郎廷佐,而是郎廷极(见《童书业传》159页);用资料排比、分析而断言唐英自著之《陶务叙略》在辗转刻印中致使年代有误(见《童书业传》第159-160页)等,其学问之精深、逻辑之缜密着实令人叹服。
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向有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童书业则鲜明地提出,除信古外,其他三派其实是学问的三个阶段。由疑而考,由考而释,多归纳,少演绎,这是他对于学问的最本质的体验,相信也会是许多受教于他的后代学者都能体会和受益的学问之“道”。
从学问之道的养成角度读《童书业传》,有几点是令我十分感慨的。一是1935年到1937年在北平做顾颉刚先生的助手,这期间童先生的学问精进,跻身一流学者之列。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学者,累层说是他的首创,童书业则将“累层地造就古史观”与“分化说”融会贯通。他们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结下深厚的、终生的师生之谊,此后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童书业与顾先生的学问切磋从未间断。1972年,童教英把父亲的《春秋左传考证》遗稿交给顾先生审定,顾深为悲哀地说,他原拟在自己身后之文章交由童书业整理,不想反倒替自己的学生看遗文。这表明了顾先生已将童书业作为自己在学识上最信任的弟子了。这是童书业先生在学问道路上的一次“嘉会”。
在1946年,杨宽先生掌上海市博物馆,聘童书业先生为历史部主任,童书业因此接触到大量的馆藏文物,也开辟了器物研究的新领域。童先生本来就精通绘画,在博物馆耳濡目染,对于古器物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
童书业先生每钻进一门学问,就会有惊人的专注,不久便会出现一流的成果,这是被反复验证的,而这其中,最令人称奇的,当属于精神病方面的研究。他自幼被娇宠,自述患有“强迫观念症”,遇到外部环境变化,生活压力增大时,就会表现出来。在1946年童书业的神经衰弱发展到了强迫观念症,于是他求助上海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两人交谈数次后,童自感大有好转,并在此期间开始钻研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陆续在《西风》《大中华》等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童书业在学问上的非同凡响可谓处处得到表现,就连为精神疾病所折磨时也不例外。1949年,童先生应出版家舒新城之邀,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其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科学的辨析,此后还于1949年后给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讲《护士心理学》,在山东大学引起轰动。“文革”开始后,他居然写就了《精神病诊断术》,并准备转行去做精神病医生。而他在精神病领域的许多论文其实并未发表,仅是寄托、倾诉,并借以自我疗救,其中的滋味,外人难以想象。
自1949年后到山东大学任教后,童书业先生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几番起落,这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屡见不鲜。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幻莫测,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有许多时间是令人苦闷与彷徨的。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在历史理论、手工业商业史等诸多领域有开拓性的成果。
余英时先生在《历史与思想》一文中说:“无论多少外缘因素,皆无法充分地解释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句话也可以成为解开童书业一生经历的一把钥匙,他的一生中,不管外部环境有多糟,总能深入到学问的深处,沿着知识发展所自有的逻辑,迅捷前行。我想象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先生,其实是时常处于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魂游”的状态,所谓“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是人生至境,而对童先生来说,这天地精神就是学问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