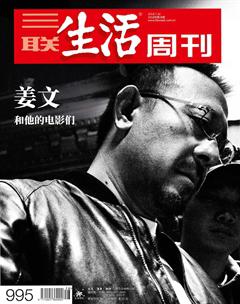读者来信
莫迪改变了印度吗
最近这些年,印度开始成为经济学界和国际资本热炒的焦点,围绕印度的话题都指向硅谷科技新贵、投资银行家和商业咨询顾问,印度正在飞速创造奇迹。但在这样的奇迹发展之下,印度仍有贫民窟、污染严重的空气状况和高居不下的性暴力犯罪,这两个极端都是印度的现状。这期封面故事,记者在实地探访中带来了翔实的“印度奇迹”的报道,不仅是印度的真实写照,其中反映出的新旧融合、高新产业的某些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莫斯)
县里的离婚热
上个周末,老家的四叔给父亲打来电话说,小堂弟又去相亲了,女方带着一个3岁的小姑娘。小堂弟离婚两年了,有一个6岁的儿子,平日里都是四叔四婶带着。
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城,原是紧靠城关外的小村子,这些年随着县城发展,早已成了县中心地带。农民土地不多,打下的粮食也仅够自家吃用,多以副业为生,比如开门面做点小生意,在商场超市做售货员,小厂子里做工人,建筑工地上打短工等。
我曾经以为,我们这样的县城人衣食压力并不很大,家庭结构也甚是稳定,谁知,像小堂弟这样离婚的年轻人真多。
我家所在的那条胡同里,20多户人家,竟有一半家里的儿女离了婚,多半是20多岁的年轻夫妻,还有一对30多岁的。因县城结婚早,虽数年夫妻,也铁了心要离婚。
老人们不明白,好好的日子怎么就要离婚呢?现在都机械化了,地里的活轻省了,不缺吃不少穿,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生了孩子都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带着,怎么就过不下去了?老婶们甚至怀疑,前几年胡同口盖起的大楼坏了风水,要不然,怎么这些孩子们赶着赛着地非要去离婚呢?
另一方面,老人们又埋怨离婚的孩子们吃不得苦,受不了累,咽不下一点委屈,事事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一个不满意就撂挑子不干了。都是“80后”,虽然不都是独生子女,也都是宠着长大的。
父母离婚,苦的是老人和孩子。
离婚的家庭大都有了1到3个孩子,年龄从2岁的奶娃娃到10岁的小学童不等。孩子多半是留在婆家,偶尔也有生的是女孩的,男方让女方把女儿带走,若是生的儿子,女方是断不能带走的。
现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县城里尤其严重。女孩不管是未婚的、二婚的都特别“抢手”,只有女方挑男方家的,没有男方挑女方的。胡同里离婚的两个女儿家,没过多久就再嫁了,剩下的几个年轻光棍带着孩子跟着父母过活。孩子说是爸爸抚养,其实不过是担个名,孩子从出生就是爷爷奶奶带着。爷爷奶奶们大多五六十岁,身体还算康健,爷爷要去打短工、做保安,奶奶管着孩子的吃喝拉撒、入园上学。
三婶家对门的英嫂子,比别人更累一些。她的儿子和前妻生下两女一子,大的5岁,小的才2岁,去年离婚后,3个孩子一直是她带着。今年儿子娶了新媳妇,进门之时,媳妇肚子已经大了。英嫂子照顾3个小孩之余,还得照顾怀孕的儿媳妇,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别人家虽然不如英嫂子家孩子多,却也都存在着前儿媳妇、现儿媳妇生的孩子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老人们有一条不得不接受的“默契”:前妻生的孩子由爷爷奶奶养着,新妻生的孩子才由夫妻两个养育,否则娶不了新媳妇进门。
我三叔家的堂弟也离了婚,孩子正上小学。每次我回老家,三婶就跟我抱怨,现在学校花样太多,以前是老师留了作业,孩子写就是了,现在都用手机了,老师把作业留在微信群里,还要求做完作业之后要拍照上传、要录制孩子读书的视频上传到微信群里。孩子爸爸天天上班、出去玩,也不知道忙什么,反正就是忙。她一个老太太,年岁大些,眼早花了,哪里会弄这些,可是也不得不学着摆弄智能手机,实在弄不明白,就去对门麻烦英婶子家的女儿。
谁也不知道这些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对于妈妈的离开,内心里有怎样的触动。有人问小堂弟家6岁的侄子想不想妈妈,小侄子说:“不想,妈妈是个大骗子,她说来看我,从来没来过。”他不知道,她的妈妈已经再次结婚,前几天刚生下了一个男孩。三叔家的孙子大一岁,懂事多了,听到爸爸说以后不许他去见妈妈了,小男孩拿被子盖住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北京 渐无书)
伤不起的意外伤害险
婷婷是S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所在的社区平时工作繁杂,既要为辖区居民服务,又要承接政府千头万绪的工作,但最让她头疼的还是那些不合理也不讲理的指标任务。果然,大清早QQ工作群一条信息吓得她睡意全无:“今年上半年意外伤害险完成不理想,各社区存在懒政、怠政的工作态度,请自己认真检讨。全区今后每月底进行意外伤害险完成度排名,排名垫底的社区要扣工资并在全区通报批评,并计划每月至少辞退一人!”
“意外伤害险”的办理流程简单,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即可,费用也不高,只要50元就可以参保一整年,客观来说还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好政策。但再好的保险也得建立在参保人心甘情愿的基础上,强制社区卖保险,不仅让工作人员犯愁,更让老百姓为难。
为了完成任务,婷婷每天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说来办事的居民买保险:“朋友,你听说过意外伤害险吗,要不要了解一下?”“阿姨,我看你慈眉善目的,还总来咱社区活动,帮帮我买个保险吧。”“大爷,办个保险吧……你别走啊,大爷,大爷!”好好的社区办事大厅,搞得像传销窝点一样。
其实社区的任务远不止卖保险这一项,平时要动员居民订机关报,有活动时要找人冒充观众,领导下来调研还要请老百姓说好话,要组织大学生“被创业”“被就业”,为办事部门公众号拉“粉丝”。总之,让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婷婷,长了不少见识,听说下个月开始还有更惊悚的任务——卖墓地。
给社区下任务、定指标,不仅会影响基层的日常工作,还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个别地方在管理方式、工作方法上仍然僵化保守,不尊重市场规律,这在东北地区尤甚。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就会让国家的好政策变成压在基层的指标,让社区沦为晒政绩的“朋友圈”。(一读者)
乡村的“问题馒头”
端午节回甘肃天水农村老家,30个本家人来我家议事,家里没烙馍馍,到乡上的馒头坊取了60个馒头。馒头特别白,应该是滑石粉的颜色,这馒头比我在北京吃的馒头白出10倍不止。我推定,乡里馒头过分添加了增白剂,而增白剂会分解成二氧化硫和甲醛,损害肺肝肾,或致癌。这是我漂泊在外20年,第一次在端午节回农村老家,想不到碰上了问题馒头。
从我小时记事起,村里人都是自己烙馍,一来没钱,二来即使有钱也没处买,乡里没饭店也没馒头店,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我离家外出打工。乡里何时才有的馒头店?家人说,四五年前吧。一个乡家家都是花椒地,半数人家不种小麦了,也就没了粮没了面,这时乡里便有了馒头坊,许多人骑摩托车到乡上买来好几天吃的馒头。后来,就是种小麦的人家,一年采摘花椒的忙季,也雇了大量外地人摘花椒,顾不上烙馒头,就去乡上买现成的馒头。再后来,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去乡上买馒头。
乡上的馒头比以前家里烙的馒头白,而山里人又不懂白是咋白的,就抢着吃“超白馒头”。端午节,我在家吃了两个,没有一点儿嚼头,食之无味。在北京,馒头有食品安全执法者抽查安检,即使有添加增白剂的也不过分,而老家没有一点儿监管。现在的农民啊,图省事,自己不烙馍却买人家的超白馒头,往往忽视了健康。
然而,乡里的“问题馒头”也不是新问题了。我们是甘肃天水的偏远山区,没有污染工厂,空气清新,水基本干净,以前粮菜自种,属绿色环保生态,可是,仍有一些老人得了癌症,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浪费”惹的祸。家里烙馍馍一下子烙三四天的,甚至六七天的,留着慢慢吃,馍馍有了霉点,老人舍不得扔,就用面湯泡着吃,这在我们老家叫“泡着吃馍糊儿”,殊不知,三四天的馒头最易滋生黄曲霉毒素,位列一类致癌物清单。这几年,我一直告诫父母,告诫本家的老人,一次少烙点馍,最好两天吃完,超过三天就赶紧扔。去年春节,我斗胆将家里的50个霉点馒头倒掉,一时成了村里人议论的话题。(北京 李成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