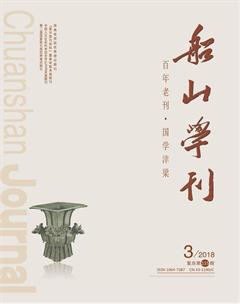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
田希
摘要: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際,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关键词:德治;牟宗三;董仲舒;《春秋繁露》
儒家外王(政治)思想,公羊学家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一大代表。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富有生命力,而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以“人副天数”、“性三品”、“德治”等思想见世,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反而失却生命力。牟宗三对此曾引用陆九渊之言,“象山云:‘秦不会坏了学脉,至汉而大坏。象山说此话之底子,其眼目当然很高。……归根结蒂还是君主专制家天下之大私一问题。……儒者以圣王为政治上之最高格,此在根本上是反英雄情欲生命之非理性,故贱视五霸以及汉高祖马上得天下所开之英雄。”[1]259这里不仅仅是儒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之问题(德治、治道),而且关涉到政治层面君主专制问题(体制、政道),这二问题内在蕴涵于牟宗三政治哲学运思——《政道与治道》中。《春秋繁露》与《政道与治道》二者都以德治为研究对象,但思路却不甚相同。《春秋繁露》代表传统德治思想,从“人副天数”、“性三品”等方面诠释德治,流于主观理想。传统德治其可行性、不足方面,也未加阐明,这一点也被学界所忽视。依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来判摄《春秋繁露》,考察如下问题:传统德治思想到底有有何不足?其根源何在?如何解决可操作性问题?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利于对儒家政治哲学进行多元化视角把握与认识,并在古今思想对比中对同一问题进行消化与再理解。
一、“人副天数”、“性三品”说与“德化之治道”
(一)范畴厘清
首先需要界定牟宗三几对概念范畴:“治道”、“政道”;“理性之运用表现”(亦作“理性之作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表现”、“理性之外延表现”。这几对概念其实是两对范畴:一种是德治、人治、泛道德主义、传统治理方式;一种是法治、体制架构、现代治理方式。
治道,有儒家治道、道家治道、法家治道等,牟宗三主要阐述儒家“德化之治道”。德化治道主要落实在具体人格上,针对对象为主政者、治者个人,牟宗三称之为“圣君贤臣”。政道,则是指科学民主政治。“理性之运用表现”,属于“德化之治道”,而最高境界,则是“彻底散开之个体主义”。牟宗三所谓“架构”,“依以下两义定:一、从自己主位中推开而向客观方面想,自己让开,推向客观方面,依此而说架构;二、推向客观方面,要照顾到各方面,而为公平合理之鉴别与形成,依此而说架构。”[1]261“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指科学与民主政治,侧重于体制层面建构。在君民关系上,“理性之运用表现”是隶属方式(Sub-Ordination),“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对待关系、对列格局(Co-Ordination)。在牟宗三看来,“理性之内容表现”,表现为仁者德治,是人治主义;“理性之外延表现”,则表现为政道、政体,属于法治主义方面。“内容表现”、“外延表现”这对概念与“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大致相类,只是角度稍异。而《政道与治道》一书中,牟宗三大多以“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表示,而“内容表现”、“外延表现”只在妙处与缺点处说明。
虽然提法甚多,但牟宗三与董仲舒相同,核心都是在说“德治”。这二字已涵盖了两重含义,首先“治”,是针对主政者而说,而“德”也是同一对象,要求道德高尚,能负起教化万民之责,行不言之身教,化民风、平民心,要求主政者与圣人二合一,内圣外王。且不论其理论实现概率,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等语言犹在耳,后世儒家如董仲舒不可能不受影响。治理权力越高,道德要求相应越高。所以德治对象不是对所有人,而是针对主政者而言。
(二)“人副天数”:德化之合法性与治道之落实
范畴厘清后,再看依牟宗三观点如何判摄《春秋繁露》德治思想。
董仲舒所处时代,西汉夺取政权才几十年,国家初步稳定。前朝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吏治酷烈,最终不得人心,二世而亡。汉朝自刘邦以来,深以为戒,一度以黄老之学宽慰民心。而后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人副天数”、“性三品”说等思想博得汉武帝重用,使得儒家地位得以占主流。他主张儒家德治,重视主政者个人德行品质对于国家之良性影响。
《春秋繁露》讲德治之前,先以一套哲学理论奠定基础,以“人副天数”将君权神化,使政权具有合法性,然后以“性三品”说赋予君王以圣王人格,使圣与王(即政治权位与道德境界)统一于一身,使主政者德治具有合法性,德治教化也成为主政者应有之职责。
董仲舒认为,人是天之副本,人性来源于天,君权由天所授,君主以天为准则,法天做事,君主以天象自警。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2]319“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34“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2]333“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2]170-171“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2]165“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2]156“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民者,瞑也。”[2]286
在董仲舒看来,人形体气血、性情精神符合天道,是天之副本,这是理论基础。更进一步,人应该以天道为规则,形成一套“法天”行为体系。人们瞑而不觉,唯天子受天命而成圣人,教化百姓,管理国家,行事效法天道。这一套“副天”、“法天”理论行为体系,都宣告一种命定观、英雄观、不平等观。对于不同身份地位者而言,这套理论产生了不同作用:对主政者汉武帝而言,便是一种维护,天下是天所赋予,自己是命定天子,更易滋长个人欲望,骄纵放任;对百姓而言,愈发柔顺卑弱,因为自己身处社会地位、道德等级最底层,只能被动接受天意,从而失去抗争合法性。于是千百年来中国百姓在这种专制统治下养成卑弱性格。这种“损下益上”思维形成定势后,一方面是国家易于维持長久大一统局面,另一方面是百姓心性被压抑。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平等观,将社会地位不平等与道德捆绑,人为造成道德不平等,剥夺其相关权益,对底层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牟宗三也诠释德治是“法天”。他认为,天地不独裁,主政者亦当如此,故其教化、治理,都以顺化百姓为重。德化之治道,“其极就是法天”,目的在于“让任何物皆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这是“圣君贤相”之德,也是“天地之德”,“忘掉他现实上权位之无限,而进至法天以成德之无限,当然不把持独裁任何物”,当然这种治道缺点在于无政道。[1]32牟宗三与董仲舒不同之处在于,董仲舒是以神权、天命观为前提,赋予主政者神圣性、必然性,不仅权位最高,而且道德最高,因此才有“法天”“教化”之责,天象警示也只针对主政者,而不是针对百姓,因此其“人副天数”只是少数人理论,多数权利与责任均由少数人分享承担。而道德与社会实际地位挂钩,天子既是圣又是王,诸侯、士、民随着地位降低,道德境界也转低,因此也有种划分先天道德等级之弊,这容易导致高层愈放肆、底层愈无信心,都是隐患。牟宗三则是顺儒家“法天”思路,但去除其神秘化、天命观因素,以自然、人本主义态度来诠释德治。
与《春秋繁露》相对照,依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思路,则有两点相符:一是德化之治道是落实在具体人格上,二是由于无政道,只有治道,只能客观化皇帝,德化皇帝与宰相,实现“圣君贤相”。
(三)“性三品”说与英雄圣贤人格
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纯善无恶,“斗筲之性”纯恶无善,而“中民之性”善恶夹杂,世人大都是“中民之性”,半善半恶,故可以教化。圣人与斗筲之性世间少有,前者不教而善,后者教之亦恶,都不能依赖教化改变,正与孔子之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3]200相应。冯友兰评价董仲舒人性论,认为其“盖就孔、孟、荀之说而融合之”[4]21。其认为性有善端,但还不是善。人之质中不仅有性,亦有情,性主仁,而情主贪,故需以性制情,导人向善。
“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2\]297“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2]300“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2]303“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2]302“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2]312“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2]313
“性三品”说是受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影响之再发挥。“圣人之性”先天即善,不需教育;下等“斗筲之性”,教也无用;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名性,可善可恶,且占大多数,需要教育。以主政者承接天意教化万民,人性论上论证了统治合理性。性如禾、善如米,性如卵、善未成,种种比喻目的是为了说明人性有善之因素,而未能呈现出现实之善。性与善不同之处在于,性是潜在性,善是现实性。如何呈现?“教之”,要靠圣王(既是王,又有圣性)。这里将最高位者道德神化,以巩固其政权,其是“圣”所以天生为善且能教化万民。将人道德贬低,人无自立成善之可行性,不具备自觉成善作圣之内因,而是依赖圣王教化为外因,将成善归功于外在、他者教化,而从根子上否定个人自体觉悟可能性。
董仲舒上述思想可以推出:(1)天意立王以善民,王乃天意所属,这是天人感应、人副天数、君权天授。(2)从性三品说,民有善质而未能善,属“中民之性”,而天意以王善民,王具有“圣人之性”,否则有何能力、权利教化人民?(3)王不仅是政治权位最高(王承天意),而且道德最高(“圣人之性”以善民)。(4)人民是“中民之性”,不能自己成善,“非质朴之所能至”,要靠圣王教化,“教训之所然”。(5)人无自觉性,暗昧无知(“瞑”),需要天子教化开启民智,由民而士、而诸侯、而天子,层层递进,道德境界与政治阶层成正比。即社会地位愈低,其道德境界愈低,反之则愈高。
可见“性三品”是种分别性、差等性理论,一方面,为圣王政权合法性辩护。性分三品,“圣人之性”天生是善,高于人民,且“人副天数”,君权天授,所以说帝王、主政者是“圣人之性”,是天意赋予,则政权合法性方面上承于天,不可更改,暗含命定论,政权不可推翻(即政道方面不可改革)。另一方面,中民为多数人,纯粹以“德化之治道”解决之(技术层面动作,局部改善)。换句话说,“性三品说”是论证政权合法性,全是“理性之运用表现”,否定“理性之架构表现”。然而它是种不平等观、命定论、英雄观,否认偶然性,封闭政道,为“德化之治道”铺路。
《春秋繁露》将圣与王融为一身,且认为是天命所授,对此,牟宗三有不同意见。他将二者分开,认为一种是英雄,一种是圣贤。他指出,圣贤人格难于做事,重在立德,英雄人格反之,其使命是解决时代问题,二者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道德消化自身命运感,而后者不能,后者层次虽低于前者但不可或缺。[1]95并且他说:“人总渴望着一个真生命真人格出现,王者可,圣者亦可。从现实上说,王者比较有力;从理想上说,圣者则更伟大。”[1]99英雄立功,圣贤立德。牟宗三将《春秋繁露》里圣王一体分开为圣贤、英雄,赋予两种人格不同使命,使其各得其所,他虽然对圣贤与英雄有不同评价,认为前者较高,但同时也肯定后者对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与董仲舒所说王承天意之说不同,牟宗三认为,“仁者德治”达不到,不能在政道上设立制度以实现,在“仁者德治”观念下,“‘唯仁者宜在高位,此即必须以圣人为王,故曰圣王。”[1]138董仲舒是将圣与王统一,但实际政治由王操作,即暗示王即是圣。而牟宗三认为不妥,出发点首先是政道,退而求其次才是德治,且德治将德性置于首位,即道德优于政治,要求圣人做王。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这也反映出,要求圣人作王与他将圣贤人格看得比英雄人格高,其思想具有一贯性。
更重要之处在于,《春秋繁露》以圣贤人格或宗教家来要求政治人物,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行不通。牟宗三指出,在政治中,“有力而不用可,然不能无力”,向内发展德性固可成圣,但政治人物主要是解決问题,发展德性上“常无此耐力”,即英雄有力,但内在德性有所欠缺。[1]2而《春秋繁露》将英雄圣贤集于一身,未免理想化——既是道德境界最高者,负责教化人民,又是实际政治统治者,有治理天下之权。所以董仲舒将英雄人格与圣贤人格集合,实际是拔高了主政者之资格、条件。虽然这种圣贤英雄合一人格在理论上能最大程度发挥“理性之运用表现”作用,最能实现德治,但在实际中,却难以保证这种情况必然实现,因为要求过高,理论超出实际过多。
二、“理性之运用表现”:治道单线化
由《春秋繁露》可见,在政道不得更改之前提下,中国传统文人只能极力发展治道,导致单腿走路,治道单线化发展。董仲舒在德治方面,对主政者提出诸多要点,比如,重文轻武、举善去恶、自谦聚贤、居无为行不言、仁人义我、大德小刑、教化等,但都属于治道。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2]101“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2]133“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2]146“不可先倡,感而后应。……常尽其下,故能为之上也。”[2]170“万物各得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2]178-179“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2]175
“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2]102
“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250“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2]255
“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度而调匀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2]228“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2]174
所引语句,按类划分,分别表明董仲舒“与民同欲”、“教化万民”、“仁人义我”、“调匀适度”等观点。而牟宗三也曾表达相似观点:一、“让开一步,物各其物”,成儒家德化之治道;二、“圣君贤相”,要求有圣贤人格。二者在治道上共同点有:在社会政治层面,与民同欲,“让开一步,物各其物”,对于人民群众,主张同民所欲、教化,行不言之教,在潜移默化中改善民风习气;在个人生活层面,追求圣贤人格、道德境界,仁人义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也是德治具体要求。
与牟宗三不同,《春秋繁露》不止于“让开一步”,仍要调节、调匀,可见董仲舒有儒家积极之风,并非纯然无为,但其本质上不属于“理性之架构表现”层面,仍是“运用表现”这一路;而牟宗三“德化之治道”,境界很高,最终推到“道化之治道”,实际归于道家一路,颇有垂拱而治、无为而治之趣。
而在牟宗三看来,个人道德实践与政治道德教化有分际,不可混淆。前者“全为内在”,是一无限追求过程,而后者则只能维持一般人道生活规则,是外在维持,不可“精微地苛求”,这是政治限度。[1]127可以说前者是严于律己,不断追求,后者是宽以待人,守住底线而已。这与《春秋繁露》所谓“以仁治人,义治我”有相似之处。董仲舒“仁人义我”实际上还是圣王大一统式治道,虽然也讲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没有政道理念,是主政者一个人说了算,且暗含有道德等级思想,宽以待人是因为群众道德低,而不是从现实、人性角度出发。而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为政道留下地盘,考虑现实治理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具有现代意味。
那么对于传统德治而言,“理性之运用表现”如何展开?
牟宗三指出,皇帝权位最高,超出法律之外,所以以政道将皇帝客观化不可行,只能在治道方面努力,对君、相进行德化,这即是“法天”,是为了“物物各得其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要求君、相在德性上能成圣、贤,德要落实到其人格上,君、相必须要“慎独”,向内求自身德性之“觉醒”,这是“天理”、“天地气象”,亚里士多德之“纯实现性(Pure Form,Pure Actuality)”。[1]30由于皇权具有无上地位,皇帝作为主政者,其一言一行具有重大影响,超越法律效力。因此在君主专制基础上,民主法治政体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只能将皇帝视作政道,政道落于治道,其“理性之运用表现”系于个人,要求君是圣君、臣是贤臣。正因为国家系于君臣,所以君臣道德素质要求极高,要向内修心克己,严于律己,达到“内圣”境界,以最优化君道、治道,才能使政道欠缺这一问题得到减轻。
“德化之治道”目标何在,最高境界是什么?牟宗三认为,“各正性命”即为最高境界,换言之,能使万物“各得其所,一体平铺”,即一种“彻底散开之个体主义”,这种德治是“单线孤行”之“高级政治”;而“架构表现”方面由于未能形成近代国家政治形态,只能由“运用表现”绕开架构来实现其目的;所以中国政治“有吏治而无政治”,即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法律也是治道工具,而无架构意义;而君相由于权位最高而使架构失去效力,故可以直接德化天下,以伦理道德为“自然律”。[1]49德治目的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个体自主性、能动性,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人能安排在适当位置,恰如其分,形成良性互补、资源最优化配置。因为缺乏政道、架构表现,从理想角度看,这种最高境界将本属于政道层面之法律纳入治道,将社会德化,以“德”化“法”,使人伦道德取得法律高度,从而上行下效,天下“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种德治,需要主政者个人(圣君贤臣)让位于人民,不盲目人为安排干预,让人民发挥自性,适其自性,人民为主,主政者克己内省,顺民意而落实之。单纯从理念上看,境界极高。
这里牟宗三提到,德治长处在于,儒家政治思想,不是以概念、形式予以确定,而是依靠“直觉心灵”对生活“事理之当然”作具体、实际处理,并且对于个体生命予以尊重、顺应,使事理恰如其分,此即仁德;它是“内容之表现”,不是“外延之表现”,但也因为其缺乏确定形式,导致“内容表现”难以把握;但牟宗三却认为“事理之当然”属于客观,仁德是主观,从具体、实际理性中可以表现出“活泼”与“幽默”。[1]129-131对于牟宗三这种观点,见仁见智。从好处说,德治没有标准,不可量化,只能凭借主政者个人对国情、民意、人性之深刻认识,结合实际作出最优解决方案,大方向上容易把握;从弱点说,德治没有确定形式,难以实行,或者实行也难以达到良好效果,因为主政者个人是靠感觉、感受、理解来制定决策,比较笼统,政令到基层则难以达到具体效果,使人无所用力。也正因如此,德治长处在于其不受形式束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
三、德治之不足:“理性之架构表现”欠缺
(一)治道有三大缺陷
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可以看出,“德化之治道”虽然有其高明之处,但缺陷也十分严重。对此,有三条可究:(1)德治“可遇而不可求”,表明这种机会有稀缺性;(2)“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表明这种现实有暂时性;(3)德治压力全在于在位者个人,“担负过重”,表明这种操作具有不可行性、危险性。[1]134牟宗三分析出这三条,表明德治全靠个人德性支撑,其实现条件难以具足。
鉴于此,牟宗三认为德治不可靠。他认为德治只是“仁者之德性运用”,是“现时法”,“只是当下之呈现”,每一仁者之德性运用皆独一无二,“皆是实现,皆是创造,而并不能传递。虽有风流余韵,然只是其德化之振动”,“并非具有形式确定性之广度量”,属于“内容表现上之‘人治主义”,其“法”根本不是法治之“法”。[1]135其原因在于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或“外延表现”,无科学民主体制、法治主义相制衡与补益。但是关于人治与法治,钱穆与牟宗三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偏于法治、制度化,西方偏于人治、事实化,[5]168这一点颇为有趣,姑且存而不论。
总结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后,牟宗三认为德治缺点都在于只在“理性之内容表现”上耕耘,属于治道、人治主义,德治只是一个“软罢观念”,只能提供指导方向,并不是政道、法治主义、“理性之外延表现”,不能设立制度来实现“‘物各付物之精神与‘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1]137其言一针见血、直陈痛处,德治在理想上、境界上高,但落于实际则难以实践达成,具有不可行性、不可操作性。寄望于个人德性高超且代代具有延续性,其可能性太低,不如在制度架构上做整体设计,以制度弥补人性之不足。
德治要求“圣人为王”,即牟宗三所谓“唯仁者宜在高位”,对于人民要“就个体而顺成”,但其个人負担过重,因为“一切责望都集中在治者个人之德上”,而“人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即成为无担负者,或至少亦担负过轻”,并且,君主专制更加促进这一趋势,故这种政治只可能是暂时政治,难以实现传承;鉴于此,牟宗三认为,主政者、治者个人应该稍微退后,无为一些,让“理性之外延表现”得到发挥,使政治真正落实到双边关系、对待局面中,使人民有担负、有责任,而不是主政者一人唱独角戏;但如一味要求主政者做仁者,便使“政治被吞没于道德”,这是政治、道德双重失败。[1]138-140因此主政者角色定位要划定清晰,使其细化、可操作,不能将其与仁者二合一,二合一容易导致混淆不清,责任超出真实能力范围,不如将二者分开,主政者个人卸下全责担负,展开“架构表现”或“外延表现”,使人民分担主政者权责,反而具有可操作性。
依牟宗三,可总结如下要点:1. 德化治道是单线发展。2. 政道不可改,唯有革命,然而又形成新轮回。如钱穆所说:“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5]1623. 治道有三大缺陷。(1)机会稀缺性:德治“可遇而不可求”;(2)现实暂时性:“人存政举,人亡政息”;(3)操作危险性:治者个人担负过重。德治不具备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因为在政道或架构表现方面缺失,没有体制架构作支撑。4. 将科学民主式政道作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搭好架子,才能弥补治道之不足。5. 即使如此,牟宗三也认为政道与治道相通,政道是外王,是“内圣之通出去”,因此主政者与政体、法治又有密切关系。
传统德治虽然有诸多思想不符合时代,但这里牟宗三并非对德治全盘否定,认为不能实行“仁者德治”,而是从政治现实可行性来看,要对德治思想进行加工,即建立起法治体系、体制,主政者放权于人民,如此,对主政者、对人民而言才是双赢。即是说,在法治代替人治基础上,德治才真正能得以施行,否则只是空想主义,难以真正操作。
(二)“理性之架构表现”:“隶属格局”变为“对列格局”
既然单纯德治有重大不足,难以独立成功,那么从何入手呢?从“架构表现”入手,把重点从“运用表现”转到“架构表现”上来。但首先仍需要廓清这二者有何特征、实质,使认识明晰化。
按照特点来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可以分别概括为“隶属格局”与“对列格局”。牟宗三说,“运用表现”特征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主政者与人民没有对立,合为一体,好比父子关系,主政者好比父母,人民好比子女,这是种大家长式“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而“德化”就如同父母以身教、言教影响子女,父母与子女并非敌对关系;如果说“运用表现”是“实践理性”,有道德意味,而“架构表现”则是代表理性、非道德意义之“理论理性”,相对于前者,“架构表现”是一种“对待关系”。[1]53可以说,“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代表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大家长式人治作风,容易掌控全局,如果家长能力强、道德高,则福泽无量,反之则为祸极大,不可控制;一种是科学民主式组织架构,利于释放活力,使民众得到尊重、自由,德治有体制保障。
“理性之运用表现”问题恰在于缺乏“架构表现”,牟宗三指出,现代化基本精神是“‘对列格局(Co-ordination)之形成”,反对“隶属”方式。中国虽有伦理本位、治权民主,却仍然不够,“关键即在政权不民主”,也就是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如黑格尔所说,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而事实上,不是法治下之自由,而只是沦为情欲、气质之奴隶,其自由是种随意挥洒之自由,仍非真正自由。[1]26换句话说,治道是人治主义,一切都是个人权责,缺乏双边关系,是隶属格局。而由于主政者个人决策难以保障其合理性,有可能沦为个人欲望之奴隶;而政道则需要主政者与人民成为对待、对立关系,这一对立关系在法治政体中取得统一。前文已阐明德治有重大不足,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就是“理性之架构表现”要起作用。
传统德治中,由于“架构表现”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单线发展“运用表现”,以“德化之治道”呈现“理性之运用表现”。然而问题是,传统儒家无法对于政治、政权给出概念性、义理性、思辨性理论支撑,而是诉诸直觉、具体或感性认识,所以容易牵强附会,而缺乏说服力与论证。鉴于此,牟宗三认为,政权概念需要“思辨出应然之理路,则至少先在观念上可开出一模型”,而“以往儒者却甚欠缺”,“公羊春秋亦甚有审辨力,然未能就其所开出之端绪,辨解而通之。何休而后,再无第二何休。清末公羊学派多无义理之训练,其学与识俱不足以任此”,之所以诸大儒不能开出一个理路,是因为中国学人思考方式多属于“直觉而具体”这一路,“不能经由概念之思辨以撑开”。[1]9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学者欠缺概念性、思辨性理论,这是由中国人思考方式所决定的。或许有部分该方面因素,毕竟古代学者受传统思考方式局限,还未接受科学观念、逻辑体系熏陶,而当今学人已接受西方思维方法训练,倒有可能开出一理路。
另外,除了思维方式层面,牟宗三还从文化层面分析,指出中国文化其实不具备“架构表现”特质,中国文化可以总结为“社会是五伦,政治是大皇帝,学问是‘灵明(良知)”三点。[1]45中国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修齐治平”之学、“学而优则仕”、官本位,对社会而言是君臣父子伦常体系,对于政治而言是皇权大一统思想,对于学问而言是儒家内圣修养工夫论模式。从《春秋繁露》可见,整个社会体系各个环节确实都属于治道层面,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文化风向自古以来一向受政治影响较大。
君主专制家天下,其思维是英雄圣贤一体化,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实际问题在于政体问题、“架构表现”。当然问题不能全部归于儒家学者,他们也无力改变政体现实,只能寄望于圣君、德治。所以中国学者自古以来讲究“德治”,希望以道德为政治划定界限,但这也侧面反映出,实际上社会对于主政者个人缺乏有效束缚力,故只能寄希望于道德束缚。牟宗三指出,英雄、圣贤作用“落在直觉主义、主观主义、命定主义”,属于主观,而架构属于客观;道德理性对政治历史要作批判性鉴别,“首先应在‘家天下之大私处说话”,大私处即是历史演进中之客观政体问题。[1]261可见,不解决“家天下”这一根本问题,光作治道上英雄圣贤之论会沦于“主观”、“命定”主义。或许,这也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及其他德治思想难以成为理性、客观、思辨性、体系化理论之一大原因:前提不可行,推不出来。
《春秋繁露》将治道看作唯一不变之实法,而对于牟宗三来说恰恰相反,治道是权法,政道是实法,而且后者不可或缺。由于“根本不合理”处在于“政权在皇帝”、“君主专制”,政权缺乏“常轨”,所以只有“革命”一条路才能更改政权,而缺乏其他方式;但一直“革命”最终也不是好办法,儒家改不了政权,只能在治道上想德化皇帝,“以治道之极来济政道之穷”;本该是政道、治道二路并行,结果变成了治道一条路,可見将一切系于皇帝人格上,其实是一种“权法”,不是根本办法。[1]48牟宗三还认为,“理性运用表现”境界上比“架构表现”高,但“运用表现”离不开“架构表现”(以逻辑科学与近代国家政法一套体系为代表),他以城市为喻,将前者看作一种气象,如自然山川,很伟大,但很虚,而后者是城市具体建筑,一座城市只有山川气象不成其为城市,必须以各种具体建筑物来填实、架构、表现,而依目前现实形势来看,架构表现还不足。[1]51他还从政道、政治、国家、法律、科学知识等五个方面对“架构表现”加以说明,并主张要对权力来源加以限制与安排,使人民产生政治自觉,最终将政权寄托从具体个人(主政者)上转到抽象制度上。
在中国文化视域下,“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关系该当如何呢?牟宗三表示,“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政道与治道、内圣与外王相通,“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1]13所以“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虽各自有独立范畴,但从根本精神上却也相通,在牟宗三看来,政体是最高道德价值之实现,只是由于政治与道德各有分际、作用,所以需分开独立处理。由此可见,他并未因现代政治思想而抛弃儒家。这一点是牟宗三具有儒家精神之表现,亦是现代新儒家之“新”处。
结语
《春秋繁露》与《政道与治道》都以德治为重点,但不同在于,前者纯为单线化治道,政道未开出,不可操作;后者要求开出政道,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各自独立,使政道与治道相配合,政道其实是治道之延伸。前者有道德等级之分,道德与地位挂钩;后者无此分别,考虑以现代法治体制弥补个人人治之不足,反而符合人性。就主政者方面而言,前者权力高于后者。《春秋繁露》是主政者全权全责、既圣又王,所有方面一把抓,人民方面全然无权无责,双方关系失衡,造成“隶属格局”,反而不利于现实政治发展,对于政治、道德都是损失,且就现实来说,几乎无人具备“内圣外王”资质,这种德治也难以传递,即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而牟宗三在思想上厘清了传统德治思想特征、实质,并分析了其长处与不足,汲取近现代政治思想,意在用“理性之架构表现”弥补“理性之运用表现”,换句话说,通过建立现代科学民主政体与法治弥补君主专制式德治(人治)之偏。他虽然是老话重提,却是旧瓶装新酒,能关注现代思维,以法治代人治,使德治话题焕发新活力,从可行性上将“德治”从“天上”拉回到“人间”。
结合牟宗三与董仲舒思想,可作如下几点概括:1. 董仲舒《春秋繁露》德治思想受到其时代局限,暗含命定观、不平等观,其思想要扬弃地看。2. 传统德治思想有治道,无政道。3. 传统德治长处在于“直觉而实际”,境界高而难操作。4. 传统德治有三大重要缺陷,不具备可操作性、可持续性。5. 治道不能离开政道,必须开发政道——“理性之架构表现”、科学民主体制,才是根本。以体制架构支撑德治,这是人性要求,而传统德治之人治主义、单线化治道是圣人要求,不现实,也达不到。6. 政道是治道之“通出去”,二者异中存同,在认识论上要明白其一体性,但在现实操作上又要知道其分际,不可一体化。
将董仲舒与牟宗三从德治方面作比较,可以见证传统思想史之不断发展、不断诠释,也可以见证现代思想对传统文化之渗透与影响,这有利于丰富学界对德治问题之研究视角。对德治概念从可行性与不足方面进行分析,以便于在扬弃中提高理论鉴别力,加深理论认知。面对时代问题,将古今德治思想进行对比,从中汲取养分,或许能为未来提供一种思路,希冀对类似问题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朱熹. 四书集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4.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编校:马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