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就不再是女人?
杨时旸
《塔利》的核心是一个人与这种观念的抗争,以及更重要的——作为母亲的“我”与作为自我的“我”之间的抗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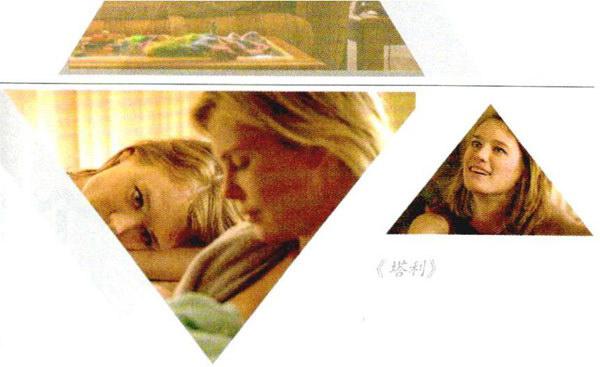
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是针对女性被物化为生育机器后一种抽象的、象征的、未来化的恐怖图景,那么《塔利》或许就是更真实的、可切实感知的、每个母亲都感同身受的实际困境。它讲述了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被生活压垮的故事,所以,很多观众一尤其女性观众,把这个故事当做了一种醒世恒言。但这个故事绝不是单纯的展露生育与养育之苦,不是贩卖女性悲戚,更无意于批评其中作为男性代表的父亲的责任感缺失。《塔利》中的故事并没有男女对立,不存在口号和拳头式的表演性女权,也根本没有令人反感的大男子主义,它更多的只是在真实展现家庭生活的真相,一种繁杂的、琐碎的、甜蜜与窒息交替上演的真实图景。生活走到这一步并不是谁痴傻,谁算错,谁懦弱,只是生活本身有时像甜蜜陷阱,让人就想纵身一跃,却发现糖浆之下满是泥淖,而泥淖中又潜藏宝藏。
《塔利》的主角是两个女人,即便再加上这故事里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但它仍然算是独角戏,那个夜间保姆塔利更是个幻影。很多人会觉得这故事到结尾处算是一重反转,揭开真相,但实际上对于熟悉这类套路的影迷而言,故事发展到一半——母亲马洛和塔利在后院喝酒畅谈的时候、一起去往酒吧的时候,一切就都已经昭然若揭。因为她们互相聊天的内容、方式、来言去语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这就是自我的独白与剖析,而之后那些两个人愈发契合的知心话与爱好,那些明确透露着“我当年就是你的模样”的言辞,简直已经不是暗示,而是明确了一切。塔利是马洛的分身、本我、曾经的自己和幻想中应有的样子,在被现实重压之后,挤压出的一个斑斓的泡泡,放置于自己的旁边,以便能够对话、能够解惑、能够屏蔽现实,能够当做借口,能够增加勇气,能够让自己重整旗鼓。马洛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中呢?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有些心理问题,第三个孩子又刚刚降生,丈夫忙于工作养家,闲暇时只依靠打游戏解压。马洛不得不闲于琐碎,送孩子上学,给婴儿喂奶,独自面对走形的身体、渐渐流失的自信,所有惶惑无人可诉,但生活依旧步步紧逼。
《塔利》并没有批判一方而歌颂另一方,丈夫在床上戴着耳机打游戏,并不是要用凌厉的眼光去审视他的不负责任,而描述母亲马洛的操劳也不是赞扬母性光辉。生活就是如此,总莫名其妙地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格局,无法像公益广告里呈现的那样,烦恼似乎永不存在。《塔利》中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对照体系,马洛弟弟一家,但看起来,那一切更像是嘲讽,那注定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所以那些情境被展現得造作又扭捏,而一旦转换回马洛与丈夫房子,一切就事无巨细地真切起来。
《塔利》之中有一个有趣的暗示,关于性别,“母亲”这个角色被塑造成一个超越性别而存在的客体,一旦一个人成为母亲,她就已经不被当做一个“女性”,而只是一个“母亲”。女性所有的特征、欲望、需求都被母亲的身份所遮蔽和覆盖,进而,甚至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权利也被下意识地缩小和隐藏,“母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概念,无限延展,吞噬一切。从这个意义出发,《塔利》的核心则是一个人与这种观念的抗争,以及更重要的——作为母亲的“我”与作为自我的“我”之间的抗争。个人身份与母亲身份之间会形成奇妙的张力,文化惯性、家庭现实与自我意识之间彼此拉锯撕扯。故事中的马洛则代言着文化惯性的一端,而她臆想出的保姆塔利则是内心和本能的一端,她们彼此试探、交锋的回合,就是一个真实的陷于生活的母亲的内心自我缠斗。
游弋的美人鱼是自我的出窍,最终拯救自己,给孩子的心理治疗最终变成了拥抱,幻想的塔利消失无踪,现实的马洛最终还魂,她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应对生活,应对母亲的身份与自我的索求?所以,这故事无关女权抑或男权,更关乎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