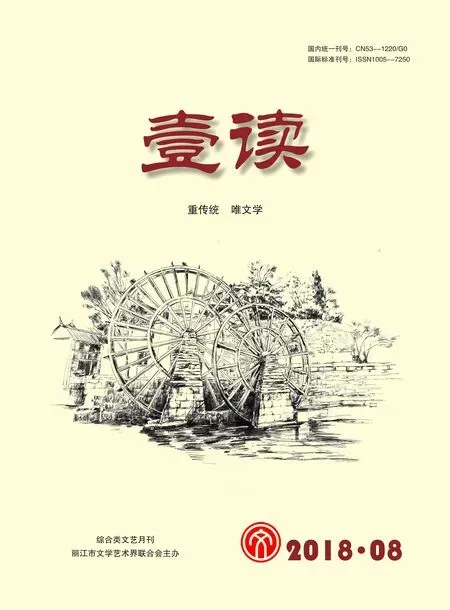浅析东巴教布卷画的风格成因
苏 泉
东巴教美术,是祭司们在图画象形文基础上,兼收纳汉、藏民族多元美术样式而形成的独特美术体系,包括木牌、纸本、布卷、面塑等种类。布卷画,纳西语称“普劳幛”,“普劳”意为“神”、“菩萨”,“幛”乃汉语“幛”的变音,故又称“神轴画”,(图1-1)分作长卷、多幅、独幅多种类型,在举行东巴教仪式活动时,悬挂于神坛上方。
早期绘制布卷画的材料,以麻布居多,后则用土白布绘制。画布的制作,需用鹅卵石砑光,再刷浆、涂粉。绘制时,先用碳条起稿,敷以颜色,最后拿毛笔勾勒墨线,画技高超的东巴,可直接以墨笔绘制,而后填色,画法因人而异,尚无定式。
另有一类布卷画,称为《神路图》,纳西语称为“亨日皮”,“亨”意为“神”、“日”意为“路”,“皮”意为“评断”解,或作“裁决”、“判定”之意。完全展开的神路图,长度可达9至15米,宽约30-50公分。这是一种只在超度亡灵时才使用的绘画,它的作用是引导亡人顺利回归祖地。全图亦多用麻布制作,也有以白棉布或纸张代替。(图1-2、3)这些独具特色的布卷画,区别于此前东巴教的木牌、纸本等美术形式,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绘画属性,以具象而完整的画风表现经书中的文本内容。

图1-1 布卷画

图1-2 使用神路图

图1-3 神路图(局部)
一、 明代汉、藏民族美术的交互影响
13世纪中叶,丽江地区纳入云南行省。此后汉、藏民族文化便通过“茶马古道”在丽江地区展开更为频繁的交流,纳西文化圈也形成了以东巴教为主体,兼收汉、藏、白等宗教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为布卷画的发展与完备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以宗教文化交融为桥梁,多元美术的交融,促使东巴教祭司们创造出新的美术形式。
(一)汉地美术根植丽江
明代丽江地区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了璀璨的艺术杰作。创作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延续至清乾隆八年(1743年)的丽江壁画,共计二百余幅,主体分布于白沙、束河两地。此外,在显觉寺、漾西万德宫、大研镇皈依堂、寒潭寺、崖脚村木氏故宅、芝山福国寺、雪嵩村的雪松庵、珊碧院等15座寺庙中也有分布。
白沙壁画的最大特点是融汉、藏佛教、道教神话题材于一炉,由汉、藏、白、纳多民族画工共同绘制完成。陈兆复先生1963年在丽江调研时曾了解到,天启、崇祯年间,木氏土司从浙江宁波邀请汉族画家马肖仙至丽江参与壁画绘制。马肖仙本人擅长花鸟、人物,其绘画风格继承陈老莲衣钵,有高古之风。另外,木氏还邀请了浙江张道士至丽江创作壁画,张氏亦是水陆画高手。
马、张二位画家,只是同时期由汉地前来丽江的众多画家中的一员,还有更多的人并未记载于史籍中,他们在创作壁画的同时,也在丽江传播了汉地的绘画技艺。东巴教布卷画中出现的许多具有汉地风格的神像造型与花鸟式样,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汉地美术在丽江的传播。
另外,至今在白沙,尚有属于和姓东巴的田产,当地人称为“画匠田”。此户东巴祭司,因参与了白沙壁画的绘制,而得到土司赏赐的田产。可见在明代,东巴教的祭司就已经与汉地画家们有所交流,因此也就有可能借鉴汉地美术,并运用于东巴教美术中。在白沙壁画一些不太显眼的位置,至今仍能看到一些与东巴教布卷画造像类似的形象。因此明代汉地美术的影响,可以说是东巴教美术吸收多元养分的肇始,潜移默化地为东巴教布卷画准备了生发的土壤。
(二) 藏地美术的传播
明代中叶以来,木氏土司洞悉朝廷治藏国策,加强了与藏传佛教主要教派领袖的关系。万历四十六年(1616),噶玛噶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杰来到丽江,土司木增奉如上宾。
却英多杰(1607—1674)作为嘎玛噶举派领袖,不仅精通佛教法理,更在绘画、雕塑方面有卓越天赋,他率先创造了融合唐卡与汉地绘画、克什米尔佛像画绘画风格,突破经书规范的束缚,以“美”为标准来塑造形象。
为报收容之恩,却英多杰特绘制十二幅密教唐卡供木氏修习。藏地美术因此也在纳西人的上层社会中传播,为纳、藏美术的交融开辟渠道。随着纳系族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茶马古道”上商贸、文化活动的日益兴盛,纳、藏文化交融也日益密切。藏地美术的影响范围,因此也由官府逐渐扩大至民间,最终对东巴教产生影响,祭司们开始借鉴藏地美术的风格样式,创造新的美术。
二、清代东巴教布卷画形成
(一) 汉藏文化促进布卷画形成
清代,藏传佛教在丽江得以大规模发展,融入到普通纳西人的日常生活中,使民间的东巴祭司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藏地美术,并将之运用于东巴教美术中。
同时,清初的纳系族群,仍处于农牧结合的社会生产状态,保持着不习纺织,服食俭约的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丽江知府庄粤台在丽江城中设置机房,教当地纳西人学习汉地先进的织布技术。此举为布卷画的出现提供了原料,麻布也成为东巴教美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画材。
可见“改土归流”之后,汉地的文化在冲击纳西古俗的同时,也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带到纳文化圈,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东巴教美术产生出新的形式。
(二)唐卡对东巴教布卷画风格特征的影响
“唐卡”为藏语“thang-ga”“thang-ka”,或“thang-kha”之音译,汉译为“卷轴画”。布卷画的渊源,可追溯至印度古老的布画“pata-madala”,此类绘画作于布帛之上,常用于宗教仪式,信徒利用它宣扬教义,凭此积累善功。东巴教布卷画主要吸收唐卡中的对称构图,以及神佛造像的范式,但二者在画面效果上有所差异。较之唐卡,大多数布卷画,则显得有些粗糙稚拙。
首先,社会生产力起到决定作用,唐卡的绘制者多是佛教僧侣,他们依靠信众的布施、收缴田产租税,拥有相对充裕的生产资料。因此,有条件使用珍贵矿石及金银为颜料,以锦缎作装裱,唐卡也显得富丽堂皇。而东巴教布卷画虽效仿唐卡形制,但祭司们多居山野,在农牧劳作之余绘制作品,只有因地制宜,运用生活中常见的布匹、土石、植被制作图画。画材质量的不同,决定了画面效果的差异。
其次,并非所有的布卷画都因工具的简陋而效果粗劣。仍存在一些精致程度堪比唐卡的作品,但由于没有款识,难知其作者与年代。虽不排除它们出自精于绘事的大东巴之手,但更可能由画技高超的民间画师完成,或由一些被称为“仓巴”的在家苯教徒绘制。他们常受东巴祭司邀请绘制布卷画,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与宗教的画家,促使东巴教的布卷画具备了丰富多样的面貌。
(三) 独幅布卷画的风格特征
与木牌、纸本绘画不同,独幅布卷画中的形象大多来自于外来宗教,尤其是苯教与藏传佛教。在布局上,独幅布卷画直接借鉴了唐卡的对称布局,造型式样则依据东巴教经典,同时吸收唐卡造像仪轨,创造出多样的神话形象。
据东巴教经书《萨英威登飒》记载,萨英威登是至尊大神,他的父母是窝金鲁柯布与窝金鲁汶,他们生于天上白露与地下热气交融而成的一枚白卵,夫妻又生下一座白塔,白塔生又生出白卵,经天、地、日、月、星、辰、龙、鹏、狮、父、母、云、风的孵抱,白卵发出耀眼光亮,从中诞生脸似日月、目光如电、声如雷震的萨英威登。
在表现这尊大神时,上述文本内容以图画形式得以呈现。画中的萨英威登,面庞圆润饱满,二目圆睁,肤色呈现纯净的白色,体现了他“脸似日月,目如电光”的形象。双手结印,结跏趺坐于恩多宝座上,宝座的左右两侧,以东巴教图文分绘日月图形,象征他所吸收的日精月华。
在他的左右,则绘有多位神灵,代表由他变化的三百六十枚卵化育,掌管鱼、岩、天、地、日、月、山、署以及祭祀王者的祭司,还有董部落的首领美利东主及其管辖的白天白地、白色的日月星辰及山川草木。
在萨英威登的头顶及两侧,则有鹏、龙、狮三兽,在经书中,它们护卫萨英威登斩妖除魔。而在大神座下,又绘有九头战神格空都支及三头的尤麻战神,二者代表了他为下界除妖而率领的千万盘、禅、高、吾、俄、恒、多格、尤玛、本当等战神,消灭鬼怪后,此神又率领神兵天将立即返回天界。故而画面中,他被绘制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图2-1)

图2-1 萨英威登
在萨英威登之下,还有居于十八层天上的依古窝格,经书中也说他化育了萨英威及丁巴什罗的父母。他的神座上以绿松石镶嵌成吉祥图案,他的征服对象是众鬼之本依古丁纳,作战时他在鹏、龙、狮护卫下,率领千千万万的盘、禅、高、吾、俄、恒、多格、尤玛、本当降妖除魔。布卷画中依古窝格的形象与表现萨英威登相似,但其头顶大写的藏文“唵”字,是其名字的缩写,也是代表他的符号。具有类似造型的神像还有恒丁窝盘、丁巴什罗等大神。(图2-2)
另外,在东巴教布卷画中还有许多兽首而人身的神话形象,它们多是战神,有强大的威力和凶悍的性格,这些形象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藏传佛教美术的影响。
以东巴教护法神“尤玛”为例,其职责是为人类降妖伏魔,造型为狮首人身,背生双翼,属于“战神”(“戛劳”,或译作胜利神),又称“尤玛战神”或“尤玛胜利神”。尤玛神种类繁多,有土赤尤玛、缪纽尤玛、依什索贡尤玛、季套纳安尤玛等。
这一形象与苯教中的“威玛”有着密切关系,“威玛”意为“保佑人类的非人(鬼神)之一种”,亦有若干种形态,称呼也不尽相同,十三扎拉神的主帅威玛多庆纳朗就是一位人身狮面,坐骑猛虎的战神,与东巴教的尤玛造型相似。
布卷画中,巴乌尤玛的形象依据经书文本被表现为狮首人身,左手持三叉戟,右手握宝剑,通身洁白,背生双翅膀。显然受到唐卡中兽首人身的空行母等造型的影响,尤其与青鬃白面,生三目,巨口獠牙的狮面空行母造型异曲同工,具有明显的苯教造像特征。

图2-3 巴乌尤麻
同时,布卷画中的“杜盘休曲”,其鸟首人型,长鬃有角,背生双翼,口衔双蛇,有着人兽复合造型特征,也借鉴了藏传佛教的金翅鸟或苯教唐卡中的琼鸟的造型。
此外,布卷画中有表现护卫神门的红虎和白牦牛、二龙抱珠等主题,以及描绘有鹏、龙、狮、牛、羊、鹿等形象,这与苯教唐卡常以龙、狮、虎、牛、羊、鹿、鸟等飞禽走兽的头部来组合寓意的画面相近似。
上述三个案例,只是东巴教布卷画中众神造型的一部分,祭司们还借鉴了佛教、苯教唐卡中的护法神造型创造了九头十八臂的战神格空都支、四头猎神卡冉牛究等独特形象。
这些各具特点的独幅卷轴画,反映了藏地美术于东巴教美术的有机融合,使原本只存在于经书中的诸神,具备了生动而鲜活的面貌,通过绘画,人们能更加直观地识别这些形象,了解与他们有关的神话传说。
(四)神路图的独特表现风格
布卷画中的《神路图》场面宏大、从天界至地狱大约绘有包括神像、人物、鬼怪、禽兽、房屋、法器在内的400余个形象。全图分作120层,大致可分做天、地、人间三部分,每层都是各自独立的画面,上下互相呼应。
《神路图》的叙事模式仍借鉴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思想,但由于绘画作品需要追思祖先的迁徙历程,为亡人指引归路,因此仍表现为直线式的构图,可以说是佛教美术与东巴教义的有机结合。

图2-4 地狱景象
在地狱部分,面目狰狞的鬼卒对罪人施以酷刑,以惩罚他们生前犯下的捕杀野兽、破坏环境等罪行。鬼卒青面獠牙,生有牛头、马头、熊头、猪头、狗头、虎头、蛇头、蚁头、蝇头等动物头颅,表明他们由这些动物的精灵幻化而成,与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

图2-5 杜盘修曲

图2-6 六道轮回图
或其他唐卡作品中的地狱众生形象相似。另外在《神路图》第九段中,名为使支次吉的鬼怪,其原型来自于城隍庙中的阎王,此类对于汉、藏美术中神话造型的借鉴案例,在《神路图》中不胜枚举。
在全图中段,表现了人间四种不同的转生渠道,东方人们从卵中出生,西方的人们则从花里出生,北方的人们则生于神树中,南方的人则由妇女体内生出。这一情景显然也是受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
最上端的天界,表现有神山、蓝湖,湖中有鱼、蛙、水獭在悠游嬉戏,山坡上出现了狮、虎、牦牛、马在玩耍奔跑,还栖息着孔雀、白鹤等珍禽,这些动物形象,基本是对图画象形文的转写。在其上,或坐或立的东巴祭司们在虔诚地诵经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天界中的部分身形,带有着域外美术特征。栖息在含英八达神树上的“杜盘修曲”,口衔“署”蛇,双翼展开的形象与印度神话中栖息于希望之树上的迦楼罗非常相似。同时,修曲鸟衔蛇尾的造型也使人联想起《六道轮回图》中以嘴咬住圆轮,以双手把持轮盘的阎罗。(图2-5、2-6)。
另外,《神路图》中还有三十三座宫殿组成的园林,在园林中居住着两位神人和长有三十三个头的大象。据美国学者洛克考证,这些形象与印度教及婆罗门教有密切关联。通过藏传佛教美术与东巴教美术的交融,来自印度的美术形式也逐渐进入到布卷画中。
和志武先生曾认为:“神路图的出现和使用,当是纳西族元、明以来深受汉、藏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实,不仅是汉、藏佛教文化中的美术因素对《神路图》的画面风格有所影响,通过“茶马古道”上商贸与文化的交往,印度及其他域外美术形式也得以对东巴教的布卷画产生影响。因此,多民族美术的融合,形成《神路图》独特的画面风格,神话文本被祭司们转化为易懂而美观的图画,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神话世界。
三、汉地水陆画对东巴教布卷画的影响
汉地美术对东巴教布卷画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明代木氏土司对汉地文化的学习与引进,使得汉地美术形式扎根于丽江,而清代的“改土归流”,则进一步将汉地文化推广到民间,水陆画也融入到东巴教布卷画中。
水陆画是佛寺、道观在水陆法会时悬挂在道场四周的画作,源自汉地,作用在于使用简明直观、通俗易懂的图像向大众阐释宗教思想。这类绘画首先兴起于佛教,是佛教思想在中国一种世俗化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的水陆画,其内容与题材已得到极大丰富,尤其是在儒、释、道合一的文化背景之下,诸天神佛都齐聚于画面当中。
这类源自汉地的民间绘画对清代的东巴教绘画影响颇深。以一幅藏于丽江市博物院的布卷画为例,(图3-1)此图中在中央大神的两侧分别站立着两只明辨是非的鹰神多格。(图3-2)其造型与水陆画中的雷神形象几乎雷同。在宝座右侧则是手持钢鞭,坐骑猛虎的财神赵公明,其造型与道观中的塑像别无二致。(图3-3)同时,在画面的左下角,向盤孜沙美求取经的拉窝拉萨,手持犬牙令旗,坐骑白马,身着铠甲,俨然水陆画中的刀马人物。

图3-1 三教合一的布卷

图3-2 多格

图3-3 赵公明
清代水陆画对于东巴教美术的影响,也在纸牌画中得到体现。在白沙地区,流行着一种与汉地门神画十分近似的五方神明纸牌(图3-4)。画中东方的格衬称布以赤虎为坐骑、南方的色日明公以青龙为坐骑、西方的纳森崇鲁以黑熊为坐骑、北方的古色康巴以金象为坐骑、中央的索于金古以神鹏修曲为坐骑。但五位东巴的造型与清代长江流域水陆画中的武将形象极为类似。足以说明,清代,东巴祭司们通过不断观摩与学习,已将汉地宗教美术的造型式样融入到东巴教美术中。

图3-4 五方神明东巴纸牌
明清时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使纳西文化圈中的东巴教祭司们接触到了来自汉、藏文化圈的美术形式,作为族群中的文化精英,他们发以宗教的交融为契机,不断吸收借鉴汉、藏宗教美术的表现形式,将原有的图文符号,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绘画,更好地传播了信仰与教义。同时,更应认识到,汉、藏、纳等民族多元文化在丽江地区的交融,也成为了东巴教布卷画多元一体绘画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