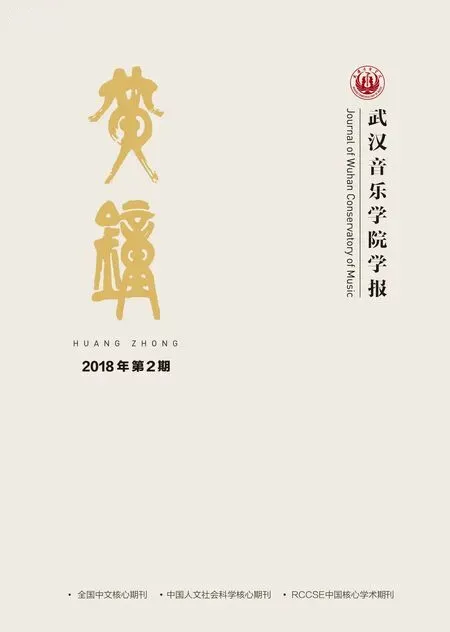扁担欢歌
——《走绛州》音乐分析
施 咏
《走绛州》,又名《一根扁担》,是一首流传于山西襄汾的民歌。绛州现称新绛,位于今山西省新绛县一带,是古时晋南地区的行政中心,春秋时曾为晋都。该地区物产丰富、生活富庶,是周边民众求生存、求发展的理想之地。歌中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去绛州途中肩挑货物、手推小车、赶着毛驴行路时的情景,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
作为山陕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在诸多与民歌、民族音乐有关的著述中都无一遗漏地涉及了《走绛州》这首民歌,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音乐分析。但这些论述大多不够全面,尚存较大的深入空间。同时,对这首民歌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也较少,在仅有的两篇学术论文①商树利:《不该被歪解或误解的小调<走绛州>——谈劳动号子分类标准的历史文献依据》,《乐府新声》2014年第2期,第90-92页;令狐青:《汉族民歌<走绛州>研究》,《中国音乐》2015年第4期,第181-187页。中,只是分别探讨了该民歌的体裁问题及归属地问题,且尚未见足具说服力的论证。
本文拟从歌词中的正词与衬词、民俗地理,曲调中的句式结构、音调框架、特性音程以及体裁等方面,对《走绛州》(见谱1)进行较为全面的音乐(学)分析。笔者在提出些许新见的同时,还冀望以此为个案,对探寻中国民歌音乐分析教学与研究的方法及路径有所帮助和启发,并以此求教同仁。

谱1 《走绛州》②乔建中编著:《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一、歌词分析
(一)正词与衬词
《走绛州》的歌词由“正词”和“衬词”两大部分组成。
以首段歌词为例:

软溜软溜软溜软溜溜(呀呼嗨),——衬句

青呀青呀青呀青呀青呀(哎咳哎咳哟啊嗬)走绛州。
歌词中,第一、三句为正词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句结构的七言两句体。其余均为衬词部分,分别运用了篇幅不等的衬字、衬词、衬句及衬段,生动地描绘了去往绛州途中热闹欢快的场景。
其中,第二句是穿插于两句正词间的衬句,重复了上句句末的“软溜溜”一词,以富有律动感的节奏,形象生动地模拟了扁担晃动之态。正词“担上扁担走绛州”后有一个较为长大的衬段,以“刺拉刺拉”“咕噜噜噜”“踏踏踏踏”等拟声词,对正词内容进行补充与引申。衬段结束处以“走绛州”点题,与正词形成合尾呼应,突出主题。
《走绛州》歌词中的衬词丰富多变,先是用“软溜软溜”对肩挑扁担的动作进行“动态声拟”,再对挑担行走中筐、绳、轱辘转、驴儿跑,以及路边的柳叶、鸟叫、敲鼓声等进行“拟声绘景”,塑造了声像同步、声色立体的热闹场景。
(二)民俗地理
在汉族民歌中,类似《走绛州》这种将动词置于地名前,构成固定的动宾结构,以表达歌唱者将要去往之地的例子数量众多,如《走西口》《跑四川》《过四川》《下四川》《上四川》等。
在此动宾搭配中,其宾语“西口”“四川”“江南”“扬州”等,多为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都是由于理想中的彼地在经济生活方面高于本地而形成的歌唱对象”。③乔建中:《〈下四川〉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36页。《走绛州》中的绛州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中心位置,是西接山陕、南邻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要塞,经济繁盛、交通便利、物资丰足,是周边地区人们所向往的理想之地。而动词“走”“跑”“过”“下”“上”等的区分使用,是源于地理地貌、劳作方式、表演形式、行为意义等方面的差异,如《下四川》《下江南》《下扬州》之“下”多为地理位置之故,即顺流而(南)下之意。此处《走绛州》之“走”,虽也出于离开家乡讨生活之动因,但与《走西口》中偏于表现背井离乡时的不舍与悲伤则大不相同。《走绛州》的“走”指的是肩挑扁担、活泼风趣、欢快诙谐的走态,与商业贸易流通等行为相关,表现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走往绛州开辟新生活之意。
此外,收入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中涉及去往绛州题材的民歌共有四首,除了这首襄汾的《走绛州》外,还有安泽县的《下绛州》④《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722-723页、沁水县的《下绛州》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第306页。以及运城县的《扁担歌》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第722页。。从这几处与绛州的地理位置关系便可看出:襄汾位于绛州之北,且是距离最近、交通最为便利者,故可以用“走”体现;安泽县与沁水县都位于绛州的东北方向,故用“下”绛州;运城则位于绛州之南,故在《扁担歌》的歌词中是“担上扁担我要上绛州”,体现了从不同地理位置去往绛州的不同表述。
二、曲调分析
(一)曲体句式结构
关于《走绛州》的曲体结构,分别从歌词和曲调出发,有以下两种观点:
1.上下句结构⑦持此观点的文献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王耀华主编:《中国民族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杨瑞庆:《中国民歌旋律形态》,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音乐出版社编:《音乐欣赏手册》,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党音之:《<走绛州>赏析》,《音乐天地》2004年第5期,第51-52页。
承前文,从歌词的角度出发,除去所有衬词后,正词部分只有“一根扁担软溜溜,担上扁担走绛州”,可将其视为上下句结构的七言两句体。两句为不严格的五度模进,上句落音A商,下句落音D徵(见谱2)。

谱2 《走绛州》中的上下句
在上下句之间有一个由4小节衬腔构成的 乐句,其音乐素材是对上句旋律的部分重复,可视为是上句旋律的“重句”⑧重句:指将某一腔句作完全或部分重复,较为常见的形式是换头和重尾。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补充了上句歌词所表现的内容,营造了活泼、乐观的情绪。
下句之后是一个扩充性的衬段,可分为4+6(4+2)两个衬句。第一衬句变化重复了下句旋律的后半句,加入了十六分音符均分律动的密集节奏型,打破了上下句中的稳定感,增加了音乐的动力性。第二乐句则是下句的换头重复,以合尾的手法结束全曲。
因此,《走绛州》在上下句结构的基本框架下,通过加衬、重句等变化手法,增长句幅、扩充结构,完成了音乐的陈述。
2.四句体结构⑨持此观点的文献有,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周青青:《中国民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种观点是将《走绛州》视为起承转合的四句体。因为从曲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歌曲中“软溜软溜”(第3小节、第6-9小节)的拟声性衬腔,以及位于结束句前、结构上起着铺垫准备作用的辅助性衬腔(第18-19小节)等部分略去,“这首号子就成为非常规范、整齐对称的四个乐句,并不影响乐思的陈述”⑩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第19页。。因此,根据音乐材料间的发展关系,《走绛州》的曲体结构亦可划分为4+4+4+4的“起承转合式”四句体方整型乐段(见谱3)。

谱3 《走绛州》中的四乐句
如上图谱例所示,从乐句层面来看,四个乐句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乐句曲调上扬,落于A商,具有不稳定感;第二乐句承递了第一乐句后半句的材料,整体旋律呈下降态势,落于D徵上,两句落音呈五度关系;第三乐句为转句,由2+2的两个重复性乐节构成,承递发展了第二乐句后半句的材料。其“转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节奏上,具有较强的动力性,使音乐情绪得到进一步的渲染;第四乐句在曲调上综合了前三句的音乐材料,并与第二乐句形成合尾,是全曲的总结。
全曲虽短小精悍,但结构紧密统一。从每两小节为一乐节的划分来看,四个乐句的图示可表示为ab+bc+c1c1+b1c。乐句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均在重复前句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发展,呈链条式的结构关系,体现了旋律运动之间极强的内在逻辑。
(二)基本音调框架
《走绛州》为缺角音的六声徵调式,音乐材料精炼,全曲以徵音sol及其上下四度的do、re为骨干音,以下行双四度sol-re-do-sol为基本音调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相较陕、甘民歌,山西民歌中的双四度进行在具体的运动形态上有若干差异。首先,在《走绛州》中,就并无陕北《脚夫调》中一气直上的sol-do-re-sol,而是采用下行进行的sol-re-do-sol,或拆分为下行do-sol及下行sol-re的单四度进行。其次,往往会在四度音调框架的进行中,穿插较多的非四度音,使得双(单)四度音调的构成过程往往复杂于陕、甘民歌。例如,在《走绛州》的第一句中,前两小节均以do-sol的单四度下行进行为框架,在第二小节的do-sol之间,用si、la作为过渡,后三小节为连续下行的两个四度do-sol-re,则以fa音穿插其中;第二句,其音调框架为下行的双四度sol-re-do-sol,但在do-sol之间穿插了si-do-redo,即类似于围绕着宫音do的回转音进行。
在《走绛州》四度音调框架中穿插进行的这些色彩音起到了过渡、柔化的作用,“冲淡了陕、甘民歌中常出现的直上直下的质朴和酣畅感……作为do至sol四度进行之间的过渡,进一步淡化了双四度音调结构的空阔、平直感”⑪周青青:《中国民歌》,第185页。,而增添了抒情柔和的成分,这也成为了在秦晋支脉(或称之为西北色彩区)中,相较陕、甘民歌,山西民歌在整体色彩上要显得更为委婉细腻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扁担”特性音程
《走绛州》中对扁担动态的模拟除了通过衬词“软溜软溜”进行“声拟”,并辅以动感的节奏以外,在音调上还通过与歌词“软溜”对应的四度音程sol-do作为模拟扁担弹性运动的特性音程,加以反复运用与强调。四度音程sol-do在第一句中呈现(第3-5小节),而在紧接的衬句(第6-9小节)中,四度音程还配合着节奏的紧缩和语气的顿挫,使旋律与歌词表义同步同构,生动描绘了挑担行路时扁担晃悠的形象。
无独有偶,这一特性音程在其它与挑担关联的民歌中也多有出现。如河北阜平的《扁担歌》⑫《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第717页。中也有四度音程sol-do,并同时以“颤悠颤悠”“刺溜刺溜”的衬词配合表现扁担的动态。而在河南邓县小调《王大娘钉缸》中,则是通过四度音程re-sol的重复进行来模拟扁担的动态(见谱4)。

谱4 《王大娘钉缸》⑬乔建中编著:《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第249页。
推而广之,这一“扁担”特性音程还会在表现同一题材的民族器乐曲中得到应用。以二胡曲为例,在《小扁担》⑭高金香曲:《活页器乐曲·二胡——22》,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年版。中,其首句也是通过solre、sol-do两个四度音程来模拟扁担运动。而在以la-mi定弦、羽调式的《喜送公粮》⑮中国音乐家协会编:《二胡曲选1949-1979》,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版,第82-86页。中,则是通过 la-mi、sol-mi和 re-la、do-la两组强调调式主音,以及四度、三度音程的交替对比,来对扁担的动态进行更为细致的模拟,同时还辅以左手滑音和右手跳弓,来模拟挑担的律动,以表现挑担送粮之轻快喜悦。类似的手法在《肩挑扁担喜洋洋》⑯王国潼:《二胡曲九首及其演奏艺术要求》,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中亦存在。
可见,这些乐曲中的“扁担”特性音程展现了这一现象的物理学及心理学基础,以及在具体调式、骨干音的影响下,多种四度音程(soldo、re-sol、la-mi、re-la)的变化。同时,还反映了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声乐先行,并对器乐产生影响的这一规律。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个可称为“扁担动机”的四度音程多出现于山陕、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而在四川、湖南、江苏等地的同类民歌(器乐)中则几无出现,更多的是被柔化为级进。这是由于在南北性格、语言等因素影响下,民歌旋律进行的共性规律所致。
三、体裁辨析
关于《走绛州》的体裁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首民歌属于小调类。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认为:“《走绛州》是一首歌词为一个简单的上下句,但由于运用衬句,曲式结构有了很大扩充的陕西小调。”无独有偶,乔建中在其编著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一书中也认为“这是一首山西民间小调。”在《中国民歌集成·山西卷》《音乐欣赏手册》,以及王耀华的《中国民族音乐》中也都将该曲归入小调体裁。此外,在商树利的《不该被歪解或误解的小调<走绛州>——谈劳动号子分类标准的历史文献依据》以及令狐青的《汉族民歌<走绛州>研究》两篇文章中,也通过从历史文献、音乐地理、音乐本体等方面的辨析,将其界定为小调。
第二种观点则以周青青为代表,将该曲划归为劳动号子。其认为《走绛州》虽旋律与小调特征相符,但其弹性的节奏、具有重复性的音调、曲调的跳荡与挑担者动作之协调等,具有劳动号子的艺术特征,属于搬运号子中的“挑担号子”。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大能的《民间歌曲概论》以及冯步岭的《民族音乐基础教程》、何晓兵的《音乐作品赏析教程·中国民歌》等。
诚然,以上两种观点的提出都有着一定的立论基础,各执其理。但如果要对其体裁类别作进一步的辨析,还是要结合它的节奏特点、音乐行为的目的、民俗背景及音乐功用等角度加以全面综合地考量。
首先,从节奏特点来看,《走绛州》中由于表现内容(如挑担、推车、赶驴)的需要,在节奏律动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与赶路挑担时的步伐相协调一致,使其具有劳动号子的某些节奏特征。但从其音乐的功用性来看,却并非是出于协调与统一挑担步伐的实用功能,而是以“软溜软溜挑扁担”“吱扭吱扭推小车”“踢踏踢踏赶毛驴”,以及路边的鸟叫、鼓声等立体化的视听系统,来渲染营造轻松热闹的气氛,重在表现赶路者的情绪。而且,即使从节奏层面来看,第14-19小节出现了三次××××∣ ×××××∣的节奏型,也已与挑担号子不甚吻合,而更类似于敲锣打鼓渲染气氛的节奏型。因此,无论是从节奏型还是从音调的发展来看,《走绛州》相对于较为典型的“挑担号子”而言,更平添了几分小调音乐的细致与多变。
其次,从音乐行为的目的来看,如前文所述,绛州自古为富庶繁华之地,因而为周边地区所向往,所以走绛州者其行为目的是走往富地。前文所举例的安泽县《下绛州》者,白天肩挑货郎串巷,晚上悠哉自得观灯。更有甚者,在沁水县的《下绛州》中则是“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担子下绛州,绛州城里去耍下风流……真正是有看头。”可见,“走绛州”完全迥异于“走西口”般讨生活、求温饱,而是求“小康”、再发展。众所周知,小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集市贸易、城镇的出现,才得以产生并传播发展的。所以“走绛州”系列民歌中所唱的这些市井化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其浓郁的城镇俚巷歌谣之风,有力地证明了其为民间小调的体裁属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周边的青年男子、挑夫走卒对绛州的心驰神往,因此也不难理解其在《走绛州》中表现的是活泼欢快的走态,尽显轻松快意之乐,而毫无体力劳累之苦。
此外,从音乐产生的民俗背景来看,作为一首“扁担歌”,可将其与其它同类“扁担歌”进行比较阐释。如河南邓县民歌《王大娘钉缸》与四川秀山民歌《黄杨扁担》,两者都有“扁担歌”的节奏律动以及纯四度的扁担特性音程。但从民俗背景及音乐功用来看,前者来自流行于豫东南和豫西南的地花鼓,并伴随着一丑一旦的表演形式,完全脱离了劳动行为,而意在通过歌舞表现诙谐之意。同样,来自于四川“花灯调”的《黄杨扁担》虽以“黄杨扁担软溜溜,挑一挑白米下酉州”起唱,但往后听就会发现,这挑着白米下酉州的挑夫的注视点并不在挑担上,而是在后面的三段歌词中,即夸奖“酉州姑娘会梳头”,意在表现对姑娘的爱恋。㉘无独有偶者,另一首来自花灯调的四川阆中民歌《柏木扁担软溜溜》中也是从“柏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过扬州”起唱,但后面的歌词焦点还是会转到“我爱扬州好丫头”,以及大姐、二姐、三姐会梳头上。此外,在湖南大庸市民歌《桑木扁担软溜溜》中,也以歌名起唱第一句后,接“挑起白米下苏州,苏州爱我好白米,我爱苏州好丫头”㉙《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第874页。。类似于借扁担兴起,而意在姑娘。所以,学界对这几首民歌的体裁都毫无争议地划归为民间小调类。
而同样在以“一根扁担软溜溜”起唱的《走绛州》中,其相关分析亦正如乔建中所言:“‘走绛州’在某种意义上与‘走西口’、‘跑四川’、‘上扬州’相近……其中,‘走西口’偏于表现家庭的分离和亲人思盼之情;而‘上扬州’、‘跑四川’则因为变成了风俗活动中的演唱节目而渗入了一些戏剧因素,《走绛州》属于后一类。”㉚乔建中编著:《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第40页。其中,前文提及的四首山西“走绛州”系列民歌中,安泽的《下绛州》就来自春节的秧歌表演。因此,从民俗及功用的角度来看,《走绛州》与《王大娘钉缸》《黄杨扁担》《桑木扁担软溜溜》等“扁担歌”具有上述的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在体裁上应属小调。
而且,《走绛州》中在对行路过程中“扁担、小车、毛驴、筐、绳、轱辘、树、鸟、鼓”等众多对象的歌唱,也反映了作为民间小调类的“扁担歌”所具备的“挑着担子的歌唱者往往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㉛乔建中编著:《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第325页。这一极为重要的特征。
综上,通过从音乐形态、功用、民俗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可见,虽然《走绛州》中具有部分号子的形态特征,但在功用上已基本脱离实用性功用,而进入独立、成熟的艺术表现。其较为完整的音乐结构,细致的曲调构成,丰富的润腔手法等,塑造了生动立体的艺术形象,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小调音乐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因为《走绛州》中较为明显的小调属性,即使是认为《走绛州》为“挑担号子”的周青青,也在其著述中补充到“另外,从这首号子较完整的旋律结构来看,很可能是受到了小调的影响”㉜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第19页。,而并未否定其与小调之间的密切关联。
结 语
《走绛州》以其短小精悍的结构、细腻丰富的表现手法、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成为山西民歌的代表曲目之一。在鲍元恺的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中,还将其列入第三板块“黄土欢歌”的第三首,并进行了交响化的编配。此外,“老泥车”“八只眼”等男声四重唱组合也将其进行了重新编配演绎,并成为保留曲目,为这首传统民歌的当代传承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