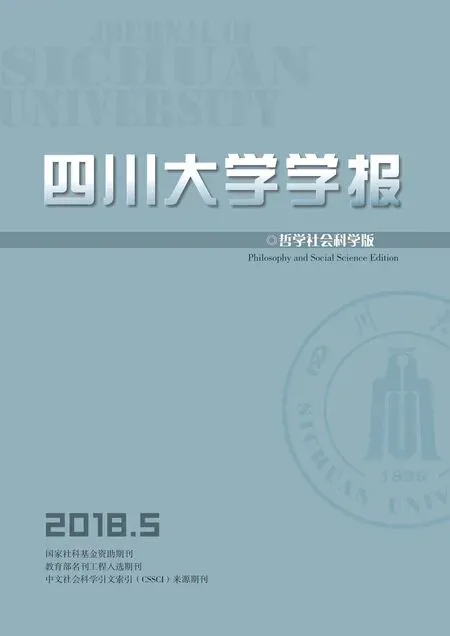明词北方图景与“南词北进”的通代考察
有关明词的文学地理学考察,学界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基于量化分析法的词人地理分布研究,余意、孟瑶等人皆有专论,*余意、齐森华:《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第97-106页;孟瑶、张仲谋:《明代词人地域分布研究》,《词学》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14页。并在此基础之上,作出宏观、整体之判断;二是以地域文学、分省文学为基本概念的词人群研究,如谢永芳的北直隶词人研究,徐德智的吴门词派研究,金一平的柳洲词派研究等,*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词学》第2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132页;徐德智:《明代吴门词派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金一平:《柳洲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虽然他们的考察范围大小各异,但都建立在某一种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属于群像研究之范畴。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明词地理空间的认识,为我们在文学史思维之外观察明词,打开了新的局面。但也不可否认,现阶段的明词地理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在籍观念的约束,缺少对明词的流动性考察。特别对相对冷清的北方词坛来说,以词人籍贯来进行空间定位,容易将之理解为静态、孤立的一种存在,而不是由词人流动、地域互动、文体竞争共同构成的多维图景。本文意在用流动的眼光重新认识明代北方词坛的基本面相及其运作机制,并在通代词史与整体文学史的双重视野下,探究明代北方词在整个北方词史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历次“南词北进”之于词地理格局变化的复杂影响。
一、明代北方词坛的“个像”与“群像”
明人观念中的“北”,有两种观看方式。一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自然地理中的南、北之分,此承袭前人观念而来,如古人所谓“橘生淮北则为枳”,汉中向以巴蜀之地视之,皆是类似观念的体现;二是行政地理中的南、北之分,洪武三十年(1397)的进士南北榜案,在制度层面落实了南、北进士定额,强化了明人的南北观念。本文所谓的“北”,取明代会试南北卷之定制,以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考察范围,在此基础上,视实际情况,因地而论。南直隶北部凤阳府、徐州等地区,历来被视为北方,但明代政区将之划归南直隶,在南北卷制度中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同属中卷,笔者从之,这些府、州的词人数量很少,不至于对考察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考察北方词坛的“个像”与“群像”之前,需要警惕幛词对北方词坛实况的扭曲。由于官场社交赠答的需要,幛词创作在明前中期词坛中相当普遍。南方地区由于词人、词作的总数较大,幛词对整体格局的影响尚不明显。但对于创作比较冷清的北方词坛来说,若不排除幛词创作的情况,率然地作量化分析,有可能得出一些与事实相距甚远的结论。一来明幛词多有代作,其归属权尚有纷争;二来有些地区虽然词人数量尚可一观,但一旦把那些只创作幛词的词人去掉,便寥落不少。故本文对北方词坛的考察,将避免使用“环太湖词圈”的量化分析视角,[注]叶晔:《江南词学版图与“环太湖词圈”的动态考察》,《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80页。而采用相对实在的社交网络视角。北方词人相对有限的规模,也为这种考察的可行性提供了便利。
在《全明词》中,第一位出现的北方词人,是北直隶濬县人王越。词学界提到王越,一般想到夏承焘先生的《满江红》伪作说。但从词人网络及师承的角度来看,王越是明代北籍词人中的典型“个像”,他有一定数量的词作存世,其词史意义亦差可评说,但与周边词人基本没有关联,属于缺少参照物的孤立人。类似的北直隶词人,[注]关于北直隶在籍词人的研究,可参阅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还有名列“景泰十才子”的锦衣卫籍汤胤勣,以词风豪放见长的边塞词家孙承宗,被王士禛誉为“寄托多牢愁侘傺之词”[注]《倚声初集》卷一《醉落魄·九日》王士禛评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的刘荣嗣等。山东、山西地区的词人情况,亦与北直隶相仿,几位创作较可观者,如弘治“七子”之一的边贡、以科举世家著称的冯惟健、冯琦叔侄,以己作为例词编纂词谱的万惟檀,热心宣府、大同边事的边塞词人尹耕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为个案聊可一观,但在词人交游与词学思想的外联性上则相对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在京城词坛最鼎盛的嘉靖时期,北直隶、山东、山西词人与京城词人没有太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导扬地域填词风气的绝好机会。
与北直隶、山东、山西的萧条、孤立景象不同,陕西、河南的词场景况虽不热闹,但词人间的联系颇为紧密。我们以政治辐射的近远为序,依次考察。除了上述王越、孙承宗、刘荣嗣等本籍北直隶词人外,北直隶词坛还有以顺天府为依托的京城词人群。其中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宣德馆阁词人群和以夏言为代表的嘉靖馆阁词人群,促成了明代京城词坛的两次高潮。在京官员的日常集会活动,以及京官与地方官在考绩、考察中的赠别互动,一同组成了京城词坛的常态景象。杨士奇、夏言都是江西人,与他们唱和赠答的,既有王九思、王廷相、韩邦奇、许讃、郭维藩等北方词人,也有杨荣、张璧、童承叙、方献夫、霍韬等非环太湖地区的南方词人,还有少数如张邦奇、孙楼、陆深、周用这样的江南词人。国家政治中心所附带的文化凝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北直隶词坛的寥落面貌有所改观。如果说“环太湖词圈”以地缘关系为纽带,那么,京城词坛则以政缘关系为纽带,构建了一个基于政治地理的词坛副中心。如此,京城词坛与环太湖词坛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南、北词坛的关系,更是政治文化与区域文化之于词坛影响力的一场竞争。
陕西词坛的主力,是以王九思、李梦阳、韩邦奇、王维桢为代表的西安府词人,实可视为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陕西复古作家群的词坛侧影。其中著有《碧山诗余》的王九思和著有《苏愚山洞词》的李应策,是明代散曲史中的重要作家,他们在创作中的词曲互动,是陕西词坛较之其他地区的特别之处。康海虽无词作存世,但王九思《菩萨蛮·戏对山子》《浪淘沙·次对山四时闺怨》《念奴娇·寄对山子》诸词,皆赠答康海之作,可知他对填词之事并不生疏。另,王九思有《满庭芳·贺西陂公生子》词,刘储秀(号西陂)为西安咸宁人,其文集中虽无词作,但《丰润县志》录其《浣溪沙·冬夜宿七家岭驿即事》二首,附许宗鲁和词二首,[注]周明初:《“司马西陂”即刘储秀考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明清文学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9页。可见刘储秀、许宗鲁于填词一事,亦有涉猎,非唯擅幛词之辈可比。
与陕西词坛相对应,河南词坛就是明中叶中州作家群的分身。王廷相、戴冠、李濂、王教、郭维藩、许讃等词人,与何景明、薛蕙、孟洋等复古诗家多有交游。李濂曾有单刻词集《碧云清啸》行世,其序曰“近世以文章名家者,多弗究心于此。……惟诚意伯刘公伯温平生所作几三百首,神藻绚烂,光溢简帙。盖自伯温之后,寥寥百余年间,有作者不过数首而已”,[注]李濂:《嵩渚文集》卷五六《碧云清啸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6页。大有步刘基绝唱之决心;他另编著有《汴京遗迹志》,收录己作《汴梁怀古》十词,追怀北宋填词风气,可视为对地域词学传统的一种溯源。[注]李濂的《碧云清啸》与马洪的《花影集》,是明前中期为数不多的单刻词集,皆已亡佚。但二人词一咏开封,一咏杭州,既是对两宋故都的追忆,亦是对两宋词学传统的接续。撰《和断肠词》的戴冠,是词史中第一位系统次韵女性词作的男性词家,他在完成《和断肠词》后,“携之游都下,以呈大复先生”[注]戴冠:《〈和断肠词〉跋》,《全明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2页。,颇受认可,且撰《虞美人·和大复先生所书此调》《浪淘沙·和大复先生所书》二首,则何景明之词学修养,亦当可观。另,王廷相、王教作为河南籍京官,存词数量不少,且多题咏、赠答之作,他们与京城词坛的密切交游,与陕西词坛后期的韩邦奇、王维桢等人颇有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以夏言为首的嘉靖京城词坛,借助中央的士大夫社交网络,牵系着河南、陕西等以地缘为纽带的北方词人群的后期发展。这些词人群虽然自有本地词学传统可倚靠,但京城词坛辐射下的同乡士大夫交游活动,也对其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这种来自庙堂的辐射效应,不应过多估量,如戴冠与何景明的词学交往,是河南词人群中的重要一环,何景明卒于正德十六年(1521),可见此前中州填词风气已具,未必受嘉靖京城词坛的影响。而且,我们应考虑到,明代北方的几个词人群,多为复古诗人群的附属产物,其群体性源于士人、诗人、词人三种身份的重叠,词体意识相对较弱,在这种复合观念形塑下的词人群及地域词学传统,不应过度阐释。
由上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明词北方群像,止京城、陕西、河南三个词人群。其中京城词人属流动之群像,而陕西、河南词人属在籍之群像。古代文人的流动,固然有游幕、经商、战乱迁徙等多种情况,但基于职官迁转之宦游,无疑是士人最常态的流动形式。这种流动基于制度性的政缘关系,而京城处于文学权力场的最上层,它所代表的超稳定的共同体,如同铁打的营盘,即使经历剧烈、持久的文人流动,仍能确保其群体风貌的经久不衰。而在籍之群像,主要依赖于语言、风俗等地缘联系,与流动之群像相比,词人间的交谊更深入和紧密,但也存在另一种隐患,即在文学相对冷落的北方诸省,某些优秀词人的作用会被放大,群体之发展容易因世代之进退而起伏。故京城词坛得以成为明词的地理副中心,而陕西、河南词坛,只活跃于明中叶,借北地诗学与北曲发展之势,有过短期的兴荣而已。
与词人群像相比,个像因其相对独立性,较少受政缘、地缘关系的牵连。但他们被文学史家所关注的与众不同的别致面目,却时常借词中政治性、地方性等要素呈现出来。如以边塞词著称的高阳人孙承宗,没有太多词学交游和师承可言,其词作中的豪迈一路,与他身居都察院、提督军务的仕途经历,及北直隶“激壮之音,伤于粗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王襄敏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8页):“(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谢永芳移评于整个明代北直隶词人,见《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词学》第21辑,第121页。的地域词风有关;又如以己作为例词编纂《诗余图谱》的曹县人万惟檀,其生平行实概不可考,但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将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结合起来,或与山东自李开先、冯惟敏而下代有延续的北曲学传统有关。
在明词北方图景中,孙承宗、万惟檀等人皆为在籍之个像,而与之对应的是流动之个像,其创作图景主要表现为纪行词、赠行词等类型。如明代宁夏词坛,主要由流寓、宗室、督抚、武官四类词人组成,在上述明词北方图景的认知体系中,作为其词坛主流的督抚词人,显然属于流动之个像。但当这些词人的吟咏主题被维系在同一创作传统中,便可能构成广义上的流动之群像,只不过维系此流动群像的要素,不是京城词坛的政治勾连,亦非陕西、河南词坛的地缘社交,而是某个稳定的创作主题。如在流动至宁夏的词人的创作中,作为文学景观的贺兰山和作为言志对象的西北边事,因其承载着强烈的陌生感和政治责任,成为经久弥新的文学主题,它们也是地方性、政治性的一种文学表现。
综上所论,我们根据个像、群像之差异,以及在籍、流动之不同,将明代北方词坛分为四种图景。每一种图景,皆有其典型之案例,并承载起各具特点的词史意义。但不同图景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似没有前代那么细密。我们讨论两宋金元京城词坛的活跃,经常说它们带动了河南、浙江、河北等畿辅地区的词坛风气和词人涌现,如汴洛词人群、杭越词人群、东平真定词人群等,这些群体固然有倚靠京城而形成的流动性,但即使只考察其本籍词人,亦已成群像之规模。而明代京城词坛对北直隶地区的辐射,却效果甚微;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区的词坛面貌,与京城词坛之盛衰亦非同步,主要根源于地域文坛的某些特征,如复古诗学、地域曲学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群像如何带动个像,流动如何激活在籍,或是接下来词学地理研究中可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
二、从燕乐到赠答:京城词坛娱乐性的消退
唐宋词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唐宋歌妓制度,对此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已有详论。而京城词坛,又是歌舞燕乐最热闹的地方,故北宋汴京词坛的兴起,与歌伎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此为词史之共识,自不多言。
与燕乐之于宋词繁荣相对应的,是学界将元明词之衰归因于词乐式微,即作为音乐文学的词,在文人化、案头化过程中渐失生命力。这一解释固然没错,但词乐式微这条主线实在太显眼,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可能的追寻路径。严格意义上,燕乐不止有“乐”,还有“燕(宴)”,乐不存固然词不振,但宴不存同样可以造成词不振。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官吏挟妓饮酒,律无明文,有犯,亦依此条科断”一句,这里所云“此条”,指“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一条,即官吏挟妓饮酒的行为,视同宿娼处置。此处的“娼”,亦有注曰:“娼,即教坊司之妇,与各州县所编乐户是也。”[注]《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官吏宿娼”条,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而在明万历六年王藻刻本《大明律例》中,此句作“官吏挟妓饮酒,律无明条,问不应从重”(《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4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111页),可见此律禁之宽严,亦在不断变化中。相关禁制,始于宣德四年八月,“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66页。也就是说,官吏挟教坊女子或州县乐户饮酒,按宿娼罪论处,杖六十。这样的处罚力度,相当严厉。虽其本意是为了树立清廉朴实的官场风气,但对依赖于燕乐而生存的词文学来说,无疑是元代词乐式微后的又一次致命打击。
关于禁挟妓饮酒对词文学发展的抑制作用,至迟在明中叶,已有人察觉:“宋时名公如欧、苏、黄、蔡辈,虽尝挟官妓以燕集,然不过假以佐欢,或酒酣赠之诗词而已。顾以名检郑重,莫有与之昵者。我朝则尽革而禁之,法制正矣。”[注]陈霆:《渚山堂诗话》卷一“东玉心儿”条,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页。此说虽然是从正面的角度来为北宋诸名公及国朝制度的典正形象辩护,但其中隐约之意呼之欲出,即在歌妓制度与词文学的关系上,宋、明两代有云泥之别。当然,任何制度的制定与落实都有一些差距,谢肇淛的说法,可能更真实一些:“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可见这一律规的执行,亦有一个时间上的渐进过程,以及在任官员和家居官员的区别对待。至少宣德年间的京城词坛,对挟妓饮酒一事,执行禁令尚不严格。皇甫录《近峰闻略》曰:
《大明律》有“官吏挟妓饮酒”之条,然宣德三杨公犹及用之。尝闻其与一兵官会饮,文定倡为酒令,各诵诗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时。令毕,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谓秦无人。汝辈有能者乎?”一妓遽成小词,捧琵琶歌曰:“到春来,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来,低舞杨柳楼心月。”文敏句:“到秋来,金铃犬吠梧桐月。”兵官句:“到冬来,清香暗度梅梢月。”文贞句:“呀,好也么月,总不如俺寻常一样窗前月。”诸公剧饮霑醉而去。[注]皇甫录:《近峰闻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101-102页。
就此段记载来看,三杨所咏实为散曲小令,但可见在宣德年间,词曲倚赖的歌妓宴唱环境尚在。明代的赠妓词虽没有北宋那么多,但仍有不小的市场。一来缙绅家居者不在禁官妓佐酒的处罚范围内;二来很多法令离开京城,其执行力大打折扣。如杨慎被贬云南,离京城有万里之遥,相关法规几无约束力。其《昼夜乐·中秋董太守席上》曰:
螳螂川上清秋节。爽襟怀、消烦热。香醪桂馥兰薰,官妓舞琼歌雪。五马风流华筵设,金屏燕颃莺颉。软语劝飞觞,有如花连舌。座中豪兴称三绝。高阳并,斜川埒。且偕仙侣逍遥,肯叹群儿圆缺。未害广平心似铁。看霜鬓、半成耄耋。倩横玉叫云,把寥天吹彻。[注]杨慎:《昼夜乐·中秋董太守席上》,《全明词》,第814页。
螳螂川是滇池入金沙江的唯一水道,所谓“柳市村村接,松灯点点明。家家倾蚁酒,夜夜鲙鱼羹”,[注]杨慎:《升庵南中集》卷一《螳川独泛》其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6册,第453-454页。向为云南文人游宴之地。词中有“官妓舞琼歌雪”“金屏燕颃莺颉”“软语劝飞觞”诸句,则官妓在云南知府宴席上歌舞佐酒之场景,清晰可辨。
以上数例,皆可证明前中期尚有歌妓佐酒的场景。但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这一风气日渐萎顿,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宣德词坛的杨士奇、杨荣、黄淮、王直等人,其词中已少佐酒欢愉之场面。如果说宣德诸家之词尚是台阁诗风的一种附庸,那么嘉靖年间的馆阁词人群,则有着较自觉的词学诉求。作为京城词坛的领军人物,夏言的词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京城词坛的走势,也反映了当时整体词坛的一种趋向。
从词学传承来看,夏言之所以擅长填词并得以引领嘉靖词坛,得益于家族、地域、馆阁三种词学传统的聚合。首先,他的叔父夏旸,虽只是广信府司狱一类的低级吏员,却有《葵轩词》一卷存世,词风清丽,是典型的南人气象,夏言早年多有学习。如夏旸有《菩萨蛮》回文词二首,夏言亦有同调回文《秋夜》《弋阳道中》二首,自注“十九岁作”,为其早年乡里时的作品。在清丽词风之外,夏旸词中多人生往复之感慨,如《天仙子》:“鸟儿匆匆朝又暮。富贵不来年少去。百年身世一瞬间,且笑歌。休自苦。”《烛影摇红》:“世态轻浮,翻云覆雨纷更变。落花飞絮雨悠悠,冷暖随人面。物欲蔽蒙得惯。日夕频频计算。蜗角之名,蝇头之利,井蛙之见。”[注]夏旸:《天仙子》《烛影摇红》,《全明词》,第439页。这与他兼擅散曲不无关系,叹世主题本是元明散曲的创作传统之一。而夏言贵为进士,甚至官至首辅,亦有人世吁叹之句,如《木兰花令·睡起感事》:“怀抱无端谁可语。闲拈世事从头数。愁如急浪滚将来,身似弱云飞不去。”《西江月·寄醒斋》:“举世昏昏醉梦,几人心眼惺惺。”[注]夏言:《木兰花令·睡起感事》《西江月·寄醒斋》,《全明词》,第692、718页特别是夏旸《贺新郎》(世事如棋局)、夏言《浪淘沙》(世事信难凭)二词,对是非名利、得失荣辱之洞若观火,多相近之处。诚然,在词作中注入个人的生命哲思,是对词主题的一种拓展,但作为词坛领袖,夏言经常涉足这一类型的词作,难免对词坛风气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明代日常类书中,有不少托名夏言的劝世词,一方面,固然是看重他朝廷阁臣与词坛领袖之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原本就有这样的创作习惯有关。
其次,作为江西贵溪人,江西词学传统在夏言作品中亦有体现。如其《渔家傲》次欧阳修韵二十首、《桂枝香》次王安石韵三首、《苏武慢》次虞集韵十四首等,远绍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北宋词人,近接虞集、杨士奇等元明台阁作家,可谓一脉相承。当然,对江西词学的真正继承,并不在于次韵作品的多少,而在于内在风骨的习得。无论欧阳修还是虞集,皆以词风流丽著称,而在明清人的眼中,夏言词风雄放,最近于辛弃疾。王世贞曰:“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注]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卷一,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61页。邹祇谟亦曰:“公谨之于幼安,犹宣武之似司空也。”[注]邹祇谟:《远志斋词衷》“阮亭词序略”条,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61页。辛、夏二人之所以有词脉上的牵连,亦归因于二人的地缘联系。[注]汪超:《明人夏言词与稼轩词比较刍议——以夏辛二人信州词作为中心》,《长江学术》2008年第2期,第47-50页。贵溪县属广信府,两宋时为信州,辛弃疾常年寓居于此,对夏言来说就是半个乡贤。他不仅在词风上效仿这位先贤,并有《沁园春·彭编修凤过白鸥园,用辛稼轩韵》《水龙吟·次辛稼轩,贺末斋阁老霖雨堂落成》《水龙吟·夜宴未斋宅,赏坐上牡丹,再和辛稼轩》等多首次韵之作。故较之传统意义的江西词人,夏言的创作又多了几分豪气。
总的来说,夏言词风比较多元。其婉约一面,来自宗族、地域词学传统之主干,正体现了词的南方文化属性,而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将是“南词北进”的又一次重演。然而,对夏旸人生哲理词的接续,以及对稼轩豪放词风的承继,作为夏言早年所受词学遗产的一部分,在他入京后的词创作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面对京城文学传统,夏言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词风,将其中与馆阁文学相近的词学元素发扬光大。正是这些其早年承继的词学元素,使夏言较之其他南方词人,更快地融入京城词学传统之中。在禁止歌伎佐酒的大环境中,他将人生哲理(来自宗族传统)、雄放风格(来自地域传统)、学术论争(来自馆阁传统)较好地融入到士大夫的社交场景之中,引领了新一波的京城词坛创作热潮。这一优势,是那些非专力填词的北方词人和风格过于鲜明的江南词人所没有的。
通观《全明词》及其补编所收录的嘉靖京城词人群之作品,不难发现,较之北宋汴京词坛的词艺活动,明代北京词坛更热衷于赠答交谊,偏重于士大夫身份,而非词人身份。如果用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眼光看待京城填词活动,则北宋词人的文人气较重,而明代词人保持了较矜持、典雅的士大夫之气。在北宋京城词坛辉煌成就的参照下,夏言等人的努力,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对词心的偏离,徒有社交体用之表,而没有把握住词的核心内涵,算不上真正的词人。
从文人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这无疑是一种娱乐性的消退。同为京城官员,对词之题材、场景的认知,从日常生活转向政治生活、学术生活;词的私人性的抒情功能逐渐淡出,公共性的社交功能在不断强化。这一发展走势,在南宋、元代词坛已显现。只不过南宋首都地处环太湖词圈,而元代京城缺少集政治、文学于一身的词坛领袖,加上词乐尚未完全消亡,故这种消退之势在周边婉约词风的掩映下,显得不那么突出而已。
如果说应制、应酬之词,属于从日常生活转向政治生活,至明代已无甚新意,那么从日常生活转向学术生活的论学词,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说,更值得深究。现存夏言《柬浚川司马论诗》《答黄致斋论学》《答霍渭厓论学》《谈玄柬浚川》《谈禅柬顾未斋》、张邦奇《答桂洲论诗》《论学答致斋》、王廷相《和答桂洲夏公论诗》《奉和夏桂洲论学》《奉和夏桂洲谈玄》、霍韬《次论诗答甬川》《次论学答甬川》诸词,皆用《水调歌头》调,且同韵唱和,已是相当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行为。但学术性的强化,意味着词的体性在淡化,体现出一种与诗文趋近的发展态势。
就词的功能而言,将词体作为诗论的一种媒介,无疑是对词体格调的一种提升。从论学的常见体式来看,或用高位体式来论述低位文体,如论诗尺牍、论词绝句;或等位论说,如论文尺牍、论诗绝句;很少有用低位体式来论述高位文体的。也就是说,用词体来论学、论诗,多少有对学问、诗文的不敬之意。而夏言等馆阁词人创作了不少论学、论诗、谈玄、谈禅之词,无疑是从功能上把词体置于与诗文等同的高度。这已不是娱乐性消退的问题,更是文学性消退的问题。词的功能,不仅从缘情上升为言志,还从言志上升为载道。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将南词的婉约风格挡在京城词坛之外,只不过不是以北词的豪迈来抗衡南词的婉约,而是用词的诗文化来阻滞南词的侵入。就词的固有体性来看,北词自成一格或有可能,但要想与南词分庭抗衡,多少有些力不从心,而借助京城庙堂文风的独有优势,将词的风气转向典正的诗文化之路,确是一种可能。从宋词审美范式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对词本色的侵蚀和污染,但在词乐衰落的大势下,亦是对词之格调提升的一种新尝试,也是明词风格多元化的一种反映。只不过这一类尝试终将在情致之南词与典雅之诗文的夹击中步履难前。
三、北地诗派及北曲阴影下的词体发展空间
明人在诗、词起源上并不做细分,常将词源追溯至六朝乐府,甚至《诗》三百篇;在体式上词、曲亦少区分,经常词、曲杂编,“南词”“乐府”等称谓混用。在这样的文体观念下,诗歌、戏曲的风格及发展态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词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复古诗派,以陕西、河南诗人为主,强调北方雄浑、高亢之诗风,在诗坛独树一帜,影响久远;而明代北曲继承元曲的辉煌,有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冯惟敏等名家,曲风雄放,更不乏擅长填词之人。明代北方词坛,在千年词史中虽然影响甚微,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北地诗派,与以康海、王九思为代表的陕西曲家群及以李开先为代表的山东曲家群,却是中国诗歌史、戏曲史中的重要板块。北诗、北曲的豪迈景象,与“南重北轻”的词坛格局,在北方词人身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张力。北方词的发展将何去何从,表面上看是从南、北两种词风中选择其一,实际上却没这么简单,其最终的方向,还受到同一地域的其他文体风格的影响。
元代词乐式微,之后,诗化、曲化成为词演变的两个常规方向。自北宋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创作传统,因其雅化之追求,致力于提升词品、词境,向来为文人所推崇与发扬。而在明代文学思潮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弘治文学复古运动,其北方文学色彩尤为浓郁和自觉。在这一走势下,文学思想中的“南北之辨”,自康海、陆深以后便逐渐取代“词亡曲兴”之议题,成为音乐文学的热点话题之一,如蓝田、张綖、李蓘、李开先、胡侍等人多有发明。其中,作为嘉靖山东文坛领袖李开先,以整体文学之视野,有一综论:
北之音调舒放雄雅,南则凄婉优柔。均出于风土之自然,不可强而齐也。故云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其实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凄婉优柔之分耳。吴歈、楚些及套散戏文等,皆南也;康衢、击壤、卿云、南风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杂剧等,皆北也。北,其本质也,故今朝廷郊庙乐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验也。[注]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五《乔龙溪词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第554页。
显然,李开先将古代音乐文学之南、北沟壑区分得很清楚,在这套音乐文学的体系中,歌诗、词、曲之边界,远没有南、北之边界那么重要。当时不少复古作家,都身兼诗家、词家、曲家多重身份,文体的切换与混一,近乎常态。如王世贞云:“北调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韩苑洛、何太华、许少华,俱有乐府,而未之尽见。予所知者,李尚宝先芳、张职方重、刘侍御时达,皆可观。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注]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卷一,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2573页。这里所举,除冯惟敏为曲家外,李梦阳、王廷相、何瑭、韩邦奇、许宗鲁、李先芳等,都是明代诗文复古运动中的人物。与下文所引康海的“北曲难借”“南词易调”看法中流露出的南北高下之别相似,李开先也有“北,其本质也”的地域优越感。结合弘治至嘉靖年间的整体文学走势,北地诗歌于当时诗坛正风起云涌,明代曲坛亦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唯独北词尚无自觉、成熟之面貌。身处明中叶的复古思潮大环境中,北方词人作为北方诗人的一个分身,即使他们明知诗歌、戏曲的南北发展各有其不同的地域传统及创作体制,与词独尊南方《花间》的格局迥然有别,但面对北诗、北曲的蓬勃之势,在词创作上顺应婉丽而不谋求突破,实不符康海等人自觉的文学发展观。
另外,李开先还指出“朝廷郊庙乐章,用北而不南”,这种将音乐文学中的北风与郊庙之风相类比的做法,带有很强的文化高位意识。胡侍有类似言论:“北曲音调大都舒雅宏壮,……南曲则凄婉妩媚”,“故今奏之朝廷郊庙者,纯用北曲,不用南曲。”[注]胡侍:《真珠船》卷三“北曲”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2册,第327页。蓝田曰:“今之太常所用乐沿有元,有元袭宋之东都,盖崇宁乐府之遗法。”[注]蓝田:《蓝侍御集》卷三《跋胡可泉乐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3册,第382页。明代郊庙乐章较之前代的一大特色,便是诗、词、散曲杂用,[注]叶晔:《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8页。洪武三年定《宴享乐章》《十二月按律乐歌》即用词体;嘉靖年间廖道南、夏言、陆深、王教等词臣,则有乐章散曲之作。这种“郊庙用北”的观念,可证在北人眼中,京城词坛被归为明词北方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因其地理位置,还因其趋近庙堂的作品风格。这也意味着北方作家在创作或评价词的时候,其首要标准不是文辞,而是气格。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追求北方音乐之特征,未必需要符合已有的文体典范,落实在词创作上则应摆脱基于唐宋南词本色的诸多特征。而事实上,有机会将文人诗词、乐章词曲融贯在一起的作家并不多,夏言是较典型的一位。虽然身为阁臣的他,与康海、李开先等人的文学宗法观念有较大的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在音乐文学的地理特征上同声相求,只不过夏言有资格从事乐章的实际创作,而李开先等人只能进行学理上的言说罢了。
与诗、词在整体上已脱离音乐不同,明代的词、曲之别要复杂得多。在明人观念中,词出南方《花间》一脉,“南词”即“词”之别称,故所谓词、曲之别,在他们主要表述为南词、北曲之别。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对词、曲的渊源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但不妨碍他们对不同文体作出直观上的风格判别:
北曲自蒙古、女真入我中原始有之,南曲则五代宋所遗慢词是也。南则流于哀怨,北则极其暴厉,皆非古乐府之音也。[注]蓝田:《蓝侍御集》卷三《跋胡可泉乐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3册,第382页。
诗之变也,宋元以来益变益异,遂有南词、北曲之分。然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惟朴实,故声有矩度而难借;惟流丽,故唱得宛转而易调。此二者,词、曲之定分也。[注]康海:《沜东乐府序》,陈靝沅:《康海散曲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页。

对于这三段文字,有几点值得留意:第一,明人对南词和南曲并没有很清晰的区分,如蓝田、李蓘都将词和南曲混为一谈,康海笔下的“南词”,是词是曲,亦难判别。第二,明人对北曲的来源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自蒙古、女真入我中原始有”,是纯粹的外来文化;但也有主张“体南曲而更北腔”,即其文本、文体属性植根于汉文学传统,而音乐、表演属性借鉴自外民族传统。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两点可达成共识,一是北曲自金元以来盛行;二是南、北曲的风格存在较大的差别。
以上词曲观,势必造成一种困惑,北人填词应如何取法?是继承前代的南方文学遗产,还是视之为北曲发展的一种附变?事实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为代表的北方在籍词人群,与北地复古诗派及北方杂剧、散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康海甚至将南、北与词、曲对应,强调北曲朴实“有矩度而难借”;南词流丽“得宛转而易调”。对这段话的理解,与其说杂剧、传奇是戏曲内部两个不同的子系统,不如说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词、南戏、传奇是分立的两个音乐文学系统。在这种观念下,康、王等人创作的词,属于南方系统还是北方系统,或可商榷,不应想当然而论。我们应依据文学之体式、格律,将之纳入词演变之轨迹?还是依据音乐特性之不同,将之纳入北方音乐文学之范畴?在当下的分体文学史观中,文体明辨固然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音乐文学史观下明词的另一面。明词北方图景的复杂性,需要多维度的深究才能呈现。
综上所论,明代北方的填词风气,受到来自北地诗派与北曲潮流的双向作用,由此产生的影响,亦利弊各半。一方面,与乐府、杂剧同处北方音乐系统,明代北方词人的创作,有机会摆脱南词在观念、体制上的约束,形成了与北方诗、曲同质的文学风格;另一方面,明代北方诗歌、戏曲的发展声势浩大,北词在两种强势文体的夹缝中生长,难免走上诗化、曲化之路,词体新特性的养成,殊为不易。但不管怎样,较之金、元两代,北方词在明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独特而不成熟的面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代复古在北、庙堂在北、边事在北的整体格局。可惜入清以后,复古思潮衰落,北曲渐歇,传奇独大,花部又难登大雅之堂,北方作家寻求突破与另立词体典范的尝试,在江南词学与曲学的双重压制下,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四、通代视域下的“南词北进”与明代北词的独立性
“南词北进”这一概念,由沈松勤先生在《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一文中提出,用来论述北宋仁宗朝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词人先后由南入北,使汴京成为继西蜀成都、南唐金陵后的词坛中心,开创宋词一代新风。[注]沈松勤、楼培:《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4页。其对“南词北进”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对中观文学现象的梳理和概括。而如果跳出北宋词史的范畴,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千年词史中,则须厘清其核心语词,一是所谓“南词”,应该理解为南方词人,还是南方词风,抑或只是“诗余”的别称而已?在北宋前期词坛,北方创作冷清,三者不作区分亦无妨,但在通代词史中,就必须对“南词”作更精细的界定。笔者以为,南词当指南方词风,或称为“南派词”。纯粹讨论词人籍贯的南北与流动,只是文学地理之表象;把“南词”与“诗余”划上等号,是把“南词北进”理解为文体竞争的一种空间表现,亦有悖文学地理之初衷。只有强调词的南方体性与本色,及由此分化出来的南、北词风之差异,才能把握住文学地理的本质,进而更好地关注千年词史中的南、北互动。
与之相应,“北进”的本质,是指北方词坛的相对崛起,还是指北方词风的南方化?虽然在千年词史中,北方词坛的几个高潮,大多与南方词人、词风的侵入有关,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如金元之际的真定、东平词人群,元代前中期的大都词人群,其创作都与南词关系不大。笔者以为,将“北进”现象放在时间、空间的双重参照系中考察,更有其深刻的学术意义。金末至元前期的北方词坛,与北宋前期的北方词坛境况相类,都有一个崛起的过程,但却有实质上的差别,一个是北方词风的自我形塑,一个是南方词风的向北侵入。
一旦我们确定了“南词”“北进”的内涵,就可以发现,类似的“南词北进”景象,在千年词史中不止一次。元代后期以李齐贤、张翥为代表的大都词坛,已经压倒其前期的豪迈词风,深受南词婉丽风格的影响。清康熙年间,纳兰性德、顾贞观、曹贞吉三人并称“京华三绝”,为京城词坛的标志性人物,其填词“极情之至”,选词“铲削浮艳,舒写性灵”,[注]毛际可:《今词初集跋语》,《今词初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第729册,第548页。可谓南唐二主词之振声。其中的张翥和顾贞观,皆是由南入北的关键词人。
从表面上看,与元代、清代同为大一统王朝的明代,其首都亦在北京,甚至有过从南京迁都北京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诗歌、辞赋等领域掀起过一股创作热潮,出现了诸如《北京赋》《燕台八景诗》等作品。但是明代词坛的北方气象,却远没有北宋、元、清三代那么明显。较之北宋汴京作为全国词坛的中心,元代大都、清代北京成为千年词史中的重要板块,明代的北京词坛似不够成气候。在常规的词史评价中,杨士奇、夏言尚不能与刘秉忠、张翥、纳兰性德、顾贞观等人相比。
学界对夏言词的评价,一贯不高,多以“应酬之具”视之,唯近来余意《明代词史》给予较为多元与另相的评价。[注]张仲谋:《明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余意:《明代词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0-224页。笔者以为,不妨将夏言放在“南词北进”的视野下重新认识,或可见与其他同时期词人不一样的新意,及明代在此文化地理流动中的特殊意义。
北宋作为“南词北进”的第一个阶段,可视为对词创作荒芜地区的“北部开发”时代,[注]中晚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地的词创作景象如何,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其时声诗与词的边界较模糊,词尚未成长为一种独立、自觉的文体,进入到作家的文体创作观之中。面对来势汹汹的由西蜀、南唐词浸润出来的南方词人,北方词坛基本上没有抵抗力,汴京、洛阳等地虽聚集了不少北籍词人,但词风很快被柳、张、晏、欧等人主导。第二个阶段,是南北隔断状态下北词的自然成长期,即金、南宋的对峙时期。因为政治地理之沟壑,文化传播被阻隔,词作为一代之胜,其入南宋后的新变风貌,无法及时地为北方文人所了解和接受。总的来说,金人主要继承北宋苏轼一派的词风,涌现了真定、东平等词人群,对词之地域特征的思考与追求,已显露一些苗头,但不够自觉。第三个阶段,是在元代大一统帝国中,南北的文化交流回到正常状态,南词作为强势一方,得以重新进入北方词坛。但与北宋前期北方词坛的荒芜面貌不同,元代初年的北方词坛,至少还有金人留下的词学遗产,词人数量及多样性亦颇可观,南北词的互动与拉锯,在所难免。当然,由于金元词人缺少对词之地域特征的深入思考,加上北曲的异军突起,北词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相关竞争又一次以南词的胜利而告终,其景象就是元后期以张翥为代表的大都词坛。[注]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7页)论及元代大都词人群,认为“其成员来源不同,存在着‘北派’词与‘南派’词的差异,在发展阶段上也体现出由‘北派’为主,向以‘南派’词为主转变的趋势”。第四个阶段即明代,仍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正常状态,但北词开始进入自觉成长期,发展出一些较之南词不同的体性特征,如边塞词、论学词的成熟,词与北曲的交融,词曲乐与礼乐的互动等。当然,在“环太湖词圈”的压倒性优势下,其自足之发展举步维艰,但嘉靖京城词坛作为当时北方最热闹的词景之一,置于这一长时段脉络和动态格局中,自有溢出传统词学评价体系之外的一些意义。第五个阶段,为明末及入清以后,南强北弱的整体格局固然无力改变,但随着明代北词的自觉发展,并以前代词学遗产的形式为清词所继承,南北词进入一个互融与相对平衡的状态。纵观整个清代,北方词坛涌现了以龚鼎孳、梁清标为代表的京城“辇毂诸公”,及代表“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注]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7、114页。的秋水轩唱和活动;新政权意志下的数次文字狱,造成了前代少有的流人词人群及其创作;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词坛重心移北,形成了以“京华三绝”为代表的京城词坛新景象等。虽然龚鼎孳、顾贞观皆为南人入北,但梁清标、孙承泽、纳兰性德等北籍词人在词坛网络中的功能及其影响力,同样至关重要,显然没有哪一位明代北籍词人可以企及。京城词风渐趋平衡,表现出政治中心应有的自信与包容。
若不论南、北词坛的创作规模,仅从南、北词风的角度来考察,北宋、元代、清代三次“南词北进”,都是南方的婉丽词风攻陷了坐落在北方的政治大本营,其本质就是南方词风的地理扩张。诚然,这一进程开拓了地理空间,促成了词坛中心的转移,或词坛副中心的形成,但在词的题材、风格等方面,并没有充分汲取北方文学之养料而有同等幅度的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其词创作仍强调词体之本色、正宗,体现为内敛、保守之势。相反,金、明两代作为“北进”受挫期,倒在客观上促成了北方词风的登场,其词创作与北方的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形式相融合,谋求本色词风之外的发展新路,不断地走向独立与成熟。合而论之,南词的每一次“北进”,固然是对北方词坛之创作风气的一种激振,但也是北词自我摸索之路的一次退让与失败;而每一次“受挫”,则对应着北方词坛独立性的增强,更是对词题材、风格之丰富性的一种提高。这两种情况交叉演进,不断强化北方词人阵营,将北方文学之特质注入词创作之中,最终形成自具一格的“北派词”。

明代北方词坛出现的这些区别于南词的别样词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坚持“袭陈”,面对强势且渐趋丰富多样的南派词风,继承宋金元三代的苏、辛词风。如明中叶河南人李濂,刊刻《稼轩长短句》,撰《汴京怀古》组词,此固袭陈稼轩之举,但在当时的词坛格局中,属于未随大流的少数分子,仍值得称耀。另一种是尝试“出新”,在已有的词类型之外,另辟创作上的新径。如韩邦奇、孙承宗结合蒙古、女真边事,开拓边塞词创作的新局面;夏言、王廷相借馆阁问学之风,以论学之体提升词境。此皆出新之举,更具词史意义。总的来说,在明词的南北格局中,无论袭陈还是出新,都是在南派词风之外的自觉追求,是对北词之丰富性和独立性的一种充实。
综上所述,对明词北方图景的研究,以词作、词人、词群为基本单元的个案考察和动态阐释,属于常规的研究路径。然就“北”论“北”,难以另出机杼。若以他者视野或南北流动视野讨论“北方”之“词”,结合南方图景作一互动考察,或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本文的尝试,就是希望通过词之“流动”,而不是对以往的数据之增减、版块之组合,来重新认识词地理格局的历时变迁。这样的研究路径,仍是为了解决宏观之问题,却对微观之文学图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明词研究摆脱粗放、平面化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打造明词世界的立体感和纵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