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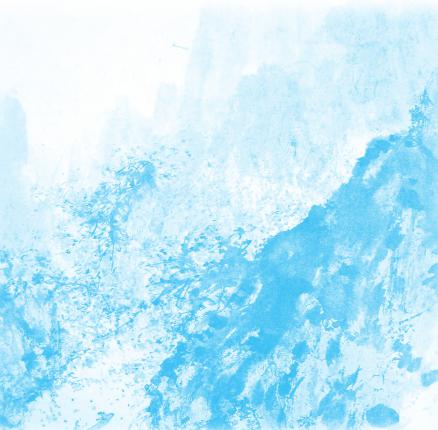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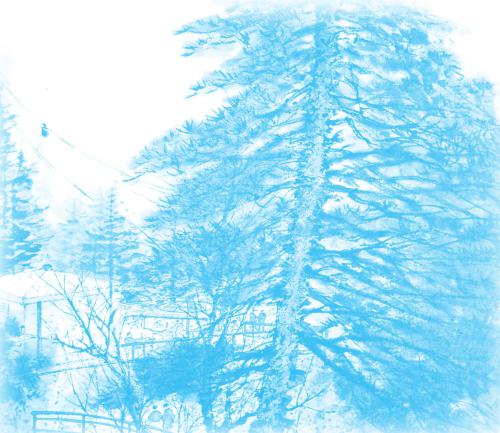
一
和大哥约定了扫墓的日子后,我照旧去老街上买钱纸,香烛,爆竹。以往这些东西都由祖父准备,他挑一个不落雨的天气,从石嘴头把折表纸买回来用刀裁开,然后一手拿着钱錾,一手拿着木锤,在雨脚般的敲打声里,一个个神秘的印子从薄薄的草纸里钻出来,钱錾的空隙终于被填满,祖父的手轻轻一抖,纸屑儿像巫师嘴里的咒语一般飘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认识了这些东西,人们拿来敬神和祭祖,试图用它们叩开天堂和地府的大门,完成两个世界的对接。
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开车回去,把车停在三哥屋坪里,大哥他们已在等着我们,三个侄子也从外地回来了。我们沿着村庄里的小河往上走,天时阴时晴,阳光在我们身上沉下又浮起,风雨过剩的季节,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了。树木抽芽,路边和田垄里的草忙着返青,李花细细密密地开着,裹满一根根枝条,仿佛听得到窸窸窣窣的碎响。桃花还在酝酿,淡红的花苞掩映在农家屋角。这个青蓝色的村庄,是我少年时的翻版,正蠢蠢欲动赶往春天的纵深。
经过大屋门前,进老屋冲,然后开始爬山,一条野鸡路东躲西藏,拨开杂草,地面潮湿,浅浅的青苔东一丛西一簇,像一副神秘的地图。一路陪着小心攀上山腰,来到曾祖父的墓前。侄子们拿着镰刀砍墓前的树,这些树性子野,背着我们偷偷摸摸地长,一春风催雨赶,就高出了曾祖父的视线。我和三哥铲墓地里的草,大哥摆好三牲,再摆三个酒杯,一个茶杯,茶杯里没有茶,就一小撮茶叶。大哥把香点燃,跪下分三炷插好,香冒出烟来,直直的一线,不知停留在哪里的风相准了时机,跑过来把它们粗暴地揉乱,墓地里纷乱起来,像是刚刚铲掉的草又活过来了。大哥用手扇了几下,拿起瓶子往杯子里筛酒。大哥说,老阿公,你多吃点啊,保佑子孙顺顺序序。
我们默默地看着大哥做这一切,大哥的声音不大,就像和曾祖父坐在一张桌子前,吃着饭,说着话,还不时往曾祖父的杯子里添酒,我不知道曾祖父看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但我确信他看到了,也聽到了,正以一副长辈的满足打量着我们。
我们和曾祖父彼此陌生,我出生以前,他就把家安在了这里。四周青山绵延,往前面的山垭里望过去,长着绒毛的天际线缓慢地划过,远山如岸,幽蓝地横在眼里,一重高过一重。祖父在世时不止一次说起过这座坟,他说风水先生说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管六十年事,六十年都不要去动。
曾祖母去世早,祖父是由曾祖父一手拉扯大的。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山外的狮子庵,那里有一座水碓,几十户人家轮流舂米,湿漉漉的水碓声嘭嘭地响着,以终年不变的节奏占据了祖父的童年。曾祖父觉得守在那里只能穷一辈子,攒了些钱在大屋里买了块地皮起了三间瓦屋。大屋里是我们这个小村庄里最大的一个屋,东边是王家,王家过来是张家,一个大地主,穿一身绸布衣服,戴着礼帽,拄着自由棍,他把自己的前半生劈成两半,一半给了女人,另一半给了赌桌,走背运的时候,一垄水田或者一片山林就在两枚铜钱的丁当声里化为云烟,没钱了就接着卖地,我们家的地皮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再过来还是两户姓张的,加上我们家,一共是五户。
搬到新屋里后,曾祖父学郎中出了师,在杜家排开了个药铺,起初生意清淡,很多人劝他趁早关门,这样不至于把借来的本钱亏光,曾祖父死活不肯。这样的选择,源自他体内日益堆积的反叛。我曾想象过当时的情形,曾祖父孤独地守在药铺里,像一个落魄的诗人一样,打开一本线装的药书,把每一位中草药还原到泥土里的模样,看着它们发芽,开花,结实。门外,一场雨就要来了,过路人大步流星,还是不忘看一眼曾祖父,曾祖父感觉到了来自那道目光里的同情和蔑视。他笃定在潺潺的药香里,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计较这些东西,他只想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对和错。
大哥把钱纸烧完,说都坐一会,等老人家慢慢吃。我们都坐下来,好像真的在等曾祖父把饭吃饱,把酒喝好。阳光冷不丁地刺破云层,把青山抹成橘黄,一些新叶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摊晾着春意。命运确实短暂地垂青过曾祖父,可就在生意红火起来不久后,曾祖父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把药铺关了,不再重操旧业,开始扶犁打耙,他赶着牛犁开一丘丘水田,把种子播到地里,把秧苗插下去,把稻子收回来,用汗水和隐藏在笑容里的泪水驮着一个家。一双抓惯了药把惯了脉的手,如何会与泥一脚水一脚的生活苟和?其中的缘由,如果他不肯说,即使我穿越到百多年前,也还是想不透。
一直以为,一个人应该在冬天里死去。事实上,死亡不像植物的荣枯,要屈从于节气傲慢的指令。什么时候困了,就躺下了,只不过这一觉睡得比平常沉一些,醒来这个词语已归入遗忘。我的曾祖父就是在一个夏天积郁而终。他睡得太沉了,忘了醒来看一眼,他亲手栽下的早稻用粒粒金黄照亮了整个村庄。
曾祖父是一个郎中,熟悉脉象和药理,虚实洪细,君臣佐使,了然于心。他为很多人开个方子,却无法为自身的命运开一剂良方。
祖父生前隔一段时间便会到曾祖父的墓前坐坐,回来后跟我们说,你老阿公那座坟很好呢,坟堆还是原样子,一点都没瘪。对这个话题,我们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保持沉默。祖父顿了顿,叹息一声,六十年不能动啊。我知道祖父一直记挂着给曾祖父改坟的事,他想活着的时候再见自己的父亲一面。这个简单的愿望其实随时都可以变为现实,只是祖父最终还是把它带进了坟墓。
父亲是单传,家里缺钱是事实,但最缺的还是人丁,自从母亲嫁过来后,一连生了我们十一姊妹,一个家从冷火秋烟变为儿女成行,祖父用爽朗的笑声来安慰他心底的遗憾。而他生怕我们曲解了他的意思,在适当的时机,总不忘提醒一句,你老阿公那座坟葬得好啊。
祖父去世十多年后,我们决定给曾祖父改坟。准备了筋坛,墓碑,请了风水先生,又请了我的一个表哥来捡筋骨。挑了黄道吉日,一家人浩浩荡荡来到墓前。父亲跪在墓地里喊,阿公,我们来给你改坟了啊。父亲后来解释,这样喊一声就是好让曾祖父知道这回事,动土时别吓到他。
刨开坟堆,棺木还剩最后一点没有腐烂,小心地拿出来,丢到地上就断成了几截,风仿佛糜烂了,一股没落的气息猛地撑开我的肺叶,让我想起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里达尔为他即将死去的母亲做寿材的情节,“他站在碎木屑堆里,正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给两边的阴影一衬,木板金黄金黄的,真像柔软的黄金,木板两侧有锛子刃平滑的波状印痕。”当年,曾祖父的寿材也是这样做成的,一根根上好的圆木臣服于锋利的钢铁,其中一部分变成一卷卷木花,以及细碎的木屑,飞出木匠的刨子和斧凿。六十多年过去,这些朽木已经没有了木质的纹理和气息,与阳光雨露彻底绝了缘,再也回不到春天,回不到树的序列,恐怕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棵树。
骨殖是跟着棺木腐烂的,扒开松泥和木屑,才找到几根细小的骨头,无论表哥动用多少经验,都无法再还原一个空洞的人形。那双粘满药香和泥土香的手,那双深邃睿智的眼睛,那些历经过的欢乐苦痛,那么多曾经鲜活的存在,到如今已找不到一丝可供追忆的痕迹。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也没弄明白生命的奥义,活着时不断宣示着自己的存在,那么执着,那么偏激,试图挣脱自然的律条,与时间争锋。就像琦君说的:“这个世界,有什么是永恒的呢?”我们所处的,无非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所有的悲喜浮沉看到尽头都是云烟。
表哥把曾祖父的骨殖放进筋坛里,然后盖上盖子,在风水先生用罗盘定好朝向后,再盖上泥土,树起那块青石墓碑。我看到那几根骨头惊惶不定地缩在坛子的一角,而筋坛并未因为骨头的进入而缩小空间,依然空空洞洞。曾祖父就住进了这样一片空洞里,这里,成了他最后的家。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坛子,相对于曾祖父来说,却有如辽阔的世界一样空茫。这样想的时候,悲伤像藤蔓一样爬满了我一身。
复杂的仪式结束后,站在刚刚竖起的青石墓碑前,父亲显得很高兴,他吐了一口长气说,总算把你们阿公牵挂的一件事办好了。我想父亲的高兴并不仅仅是完成了祖父的一个遗愿,想想这深山野岭里的夜晚,还有多少阴森森的磷火在暴露的白骨上游移?一个人像陀螺一般旋转,到头来能有一个这样体面的归宿,也算是圆满了吧?
大哥说,差不多了,打爆竹吧。二哥把爆竹点燃,一些爆竹跌进新泥里再炸开,声音渺茫,像卡在时间的齿轮里。我们踩着暗沉沉的爆竹声往山上走,我边走边在脑子里勾勒曾祖父的样子,高挑,瘦弱,穿着长衫,他在山脚慢悠悠地走过,阳光投下他清癯的背影。这当然只是我的虚构,但不必虚构的是,曾祖父曾以飞蛾逐火的方式介入到另一条生活的洪流,在我们这个世代农耕的家族播下了一粒夢想的种子,虽然他的梦想像缺乏营养的植物一样很快凋谢了,但宿根一直都在,爬满了一条血脉。
二
祖父葬在老屋场里,小地名叫丝茅坪。
当初,祖父是最后一个从老屋里搬出来的,我们把最后一条凳子都搬走了,他还是留在屋里不肯出来,谁都不知道他呆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说,要是还年轻十岁,我死都不会搬到新屋里去。祖父说的当然不是气话,一个人在一座屋子里住了大半辈子,人熟悉了屋子的气息,屋子容纳了人的悲悲喜喜,到了八十多了还得打破这种默契,换了谁都难以接受。后来拆这个老屋的时候,祖父一声不吭地看着买主把屋顶掀开,把门窗卸下来,自始至终用沉默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我从未怀疑过祖父对这个老屋的感情,家里人多以后,原先那三间瓦屋住不下了,祖父在更深的山里买了块荒地,起了六间两层的大瓦屋。这是祖父领头一架土一架土夯起来的,天断黑后,活没有停,支在墙头的火把在他油光闪亮的脊背上漫天漫地地燃烧,据说起好后,墙架子都用烂了三副。这一次,我们确实把祖父伤得太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座深山里的老屋,四处漏水,雨打风吹,用不了多久就会倒掉。后来祖父说,我死了,你们就把我葬在那个屋场里。祖父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这副表情不时楔入我的内心,并由此招来一场场冷雨凄风的洗劫。
祖父的坟在厅屋正中央,土地的磁场对应着他的磁场,他的魂和身边一众生灵的魂遥相呼应,一切都退回到了熟悉的过往。墙基默然无声,在四周的泥土里爬过。地暖草生的季节,他会默默凝望左边清明如鉴的池塘,听一听右边竹林里摇碎夕阳的枝叶,把那头老黄牛从对面的田垄里牵回来,牛头上挂着稀薄的暮色。屋后沙沙过来的,还是昨天那一缕风声,远处,群山摇响,布谷鸟开始歌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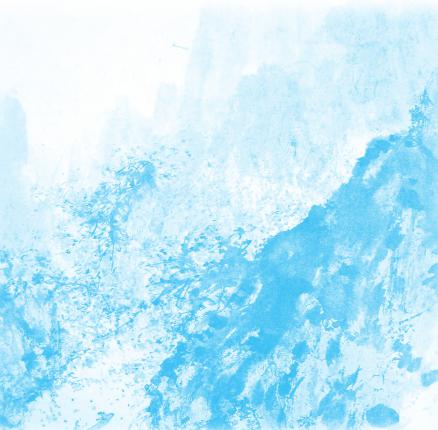
每次来到这里,一些细枝末节总是乘虚而入,等我回过神来,大哥摆好了三牲,倒了酒,和祖父说着话。我点燃一根芙蓉王插在祖父的坟前,白色的烟灰以一种缓慢的节奏在静默中燃烧。祖父的烟瘾很大,他不抽纸烟,说纸烟太淡,抽了跟没抽一样。他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每年割烟的时候,用撮箕挑满满一担回来,宽大的烟叶分成小把用棕叶扎了挂在吊楼上,在风吹日晒里,淘尽最后一丝青色。祖父把金黄的烟叶卷起来压紧切成丝,装满他那个铁皮烟盒。抽烟的时候,拿出那把长烟杆,从烟盒里撮一撮烟丝填满烟斗,对着炉火叽哩咕噜地烧,一次要抽上五六袋。烟雾抚平他一脸皱纹的时候,他是没有心情来跟谁说话的,他一副沉醉的样子,似乎那些茫然无绪的烟雾能把他引向一条幸福的路途。时间一长,我们竟适应了那股呛人的草烟味,凭着这股味道的浓淡就能判断出祖父身体里的零件是否在正常工作。
一根烟烧完了,我接着点上一根,拿起瓶子往杯子里添酒,大哥说,倒了三杯了。我说阿公这里就倒六杯吧。大哥愣了一下,很快若有所悟地点头。我说阿公,没有自己栽的草烟了,只有纸烟,你将就一下啊。你说的,酒就六杯,我给你倒满六杯。祖父听到这些话,肯定是高兴的。以前和祖父喝酒,他总是笑吟吟地端着杯子,喝完一杯便问我,几杯了?我说六杯了。六杯了啊,那喝完就算了。喝了那一杯,祖父把杯子放了,拖着椅子离开饭桌,坐在一边默默看着我们吃饭,那张被酒精烧红的脸,皱纹一扫而光,如一汪平整的水面闪烁着快意的光芒。祖父喝过最好的酒是浏阳河小曲,五块五一瓶,有一次祖父说,这酒好是好,就是太贵了。平时他都是喝七角五一斤的五加皮,就像他买肉一样,作为一个厨师,他告诉我们猪身上最好的肉是里脊肉,然后是臀子肉,但每次提回来的往往是半边猪脑壳,放到砧板上把火铲烧红了烫毛,再用剔骨刀一点点刮干净。他笑呵呵地说,猪脑壳好啊,又好吃,又划得来。
在村庄里,祖父年纪最大,又有一身好厨艺,村庄里的人都是乡里狮子乡里滚,去过县城的掰着手指数得清,祖父不仅去过县城,还去过省城,江西的袁州。因为这些原因,大家都很敬重他,年长一些的叫他执叔公,年轻的叫他老叔公。年底家家户户摆杀猪酒,最上座的位子总是留给祖父。谁家做红白喜事,都要把他请去,听听他的意见。村庄里的人都说,你阿公,真是个有福的人啊。

只有我从来都不认为祖父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从小失去了母爱,我的祖母,这个祖父从未在我们面前提及片言只语的女人,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就撒手而去,为了这一大家子人,祖父一次次掐断了续弦的念头。从而立之年起,在孤灯照壁冷雨敲窗里,走完漫漫人生。就算在我们懂事以后,也从未听到过祖父有什么花花草草的故事,或许有过一两个女人像流星一样在他的天空里划过,照亮过他琐碎的日子,但为了顾及一个家庭,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她们离去。那时候,一个十几口的家嗷嗷待哺,在最艰难的时候,祖父四处借钱,有一次连早饭米也没着落了,他吃过晚饭从家里出发,到江西桐木一个朋友家借了钱又连夜赶回来,来回二百多里的路,脚上磨出的一个个血泡,像一双双饱含委屈的眼睛张望着这个世界。生活处处与祖父为敌,但我从未见到过祖父的愤怒和悲伤,更不用说流泪了。我见到的祖父,从来都是笑着的祖父,哭着的祖父,那不是我的祖父。
我再一次给祖父倒酒,我说阿公,六杯了啊。我恍惚听到了祖父的声音,好,不要再筛了。然后是他挪椅子的响动,我双膝跪下去,磕了三个头,眼睛里突然爬出晶亮的东西。有风过来,门前老梨树上的花飘飘洒洒,落了一地的雪。
三
离开祖父的坟前,已过了晌午,我们沿着河往回走,去母亲的坟地。
母亲在住院的时候就交待我们,我死了你们不要把我葬到老屋边上去,要找一个热闹点的地方。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照她的意思,在离三哥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块地,这个小山冈,周围是一个爆竹厂,每天有人进进出出,前面是村庄,望得见田垄,水泥路,菜地,人家,听得到鸡鸣狗吠。
爬上山冈,母亲的坟上没什么草,一边长着一丛丛水竹,另一边是茂盛的油茶林。摆好三牲酒杯,插了香烛,接着烧纸钱,留下的纸钱太多,得慢慢烧。这也是我的意思,得多烧点给母亲。我这样做,并非要在先人面前分出个远近厚薄来。生前,母亲当家,一大家子的吃喝用度全由她一手安排,受尽了捉襟见肘之苦。有次母亲去给我借学费,我的一个亲戚不但不出手相助,还冷嘲热讽,没有钱读什么书,这么大的崽了,不晓得让他去做事赚钱。因为钱的事,我三年初中停停打打,分三次才读完。所以母亲总是告诫我,穷人家的孩子,不要去和别人比吃比穿,要勤快,吃得苦。
母亲在临终前都还在念叨家里的鸡鸭没人管,像母亲这样操心的命,在那边肯定也是要当家的,那个家更大,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要买这买那,不知得花多少钱。而且母亲从未托梦给我,不知那边的物价是不是也在疯涨,因此我为母亲准备了一扎扎的钱,有一万一张的,一万亿一张的,也有五块十块的,方便找零。我一边烧纸钱一边说,妈,在那边别为钱的事担心,没钱了托梦告诉我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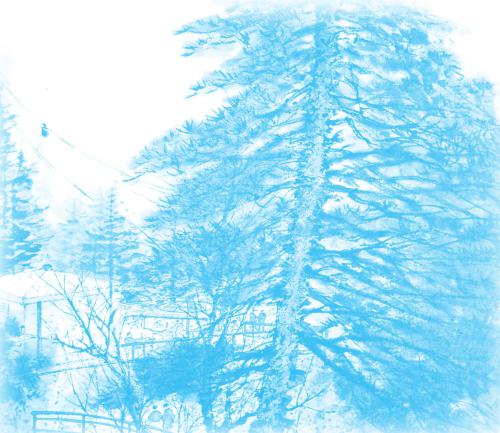
我相信母亲在安静地听,听得明明白白。要在以前,母亲是没有耐心听我在这里絮絮叨叨的,她甚至会面有愠色,有什么事,快点说。这个时候,她正起身赶往菜地,系着一条青围裙抖抖索索地穿过田埂,田垄和里面薄薄的绿色一样沉默,风尾随着她头上的绿纱巾,准确无误地挑起两个尖角。她要去看辣椒秧长得壮不壮?四月豆发了芽没有?洋芋是不是该淋肥了?一家子人要吃菜,这些事容不得半点马虎。若是情况满意,母亲的耐心就会像那些菜一样噌噌地往上长,回来后眉飞色舞地向我们描述几个月后的好收成,其实这只是母亲一厢情愿的想象,但她会努力地选择措辞,尽量描述得活灵活现,跟看到了一般,尽管她心知肚明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若是菜长势不好,脸便沉下来,话也没有了,好像我们和这些菜都成了她的敌人。
母亲去世时是冬天,白菜和青菜都还是菜秧子,病殃殃地缩在地里,此后一直无人料理,到了来年春天,杂草呼朋引伴,拼命地抢夺地盘,以致泛滥成灾,那些仍然是菜秧子的白菜和青菜饱尝杂草的肆虐,仿佛在等母亲前来拯救,只是它们并不知道,那个人从此不会再来了。以前每次回去,临走时母亲总会说,你等一下,我去摘些没打农药的菜给你带回去。从菜地里回来,她手里就多了白菜,萝卜,辣椒,或者是一个冬瓜,几条丝瓜。她把菜放到我车子的后备箱里,对着我说,在街上什么都得用钱,钱又用了,还尽买些打了农药的菜。她一副心痛不已的表情,仿佛她这个儿子受尽了城市的欺骗和压迫。
我到城市里生活后,经常会回村庄里去,那片并不起眼的土地让我与生活之间的隔膜大片大片地剥落,那些埋伏在山间田垄的小路,每一条都能通向我灵魂的归属和自由,而我一直误以为这就是所谓的故土情结。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发现这片土地突然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张僵硬的壳。每次不得已回去都会去母亲坟前看看,坐下来,慢慢抽一根烟,向她说些我生活中的琐事,倾吐我心底的一些困惑和悲伤。巴别尔说,“每个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我知道,母亲就坐在我身边,听我说着话,她会宽宥我行事的莽撞和过错,会敦促我反思我的所作所为。她的灵魂就如一面高悬的镜子,一直在照着我,看着我早出晚归,穿过一条条城市的街道,每天做些什么事,说些什么话,交些什么样的人。这也使我不断地省察自己,等到有一天我和她在地下相逢的时候,不至于面有愧色,无地自容。
四
房子和坟墓活在对方敌视的目光中,平常的日子里,这样两样事物,实在找不到交集的理由。
我在离开母亲的墓地下山的路上,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坟墓成了房子的影子,房子去哪,坟墓就跟到哪,它们排斥,依偎,暧昧,纠缠,恨不得把对方甩得越远越好,却又不时回头看看跟上来了没有。这样一段若即若离的距离,完成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人在屋檐下出走,就将回到蔓草丛生的墓园,摇身一变成为山上的祖先。
这些散落在山上的祖先,不單单是一张灰暗朦胧的脸,一些残缺朦胧的往事。那些竖起的墓碑,隐藏着一个家族的秘密。是一条血脉和情感的归途。
【作者简介】晓寒,本名张晓,湖南浏阳人,作品散见《湖南文学》《四川文学》《雨花》《野草》《山东文学》《雪莲》《青年作家》《文汇报》等报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