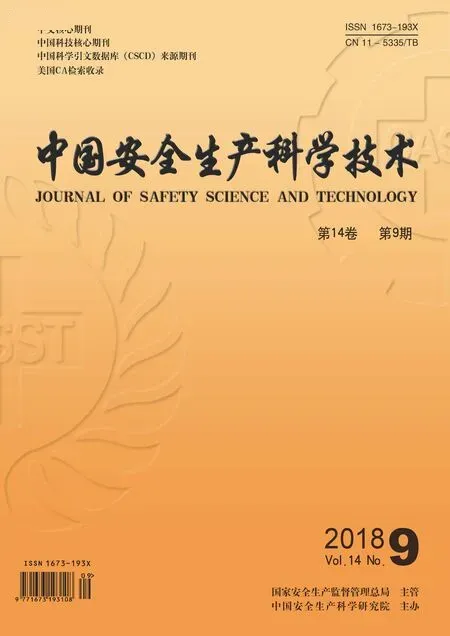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雄安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吴 平,林浩曦,田 璐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10;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3.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4.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
0 引言
伴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自然生态系统逐渐向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转变,由此带来的物质和能量流改变影响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危及区域生态安全[1]。基于格局-过程相互反馈原理,以优化生态系统结构、维持生态过程完整性为主体思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可为实现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新视角[2]。作为未来生态城市标杆,雄安新区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进京津冀生态建设中战略地位重要[3],有必要在建设初期先行识别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其高标准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Yu借助景观生态学思想来诠释生态安全,提出了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4],自此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格局构建和规划应用等[5]。就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而言,基本遵循“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的基本思路[6]。源地是指对保持地区生态健康和保障地区生态安全意义重大的生态用地[7],现有源地识别方法可大致分为直接识别和间接评价2种,前者直接以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林地、水域等作为源地[8],后者则主要从生态适宜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来评估斑块重要性,进而确定生态源地。阻力面构建是廊道提取的前提,现有研究主要依赖于赋值法,即依据土地利用类型赋予其不同阻力值[9],亦有研究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自然本底特征对阻力面进行进一步修正以区分同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内部差异,诸如夜间灯光强度[2]、湿润指数[2]、地形特征[10]、地质灾害敏感性[11]等。廊道提取方法主要有最小累积阻力模型[12]、斑块重力模型和指标体系[13]等,其中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法应用相对较广。总体而言,在源地识别方面,已有研究大多考虑生态用地本身的重要性,对人类的生态用地需求考虑较少[9],可能会造成评估结果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脱节;在阻力面构建方面,基于社会经济数据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阻力面修正可以大大提高结果精度,逐渐为学界青睐;廊道提取则多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下文简称“新区”),规划范围涉及保定市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着重强调了新区规划要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方面,新区现有土地开发程度较低,生态本底良好,区域环境承载力较高;另一方面,新区承载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双重使命。新区面临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多重压力,因此在大力投入建设前,深入研究新区生态系统状况、构建新区生态安全格局,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建成生态化发展模式的示范性城市具有重要指引作用。鉴于此,本文针对新区自然本底特征,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维持5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并充分考虑人类对于生态用地的需求,以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土地利用程度共同表征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状况识别重要生态源地;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修正基于土地利用类型赋值的基本阻力面,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旨在为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新区地处河北省保定市,同时为北京、天津、保定腹地重合地带,规划范围囊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地区,与京津相距分别约110 km。本文选定雄县、容城和安新3县为研究区,土地总面积为1 557 km2,城市化水平较低,可供开发建设空间充裕;属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地势西北稍高、东南稍低,总体较为平坦开阔,以低海拔平原和洼地为主;境内耕地分布广泛,南部的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对于维持区域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1.2 数据来源
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率30 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空间分辨率30 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土壤类型图,空间分辨率1 km,来源于中国1∶1000000土壤数据库;2015年MOD13Q1数据,空间分辨率250 m,来源于NASA;2015年MOD17A3数据,空间分辨率1 km,来源于NASA;交通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2015年日均气象数据(气温、降水),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2015年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保定市经济年鉴》;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空间分辨率500 m,来源于NOAA/NGDC;2015年公里网格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空间分辨率为1 k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源地识别
生态源地一方面要保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另一方面要满足人类对生态用地的需求。鉴于此,本文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属性综合识别生态源地。
1)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生态系统服务涵盖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所有收益[14],是测度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关键指标。进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评估,明确界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优势区,筛选生态价值较高的关键斑块,是识别生态源地的基础。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植被覆盖良好,且分布着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为人类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针对新区自然地理特征,本文评价粮食供给、产水、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维持5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具体估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
2)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人类对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消耗或偏好需求,本文从人口、经济和土地3方面选取指标以表征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其中,人口需求以人口密度表征,反映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数量,人口密度越高,需求越高;经济需求以地均GDP表征,反映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偏好,地均GDP越高,需求越高;土地需求以土地利用程度表征,反映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越高,需求越高。
整合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指标,分别选取每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前10%的区域作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区域,除产水服务选择产水量最低的10%区域(即蓄水量位于前10%),土地需求选择土地利用程度为4的区域外,对所筛选区域取并集并剔除非生态用地部分,得到生态源地。
1.3.2 阻力面构建
物种在水平空间的运动以及生态功能的流动与传递,主要受土地覆被状况和人类活动影响,即生态阻力面[12]。参照前人研究[9],设定新区基本生态阻力系数值:林地植被覆盖程度最高,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最强,赋值为1;建设用地承载的人类干扰最强、阻力最大,赋值为500;水田、旱地、水体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依次递减,分别赋值为20,30和50。
阻力面构建是廊道提取的前提,其精确程度直接影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然而,依据土地利用类型赋值的生态阻力系数设定方法掩盖了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阻力差异。夜间灯光数据可综合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反映城市发展水平,本文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灯光亮度值作为指标,修正基本生态阻力面,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1)
式中:NLi为栅格i的灯光亮度值;NLa为栅格i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a的平均灯光亮度值;R为基本生态阻力系数。
1.3.3 廊道提取
廊道是景观中与相邻基质区别明显的狭窄通道,用于相邻2源地之间的物种迁移和扩散,通常为源地之间的阻力低谷。本文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进行生态廊道识别,重点考虑源地、距离和景观介质3个变量,估算物种从源地至目的地之间克服阻力做功的水平过程,进而提取相邻2源地之间的最小阻力作为生态廊道,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2)
式中:MCR为最小累积阻力值;Dij为物种从源地j到景观单元i的空间距离;Ri表示景观单元i对某物种运动的阻力系数;f为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
2 结果分析
2.1 生态源地识别
2.1.1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新区各生态系统服务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见图1)。粮食供给服务高值区主要位于容城县和安新县南部,该区域耕地分布广泛,以旱地为主;安新县东部主要为水域,无粮食供给。产水服务高值区分布于建设用地,平均产水量达393.88 mm,这是由于建设用地不透水表面占比高,地表蒸散量低,产水量高;而林地覆盖率高,植被蒸散量高,因此产水量低,平均产水量仅为152.09 mm。土壤保持服务则呈现西部和北部高、东部低的格局,与新区总体地势较为平缓密切相关,3县平均土壤保持量为20.11 t·hm-2·a-1,实际土壤侵蚀和潜在土壤侵蚀均较低,因此土壤保持量也较低。固碳释氧服务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3县平均固碳释氧量为1 959.55 gC·m-2,林地和耕地平均固碳释氧量最高,分别为2 073.32 gC·m-2和2 027.79 gC·m-2,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建设用地和水域。生境维持服务的高值区位于东南部白洋淀,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该区域已于2002年被确立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物种资源丰富;而极低值则分布于建设用地、道路等人类干扰强度较大的区域。

图1 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空间格局Fig.1 Spatial patter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supply in Xiongan New Area
2.1.2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图2 新区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格局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demand in Xiongan New Area
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来看(见图2),新区人口需求和经济需求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北部容城县和雄县较南部安新县高,北部地区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快,对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较高,而白洋淀85%的面积分布在安新县内,占安新县土地面积近50%,白洋淀区由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人口相对稀疏,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旅游业,相对来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较低。从土地需求来看,新区内林草地和水域的开发程度最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最低,集中分布在白洋淀及其周边,约占总面积的11.9%;耕地受人类扰动程度较高,相应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较高,分布广泛(69.1%);建设用地开发程度最高,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最高,但分布零散。
2.1.3 重要生态源地

图3 新区生态源地空间格局Fig.3 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sources in Xiongan New Area
从空间分布来看,生态源地主要位于新区西北部旱地和东南部水域(见图3)。从总量来看,生态源地总面积约484.33 km2,占新区总面积的31.3%,其中59.6%分布在安新县,26.0%分布在容城县,14.4%分布在雄县。从各县内部来看,容城县和安新县生态源地面积占比分别达40.0%和39.8%,生态本底良好,而雄县仅为13.7%,生态本底相对一般。一方面,雄县近年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迅速,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雄县内耕地广泛分布,但植被覆盖程度较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相对较弱。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生态源地所处地类主要为旱地和水体,分别占总面积的64.1%和32.1%,林地虽然仅占总面积的5.9%,但其中93.4%的林地均为生态源地,说明林地总体质量较高,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生态阻力面构建及生态廊道提取
2.2.1 生态阻力面
夜间灯光亮度值能综合表征城市发展程度,由图4(a)可知,各县中心城区城市化水平最高,夜间灯光亮度值也最高,向周围扩散逐渐降低。基于夜间灯光亮度值对新区基本生态阻力面进行修正,如图4(b)所示,生态阻力面在同种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空间差异明显,对于地表覆盖对物种迁移的干扰程度表示更为精确。可以看出,新区生态阻力系数空间分布较为破碎,高阻力值与低阻力值相间分布。大部分区域阻力值较低,对于高阻力值区域,城镇用地的生态阻力普遍低于农村居民点,可能与城镇用地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有关。
2.2.2 生态廊道

图4 新区夜间灯光亮度及生态阻力空间格局修正Fig.4 Spatial patterns of DN value and revised resistance surface in Xiongan New Area
生态廊道是联通生态源地、保证物种交流和迁徙空间的重要通道。本文借助ArcGIS10.2平台,分别以各生态源地的几何中心为生态节点(共16个),以剩余的生态节点为目标点集群,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测算出最小耗费路径,以此为基础提取出新区关键生态廊道(见图5)。从空间上看,新区生态廊道呈现“Y”字型格局,呈树枝状从西北和东北向南部延伸,总长度约185.86 km。在“西北-东南”一线,生态廊道主要沿农村居民点分布于旱地;在“东北-西南”一线,生态廊道主要沿城镇用地、水系分布,横穿旱地而过;2条线路在白洋淀处汇聚,继续向南延伸,与安新县南部源地联结。综上,新区生态廊道基本沿建设用地和水系分布,所处地类主要为旱地,且避开了灯光亮度值较高的区域,有效联结新区内部各生态源地,使得景观连通性较好,为生态源地之间的物种迁移和信息与能量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2.3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图5 新区生态安全格局Fig.5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Xiongan New Area
通过识别重要生态源地、构建生态源地间生态阻力面、提取关键生态廊道等步骤,新区生态安全格局如图5所示。以西北部旱地和东南部水域为主的生态源地,通过沿建设用地和水系分布、所处地类主要为旱地的生态廊道进行连接,构成了基质、斑块、廊道镶嵌的生态安全格局。区域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满足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实现区域生态平衡的基础生态构架和网络。新区建设伊始,尤其应注意这些关键格局要素的保护和改善,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方针,加强白洋淀区域的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维护并逐步提高现有植被覆盖度,保障重要生态源地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稳定供给;同时,一方面加强生态廊道周边绿化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增加绿道,优化生态廊道网络,增强源地间景观连通性;在开发建设时注意避开生态源地与廊道,避免“摊大饼”式无序扩张,彻底打好新区规划建设的“生态牌”。
3 结论
本文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2方面出发,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土壤保持、固碳释氧和生境维持5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标,以及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土地利用程度3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标,综合供需2方面指标识别重要生态源地,利用夜间灯光强度进行基本阻力面修正,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生态廊道提取,构建出新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
1)新区生态源地总面积约484.33 km2,占新区土地总面积的31.3%,主要分布于新区西北部旱地和东南部水域。
2)新区生态阻力系数空间分布较破碎,大部分区域阻力值较低,间或分布高阻力值,且农村居民点生态阻力高于城镇用地。
3)新区生态廊道总长度185.86 km,呈“Y”字型分布,基本沿建设用地和水系分布,所处地类主要为旱地,避开夜间灯光亮度高的区域,有效连接新区内部源地。
本文在生态源地识别时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弥补以往研究与社会经济系统脱节的不足。然而,本文仍存在以下3方面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予以解决。
1)囿于数据限制,本文仅选取5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以表征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况,对于其他可能存在的服务(如文化服务)考虑不足。
2)本文在生态源地识别和阻力面设定等环节,仅以栅格数据为基础,忽略了空间数据可能存在的尺度效应与区划效应。
3)本文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关键生态廊道,该方法在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但忽略了廊道宽度,而廊道宽度对于物种迁移具有直接影响,如何将廊道宽度纳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及明确最佳宽度应是未来研究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