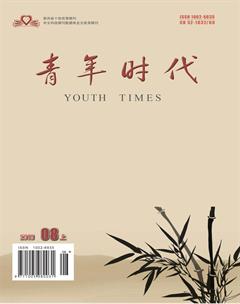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刘悠然
摘 要:在徐克电影中,有一批不可忽视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柔美、或乖张,既反映着导演的女性审美,又更深层次的反映了导演内心的反叛,本文将从徐克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入手,进行深入地探讨和挖掘。
关键词:徐克电影;女性形象;秩序与反秩序
作为香港电影中流砥柱的徐克,以巧妙的政治寓言、出神入化的视觉特技和极富魅力的空间艺术以及诸多类型片风格混用的熟练掌握,创造和带领了香港电影的潮流。香港电影五色斑斓的荧幕形象、自由奔放的内在风格经徐克瑰丽的想象构建起来。他将商业与人文创造性结合起来,从不避讳商业电影,想方设法的迎合受众,但又坚持在每一部电影中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他的电影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古代艺术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在艺术展现与技术制作这两个维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90年代的电影甚至一度被称为“徐克时代”。徐克塑造的荧幕形象中,有一群外表靓丽,内心不羁的女性形象也为这些电影留下了绚丽的亮色。本文便是从这群女性形象入手,探讨导演的女性审美和这种审美背后对社会既有秩序的反叛。
在开始分析这些女性形象之前,首先要明晰中国大陆电影人所谓的“徐克电影”并不是完全由徐克执导的。中国大陆电影人关于“徐克电影”的说法延续着80年代一度对中国电影制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导演中心论”,但这种说法却不大适用于香港的电影工业。我们所称作的“徐克电影”,只有少数是徐克执导的,更多的是由徐克编剧、监制甚至只是参与策划,但这些影片无疑例外的是,它们都带有徐克浓厚的个人色彩。本文所分析的女性形象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一、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在分析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时,很多人会从《刀马旦》的曹云或《青蛇》的小青等女性身上进行进行女权主义分析,认为这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和对男权社会反抗的表现。在女性对自我权利提出要求的时代,不能否认这些影片中角色相对于以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来说是高举女权主义旗帜的,但这和现代人的思维变化有关。在脱离了封建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会让人们的思想有所变化,这是大环境的影响,而就导演自己来说,更大程度上,他可能是没有高举女权主义旗帜这一意图的。反之,他对女性的所有刻画都是基于自身的女性审美的,是一种男性审美。徐克很擅长发现女性的美,这种美并不是某种固定的清纯或性感,而是立体的、多面的、有鲜明性格特色的美。徐克电影里的女人们几乎都是多种性格的综合体,但就她们外形和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来看,可以粗略的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外表雌雄难辨的中性女性形象。这一类形象以《刀马旦》中的曹云和《笑傲江湖Ⅱ:东方不败》中的东方不败为代表,这类形象大多性格坚强并打破了原有的对于性别的刻板成见,使得电影荧幕上的女性形象又有了新的可能性。普遍意义上来讲,由于社会大众对两性之间的定义不同,因而性别塑造上总是会存在有关性别认识的刻板印象,传统电影的女性形象总是符合女性该有的一种或几种特质。盖耶·塔奇曼在《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符号灭绝》中指出,女性被定位为被动、顺从的、享乐型的、被观赏的、被情感支配的性别角色。依赖于男性的社会范围中。而林青霞所塑造的这两个角色刚好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女性气质”,在扮演曹云和东方不败之前,林青霞扮演的多是温柔灵动的少女,如《水云》中的水樵,《烟雨》中的季春霞。徐克发掘了林青霞眉眼之间的英武之气,不仅成功塑造了曹云这个内心坚强的爱国志士,更是力排众议的塑造出了东方不败这个一身江湖豪气的形象。
第二类是清纯善良、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如《倩女幽魂》里的小倩、《青蛇》里的白素贞。这类女性大多有令人迷恋的美貌,有温柔如水的性格,有一个一心所爱之人,可以说最能满足男性审美的一种类型了。但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其他柔美良善,唯愿心系一人的女性形象又是有所不同的,虽是温柔贤淑却又有几分媚态或杀气。小倩初登场时,青丝轻扬,衣袂翩然,看似柔情如水、幽怨哀婉、摄人心神的眼眸中带着隐藏的杀机,明明意在取人性命,却无故给人一种温柔之感,明明是害人的女鬼,却偏偏清秀脱俗、长发飘逸似仙。《青蛇》中的白素贞也是如此,明明是妖媚的白蛇,一颦一笑都带着几分妖劲儿,连走路都似扭非扭,却偏偏又从中透出几分温柔大气之感,有一种让人不敢轻慢的贤淑气质。
第三类是妩媚妖娆、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这类形象在徐克电影中也很多,如《青蛇》里的小青、《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七剑》里的绿珠等。她们同样有美丽的外表,但却魅惑似妖姬,如果说前面温柔的女性是那窗前的白月光,那么这里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就是那心口的朱砂痣。不同于前面温婉似水的女性,这类女性大多如带刺玫瑰,美则美矣,却天生反骨、个性突出。《青蛇》电影甫一开场,白素贞就告诫不愿学人走路的小青要好好学习人类的身形,而小青却反诘: “做人有什么好?”是呀,做人有什么好,不过是跳入一堆世俗的条条框框之中,媚态天成的青蛇自是不愿意学做人的。后来为许仙去求灵芝草,遇到法海,法海要她助他修行,最后却被小青弄得心神大乱时,小青还挑釁说法海输了。面对捉妖的僧人,小青也不觉害怕,只怕在她看来,这样毁灭欲望的修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她不愿意做人、不喜欢修行,天生就对规则这回事情视若无睹,只愿意畅意人生,随心随性。
最后一类是有着反叛精神或开阔眼界的聪慧女性形象,例如《梁祝》中的祝英台、《黄飞鸿》中的十三姨等。这类女性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有追求自由的勇气、向往更为开阔的世界。徐克在《梁祝》中描绘的祝英台,是一个带有明显反叛色彩的形象。未入书院之前,她喜欢爬上房顶看外面的世界,喜欢养蝴蝶,捉来了又放走,喜欢看蝴蝶飞走的样子。不喜欢涂脂抹粉,不喜欢学那些大家闺秀应该学的琴棋书画,也不喜欢把她困在深闺中的大院高墙。《黄飞鸿》中的十三姨,也是如此。她自海外留学归国,一方面倾慕颇有担当的黄飞鸿,成就了一段电影中英雄佳人的故事。另一边,她是黄飞鸿接触和了解广阔世界的媒介,让黄飞鸿了解何谓西学,给这位武学大家增添了一丝置身中西方文化下的矛盾心理,真实又有趣味。
这些类型的女性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在徐克电影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一方面反映着导演对女性的审美态度,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导演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
二、导演的女性审美理想
徐克电影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虽然千差万别,却都反映了导演自己的女性审美理想,总的说来,主要表现在外在的美貌和独特又独立的内在个性两个方面。
首先是外在的美貌。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林林总总,温柔的、妖媚的、英气的、反叛的,人、鬼、妖,她们都无一例外拥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在塑造小倩这个角色时,徐克放弃了前人在塑造角色时中规中矩的服装造型,换了更为飘逸的白裙,为了让角色看起来更有美感,还给小倩在出场时加了一条长飘带。关于小倩的服装造型在后来的采访中,徐克自己也曾经说过,小倩挽在臂间的飘带不仅无用还时常绊倒演员,但为了使角色在呈现时更美,即使不便也要克服。于是,从王祖贤扮演的小倩在兰若寺的窗外惊鸿一现之后,这个荧屏形象就成为了经典,之后再拍的其他版本的小倩,都多多少少从王祖贤这个造型中演变而来。
在塑造东方不败这个人物形象时,金庸曾明确表达过林青霞不适合出演片中的东方不败,徐克导演力排众议,最终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这一角色 。而徐克之所以选中林青霞来饰演东方不败,主要原因便是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和她眉眼之间的英气。为了将这个在原著中着墨较少的角色塑造的更加生动,东方不败的服装造型还融入了和服的特点,这样的服装造型也让东方不败这个角色的整体效果更好。
然后是独特又独立的个性。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或温柔、或灵动、或妩媚、或英气,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例如心心念念想学做人,同凡人闺秀一般温柔贤淑的白素贞;又如英武豪气,一心为国的忠义志士曹云;还有风情万种,快意江湖的金镶玉,渴望成为刀马旦的白妞,向往自由的祝英台……可见站在对女性欣赏的角度上,徐克是很博爱的。
但从这些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察觉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有着独立的思想和追求。即使是温柔似水的白素贞和小倩也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矫揉造作、拖泥带水的小女儿,而是自有一种江湖儿女、爽朗独立的性格。这样一种独立性格的女性形象,并不拘泥于他的武侠电影中,而是在许多电影中都有体现。
三、秩序与反秩序
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导演的女性审美理想,但更值得探讨的是通过这些性格各异的女性,导演还表达出了他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危机感和反叛力。
当1997年逐渐迫近,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在文化表述上呈现为一种充满紧迫感的身份危机。这份强烈而急迫的危机意识与离弃或归属意欲,在处于极盛状态的香港电影工业及其影片中凸现而出,并集中体现在经常为中国内地影人冠以“徐克电影”的多个香港动作片序列之中。置身于这样激变的中国社会之中,一面是渐渐远离的英国殖民主义和香港社会的解殖过程,一面是香港与中国内陆之间存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境线”和香港社会与文化所呈现的自我与异己。
徐克电影以其带有明显的港片烙印的新武侠电影为先河,成为了香港社会文化强有力的继任者。在这之中出现的重拍和改写,如《新龙门客栈》、《梁祝》、《黄飞鸿》等,在向历史、主流、新秩序“致敬”的同时,也将香港社会身份的确认和困境推到前景之中。《梁祝》中的祝英臺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身份的确认和困境。《梁祝》中以过分夸张的表达展现了魏晋时期时文人傅脂粉的病态审美,整个社会都以粉白面色为美,反而使原本的面貌落了下乘。这种过分的容貌修饰已经不再是为审美而存在,而是成为了锁住本心的枷锁,这样的枷锁就好像是锁住当时香港社会文化的不可逆转的大环境。祝英台在影片中的表现则像是坚守着身份,渴望得到身份确认却深陷无力的困境中的香港社会和文化。祝英台是排斥涂脂抹粉的,最终却只能带着满脸脂粉走上花轿,虽然电影的结尾,祝英台在一场大雨中冲刷掉了脸上的脂粉,回归了本来的面貌似乎是得到了身份确认,但下一秒她就落入墓中,化作蝴蝶。这样的结尾与其说是寻找到了所谓的身份认同,还不如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梦。毕竟现实看来,香港社会和文化是不可能为了坚守自我而选择消失的,那么它就会如影片中涂上满脸脂粉的祝英台一样,只能顺从于那个时代,即使这种顺从中既有无奈又有不甘。
不仅是祝英台的整体命运有这样的暗示和隐喻,影片中许多地方都有导演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叛和讽刺。祝英台在接受父亲考察琴棋书画时,曾念过一首诗,是诗经中《月出》,后来到崇绮书院学习时,夫子教的也是这首诗,最后学成归家,在父亲面前写的还是这首诗。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培养中的大家闺秀,这首诗是不符合当时境况的。这首诗原本是写男女爱情的,虽然同电影所讲的故事相合,但却不适合讲学。再有就是祝英台初到学院,老师安排座位时原本让她坐于后排,与梁山伯一同坐,但思索片刻后便问她是坐什么车来的,又问车驾有几匹马,行李几箱,书童几个,住宿何处,膳食如何,待英台一一作答之后,便坐到了前面的位置上。原本书院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却被这样生生添上了几分势力气息。
1997年的到来使得徐克电影中的身份危机和现实意识的部分突然涌现,但想要打入内地市场,他需要继续发展香港电影中娱乐性的一面。这一时期,电影的创作既面临迫切的香港身份的表达,又需要充分的秩序认同表述。徐克早年表示,“电影是大众媒介,群众是用感觉看电影,不是用脑袋分析电影。”这样的妥协在电影中的表达则可以体现为不涉及“皇权正统”江湖背景,讲的都是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而体现在女性形象上,《七剑》中风火连城的宠姬绿珠虽有反抗之心,却依然匍匐于风火连城的脚下;《青蛇》里的白素贞在学做人的路上渐行渐远;《梁祝》里的祝英台即使以身赴死,也不能避过穿上嫁衣、满面脂粉的走入花轿。这些女性形象无论最终如何,都会有违背本心、本性的妥协。
徐克电影中庞大的女性群像,不仅刻画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荧幕形象,反映了导演的审美理想,更是一种秩序与反秩序博弈的结果。这样的女性群像,是在任何导演手中都看不到的,也可以说是徐克电影中独特又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若要概况,可以形容为:“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同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一样,电影中的女性也是夸张、瑰丽又癫狂。
参考文献:
[1]肖雅,走向极致的绚烂——浅议徐克电影的女性群像与情爱观,电影评介,2008年,第11期.
[2][美]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
[3]戴锦华,沙漏之痕——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
[4]盖耶·塔奇曼.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的符号灭绝//[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英]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5]戴延青,打破刻板:电影《刀马旦》中女性形象分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