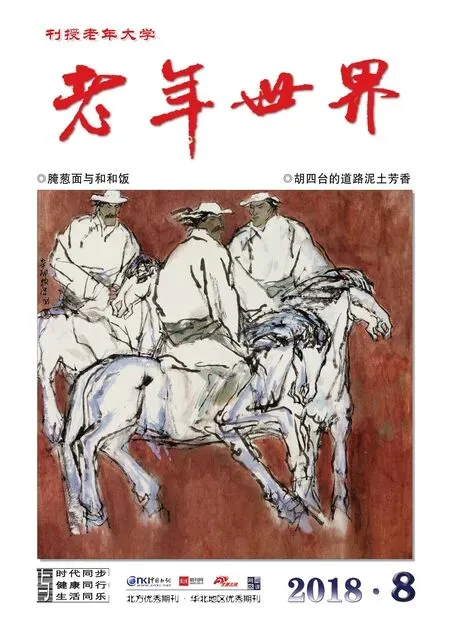延安忆往
云照光
民族学院
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非常紧张,边区财政经济也更加困难。在这个时候,党付出人力物力,把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的包括7个民族的数百名学生合编在一起,成立了陕公附属的民族部。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清泉旁边的岩石下上课,学员不断地增加着。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更加具体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各民族抗战和建国的骨干,中央作出了使人无比兴奋的决定:成立各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民族学院。这个消息,很快在教职学员中传开了,大家的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1941年9月18日,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好日子,就在这一天,各民族子弟向往的民族学院正式诞生了。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首长送来了贺词,祝贺这所新的学府的诞生。兄弟学校也派来了代表,送来贺信、贺词,和我们共同欢度这个快乐的日子。成立一所真正的、各民族人民的学院,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是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头号大喜事,谁能不尽情地欢庆呢?我们由五十五队变成民族部,又变成了民族学院,是由小到大、突飞猛进地发展着。除了各民族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党,是绝对办不到的。况且,那时是在抗日战争紧张的年头,是在艰苦困难的环境里,不惜用最大的努力,修建校舍,添置教学设备,配备坚强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使各民族的子弟们团聚在一起,在温暖的大家庭里学习、生活,这确实是伟大的创举。我们都以无可比拟的感激心情,来欢庆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各民族的代表,不断拥到主席台,向中央、向学院首长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决心。到处敲锣打鼓扭秧歌,到处张贴标语和墙报。晚间举行了庆祝晚会,各族青年演唱了自己民族的歌曲,演出了自己编排的话剧和秧歌剧。就在这一天,我们全校数百人,用激昂而又洪亮的声音,第一次唱出了我们的院歌:

民族学院旧址(资料图)
我们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孙,
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
汉、满、蒙、回、藏、苗、彝,
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各民族学习的伙伴,
明天是革命战斗的先锋。
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
高举起民族革命旗帜,
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
庆祝晚会一直进行到深夜结束,但大家激动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学院,在延安文化中心的文化沟,和西北文艺工作团、西北青年剧院、文化俱乐部是邻居。北边翻过山就是中央党校,对面是规模庞大的中央图书馆。南边有能容纳近2000人的八路军大礼堂,医疗上有比较正规的八路军医院,沟口有当时延安最大的运动场。往前走,就到了清澈似镜的延河边。四面的山头上,长满野草,还有一片片红红绿绿的酸枣林,真是一个优美而又热闹的环境。来自四面八方的7个民族的青年,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紧张地学习着。院长由中央负责同志兼任,云泽(乌兰夫)同志是学院的教育处长。我们的课程有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时事政策、政治理论、生理卫生、新文字以及不定期的民族问题的报告。最使人感动的是,虽然延安条件很差,但是党尽量设法从别的机关、从前方调来一些教员,担任各民族的文字教学工作。因为苗族没有文字,西北局还专门组织研创苗文。为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为回族学生另立了食堂,每逢吃肉,都要由阿訇亲自屠宰。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还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供回族学生做礼拜,使伊斯兰教信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学习着。少数民族学生的身体健壮,按一般伙食标准不够吃,边区政府特意每月多拨粮食,作为补助。图书馆、体育场、俱乐部、课堂等各方面的设备,也比别的学校好。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

1942年秋天,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这是一个东方各族人民团结的大会、战斗的大会。几十个民族的代表,都聚集一堂,一致声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在会上听到了各被压迫民族的血泪控诉,也听到了各民族反抗侵略者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使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这个大会,增强了我们争取胜利的信心。大会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也来了。正当蒙古族代表的讲话刚结束,突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我坐在过道的旁边,也跟着大家站起来,随着大家的眼光向后看去。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已经匆匆地从我的旁边走过去。我喜出望外,把头伸过去,用尽所有的力气鼓掌。这时,毛主席已经走上主席台了,接着就开始了讲话,声音是那样清脆洪亮。毛主席号召各民族亲密团结起来,打倒一切法西斯侵略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发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运动。毛主席的讲话,给了我们更大的温暖和鼓舞。
通过系统的学习,经过几次政治运动,我们在政治上大大地进步了,各民族的大批优秀青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大批的同学毕业了。有的到敌占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大部分到了抗日的最前线,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在和敌人的斗争中,体现了忠于党、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像关起义、朱玉珊、赵青山、云晨光、图布新、云贵生、巴增秀、李世昌、金玉、杨秀清、秦子华、雷明利等许多优秀的党员,就是在艰苦的战斗中牺牲的,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的同学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有的成了模范和英雄。各族青年,没有辜负党和母校的希望,投身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忠心耿耿地尽了自己的责任。
母校啊,你培养了多少少数民族的干部!你把我们从无知引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你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无限的智慧和革命斗争的知识,你教给了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这伟大的功绩,归功于党,归功于我们敬爱的母校。母校,你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烧木炭
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都住在窑洞里。人们都说窑洞是冬暖夏凉的神仙洞。不过到了冬天,也并不见得暖和,因为没有像样的行李,床上只铺着几块薄门板,洞里又潮又湿,还是怪冷的。过冬怎么办呢?买炭,一个钱也没有,做饭还是同学们上山打回来的木柴。就是有了炭,也很难找到一个火炉子。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到深山里烧木炭。陕北有许多原始森林,只要出劳动力,不用花几个钱,就能烧出木炭来。况且,这木炭实在是宝贝,它既不用火炉,也不冒烟,只要在地下围几块土坯,见火就着,一夜都不熄灭。1940年冬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去山里烧木炭。当时因为我年龄太小,做了“火头军”的助手,担水烧火。1943年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了,好几千人的过冬问题,是个大事情,学校首长和校党总支把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支已经经过烧炭考验的生产大军。出发前,周扬副校长、宋侃夫总支书记给我们做了动员。
从桥儿沟出发,走了20多里地,就拐进一个小沟。走不多远,就看见满山满沟一片绿,到处是原始森林,山沟、山坡到处都是野花、野草,还有许多野生果树。我们的生产地点是瓦房,其实并没有几片瓦。养蜂的人家倒挺多,都住在窑洞里。因为我们都是烧木炭的老手,用不着什么训练,第二天就动手劳动了。
出发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这次再不干“火头军”了。但事与愿违,生产队长偏偏分配我当“火头军”,有什么办法?只好接受了。我和队部住在一间快要倒塌了的窑洞里,每天收工回来,我就磨蹭,要求干点别样的事。可能是让我说得有点心软了,不久,队部决定把我正式升为烧木炭工人。但重要的活还是不让我干,我只好满山跑,割苧条,捆木炭包。我们的小组长是彝族同志,是个大胖子,我们小组5个人经常在一起,分开就很危险,因为不时会碰到豹子、碰到成群的野猪和各种可怕的野兽。
腰粗的大树,被我们几斧子就砍倒了,再锯成好几节,粗细搭配开,放到一个土窑洞里,用土埋上,只留一个通风孔和烟筒。说起来,烧木炭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道工序都有技术。白天黑夜都要留神放哨,稍不注意,一窑炭就化成灰了。只要看到烟筒冒青烟,就堵好通风孔,过几天取出来,木头已经变成木炭了。取木炭的时候,因为是高温,脱光衣服进去一分钟就满头大汗,呼吸都很困难。我们有几个得了感冒的人,进去取了一趟木炭,病也给治好了。砍大树的人都是彪形大汉,分布在四处的山上。你站在沟底听吧,这里哼嗨,那里哈呀,有的唱着,有的叫喊着,手起斧落,噼啪乱响,大树嚓的一声便倒下来了。你看吧,砍树手站在那里,满头大汗,满手血泡,掏出毛巾,擦上几把汗,又开始征服第二棵大树了。一直把一片树林砍成光秃子,这一窑木炭的材料才算准备完了。
劳动虽然累,但那是快乐的累。收工回来,大家蹦蹦跳跳,有的还赶着排剧。不久,一垛一垛的木炭就用骡子、毛驴、大车运回学校了。
有一天正要开饭,队长王铎同志拿出一封学校给我们的慰问信,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张。当他念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但是谁也没有鼓掌,有几个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刘金(云世英)同志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用什么行动来报答这种关怀?请队长转告全校党员,告诉全校师生,我们一定要超额完成任务,保证全校过冬!”谁能不同意呢!学校不但在慰问信的字里行间表现了阶级的爱、同志的关怀,还用全校党员缴纳的党费,给我们买了5只羊,随慰问信一起送来了。要知道,那时一个党员能交多少党费呢?有的同志尽量节省,只能交几分钱。是的,这是党、这是全校对我们的慰问和支援,我们不但要保证胜利而归,而且要用劳动的热情,投入到整风学习中去,投入到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去。
学习武装了我们这些少数民族青年的头脑,劳动锻炼了我们这些少数民族青年的意志。我们不仅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了阶级斗争的知识,也学习了生产斗争的知识。我们在党的直接关怀、教育下,一天天成长起来。
延安是我再生的第二故乡,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有多少事情值得我们回忆和怀念啊!延安,当我忆起往事,又看到现在,怎么能不感激你,怎么能不向往你!啊,延安,我多么想再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现在的千变万化呀!
选自《延水情深》
云照光,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9年10月出生,1939年7月参加革命,1945年5月入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9月转业,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文教委副书记、副主任。“文革”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宣传部副部长、党委顾问、文明办副主任,自治区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文联名誉主席、关工委副主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著有《云照光电影剧本集》《云照光文集》《云照光摄影集》等,主持编辑了《土默特文化》《圣地之魂》《一代英豪》丛书。现任延安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内蒙古校友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内蒙古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2003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