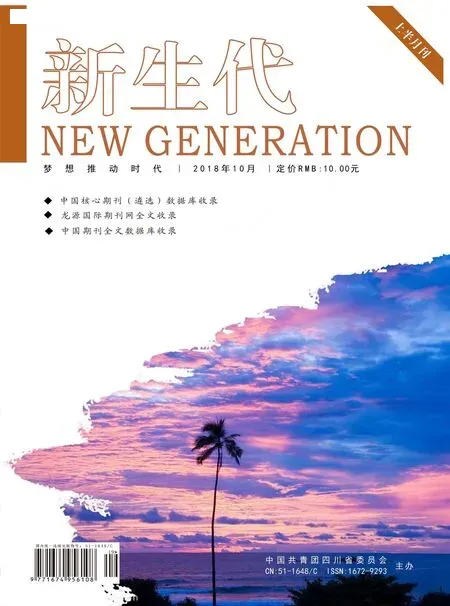绑架罪“情节较轻”的阶段性认定分析
陈恺雯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 310018
一、“情节较轻”设定的背景释义
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高级检索功能,笔者在其网站上一共收集2016—2018年3年内(截止至4月止)“判决结果”中有绑架罪的607起案件,其中被判无期徒刑的一共只有9起,被判死刑的一共只有4起,属于绑架罪“情节较轻”而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323起(如图1)。由此可见,绑架罪不再是过去那种手段严重、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处罚较重的恶性刑事犯罪,而逐渐转变成手段轻微、情节较轻、性质轻微、处罚较轻的“非典型”刑事犯罪。此时若是对该种“非典型”的绑架行为一律按照基本刑来定罪处罚,不仅会严重违背公众淳朴的法律价值情感,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法律的公信力,破坏公众所坚信的法律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正是为了适应绑架罪这种变化,给实施绑架行为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人提供一个减轻处罚的期契机,更是为了实现罪行均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为此增加了“情节较轻”的规定。
二、“情节较轻”的司法乱象管窥
本文通过搜索权威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3年来发布的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裁判文书,试图归纳出司法实践中影响“情节较轻”认定的相关因素。笔者随机抽取了全国各个省份地区和不同层级的法院裁判文书一共80件,以达到文书选取的全面覆盖和公正性。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并达到对比的效果,一共80个样本中,设置实验组即绑架罪“情节较轻”的一共40个判决书,对照组为“一般情节”的绑架案件一共40个判决书。
法律和司法解释至今都没有对绑架罪“情节较轻”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标准,导致了实践中对于其认定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地域和层级上的较大差异。据统计,一共80个案件中,对于情节较轻进行具体的阐明说理的案件只有34个,其中包含了“情节较轻”案件中法官认为适用“情节较轻”的理由,以及“一般情节”的案件中法官认为排除适用“情节较轻”的理由。部分抽样的案件判决理由如下表1所示。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较少法官在适用“情节较轻”时进行阐明说理,说理程度也深浅不一,甚至有些法院在最终认定案件为“情节较轻”时,并没有给出任何依据和理由。

部分抽样案件判决理由一览表(表1)

其次,对于同一个案件,也存在着上下级法院对“情节较轻”认定不一的情况。例如,2017年江苏镇江的孙林绑架案件中,一审法院认定其符合绑架罪的一般情节,但是由于其犯罪行为因为意志以外的因素没有得逞,因而认定其为犯罪未遂且有坦白情节,最终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但二审法院综合考量了本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为孙林属于绑架罪的“情节较轻”,最终将刑罚改为二年三个月有期徒刑。由此可见,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较轻”的认定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和界限,司法人员对于案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着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的司法乱象。
三、新思维构建——对绑架罪“情节较轻”进行阶段性的认定分析
学界将绑架罪主要分为“人质型”和“勒赎型”两种类型,“人质型”绑架主要是指以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从而达到其非财产性的目的,而“勒赎型”绑架主要是为了勒索财物而进行的绑架他人的行为。在整理案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人质型”绑架案件的数量较少,大多是由于婚姻、情感、财产继承分割等问题所引起的纠纷,因而不具有典型性,所以笔者主要针对“勒赎型”绑架案件进行类型化的研究分析。
经过研究分析可知,“勒赎型”绑架案件在其行为的行进过程中,较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因而笔者将其按照行为发生的先后分为掳掠人质、控制人质、勒索赎金、处置人质四个阶段。通过对其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提炼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所具有的特征因素。
(一)掳掠人质阶段
第一阶段是掳掠人质阶段,其所体现的是绑架罪行为的“抽象危险”,该阶段所使用的手段、体现的暴力程度,都影响着“情节较轻”的认定。
根据掳掠人质所使用的手段不同,手段所包含的暴力程度不同,具体可以将掳掠人质的手段分为暴力手段,使用暴力手段相威胁,以及非暴力手段三种情况,分别编号为ABC。使用暴力手段掳掠人质主要是指持刀枪胁迫,持棍棒殴打,徒手殴打,下迷药迷倒等情形;使用暴力相威胁,主要是指以手持棍棒、刀枪等暴力工具对人质进行威胁、展示,以致人质内心感到恐惧和不安,从而掳掠人质;非暴力手段是指,不使用任何犯罪工具而将人质强行带至某地点,或者未使用暴力将其强行控制在某地点,诸如诱骗、哄骗被害人到指定地点,被害人事后才发觉自己被绑架的情形;或者直接将人质徒手、非暴力地进行控制。根据统计分析(下表2),“情节较轻”的40个案例中,使用暴力手段的有5件,仅占13.2%,使用暴力相威胁的有7件,剩下的都是未使用暴力的。而“一般情节”的40个案件中,使用暴力的有9件,占总体案件的22.5%,明显多于“情节较轻”中使用暴力的数量。由此可见,“情节较轻”的案例中,绑匪通常使用诱骗,拐骗等非暴力手段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掳掠人质。而在“一般情节”的绑架案件中,绑匪通常使用暴力手段掳掠人质,手段的暴力程度也更高。

掳掠人质的手段情况一览表(表2)
(二)控制人质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控制人质,其中控制人质所使用的手段,控制人质的地点、空间范围、时间长短等等都会影响案件“情节较轻”的认定。为了和上文“掳掠人质的手段方式”的研究保持一致性,笔者主要对控制人质手段方式进行研究。
根据行为程度的由轻到重,具体可以将控制人质的手段方式分为“随时加害式”“捆绑式”“关押式”和“软禁式”四种。“随时加害式”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控制人质,如殴打人质,拿枪或持刀威胁人质使其不敢反抗和逃跑,因其恶劣程度超过了绑架罪中基本的捆绑行为,而更加严重。该种方式暴力程度最高,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最高,人质面临的危险也更具有现实紧迫性。其次是“捆绑式”,该种方式是绑架案件中最常见的、也是较为严重的一种控制人质的方式。实践中,大多数绑匪都会采用捆绑住人质双脚、蒙住嘴巴和眼睛,人质基本上没有身体活动的自由而极具组织损坏或者残疾、窒息而死的危险。再次是“关押式”,相较于“捆绑式”,其暴力程度较低,人质并没有受到直接的身体束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自由。程度最轻的就是“软禁式”,该种方式主要是指人质被限制在较大的、可以活动的空间内,手脚基本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离开控制的范围。该种方式虽然侵害了人质的人身自由,但是较少给其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施加身体上的束缚,因而也时常会出现人质被绑架但不自知的情形。其给人质带来的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痛苦都是最小的。将该四种方式由轻到重编号为abcd,如下表3所示。比较“情节较轻”和“一般情节”的案件,最主要的区别有以下两点:一,“情节较轻”的案件中,属于“软禁式”的数量多于“一般情节”中同类案件的数量。二,“一般情节”的案件中,属于“捆绑式”的数量多于“情节较轻”的同类案件的数量。由此可见,行为人对于人质的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越低,控制人质所使用的手段暴力中程度越低,人质面临的现实危险性越小,越容易被认定为“情节较轻”。

控制人质的手段情况一览表(表3)
(三)勒索赎金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勒索赎金。财产法益作为绑架罪复杂客体之一,虽然不如人身法益那样重要,但是也会对案件“情节较轻”的认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该阶段主要考虑勒索赎金的数额以及是否勒索到赎金。勒索赎金的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是否勒索到赎金则更为客观从被害人角度反映了其财产损失。借鉴司法实践中参照敲诈勒索罪数额标准的做法,笔者也大致将绑匪勒索赎金的数额进行大致三个等级的划分,分别是1万元以内(包含1万元),1—100万元,100万以上(包含100万元)三个等级。
从表4中可得“情节较轻”的案件中,有一部分案件勒索的赎金数额在1万元以内;而“一般情节”的案件中,绑匪勒索的数额没有小于1万元的,而是大部分集中在1—100万元,甚至有35%的案件勒索的赎金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可见,“情节较轻”的案件中,绑匪勒索赎金的数额明显少于“一般情节”同类案件的数额。另外表5显示,“情节较轻”的案件中,勒赎成功的较少,即大多数没有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造成财产损失较少;而“一般情节”的案件中,勒赎成功的则较多,更大概率地造成了被害人不同程度上的财产损失。综合以上两个因素来看,绑匪所欲勒索的赎金数额越小,其主观恶性越低;勒索到的数额越少,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越小,越容易被认定为绑架罪“情节较轻”。

勒索赎金的数额情况一览表(表4)

是否勒赎成功情况一览表(表5)
最后一个阶段是处置人质,“勒赎型”绑架案件中,绑匪在勒赎之后,会处置人质。人质主要有两种后果,一种是仍然存活,另一种是已经死亡。“情节较轻”和“一般情节”的所有绑架案件中,所有人质最终都得以存活。因而“人质是否存活”这样粗略的统计不能反映两种情节中绑匪处置人质方式的差异,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被害人的伤残情况和绑匪处置人质的具体情况。
根据人质伤残情况的不同,将其由重到轻分为重伤、轻伤、轻微伤和没有造成伤害。处置人质的方式则是指绑匪是否是主动释放人质。如表6所示,“情节较轻”的案件中人质轻伤以上(包含轻伤)的案件只有1件,重伤等较为严重后果的案件则为0。而“一般情节”的案件中,人质轻伤以上案件的数量就明显多于“情节较轻”同类案件的数量。由此可见,“一般情节”的绑架案件中绑匪对人质造成的身体伤害一般重于“情节较轻”的案件。造成人质轻伤以下伤害的,更符合“情节较轻”的认定。最后,笔者将“是否主动释放人质”这一要素具体分为绑匪主动释放人质,人质自己逃走,绑匪经他人劝解而释放人质,人质被公安民警等他人解救这四种情况。如表7所示,“情节较轻”的案件中,绑匪出于被劝解或者主动释放人质的较多;而“一般情节”的案件中,大多数情况的人质都是经由公安、民警或者群众等他人解救,并非绑匪经劝解或者主动释放。由此可推断,绑匪控制人质之后主动释放人质,也影响着“情节较轻”的认定。

人质的伤残情况一览表(表6)

处置人质的具体情况一览表(表7)
四、结语
绑架罪“情节较轻”条款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学界对其认定的讨论从未间断,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明,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认定不一、标准不明、界限模糊的乱象。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现状,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合理化解“情节较轻”的理论纷争,避免司法误区和实践尴尬,也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笔者借助司法一线数据,通过犯罪类型化的思考和行为阶段性的分析,为其认定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路径,以期解决此种司法乱象,从而更好地追求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实质,实现法律公正化、统一化、平衡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