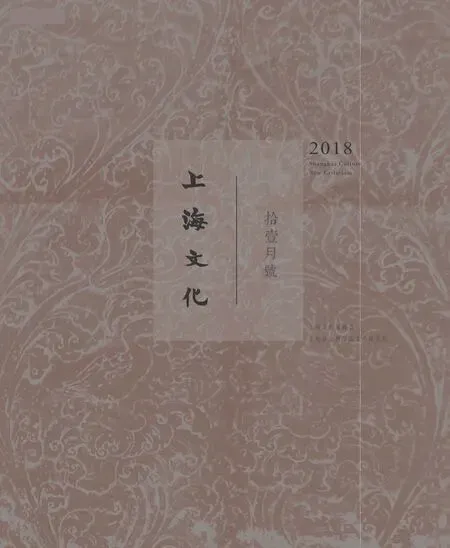他们的期限只是一个短暂的日子①戈麦的诗及改稿
何炯炯
1
从中我们将看到一首诗是如何在艰苦的劳作中逐渐锻造成形的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戈麦是到过南方的。1991年1月,他去上海拜访施蛰存先生,我猜想所谈内容大概关于小说创作。随后,戈麦在2月连续创作了几篇小说,如《地铁车站》、《猛犸》、《游戏》,以及《伪证》、《原生水的镜面》、《一个不睡的下午》等。其实,戈麦对于小说创作早有热情。中学时代,他喜欢阅读武侠、欧美侦探小说。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他写了一篇先锋作家残雪的毕业论文。毕业后,他去了《中国文学》杂志工作,编选过《鲁迅小说选》、《扎西达娃小说选》等书,采访施蛰存、艾芜,写了许多篇评论作家与小说的文章。一个作为小说创作者的戈麦,常常为人所忽略。这也映照着一种事实:在中国,极少有诗人会在小说领域开展自己的努力。
从上海回来后,南方的感觉一直存留在戈麦的记忆里。他在《戈麦自述》中写道:“戈麦寓于北京,喜欢南方的都市生活,他觉得在那些曲折回旋的小巷深处,在那些雨水从街面上流到室内、从屋顶上漏至铺上的诡秘生活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绝而又绝的故事。”“南方的都市生活”大概是指他曾到访的上海,而这些南方的生活的情状:小巷、雨水、街面、倒灌进水的室内,漏雨的屋顶、诡秘的生活,让他的思绪与想象飘到了很远的地方。1991年2月3日,戈麦连续写了三首关于“南方”的诗:《眺望南方(一)》、《南方(一)》、《南方的耳朵(一)》。十天后,他又将这些诗集中修改,分别标示以《眺望南方(二)》、《南方(二)》、《南方的耳朵(二)》。这是《戈麦诗全编》里仅有的六首以“南方”为题的诗。也正是从这些诗开始,戈麦晚期的创作中,“一题二稿”的现象频繁出现。西渡是最先觉察到这种创作现象的,他将它视为“与传统的写作方法迥然相异的一种写作方式”,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将看到一首诗是如何在艰苦的劳作中逐渐锻造成形的。它将使我们对写作中灵感、情感、节奏、词语的作用产生全新的认识……它把写作的秘密与劳动联系起来,而把一首诗的生成奇迹背后的东西揭示给读者(《戈麦诗全编·编后记》)。
我对上述几首诗的关注,也是源自于“诗与改稿”的思考。我曾在新诗课上听老师讲过林庚那首《破晓》及其修改过程,深知诗人喊出那句“如人间的第一次诞生”的不易。诚如西渡所言,在诗与改稿之间,批评者能够发现劳作的痕迹,而写作的秘密也会自足地呈现出来。本文余下部分,我将以《眺望南方(两首)》为例,去观察戈麦如何创作一首诗,又如何将它修改。并且尝试着去探寻诗歌创作过程中,那些隐秘的部分。
在诗与改稿之间,批评者能够发现劳作的痕迹,而写作的秘密也会自足地呈现出来
2
初读《眺望南方(一)》,使我回想起翻看世界地图册的情形。为了准备升学考试,我们必须记住一长串地理名词,以及这些地名所联结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诸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斯堪的纳维亚、阿巴拉契亚山脉……因而,当诗中出现巴西高原、潘帕斯草原、巴塔哥尼亚高原时,我立刻想到了如同火腿般的南美洲地形。
“我在这巴西的高原,高原的南端”,这个故意被拖长的句子,造成了身临其境的效果。“我”好像一位现场的播报员,带着话筒缓慢地移向最南端,描述所在的位置以及眼前的情况。而眼前的情状,被一些极富方向感、线条化的语言所切割:“天宇被东和西的两岬云峦/从宽阔的北方挤得越来越窄”。
紧接着,诗人转向一种更为亲密的语调,诉说着“我”所看到的一切。这种诉说的语调,被介词“在”(非个人化的表述策略)所引导,低缓而又克制。潘帕斯草原、巴塔哥尼亚,这些诗人从未到达的、陌生的地理,以一种拟人化的,无比亲切的形象出现。
在那曙光微冷的气色中
潘帕斯草原
你的茂盛有一种灰冷的味道
在这两块大洋,它佛手一样的浪花
拍击之下
你像高原上流淌下的铁
两三只高瘦的灰马
在天空映照下
使草原变得更加辽旷
在这里,出现了戈麦后期诗歌常用方法,即对象的描述多用“复合感觉”。使用“复合感觉”,有助于诗人缩减诗句,增加感觉层次,扩大联想的驰骋功能。如此诗中的兼有“茂盛”与“灰冷”的潘帕斯草原,“佛手一样的浪花”的拍击。而那句“你像高原上流淌下来的铁”,在整体感觉氛围中,显得很突兀。在第二稿中,戈麦自觉地将它删除。我反而欣赏这一句,它有一种流动感:从火热的铁,逐渐化为物质的铁的状态。这是戈麦天才的地方,他觉得光用“复合状态”还不够,还努力呈现一种感觉流动到另一种感觉的过程。
随后,诗人将视线眺望到更远的南方:巴塔哥尼亚,赋予它“冷陌”的气质。这并非是指人情世故或者情绪上的冷淡、不关切。戈麦把文字带到了最初的起点,去除掉经年累月的抽象内涵。博尔赫斯在《诗艺·诗与思潮》中提到,“我们发现文字并不是经由抽象的思考而诞生,而是经由具体的事物而生的……我们或许会说诗歌并不是像斯蒂文斯所说的那样——诗歌并没有尝试把几个有逻辑意义的符号摆在一起,然后再赋予这些词汇魔力,相反的,诗歌把文字带回了最初始的起源。”“冷陌”,回到了最初“冰冷、陌生、无人到达”这些鲜活的涵义,直接刺激着我们的感觉。假如我们足够留心的话,这种寒冷的感觉一直流淌在诗中,从“曙光微冷的气色”,“你的茂盛有一种灰冷的味道”,“瘦长的灰马”,到“冷陌的高原”,凛冽的大海,变成了一个名词“西风”。这种逐渐加剧的寒冷的感觉,与介词“在”一道,形成了某种低气压,压抑着读者的情绪,侵入我们的皮肤,这与“南方”这个词汇带给我们温暖的感觉,完全相反。
当叙述者带着誓言般的语调,带领我们走进遥远的海崖——巴塔哥尼亚,我们会被某种升腾为永恒的特质打动。
巴塔哥尼亚
我要走到你遥远的海涯
走到一些冻土上蓝色的植物
像大海抛在岸边的星星
旷古的寒冷拍打着岸上的足迹
哦,我的巴塔哥尼亚
“冻土”,意味着极致寒冷的凝固,生命的消逝,成了高原的风貌。“冻土上天蓝色的植物”,它们在诗人心灵中轻飘飘地升起,带着某种令人惊叹的圆满与完整。在最寒冷的冻土层,一切生命消逝的地方,还盛开着天蓝色的植物。这也是戈麦天才的地方,他灵巧地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令人惊叹的还不止这些,诗人还有一种能力。他将“天蓝色的植物”比喻成更为基本的东西:“大海抛在岸边的星星”。“星星”、“旷古的海风”,这些最本质的事物,遥远而又恒久,占据了整首诗的末尾。这些意象又将我们的视野回到更为广阔的夜空。最终,在持续的抒情与咏叹中,“我”凝结为一个动人的形象:一个眺望星空的人。
将“无数颗陨落的星星”隐喻为人类历史长河中逝去的那些耀眼的先辈,这恐怕是最为直接的联想,也是一种基本常识。戈麦曾经罗列过一份大师的名单:“戈麦尊敬历史上许多位文学大师,如诗人雨果、庞德,更早的有荷马和英国玄学派诗人,在当代诗人中,他愿意读曼杰施塔姆和埃利蒂斯。戈麦有时沉溺在传统小说那种漫长的阅读过程中,尤为愿读福楼拜和麦尔维尔。在当代小说家中,他对克劳德·西蒙和米兰·昆德拉经常反复阅读。”他还欣赏叔本华的哲学,给梵·高、塞林格写过诗,也给博尔赫斯写过纪念长文。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阅读者而言,上述提及的名字只不过是他所阅读的九牛一毫。因而,“眺望南方”,这样一个具体的动作,就有了更抽象意义上的指涉:一种获取先辈们的所有成就,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眺望南方”,这样一个具体的动作,就有了更抽象意义上的指涉:一种获取先辈们的所有成就,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3
《眺望南方(一)》提及的这些地理:潘帕斯草原、巴塔哥尼亚,以及遥望星空的具体动作,隐约地指向一位阿根廷籍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他的小说与诗歌创作同样非凡)。
修改三首关于“南方”的诗歌的前一天,也即1991年2月12日,戈麦借用让·保罗·萨特自叙传的题目,写了一篇纪念博尔赫斯的长文:《文字生涯》。文章中,他自述曾经过着一段“无死无生的日子”,对未来“这样一种文字生涯有些惶惑”。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人的拯救。这个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的贡献主要在语言上,语言的革新导致了情节的扑朔迷离和人物的生死轮回,导致了对世界本质的暗示、追问,导致了在一种灰濛的色调中蕴含着的血红色的激情
博尔赫斯的诗有一种很清楚的质感,这种质感是柔软但却成形的,能够铺张,也可凝缩,调子是灰色的,正适合于启发生命中的神秘
说起博尔赫斯,他对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很大。但戈麦理解的博尔赫斯与先锋派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的贡献主要在语言上,语言的革新导致了情节的扑朔迷离和人物的生死轮回,导致了对世界本质的暗示、追问,导致了在一种灰濛的色调中蕴含着的血红色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低缓的,不明朗的,犹如地下的河流,火的河流。”这个看法,也在其他人身上得到印证。譬如,翁贝托·艾柯在《拉曼查与巴别之间》一文中提到:“我们不妨将博尔赫斯定位到当代的实验主义。根据许多人的看法,这种主义的核心精神便是文学对自己的语言提出疑问,也就是说对象是普通日常语言,并且将其一直分割到终极的词根为止……博尔赫斯使得自己以书写的语文活泼起来,并且更新它”。但他不像乔伊斯那样拆解、组合语言,博尔赫斯“不会让作品的扉页变成一场杀戮。”博尔赫斯对于古奥的英文作品《贝奥武甫》的细读,对于词源学的热忱,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由此可见,戈麦对于诗的观念,尖锐而又直刺靶心:诗是语言的冒险。“我崇拜那些在语言的悬崖上重又给世人指划出路的人……人只有接受先辈们所有的语言实验的成就,才能继续走下去,才能引出反对和破坏。”他似乎在晚年失明一只眼睛的萨特、全盲的博尔赫斯,以及发出洪亮嗓音的人类第一诗人荷马之间,找到某种更深远的共通性:丧失掉手中的笔,只靠依靠语言(日常的话语),继续着他们的创作。
4
上述背景的交待,有助于理解戈麦的改稿。
《眺望南方(二)》延续着地理的叙述策略。原先那个眺望的位置被移除了,代替它的是“古堡的砖垛”。古堡,大多建筑在山崖、河岸,古老而坚固。相比于辽旷的巴西高原,古堡内在的封闭性特质是显而易见的。砖垛,又赋予这个古堡废墟的气质,杂乱而荒芜。假如我们反观自身的文化处境,似乎与“古堡的砖垛”这个隐喻非常吻合。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期,我们的心灵时刻遭遇着国外的文化冲刷。不论是生活方式、电子产品,还是流行歌曲、电影、小说、诗歌等,将这个封闭的古堡冲塌了,碎瓦陈砖满地荒芜。因而,“眺望南方”,又似乎多了文化沟通的指涉。原先那种带有方向感的语言,被切割出来的眺望视野,也都被统统省略掉了。眺望南方,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规定性的视野(东、西与北方,都去除掉了),意味着一种单一的行动,意味着“我”站在“古堡的砖垛”上,只朝着南方眺望。这让我想到雷平阳诗里的澜沧江,那条一意向南的流水。
关于潘帕斯草原,戈麦删除了那句突兀的表述:“你像高原上流淌下来的铁”。他意识到,“灰马”是更好的意象,去包裹那种低缓的、不明朗的血红色激情。戈麦清楚地说过他对博尔赫斯的诗的感觉:“博尔赫斯的诗有一种很清楚的质感,这种质感是柔软但却成形的,能够铺张,也可凝缩,调子是灰色的,正适合于启发生命中的神秘。”这种诗的质感与“灰马”更为贴近。此外,“灰马”,带有某种宗教的色彩,更像是来自《圣经·启示录》里的神谕。令人联想到耶稣揭开第四封印时,“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博尔赫斯在《讨论集·序言》说过:“我的生活缺乏生命和死亡”。不论是他的小说还是诗,频繁出现衰老与死亡。我们以戈麦翻译的十首博尔赫斯的译诗为例,死亡的命题反复出现:“棋手同样也是一名囚犯/属于死亡的黑夜和白昼”(《象棋》);老诗人的墓志铭(《给一个老诗人》);战场上的铁沦为锈土,而上尉(我们也将会)变成灰尘(《一个克伦威尔军上尉的画像》);“又老又瞎的海上冒险家吃力地走在/英吉利乡间布满泥块的路上”(《盲会众》);“死亡忍耐着/潜伏在来福枪里”(《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之死》)。对于任何一位长久而耐心的读者而言,在阅读中频繁经历衰老与死亡,涌现着带血的激情,丰富了我们对生命的感觉。
随后,诗人提到“巴塔哥尼亚”的时候,两次并列地使用了“面朝”这个词汇。想必我们都能熟背海子的那首名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的末尾,对陌生人三次真挚祝福后,而那个倔强“我”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戈麦笔下的“巴塔哥尼亚”,也有这种倔强的品质,它执意地、主动地保持这样的姿势:“面朝凛冽的大海,面朝西风”。凛冽,则更为直接地侵入皮肤,有着刺骨般的寒冷。对于欧洲而言,西风是温暖、和煦的。即便是雪莱的《西风颂》,狂野、威猛的西风仍旧吹醒大地,预示着新的生命。而在我们的语境里,西风一贯是肃杀的。单从几行古诗词,就能体察到它的冷冽,“帘卷西风”(李清照)、“昨夜西风凋碧树”(晏殊)。在戈麦诗中,西风,同样是能量感很强的名词,似乎有了雪莱诗里的某种激昂的情绪。它无形的能量,塑造了“剑鞘一样的海岬”。
《眺望南方(二)》,最明显的变化是全诗被分成了三段。“巴塔哥尼亚”独立成段,被赋予一种咏叹调式的抒情。我们会被叙述者起伏的视点牵引着,陶醉在整段的咏叹中。戈麦和他的诗,从不是外放的。桑克说过:“他是理性的。他操作诗歌——复杂的机器。他用暴力——节制性地无痕迹地将作品中的每一样元素安排得如此妥帖。每一个汉字都在它们应有的位置。”对于戈麦而言,抒情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待诗,理性而节奏,他会用“坚硬的语言”包裹住内心的抒情。因而,这种松弛,这种绵长的咏叹,在戈麦诗中很少见。
如此高密集地分析、比较两首诗,其实很一种很笨拙的方法,它会让文章变得滞重,不轻盈。但是,这种分析是贴着诗人创作与修改的思路进行的,至少能还原出诗人内心的隐秘活动。《眺望南方(二)》,去除掉了一些生硬的转折,裁剪掉许多破坏诗歌节奏的字句,清晰梳理了叙述视角,使得全诗呈现出一种干净而饱满的面貌。
这样持续而认真的修改,在戈麦创作的最后阶段很普遍。随手翻看《戈麦诗全编》第五辑《眺望时光消逝》(1991),“一题二稿”的诗占了绝大多数。这是一位年轻诗人向着想象力与诗的终端掘进、开拓的努力,也意味着走向了一种成熟的创作心态。
5
按照西渡的说法,戈麦诗歌道路的选择,表现出一种过分谨慎的态度。这在同时代人中是极其罕见的。求学时代,戈麦想改理科,未能得到学校的支持。他报考的是经济专业,结果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入学后,他一直坚持旁听经济系课程,认真做着转系的准备。1980年代,诗社林立,各地的朗诵会水泄不通,诗歌的澎湃与高潮,并未给戈麦多大的心灵震荡。他极为坦率地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
1985年的秋天,戈麦发现自己身上一种惊人的理解诗的能力,但他依旧没有迈开步子去拥抱诗。他在诗集《核心》的序文中,提到过第一次接触由老木编选、北大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出版的《新诗潮诗集》的情形:“当我一页页地向一些年纪同样不大的朋友解释其中的词句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理解力仍然没有令我兴奋地全面走向它。”
直到1987年,戈麦意识到“不去写诗可能是一种损失”。那年秋天,他从文献专业转入文学专业,与西渡成了同班同学。他开始在北大中文系刊物《启明星》上发表一些诗歌。从1987年秋至1989年秋天,戈麦自编了第一个诗集《核心》。一些可喜的作品逐渐冒了出来,如《隆重的时刻》、《冬天的对话》、《克莱尔的叙述(给塞林格)》、《这个日子》、《我的告别》等。这个时期戈麦的诗,会不断涌现出各种色彩的词汇和意象。这是一个刚开始写诗的人,爱沉湎幻想与感觉,对诗歌抱有热忱、活力与朝气的外化。譬如,用鲜艳的色彩去装点一个“隆重的时刻”:“鱼肚翻出水面的早晨/我见到了开白花的梨树/紫色的雾中的一双小巧的红靴/蓝花儿已经开发。”然而,这种色彩斑斓的词汇与意象,又会被粗粝的生活磨损掉:“北方是一条紧紧关闭的/白色睡袋……而北方是一道死门”(《隆重的时刻》)。
西渡在《死是不可能的》这篇序言中,提到一个关于写作氛围的细节:“当时同学中却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以谈诗为耻,彼此极少交流。只有他(戈麦)不怕忌讳,直言不讳地批评大家的作品。”戈麦对于诗歌完全是真诚的,这是他的道路,是他的一种过活。这个贫穷的诗人常常一边煮清水白菜,一边与友人谈诗。可他为了打印第一期的刊物《厌世者》,独自跑到中关村街,花掉四十九块钱。他爱惜这些交织着他诸多感情的诗歌,如同“爱惜一件衣柜中的旧礼服”。
在磕磕绊绊的写诗生涯中,戈麦对诗有着很长、很痛苦的思索。他也曾一度想搁置创作,“想暂时放弃纸和笔:这两件拖累人的东西”。但很快地,他内心的火焰有被点燃,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上。“他自觉减少了与人的往还,在同学的聚会上,从来见不到他的身影……他上北图,中午不出来,藏身于两排书架之间。”这是戈麦最后两年的日常生活。他几乎过着圣徒般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
自1987年至1991年,戈麦奋力写诗也仅短短四年,可他的创作数量是惊人的。除去《戈麦诗全编》收录的诗、译诗、文论,戈麦生前还毁掉了许多手稿。戈麦去世后,西渡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分门别类的阅读笔记,足足有二三十本。这是年轻诗人的一份可贵的遗产。
6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另外角度阐述《眺望南方(两首)》。约翰·济慈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他所描述的是他初次阅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作品所受到的那股震撼。博尔赫斯也将它引用在了 《诗之谜》这篇文章里。
之后我觉得我像是在监视星空
一颗年轻的行星走进了熠熠星空,
或像是体格健壮的库特兹他那老鹰般的双眼
盯着太平洋一直瞧——而他所有的弟兄
心中都怀着荒诞的臆测彼此紧盯——
他不发一语,就在那大然山之巅。
我觉得《眺望南方(两首)》也暗含着一种阅读的喜悦和激情。长久而耐心地阅读博尔赫斯,跟随着博尔赫斯指明的“道路”,意味着过隐士一样的生活,面对每一件小事,诸如沙漏,(国际)象棋,地图,词源学等,开始了他对时间和永恒的研究;阅读博尔赫斯,意味着受到持续的喂养,不断地内化,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关于“第二天性”,希尼在他《向艾略特学习》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从艾略特那里学习的,是诗歌现实的双刃本质:最初遭遇诗歌时,是作为一种陌生的文化事实,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诗歌被内化,变成人们所说的第二天性。原本是你难以企及的诗歌,引发了一种需要,就是想了解和克服其陌生性,最终变成你内心一条熟悉的小径,一条纹理,沿着这条纹理你的想象力愉快地往后打开,朝着一个本源和一个隐蔽处。”
希尼还以《灰星期三》(艾略特)诡异地出现“豹”的形象举例。以此来说明,豹的形象“不是从《神曲》里移植、劫持出来的,事实上,是从艾略特的纯粹心灵中冒出来的。艾略特受到《神曲》幻境的持续喂养,并且不断内化,但丁也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这个才气横溢的诗句,似乎成了自悼。戈麦,这一个年轻的诗人,有太多未完成的东西。可庆幸的是,他的诗里已经出现了“豹”的踪迹。
阅读博尔赫斯,意味着受到持续的喂养,不断地内化,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
❶ 出自博尔赫斯的诗《一个克伦威尔军上尉的画像》。
❷ 褚福运、桑克、西渡编写,《戈麦生平年表》,收录在西渡主编的《彗星——戈麦诗集》,漓江出版社,1991年。
❸ 引自《戈麦自述》,原题为《一个复杂的灵魂》。

❺ 桑克,《黑暗的心脏——回忆1989年至1991年的戈麦》,1991年10月。
❻ 西渡,《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戈麦论》,《戈麦诗全编》,1999年。
❼ 戈麦,《核心·序》,1989年10月8日。
❽ 《新诗潮诗集》,1985 年1月出版,分为上下两册。附录部分还选取了从李金发到蔡其矫二十位海内外诗人作品。资料参考:石佛,《老木与新诗潮诗集》。(这本诗选集,大概也是戈麦写“九叶派”那篇长文《起风和起风之后——九叶诗派现象研究与中国新诗的回顾》的材料基础。)
❾ 西渡,《死是不可能的》,1991年11月。